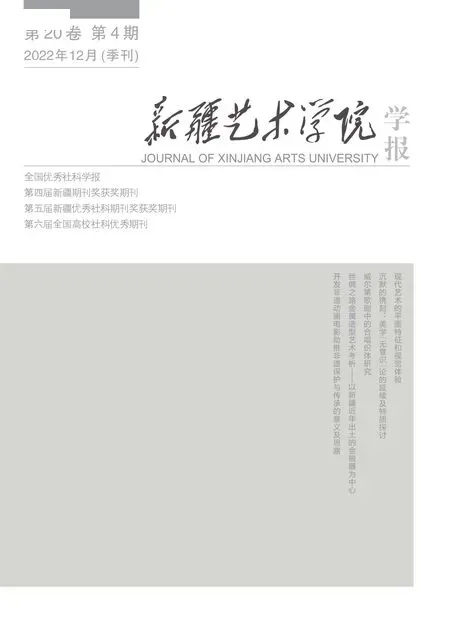非遗视角下哈密赛乃姆舞蹈的文化形态与教学传承策略
古丽米热·祖农 顾文妍
(1.新疆艺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9;2.新疆艺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9)
非遗传统舞蹈作为人类历史经验的载体、社会文化的身体记忆,展现着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成长、发展与传承。哈密,地处新疆东部,自古便是丝路重镇,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唐代十大宫廷乐中,“伊州乐”是哈密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而现今哈密地区的“哈密木卡姆”便被学界一直认为其与之一脉相承。“赛乃姆”是在民间音乐和歌舞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其舞蹈自由活泼,舞者多为即兴表演,没有固定的程式。作为绿洲文化的产物,赛乃姆普遍存在于新疆的大小绿洲,因每个地区的相异风格而在“赛乃姆”前冠以地区名称,如“哈密赛乃姆”“喀什赛乃姆”等,本文主要谈谈哈密赛乃姆。哈密赛乃姆舞蹈作为新疆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舞蹈多元文化样态,始终活跃在哈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
一、哈密赛乃姆舞蹈的文化形态概述
(一)新疆东大门:地理位置带来的文化沟通效应
哈密地处亚洲腹地,是新疆最东部的绿洲。哈密无论山南山北,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素有“西域襟喉,嘉关锁钥”之称,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了中原与西域两种乐舞文化的交流交融,激活了哈密盆地上的乐舞文化因子,使之成为哈密地区区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众所周知,文化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回授。中原乐舞文化受到西域乐舞文化的影响,而哈密赛乃姆的乐与舞也从中原文化中汲取养分来促进自身发展。像汉代的“以舞相属”礼仪舞蹈形式,在哈密赛乃姆的对舞形式中亦有彰显。形式与汉时极为相似,由一人舞相邀另一人进而成为多人舞的舞蹈表现形式,邀请者要手执“普它”(花状道具)行“邀舞传花”之礼,舞前舞后共行礼四次,极重礼仪,且邀舞时人人平等,不问长幼尊卑,人皆可舞。舞蹈场面欢乐、热闹。
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性使得哈密赛乃姆独具特色。哈密赛乃姆舞蹈同其他地域的赛乃姆舞蹈相比,有着重礼节,舞动时质朴舒缓,舞蹈性格特征含蓄、谦和、幽默等特点。且哈密赛乃姆舞蹈以女性“纤腰”“轻身”为美的特征,似与楚舞的“翘袖折腰”有相似之处。舞者舞时,时而纷飘若绝,时而魅力动人。但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舞者在舞蹈时脚下“柔软”,目视斜下,并以“点脚为节,边唱边跳”。这种“柔软”也体现在舞者的上半身。哈密赛乃姆舞蹈要求舞者含蓄直立,下侧腰的体态打破了维吾尔族舞蹈中张扬、挺拔、高傲的风格特征。哈密赛乃姆舞蹈动作运用了“摆腰”“下侧腰摆腰”“拧腰”等独特舞蹈动作,这种轻柔舒缓的“风摆柳”般的左右摆腰需舞者在舞蹈时下肢、上肢动作的协调对称。如双步垫脚接摆腰、绕步接赛乃姆步伐、横向绕步接赛乃姆步伐,挑腕接撩手臂顿步、向前单双步颠脚步接三位手挑腕、向后绕步接赛乃姆步伐等。这种闲适淡雅的风格符合中原地区传统乐舞的特征。软“折腰”动作,让哈密赛乃姆舞蹈在西域文化中更显新颖别致,别有一番韵味。
(二)多民族聚居:多种民族带来的文化融合结果
哈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多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呈现多元状态。多民族聚居下的多元民族风格也体现在哈密赛乃姆舞蹈中,哈密赛乃姆舞蹈不仅在风格上有汉唐乐舞的余韵,在动态中亦有哈萨克等民族的动态特点。哈密的哈萨克族多生活于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县。同一地区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共同生活而在文化、习俗方面相互渗透、交融。哈萨克族舞蹈动作有其独特的游牧民族特色,如手部“绕腕”。在哈密赛乃姆舞蹈中,向里“绕腕”也是其一大特征,虽与哈萨克族的向里“绕腕”动作相似,但哈密赛乃姆舞蹈中“绕腕”的手部形态呈握袖手状,“绕腕”没有了哈萨克族“绕腕”的寸劲,延续了哈密赛乃姆舞蹈中的柔和闲婉特征。
哈密地区的民间文化,亦融合了汉、满文化元素。如在维吾尔族文化的基础上,服饰沿用了汉族传统的“右衽”方式,在款式、质地、色泽、花纹图案等方面,都表现出维吾尔族服饰与满族、汉族等民族服饰相融合的特征。在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在婚后会将满头小辫改梳成为两条大辫子作为已婚与未婚的区别。女性会在发辫上缀以由金银打造的辫饰,辫饰以圆形扣饰各自固定在一根发辫上,中间以银链相连,圆形扣饰下坠有多个以银链相连的银铃,在行走和舞蹈的时候伴有清脆的铃声。①王薇,王光新.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传统服饰及其文化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2017(07):100-103.哈密赛乃姆舞蹈的摆腰动作便与其头饰有关,头饰上的银铃装饰灵动性高,身体的轻微动作也会让银铃响动,声音清脆喜人。久而久之,发展成为左右“摆腰”的舞蹈动作。加之受中原乐舞文化的影响,哈密赛乃姆逐渐形成以“摆腰”为动作基础的恬静、柔美风格。
此外,哈密赛乃姆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整合,再回到民间的历史进程,故而在舞蹈形态特征上受社会贵族文化的影响,形成高雅端庄、灵动飞扬的身体动态。哈密赛乃姆中“点脚”的动作便与哈密地区的主流文化有一定联系。在以往舞者表演哈密赛乃姆舞蹈时所穿的高跟鞋下面系有铃铛,而带铃铛的高跟鞋与哈密地区的社会贵族服饰文化有关。舞蹈中后脚跟或前脚尖快速点地即收回的“轻击”地面的动作,是目前哈密赛乃姆舞蹈中所保留的地区特色之一。
二、哈密赛乃姆舞蹈的保护与传承现状
自2008年哈密赛乃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共有14个年头,在分析保护与传承现状前,需厘清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哈密赛乃姆名称来历。哈密地区原本没有“哈密赛乃姆”这一名称,其被哈密地区人们称为“哈密嗨嗨”,在“青苗麦西来甫”和“婚礼麦西来甫”都有相类似的舞蹈形式。当善舞者伴随艾捷克和热瓦普等乐手演奏的曲子进入场内起舞时,会邀请其舞伴,并逐步扩大成一支舞蹈队伍,使麦西来甫进入高潮。与此同时,歌者、乐手与舞者相和,节奏更加急促,声音与动作更加热烈、奔放、有力,参与的人们在兴奋之时会大声喊道:“嗨嗨……嗨嗨”,在激昂的音乐、声嘶力竭的呐喊与激扬的舞动中,人们一切烦恼、忧愁仿佛随之逝去。“哈密嗨嗨”的名称也由此而来。2018年6月国家级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讲道,“哈密赛乃姆”这一名称是自从哈密文工团用乌路杜尔木卡姆嗨嗨①维吾尔语的直译,是“哈密木卡姆”九段中的第一段。、乌兰曲子(婚礼曲套)来跳以来,名称起为“哈密赛乃姆舞蹈”。在哈密地区以前没有“哈密赛乃姆”的说法,是先有哈密木卡姆,随着木卡姆的节奏和风格慢慢有了属于当地风格的哈密赛乃姆舞蹈这种表演形式和说法。
二是哈密地区大、小赛乃姆划分问题。《维吾尔族舞蹈五堡赛乃姆简介》一文首次以分布区域将哈密赛乃姆分为大、小两种:流行于哈密五城十二山区的、伊吾县等地的赛乃姆通常被称为大赛乃姆,流行于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一带的赛乃姆通常被称为小赛乃姆,也称五堡赛乃姆。哈密赛乃姆和五堡赛乃姆是分类的,哈密赛乃姆舞蹈是用哈密木卡姆的音乐来表演,五堡赛乃姆用存留的五堡民间歌曲所表演,五堡民歌歌曲有7套,7种变化,所以五堡的赛乃姆有49点节奏的形式。但有些专家并不认同在哈密赛乃姆的舞蹈中划分出大、小赛乃姆两种,因为二者舞蹈风格十分相近。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使用音乐相异,但就舞蹈而言,在观看和实践层面并未有很大区别。通过调研,笔者认同在哈密赛乃姆舞蹈方面划分出大、小赛乃姆毫无必要。
(一)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方面
哈密赛乃姆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引起了哈密当地政府、群众的重视,在濒临失传的情况下,由国家专项拨款,当地政府“搭台”,哈密赛乃姆进行表演的场合越来越多,比如每年3月会在哈密举行青苗麦西来甫,以及哈密各地群众自发或非自发的赛乃姆培训等,新疆地区的歌舞团体也身体力行,在其演出编排中融入哈密赛乃姆的舞蹈内容,为哈密赛乃姆舞蹈不断增添新的时代文化内涵。
2003年,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聘请两位哈密赛乃姆舞蹈自治区级传承人为笔者所在的年级授课,教授了一个男女共舞的哈密赛乃姆表演性舞蹈组合,为笔者后期传承发展哈密赛乃姆舞蹈播下种子。自2007年笔者留校任教,便在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课堂中将哈密赛乃姆舞蹈编入教材,并以两位老师的表演性组合为基础,重新编排,细化整理,划分出舞姿、步伐、腰带、花儿、绕腕等组合。编排组合时,为了审美性的艺术目的,舞蹈动作幅度相较于民间表演形态更大,如哈密赛乃姆舞蹈中典型的“点脚”动作,在民间,此动作幅度极小,民间艺人的脚往往在地面上一擦而过,但在教学组合中便要放大这一“点脚”动作,突出其独特的动作特性。此外,为实现教学组合的训练目的,笔者还将维吾尔族的特色旋转与哈密赛乃姆舞蹈中独特的“点脚”动作相结合,编排出旋转组合。
在后续对哈密赛乃姆的持续跟踪研究中,笔者不断与哈密当地民间艺人、老师、团长沟通,展示了笔者在教学中应用的舞蹈动作。他们认为笔者所编的教材中哈密赛乃姆舞蹈风格与本地区之前所传承的极为相似,风格上没有明显偏差和变化。因此,对笔者的舞蹈教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二)保护与传承的消极方面
1.年轻一代对哈密赛乃姆舞蹈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不够。从2003年至今,通过笔者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就民间活态传承的情况来看,哈密地区民间的哈密赛乃姆舞蹈虽在音乐上追随潮流,增加了一些现代电子乐或将其改编成了现代歌曲,但舞蹈却仍停留在固有的动作舞姿上,并没有大的技术上的发展变化。在哈密采风时,笔者发现,哈密地区的年轻人对哈密赛乃姆的关注度不够,笔者也未曾见年轻人跳过,使得哈密赛乃姆舞蹈传承的后劲不足。
2.“专业化”传承中有赛乃姆舞蹈风格同质化倾向。2018年,笔者观看哈密赛乃姆演出时,看到出现假唱、假弹情况。在现今哈密地区,已很少有人关注哈密赛乃姆舞蹈。当笔者去调研采风时,音乐并非现场演奏而是放音乐走过场,跳的舞蹈也脱离了原有的哈密风格,有些风格甚至偏向于喀什赛乃姆。当地除个别民间艺人能跳出相较于现在更加“原汁原味”的哈密赛乃姆舞蹈外,总体风格跳偏了,最起码是与笔者最初接触哈密赛乃姆舞蹈时的风格渐行渐远了。
三、哈密赛乃姆舞蹈的教学传承策略
新疆的非遗传统舞蹈作为新疆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载体,承载着某一地区的独特风格特征。就哈密赛乃姆舞蹈而言,其文化体现在通过融汇多元文化的精髓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本地区特性的审美表现。这并不代表它是多种文化的简单堆砌和叠加,而是在哈密赛乃姆舞蹈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汲取、融合多元文化及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表征,不断强化哈密赛乃姆舞蹈自身的审美特点和个性,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营养和活力,在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中发展和完善自身风格,保持自身独特的风格魅力。
作为舞蹈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非遗传统舞蹈的保护与传承建言献策。目前,非遗进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诸多学校已经开设非遗舞蹈专业或非遗舞蹈课程,如云南艺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新疆作为拥有众多非遗舞蹈的地区,笔者认为也应积极开展非遗舞蹈进校园工作,“走出去”“请进来”。以新疆艺术学院为例,虽然有多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整理民间的非遗传统舞蹈,并已整理出成套教材,但并未完全应用于学生的课堂实践,仅选择某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动律进行教授,虽有非遗传统舞蹈内容,但学生对该地区的舞蹈风格掌握不完善也并不系统,这显然不利于非遗舞蹈文化在教育中的继承与传播。
笔者认为,地方类院校有条件均可开设非遗传统舞蹈课程并系统授课。如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可总结归纳全疆所有种类的非遗传统舞蹈并按地区划分,像南疆的喀什赛乃姆、库车赛乃姆、和田赛乃姆等,进行系列、系统、科学授课,明确不同地区舞蹈的风格特征。在非遗传统舞蹈的教育教学中,首先必然要让学生们分清“生活形态”与“规训形态”的异同。因此笔者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可先选取某一地区民间的典型动态,如哈密赛乃姆舞蹈“生活形态”中的“点脚”动作、“摆腰”动作等,并讲述这一动作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文化内涵,让学生心中更加清楚哈密赛乃姆的舞蹈厚度、文化深度,了解我们如今在课堂上为何而舞,在舞什么,加强学生对非遗传统舞蹈保护与传承的意识。而后教授“规训形态”中的哈密赛乃姆舞蹈组合,将“生活形态”的舞蹈动作更加规范化、艺术化,强化其舞蹈风格特征。让学生在哈密赛乃姆舞蹈“生活形态”与“规训形态”的二者对比中产生反思与思考,形成主动思考与被动接受间的良性循环。如此,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才能不仅存在于学生的身体记忆中,亦会扎根学生心间,为其未来的传承发展铺路。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孕育出了绚丽多元的哈密文化,而哈密赛乃姆舞蹈作为哈密多元文化的载体,有着包罗万象的文化内容,充分体现着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多文化交融、多民族聚居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因此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