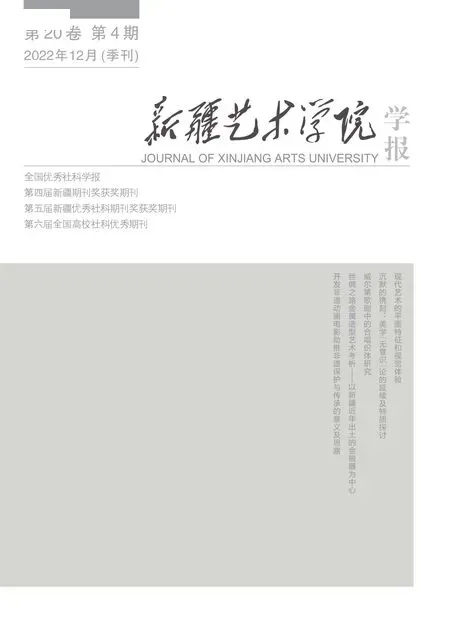关于中国电子音乐发展对策的思考
张 赢
(新疆艺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00)
音乐学家黄翔鹏曾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三对关系,即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及雅俗关系。可以说,这三对矛盾始终伴随着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发展而绵延纠结,反映在音乐创作领域,则表现为如何对待西方语言和中国民族语言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法的问题;如何对待“高精尖”的抽象艺术与符合大众审美的普适性艺术的问题等。在当今全球趋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艺术领域之间的壁垒不断打破、重构,艺术观念也随之持续更新,三对主要矛盾在音乐创作领域逐渐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而在这种发展趋势背后,中国文化正经历着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蜕变过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电子音乐发展中所伴随的“传统与现代、中西关系、科学与人文、民族与自我”等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发展路径,以期为中国电子音乐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一、持续深入地认识、挖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永远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通过研读大量关于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的文献可知,作曲家和理论家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几乎达成一个共识:中国音乐若想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西方音乐平等交流、对话,就必须充分尊重、认识、理解、继承传统。可以说,对于“中国性”的电子音乐创作理论研究,若想不流于表面,那么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由内向外地探究声音形态背后的语言发生机制。
(一)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音乐语言为前提进行创作理论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黄枕宇教授在其《西方电子与计算机音乐史》的结语部分,对科技精神引领下的当代电子音乐进行反思,他提出“音乐艺术审美所需的共识性不能靠科技思维来解决”,并且通过对加拿大电子音乐先锋基恩的审美思想“communication(传达)”的解读,提出:“我们应该清醒,音乐艺术中的这种‘communication’——感性共识性,是音乐存在的前提……今天……计算机音乐发展不再局限于技术性拓展的问题,而应该严肃思考如何正视‘communication’,如何构建音乐艺术审美共识性的深层交流”①黄枕宇.西方电子与计算机音乐史——电子、数字科技影响下的西方音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0.。目前,中国电子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分析仍多以20世纪电子音乐诞生以来的“形态学”以及电子音乐技术为主,使我们对于音乐的认识仅停留于音响形态、技术规律的总结上,甚少以语言的视角去观察音响形态背后人文意义的“传达”。可以说,缺乏对中西语言观差异性的基本认识,便无法完成“音乐艺术审美共识性”的探讨。
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曾建议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应以“语言作为美学的先导”,中国的语言观以神统形,重视意象、心性,这使得音乐语言在“活性口头语法则下”自由延展,常表现为“音腔、弹性节奏、渐进式速度、附生性多声”等特点,这与西方以形统神、注重严密逻辑思维的语言观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中央音乐学院张小夫教授曾针对中国电子音乐创作提出“用母语说话”的倡议,他认为“确认自己音乐语言的母语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基因的音乐语汇,是用母语说话的根本和前提”②张小夫,等.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的三个重要范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46.。因此,对于研究具有文化自觉特性的中国当代电子音乐作品时,应该首先认识中国音乐的“母语”,进而理解潜藏于音乐语言结构行为的审美、文化意义,同时结合形态学分析、技术分析等,方能得到全面、合理的创作理论研究。
(二)在创作中合理运用及转化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素材
中国文化数千年的积淀为艺术领域带来了极为丰厚的资源,其品种的多样性、丰富性使得中国电子音乐创作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面对当代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合理地运用、转化传统音乐素材,不仅是作品内涵深度及理性创新的体现,更是传承、延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根本立足点。
在中国电子音乐创作实践中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是大多数作曲家的选择,张小夫教授针对这一现象建议:“在创作实践中逐渐远离那些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音乐语汇,并逐渐形成一种母体语汇的认同趋势和一定的作品风格追求。”③张小夫,等.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的三个重要范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46.中央音乐学院关鹏教授的电子音乐作品曾在国际电子音乐大赛中屡获佳绩,在笔者与关鹏关于创作观的访谈中,他说道:“对于当今中国电子音乐的创作,我希望创作者能把传统乐器的符号性含义、代表性的演奏法完整保留下来,根据自身审美和艺术表达,有节制地使用变形技术。这种创作观是深受导师张小夫的作品《诺日朗》的影响,作品中没有运用夸张的电子技术手段,用loop的手法将诵经的声音作为贯穿全曲的动机,表达‘轮回’和‘圆文化’,同时,预置电子音乐部分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原生态音乐素材,如藏族民歌、藏铃等,结合实时演出的中国打击乐组及数字影像,使观众真正沉浸于作曲家营造的中国藏文化声音中,通过仪式感的演出设计感受中国藏文化魅力。
对于电子音乐的创作,应在引用民族音乐素材时合理把握技术尺度,避免传统音乐符号的无逻辑拼贴以及传统音乐资源的无谓破坏,从而使音乐表达集民族性和独特性于一体。
(三)创作、研究需从音乐语言的表层、中层到深层进行整体性互动观照
中国传媒大学的耿波曾将文化视为“一套有深度、分层次的整体系统”①耿波.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应是一个整体工程[J].社会科学评论,2008(3):20-22.,并借用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将“文化表层的符号”喻为“器”、“文化表意的深层境界”喻为“道”,指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割裂性特征”,其具体表现为“中华传统文化表层符号的炫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深层意蕴的虚无化”②耿波.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应是一个整体工程[J].社会科学评论,2008(3).。这些割裂性特征在当代中国电子音乐创作中也屡见不鲜。音乐符号和语言基因是深层意蕴的表层镜像。电子技术的普及性、便捷性、多样性等特征使得电子音乐创作容易成为满足感官欲望的“万花筒”。创作者一旦沉迷于“炫奇性”的感官刺激,则会陷入文化表层符号的空洞拼贴或膨胀放大,从而忽略音乐语言、语汇的合理建构,进而导致深层文化意蕴的虚无丧失。
综上所述,持续深入地认识、挖掘、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传承中国音乐的重要使命,更是中国电子音乐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二、持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
20世纪音乐与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先锋派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2016)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了现代音乐的问题所在:“今天音乐最重要的危机是观念与材料,即音乐创作活动中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脱节,各自独立发展,失去了相互联系,这是20世纪音乐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③黄枕宇.西方电子与计算机音乐史——电子、数字科技影响下的西方音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0.同时,他强调“创作”并不是任凭想象天马行空的臆造,也不是工程师的科学探索实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应该在精神上与传统的、过去的音乐及文化保持一贯性的联系。
那么,如何解决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联结问题?笔者认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电子音乐创作的另一重要使命。这种“创新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新发现、新理论有着敏锐的自觉更新意识。另一方面应是立足于当下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共识,利用新兴表现方式对传统进行创新性发展。
从近几年国内举办的与电子音乐相关的大型活动中,可以看出创作界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创新意识。如2021年12月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新媒体音乐大师班,论坛和音乐会的主题围绕“传统”与“未来”展开。从音乐会的介绍可以看出创新之于传统的意义:“我们总能在历史遗存中找到革新的语言,在新媒介中感应到古老的凝视。本次展演共呈现了十部原创作品。从塔吉克族的鹰图腾,到江永女书,再到上海寻常巷弄中的谣曲,在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中找寻历久弥新的生命姿态。”④引自2021年“传统·未来”新媒体音乐会介绍。音乐会总监、著名作曲家杜韵近几年积极投身于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她与包括中国戏曲艺术家、民间音乐团体的艺术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以此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更新。对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她认为:“传统和创新皆非对立。我们常常以纯粹的传统文化自封,却忘记了文化传承中无时无刻地演变和融合。历史的传统可以是创新的思潮,文化的流传不断隽永而更新。”
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概念,可以说,“媒介”定义了我们感知信息以及做出反馈的模式,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理解和思考的固有习惯模式”。就电子音乐创作的发展而言,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会随着创作“媒介”的改变而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不同样态①在陆敏捷的《中国新媒介音乐的新型样态初探》一文中,将中国电子音乐典型样态总结为三种:即1.纯听觉艺术的“幻听类”作品样态;2.与民族传统乐器、人声结合的现场表演型作品样态;3.中国新媒介音乐样态。的电子音乐由于其音乐实践过程中的“媒介”不同,从而使得创作思维、实践主体、技法、感知方式等有着不同的体现。正如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对艺术的产生有着精妙的比喻:“植物与地域相连……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②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7.可见,艺术是随所在语境、所处时代的变化而持续更新的。
随着高速发展的科技进程,未来中国电子音乐创作所面对的是更加多样的媒介,其势必会无限拓展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从而使得语言结构行为更具开放性,审美感知也会随之无限延伸,而传统文化始终作为中国音乐创作发展的“源头活水”,在与新思路新媒介新表达新方法的相互激荡中,奔腾不息。
三、持续以“美美与共”的方式展现独立的美学姿态及人文表达
“表达”,是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行为方式,通过“表达”可以传递、分享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和感悟。通过“表达”内容,可看出表达者的精神主张、审美、文化属性及综合能力。音乐属于“表达”方式之一,作曲者在无限的声音世界里构筑自己的语言以表达自我主张。“艺术创造的根本问题是艺术家文化的选择及其表达的能力。”③贾达群.梁雷的“表达”及引发的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3).既有文化底蕴又兼具超群表达力的艺术家,往往对“他者”与“自我”有着充分理性、客观的认识,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将“他我”融会贯通,进而以个性化表达方式谱写着人文精神。
(一)“美美与共”是自我表达的前提
王国维先生曾就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兼通世界”。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发展历程有着高度总结以及对其的美好理想,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学术前辈的言语中都以“兼通、融汇”为关键词,笔者以其延伸思绪,认为,站在中西古今交汇处的艺术创作,在对自身传统文化有透彻研究的同时,应对“他文化”保有积极开放的心态,深入其中去观察研究,方能在对话、比较中更好地认识本我,从而做到知己、知彼。同时,“兼通世界”“美美与共”并非简单意义上对他文化进行拼凑嫁接,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以发展的眼光、融会贯通之道展现独立开放的美学姿态以及人文精神。
当下开放、便捷的交流平台使艺术创作者能够长期熏陶于国际文化氛围之中。熟知西方理念、现代技法且浸淫于中国文化的作曲家们,以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彰显着“文化自觉”。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曾说,“有一批中国作曲家在国外走红,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他们不但在技巧上,也在理念上大大地进了一步。他们不但对西方有与前人不可比拟的更深的了解,也对本民族的遗产有更深切的爱好。在他们的创作中越来越少前人那种洋和声与土调调的表面结合,而更注重发挥东方遗产中的鲜明个性。应当说,发展是积极的”,这正是作曲家在“兼通世界”“美美与共”之后展现个人创作魅力的体现。周文中先生曾对亚洲音乐创作的发展提出“汇流”的理念:“让不同的传统交织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新的主流,并将所有音乐概念与实践全都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同时,让我们确保各自文化将保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自身的诗意。”①梁雷.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184.
(二)人文精神是自我表达的核心
反观20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技术崇拜,这直接导致了人文精神在创作中被忽视、摈弃。这一特点在科技飞速发展、技术狂飙的今天则表现得更为充分,艺术创作者享受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所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更容易陷入技术崇拜之境,从而导致个性化的创作沦为消费主义下的感官刺激和技术炫耀,人文精神逐渐消失殆尽。
对待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人文精神,不同作曲家有着不同角度的见解。张小夫教授以“返璞归真”作为创作宗旨。笔者认为,这份“质朴”和“真诚”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也应是每一个追求“自我表达”的创作者的初衷。中央音乐学院吴粤北教授曾就“中国风格的音乐创作”这一话题提道:中国当代音乐的开拓者们,往往都是自发地、有责任感地书写着具有中国内涵的作品,而当这些凝结着个人智慧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民族乐派。由上述可见,个性书写的“作品”是否称之为“艺术创作”,在于音响形态结构之下尽显着的人文意义。用作曲家瞿小松所言,总结人文精神之于艺术表达的重要性:“人之为人,艺术之为艺术,不单取决于骨架,更取决于血肉、大脑、神经与五脏,取决于心流,取决于情感与思绪。”②瞿小松.虚幻的“主流”[J].中国音乐,2011(2).
笔者认为,中国电子音乐绝不是传统音乐的粗浅翻新、传统文化的空洞展示或是音响形态的结构游戏,也不在于创作者极力的自我宣扬。中国电子音乐是建立在一种原发而深刻的文化自觉之上,以开放、包容、自由的艺术品格与世界文化互动,同时联结着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语言,最终以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谱写出属于全人类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