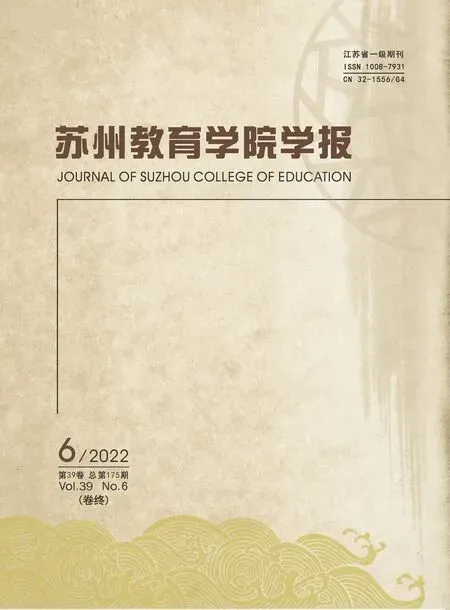身份文化的记忆书写与“再现”的集体反思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的询问
王 铮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的《一个欧洲人的悖论》[1]的主人公约瑟夫是个具有复杂身份经历与多元文化背景的欧洲人,作者借主人公的“欧洲”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了对于俄罗斯的考量。巴辛斯基评价克里蒙托维奇“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带有那个年代才有的心理和世界观‘胎记’”①转引自陈方:《译后记》,见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著,陈方、胡颖译:《一个欧洲人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第228 页。,而《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带有的“胎记”则是整个俄罗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克里蒙托维奇的创作中,“忘却与记录的记忆”是突出的主题,这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记忆的内部逻辑的统一来源,也是俄罗斯人民自身身份认同、身份定位的聚焦之处。小说对接受多元文化的约瑟夫和具有多元思想的俄罗斯的平行处理,使“记忆的双轨寻找”在“现在”理性的反思意识下,更好地再现了记忆的意义价值。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回忆并不是取回一样的东西,而是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创造”凭借的是“自我”的身体经历。[2]因此,讨论回忆或记忆主题势必要回到“再现”主体的经历与身份建构的关系上。
一、“再现”的延迟与“公私域”边界模糊
我们相信自己过去的身份已经建构完成,但是社会却时不时地要求我们在思想中再现自己以前生活中的事件,而且还要自己去加工、润色:削减、删除或完善。约瑟夫期盼着“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3]82。但是约瑟夫的记忆并非是成型的、固定的,他在再现的过程中就已经对自己的个人身份产生了摇摆,同时,这种重塑机制对过去又产生了反作用。
回忆的再现过程总是延迟的,虽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保持人类活力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危险和迷失。“任何一个人存在于社会,首先是要被命名,其次则要被给予一定的身份,只有通过事实性话语和倾向性话语的共同作用,我们才有可能明确对一个人的认识。”[4]182“被命名”和“被给予”的限定表现在当我们介绍一个人时,往往会从他的自然属性介绍到社会属性,逐级分层,将“个性”表现具体化,减少关于其“共性”的描述。被分层的人总是从属于某一国家、地区、组织、家庭等,其中,交际关系的基础是集体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在限定个人的过程中,《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存在的记忆认同出现了模糊与矛盾,这其中必然涉及“公域交错”与“私域混乱”的融合关系问题。再现的延迟最终会因为新因素的添加或消失对人造成“误导与欺骗”,“最后两类物品(纸张、书本)的需求量最有所下滑”,“哪儿都看不见布尔什维克”,约瑟夫记忆中的哈尔科夫不再是历史中的模样,“这根本不是从前的哈尔科夫”,那一点点事实性知识只是确认了外在形式的记忆,自我迷失的居民们“错以为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可以尽力忘记一切,像从前那样生活”。[1]120作为约瑟夫视域下政治生态的再现,哈尔科夫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便丢失了作为布尔什维克阵地的“公域”灵魂。正是这种整体“公域”对政治生活视若无睹的自我抛弃,不再寻找社会与人生的标志物,“记忆的迷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便改变了哈尔科夫,也给“延迟”的约瑟夫带来了悲悯与震惊,他不禁感叹“人类的天性真是不可救药”。[1]121我们不能作为定点式的个体去生活,以某段个人经历的体验来限定人生的发展与改变,否则会导致“私域与公域”的混乱交错。
汉娜·阿伦特曾剖析公域与私域的关系,认为“私人领域就是家庭生活,公共领域就是政治生活”[5],“在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之外,还存在一种既公又私,或者既非公也非私的生活,即社会生活”[4]186。约瑟夫在思想的“公域”与生活的“私域”中平衡个人的处事标准。形形色色的人慢慢地和政治、社会领域交汇融合,约瑟夫看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国家社会命运的无情混杂,这使得正在回忆中的他想要通过感受已经被剥夺的“幸福和安稳”来“试着弄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入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的”[1]109。面对回忆时的梳理与辨析,约瑟夫“抱怨”偏多,情绪的展示或从政治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约瑟夫将自己的本质置于公域中,然而这种公域又变化得太快。正如小说中的一位美籍波兰裔人谈到俄罗斯时总是抱怨:“不幸并不在于俄罗斯学新事物学得慢,而是在于它忘得太快。”[1]158乌克兰、红白势力斗争、乌克兰革命运动、努力适应苏维埃政权……约瑟夫这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俄罗斯纠缠在一起,成为了一名政治犯。本应是有所遮蔽的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削弱了个人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从阿伦特的视角来看,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公域与私域”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那种像传统社会中泾渭分明的“家庭私人生活”和“政治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含糊,取而代之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又同时覆盖二者的、无处不在的灰色地带—社会或社会领域。面对灰色的回忆,原本崇尚自由、追求解放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公爵视为精神导师的约瑟夫,能否真正以自由的个体存在于群体身份之中?是被塑造还是被禁声,是否还能追求愉悦的自主,是否还存在个体对专属集体的永远的、忠诚的归属?阿伦特对此并不乐观。甚至克里蒙托维奇本人都产生了疑虑:“是什么影响了约瑟夫?”[1]82牢狱中的约瑟夫面对记忆无所适从,除了对普拉维德尼科夫侦查员进行讲述与辩解,只有将自己沉浸到几十年前的回忆中去关注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集体的层面之外,在宏观的历史之中,作为个体的和微观的‘我’又是如何与自身达成统一的?我们能够在具体的个人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恢复我们对于社会认同的信心吗?”[6]
“在西美尔看来,个体的生成可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亦即现代性的主体是人。”[4]194个体是践行认同之合法性与理论之有效性的前提,也是贯通“公域”和“私域”的重要线索,是身份构建的最基础单位。作为具体的个体,约瑟夫的一生就是通过强烈的个体体验参与到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去的,这一点根据讲述者—作为外孙的“我”—通过查看“约瑟夫的笔记”显示了出来。从“发疯地热爱某个抽象的民族,同时彻底不尊重个体,这是俄罗斯的传统”[1]206,约瑟夫的生命形态与身份状态在历时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一个政治漩涡中的政治犯,或者是以政治追求为取向的社会活动家。但是这里所讨论的不是政治上的个人体验,而是与婚姻、亲属、情感等相关的私人生活中所体会到的时代变迁和时代变革。个体关于爱与亲属关系的内心感受和认识,是“私域”的重要内容,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被保留、被维护、并得到发展。约瑟夫的私人生活也反映了公共的社会情景,约瑟夫主动混淆了与索菲亚·施泰恩(德裔俄罗斯人)之间“公域”与“私域”的关系,作为约瑟夫身份构成的一部分,索菲亚的“已婚”身份对于约瑟夫的介入意味着时代层面上的“公域”消解了个人的“私域”。“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已婚的俄罗斯女公民,就可以被准许出国留学”[1]7,时代潜意识下的公共生活强迫约瑟夫将“个体”的自我完全抛弃,积极投身到集体的“大我”的政治活动中去,导致了约瑟夫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成了时代的碎片,特定时代要求所有人变成了“政治社会人”而不是“自由人”。约瑟夫对自己的认同无法通过爱情与“友善援助”来实现,而是需要到政治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而保证自我认同的稳定性。但是这种认同对于像约瑟夫这种在日内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移民青年组织成员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不属于现在的生命经历,给了人们再次自我重构的机会与认同的需求。有学者曾经提出:“时代的悲剧,作为社会性的人类而言,虽然认同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但我们究竟应该当何去何从?”[6]公、私域边界模糊引发的认同焦虑表现为个人无法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对个人生活的归属感,带来的是人与自我的危机。在缺乏正确性、合理性的时代框架下,认同充满了差异,变得永远也无法完成。
二、个体身份窘境与集体归属的摇摆
克里蒙托维奇对西欧与俄罗斯的描绘,折射出其所属的地方具有“排他”性质。地方与事件是重要的记忆触发要素,能够引发人物对身份的焦虑,使追寻记忆成为必然。克里蒙托维奇将文化内涵的记忆象征写入了“熟悉的圣经”“翻译工作”“历史事件”之中。同时,在约瑟夫与普拉维德尼科夫的对话中,“询问”也成了刺激记忆的触发器,促使约瑟夫不断唤醒以往的记忆。人是记忆的活动载体,随着主体对情感的移入与反射,各种记忆组成了一幅重要的图式,绘制成了“他我”记忆,触发了约瑟夫的身份危机,使其意识到搭建过去与现在的桥梁的必要性。
“他者不是物质实在的人或物,从本质上讲,他者是指一种他性,即异己性,指与自我不同的、外在于自我的或不属于自我之本性的特质。”[4]214又比如从国别所属来考虑,约瑟夫出生于意大利,又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生活。他接受教育并形成世界观的几个地方,其实就是俄罗斯眼中的“西方”。他在“革命运动活动家”“翻译”“教授”“医生”“政治犯”等多种社会身份中来回转换,由此,约瑟夫及其代表的现代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来完成。约瑟夫虽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热衷者,但作为在俄罗斯生活了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带来思想倾向的革新,“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被约瑟夫潜在地抓到了。约瑟夫在不同的地方获得了不同的职业身份,在轮换生活方式下对固定身份产生了不适。小说开篇通过“我”的梦引入“外祖父”,关于其外貌描写的文字还是在建构外祖父的形象,但是到了外祖父真正被捕的时候,克里蒙托维奇才将“外祖父”的形象过渡到“约瑟夫”的形象,这意味着尽管有外貌的描写与刻画,但只有当个体被纳入社会关系中,在社会关系中完成行为联系,才会被周围的人和社会所认可,才会与社会产生联系,因而这种职业身份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身份认同。
在窘境时的职业身份认同是否能转向对约瑟夫背景构成的询问呢?约瑟夫的记忆认知来自多元社会的成长经历,是交叉的社会观念和长久的流浪生活培养的,更多的是“只为了寻找某种荒谬至极、空想虚幻的幸福”[1]109的“整个国家”的时代所塑造的。在回答实验员扎瓦多夫斯基不友好的提问时,“‘波兰人。乌克兰波兰人。加利西亚的。确切地说,我应该是罗辛人。’他(约瑟夫)没提自己母亲那边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血统,也同样没说自己是美国公民”[1]137。一般来说,认同就是指对共同的或者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国家-个人”的认同作为一种现象早就存在了。约瑟夫成长的这几个国家所代表的“欧洲”与后来他作为政治犯所在的俄罗斯似乎形成了对比。克里蒙托维奇似乎有意突出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与西方这样的对比关系,要知道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以及东西、方之争,一直是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中的矛盾。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在思想上也一直摇摆于东、西方之间,所以说,俄罗斯的归属感是模糊的。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发展之路虽然有着欧洲的相关基因,却是在将欧洲的经验与传统加以消化后,变成俄罗斯自己的东西,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我们现在已是欧洲主义的学生,我们已不想成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而想成为具有欧洲精神的俄国人”[7]66。在对俄罗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传统民众似乎秉承着恰达耶夫的意愿,“我们毫无必要像西方民族那样,再经历民族偏见的混乱,再沿着地域观念的狭隘小径、沿着旧传统的崎岖轨道踟蹰前行,我们应借助我们内在潜能的自由迸发,借助于民族意识的巨大觉醒来掌握上天赐给我们的命运”[7]6。自傲的俄罗斯人说:“但我们又压根不想成为其他那些普通国家,就是有种这样的自傲。”[1]80约瑟夫不在以上两种思想倾向上站位,只是侧面回应,冷冷地观看,“约瑟夫对这些已经彻底厌烦了。他们谈论的东西似乎囊括宇内,但实质上却空无一物,能这样一连聊几个小时的只有俄罗斯人”[1]81。作为欧洲人的约瑟夫起初不能理解俄罗斯的文化与社会规约,经常以欧美作风来评价俄罗斯,“对,我们就是乡巴佬,我们从来都算不上是欧洲的一部分”[1]80,他认为,认同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在对俄罗斯传统居民的认知作出否定的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欧洲身份的强调,内心深处还是更加认同自己的欧洲身份。“任何个体的自我认同必须要在首先完成集体认同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个人的认同往往与对族群的认同交互作用。”[4]212约瑟夫的个体认同过程不能仅仅依靠自身建构。
三、“经验性”记忆与“现在”理性的辩证融合
当我们试图对更为久远的记忆进行定位时,就不得不把它们置于一个记忆总体中去描述,这个记忆总体相对于家庭来说更为持久。在讲述记忆总体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在体味事实的特殊含义时,“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在这种关系下,“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3]94本来这是无可厚非的约束,但是如果这个“集体”或“群体”自身就迷失了,人就失去了依靠,无法在看似最简单的、最普遍的“家庭-民族-国家”身份关系中找到合理的定位,人与集体的记忆归化与身份确认就成了左右踌躇的矛盾。
季羡林先生对于俄罗斯的混合型民族文化有过比较肯定的回答:“我是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世界上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能产生文化,都对人类总体文化有贡献。但是,各民族产生的文化,在质和量上,又各自不同,甚至有极大的悬殊,这是历史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科学的态度。”[8]但是随着现代人本体性的内在转向和身份确认的需求,“回归自身”在《一个欧洲人的悖论》中显得困难重重。约瑟夫所依赖的社会生活的框架是重叠的,这个社会框架是一种“二元”体系,“处在这种‘对生的’存在、矛盾和互补状态中的20 世纪的两种俄罗斯文化……是一种辩证的社会文化平衡,这种平衡是如此不稳定,又是如此不可避免”[9]。就算时过境迁,社会记忆的框架发生改变,那些可能被遗忘了的记忆仍然会残存在无意识的某个偏僻角落里。克里蒙托维奇在小说的《作者后记·说明》中这样写道:“第一次听到‘对付过去’(прошляпить)这个词时感到十分惊讶。”[1]214人们也许会反驳说,不必在“过去”中寻找这些东西,但它们毫无疑问就存在于“过去”当中。事实上,纵使“过去”一直在侵蚀“现在”,但一旦讲述一些东西,就必须要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
约瑟夫表现出的对于回忆的再现,进一步讲,就是克里蒙托维奇对于俄罗斯民族历史传统的反思。“记忆”与“现在的理性活动”所表征出的取舍,是“传统”与“现在”的矛盾,但是“记忆只有在这种理性控制之下才发挥其功能”,体现出“经验”的有用性,“一个社会抛弃或改变了它的传统,难道不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理性的需要”,这种观念是“集体反思”的产物。[3]304-305“俄罗斯人总是十分冷漠。他们不记得历史”[1]209,他们表面上承认自己对于“传统”的背离,想要追求更为“理性的现在”,表现出对于“回忆”的“不迎合”,却将“反思的观念”植入俄罗斯民族的价值准则。约瑟夫具有不同于俄罗斯人的对于俄罗斯思想的归属感的观念,或许作为外国人,约瑟夫比一些俄罗斯人更有俄罗斯特质,包括他对克鲁泡特金公爵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热衷,以及在乌克兰与俄罗斯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获得的对于俄罗斯人的理解,似乎证明了“生活经验”可以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现在”理性与记忆传统是相对的概念,约瑟夫的日记本承载着记忆传统的体验,“反哺回忆的责任,社会、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记忆与忘却的辩证进程之中”[4]58。回忆在这里作为必须被“再现”的东西,“每当我们始终处于成长危机中的忧伤社会开始自我怀疑时,它就会思考:是否能追问过去,追问的方式是否合理”[10]。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在”理性意识的觉醒下,俄罗斯人能够在历史记忆的驱使下尽可能地利用经验性的回忆,将历史中的每一个画面内化成民族以及个人的身份散失,以对抗现代身份认同散失下的集体意义。“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俄罗斯人为探索其自身的现代文化身份而进行的思索和著述在持续时间与深度上几乎超过其他任何民族”[11],在这个多元历史与记忆交织共生的成长环境中的俄罗斯,或许可以说它刻意构成了一种自我论证的封闭形式,“历史的书写提供了个体记忆的可能性,决定了集体记忆的背景,而记忆的传播和接续又固化了历史知识,对世人塑造某种‘被期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结构形成强有力的支撑”[4]61。约瑟夫个体记忆的固化反映了集体记忆的基础背景,在反思和再现中进一步巩固俄罗斯文化这个摇摆不定的天平。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或者说约瑟夫个人的生平所反映的价值思潮不是一种恒定的永续存在的东西,但其传播的连续性,在“现在”理性的认知下的确存在于世界文明的集体意识之中。
四、在记忆“再现”中反思对“现在”理性的补充
当人们一直回忆某些过往经历,而这些过往经历的过程性与“现在”产生“他者的见证”时,这样的主体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于自身的重构。只有通过“再现”才能使人们对“现在”产生个人的身份约束力,并对未来有着新的预期希望。
约瑟夫身份的体验变化伴随着历时性的记忆回顾,并不是透过窗户看屋里,而是从门外走进了屋里。“我的回忆肯定会得到更新和完善。诚然,这需要双重前提:一方面,在我加入这个群体之前,我的记忆像它过去那样,并不是每一处都同样被照亮的—就好像我到那时候为止还没有完全感知和理解它;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记忆与构成我的过去的事件之间并非没有关系。”[12]记忆的完善与更新都是在“关系与接触”中发生的,充满无目的性与目的性,使人在记忆再现的过程中体会熟悉的生命体验,也是为了使人们的“现在”理性更加强大,消除沉寂式的自我怀疑与迷失,构建更加自如并且清晰的身份定位。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以描写回忆来寻找答案,以再现记忆来询问自身,要求我们消解“好”与“不好”、“合理”与“悖论”的强制二元性,进一步探索充满多元意义的俄罗斯。正如尤里·那吉宾在《隧道尽头的黑暗》中说的:“俄罗斯人最大的罪行就是总自己认为无罪……俄罗斯发生的一切都是经过俄罗斯人的双手和同意造成的。”①转引自詹姆斯·H·比灵顿著、杨恕译:《俄罗斯寻找自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第141 页。对于俄罗斯不能说“非此即彼”,在历史的长河中必然保留着俄罗斯人的“异域”与“故乡”,即使在绝望的噩梦中,也要追求精神憧憬的回归。克里蒙托维奇询问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询问俄罗斯的过程。很难说这部作品通过“回忆”回答了“什么是俄罗斯”的终极询问,或许要在不尽的记忆中寻找,在混乱的记忆中询问,文化与背景对人身份的建构持续地发生着改变,或许这个建构在时间轴上没有终点,但是就此询问的意义与追述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记忆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了时代背景下的复杂的身份重构,就像西西弗斯神话隐喻的那样,“这不是一种屈从于命运嘲弄的无奈姿态,而是对永恒运动着的生命本身的尊重”[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