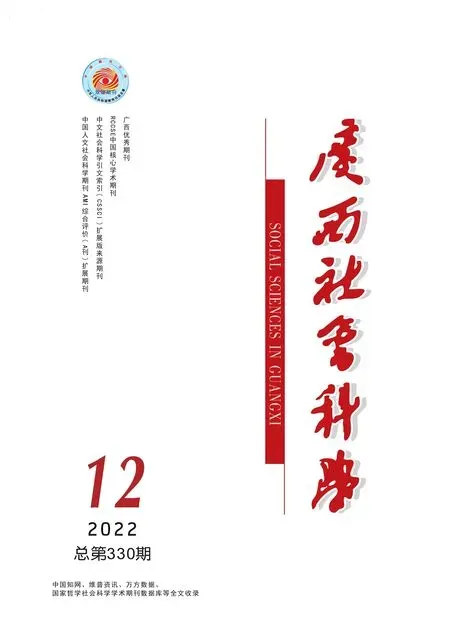中法战争后广西边境通商之议及其论争
吴新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学界关于中法战争后广西边境通商的研究,较多关注桂越边境贸易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影响[1]、广西开埠对区域贸易的影响[2],而较少涉及中法战争前后广西龙州开埠的具体议定过程,以及议定过程中发生的论争与原因。实际上,中法战争后,对于广西边境究竟是否应该通商以及在何处通商等问题,清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争议,最终设埠龙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探究广西边境通商的议定过程以及广西边境通商之议的分歧原因,将有助于认识近代大变局下中越边境体制的递嬗过程,对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与处理边贸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广西边境通商之议的根源
中法战争前,法国与中国西南边境省份通商的意图已被一些边省疆吏觉察。光绪八年(1882年)前,清王朝在海疆上面临朝鲜危机,陆疆上遭遇越南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清王朝内部围绕是“弃藩自保”还是“固藩自保”展开了激烈争论。中法战争前后,如何处置中越商务与边务关系问题成为清廷官员争论的焦点。清廷官员之论争最早聚焦于云南边境,战后关注的焦点又蔓延至广西边境,其所折射出的观念纠葛一脉相承,且为最终广西边境通商格局之形成埋下远因。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法国攻占越南河内后,意图通过红河与云南通商。对于云南边境通商,边省疆吏多持反对态度,例如云贵总督刘长佑便明确反对云南边境通商。但刘长佑清楚中法通商关系国家大局,必须由清王朝内廷议定,作为疆吏只能奉旨遵行[3]。因此,刘长佑随后向总理衙门上书,说明自己对云南边境通商的担忧。广西巡抚徐延旭认为即使不开埠,通商也不可行,甚至认为云南边境通商毫无益处[4]。尽管多数人坚决反对中国与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但清政府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此持乐观态度。直隶总督李鸿章就认为边界通商于国于民都不会带来太大损害,并用之前沿海各海口通商的实践案例来验证与说明[5]。薛福成与曾纪泽的看法相似,表示通商不仅不会对中国造成损害,甚至大大有益于边防[6]。郭嵩焘也认为选择边境一个地方通商,有利于巩固边防,百利而无一害。尽管各级官员对滇边通商的态度莫衷一是,但最终决策权掌握于清廷手中,其态度亦最受瞩目。那么朝廷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甲申政变之后,奕譞掌权,主张对法国实行妥协政策,这时清廷更倾向于李鸿章等人的看法,即赞成沿边通商以消弭衅端。云南布政使唐炯也认为“朝廷意重通商,不欲开衅”[7]。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在天津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该条约第三款便规定“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8]。至此,中法陆路通商之事已定,但具体通商地点还未明确。也正因此,围绕中法陆路通商地点设定产生了一系列论争。
二、广西边境通商的论争
《中法简明条约》第三款规定“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李鸿章本意仅仅指云南边境,并不包括广西边境[9]。然而,李鸿章显然低估了法国的野心,滇边通商仅仅是其所图的一部分。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国军队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而法军占领台湾澎湖,加强了对台湾澎湖地区的控制。两个战场,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十九日,中法双方匆匆商议停战条件并据此商订细约,战争终止。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初六日,李鸿章咨送军机处的《中法新约》正本第五款、第六款即有“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及“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等内容[10]。可见,中法陆路通商已不止云南边境,还包括广东、广西。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初七日,正忙于中法战后两广边务善后事宜的张之洞听闻中法商订广西边境通商细约事宜,急电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询问咨送军机处的《中法新约》正本里是否有允许法国与广西陆路通商的条文[11]。张之洞还致电总署,希望总署拒绝广西陆路通商之事,并敕李鸿章熟筹。随后张之洞又提出“详约关系甚巨,必宜审慎,赫德(Robert Hart,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引者注)恐有偏袒,华文洋文易致参差”,请清廷将详约“发交沿海沿边疆臣体察酌议,再许画押”[12]。然而,由于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发生甲申易枢,清流派领袖李鸿藻退出军机处,陈宝琛、张佩纶亦遭外调,这时反对通商的声音已较前为少,因此张之洞的建议并未被清廷采纳[13]。但张之洞仍不放弃。因为条款只规定云南边境在越南保胜以上一处地方、广西边境于谅山以北择一地方开埠,如能阻止入边开埠亦不失为好办法。尽管连外间舆论都承认“通商之在华边界者,一在保胜则为滇南之边,一在谅山则为粤西之边”[14],但张之洞认为条约并未明确说明法国可入边设埠,故此事仍有转圜余地。为此,张之洞于五月初八日致电李秉衡,提出在越南文渊设立收税机关,使边关远离中国边境。但李秉衡不同意,他主张“如设税关,于镇南关口外里许另筑关卡房屋,这样既不占对方边界,也可保证我国关口安全”[15]。张之洞对李秉衡的意见表示反对,坚持认为税关设在越南文渊最妥当,这样可以避免危及中国镇南关[16]。至此,广西边境通商地点争议遂愈演愈烈。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新约》,其中第五款规定:“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17]至此,中法陆路通商大致方位已定。尽管如此,具体处所并未明确,条约也未交换批准。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九日,张之洞借奏勘界事宜之机再次向清廷表达不宜在广西边境设埠通商的看法。一个月后,张之洞还致电勘界大臣邓承修和李秉衡,要求他们力阻法使入边议界[18]。后来邓、李二人确实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李秉衡向李鸿章表示:通商设埠应该选越南谅山、驱驴、文渊等地。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初四日,李秉衡再次致电总理衙门,对法国在龙州设埠导致的后果深表忧虑,李秉衡甚至向朝廷申请去职,目的是用辞官作为抗争,从而引起朝廷对其上书建议的重视[19]。李鸿章对邓承修、李秉衡与王之春等人的回应是“现议商约,拟将设埠处所暂搁”,但他同时强调:对方与“我”通商,是想进入我国境内,这个不是我们个人之微力所能禁止;可先看看云南那边通商设埠定在哪里,作为广西比照[20]。可以说李秉衡、张之洞等人的力争,对随后的《越南边界通商章程》(或称《天津协定》)谈判产生了一定影响。根据越南海防法字报载:“前法使戈高丹(当指Georges Cogordan,戈可当——笔者注)与中国所订之约只准开两处为通商贸易之所,法使初与中国大臣商立条约时,中朝亦只准其在关隘处及保胜对面之小村,只有四屋者为通商贸易地方,而法使未允。”[21]如报道属实,则说明此间中方大臣确实就不入关通商与法国交涉过,而所议内容,也与李秉衡“关口外里许另筑卡房”的意见颇相合。另据李鸿章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初八日透露的情况,李秉衡确实向法国公使戈可当提议,称中国税关应设在靠近法关之处,这样货物出入,双方都易于查核。如中国税关设在谅山城北,法国税关设在谅山城南,这样与恰克图华俄税关相似,对两国官员、商人都方便,对法国更加有益。戈可当对此未表反对,表示容后商议,可见李鸿章对李秉衡等人的意见并非全然不顾[22]。之后李鸿章向李秉衡表示,《中法新约》讲的谅山以北,地理范围挺广,不能说中国的边境就不属于谅山以北。不过李鸿章拟将此问题暂时搁置,待界务问题解决后再议[23]。而且他也强调:边界通商处所指定两处字样,目前断不能再增加,这也算是对李秉衡的一个交代[24]。
然而,与此前滇边通商所引发的争议类似,尽管李秉衡、张之洞等人力阻广西边境通商,但清廷中枢在反复权衡后,最终还是决定以商务换界务,同意广西边境通商。光绪十三年(1887年)一月,法使恭思当(Constans)再次提出滇粤通商处所要求[25]。总署此次却未作过多辩驳,是年三四月间即允开云南蒙自、蒙耗,以及广西龙州为通商口岸,交涉之快,出乎意料。连法国舆论也认为“在法国原不敢有此奢望,存斯妄想”[26],之后的界务交涉亦水到渠成。《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与《中法界务专条》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二十六日一同签押。
消息灵通的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初对清廷中枢在界务与商务上与法方交易已经有所觉察。四月初二他曾发电到京,此外,还另致电李秉衡,要求其致电总署,反对以商务换界务。是年闰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将反对广西边境开埠的疏论上陈。对李秉衡、张之洞的建议,清廷却不以为然。光绪十三年(1887年)闰四月军机大臣传谕诘责张之洞、李秉衡,称张、李二人之前会奏筹边折[指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筹议广西边防折》]内曾提到“龙州开关通商,重兵所萃,请专设道员驻扎该处”[27],认为中法通商处所首选龙州,是他们奏明指定的地方,如今二人却上书极力反对,与此前显然矛盾,其通商地点选择建议也不合常理。从近代中国与外国往来的情况看,沿江沿海与西北各口岸通商与防务可以同时进行,并不冲突,难道就唯独广西的情况特殊,与他地不同?龙州距离镇南关有百余里远,天津距离大沽口也是百余里,京都之与边省孰轻孰重?天津通商并不妨碍大沽设防,难道龙州一通商而龙州以外的地方就全部不再是我国所有?此外谕旨还特别指出:谅山以北,保胜以上,本来并没有划定边界,现经仔细谋划、广泛查求,通商一定是选择繁华处所,大江大河出口处,到处都是这样,若选择穷荒僻远、素无贸易之地,就难以安设税关,驻扎海关管理人员。况且法国已经将江平、黄竹一带及南丹山以内地方划归中国,这时如果中国不在商务上“稍为通融”,仅仅凭言语争辩,难以达到目的[28]。应该指出,张之洞与李秉衡此前的《筹议广西边防折》中,确实有在龙州添设关道的计划,但二人提出设道的建议,本来不是出于经办商务的考虑,而是因为广西边境已设边防督办,应该有文职要员一同办理边疆事务,统领沿边州县百姓事务及对交往事务[29]。而且光绪十二年(1886年)筹边折上之时,正好是李鸿章答应广西边境通商处所暂搁之后。而今天的龙州通商与之前的龙州添设关道提议完全是两码事,两者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完全不同。其实张、李二人对广西边境通商态度始终未变,但清廷却据此加以诘责,也算是朝廷为龙州通商寻找依据。至此,龙州通商已成定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中法界务专条》签订,其中第三款对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签订的《中法越南条约》中两处通商处所予以确认,即“中国所允法国于龙州、蒙自两处设立之领事官及蛮耗设立之领事官属下一员”[30]是属陆路通商处所。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履约相继将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辟为商埠,中法滇桂边境通商由此开始。同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龙州海关。根据条约规定,龙州海关最高长官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这便利了西方列强掠夺中国之原料和倾销工业品。
三、广西边境通商论争的原因
广西边境通商的论争最先发端于中法滇边通商,但此事存在诸多争议。在这场论争中,反对广西边境通商者与同意广西边境通商者各自理由如下。
(一)反对广西边境通商的原因
反对广西边境通商的主要有刘长佑、张之洞、李秉衡、徐延旭、岑毓英等,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通商后外国工业品输入将冲击广西民众生计就业。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法国攻占越南河内,逼近滇粤边境,时云贵总督刘长佑在获知法国拟通过红河与云南通商后便指出“云南向未通商,与沿海、沿江各省情形迥不相同。盖滇省本贫瘠,又经兵燹,赖开采客工,贩鬻小利,以为生计,若一旦夷船运货,机器入山,则民力皆虚,生理尽蹙”[31]。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刘长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广西边境通商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量进入,广西传统农产品和其他特产通过梧州、龙州、南宁三个通商口岸运销到国外。因关税不能自主,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广西民众因农产品无法与外国工业品竞争,遭受掠夺而日益贫困。如田西县(今田林县)“自海禁大开,外货输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城市乡村几于非洋货不生活,经济枯竭,生产衰退,为社会普通之大病态,而生活程度日高,在昔普通每人每年生活费用仅需二三十元而已足者,今则二三倍之而犹不足”[32]。象县(今象州县)“土产外销,与外货内销,价值不能相抵,因而市面金融供求不能适应”[33]。民国时期的《风山县志》对清末以来的乡村情况有记载:“自关税不能自立,洋货倾销内地,无孔不入,农工商业,衰落不振,又无金融机关……因而农村经济,宣告破产,势不得不辗转私借之高利贷。”[34]其二,允许滇桂边境通商,边民可能与传教士之间因其传教问题发生冲突继而引发教案。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广西边境部分民众对传教士等外来人士较为警惕。刘长佑认为“沿边土蛮、回、汉,种类错杂,犷悍性成”,难以约束[35]。张之洞也认为“东钦廉、西太平、上思教最多,上思教堂尤盛。民教积仇”[36]。这是对边民的偏见,但刘长佑、张之洞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云南在同治元年(1862年)发生昭通教案,同治十三年(1874年)发生马嘉理事件,而广西在光绪九年(1883年)发生三板桥教案,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上思教案。滇桂边境通商后,广西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乐里教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发生永安教案,这些案件的发生成为反对通商的佐证。其三,通商后不利于边防。筑牢边防是以两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边疆省份官员的第一责任,因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通商是否有利于边防。张之洞认为:“龙州设埠,镇南关之险虚设矣”[37]。如果允许法国人深入镇南关内的龙州开关通商,那么边防军在镇南关一线的部署便无法发挥作用。如果在龙州通商,法国就会设领事和留兵护商,这等于将敌寇引入家门。为保边防,云贵总督刘长佑甚至主动促请清廷进取越南北圻,在越南保胜、兴化、宣光适中之处驻军,认为如此则可以“固边疆于未扰,不独边军不至于战,即边地亦不劳于防”[38]。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秉衡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将反对广西边境开埠的疏论上陈:“通商条约规定在谅山以北择定通商处所,而谅山以北是就越地而言,自应在谅山之驱驴、文渊等处,法方不应违约;其次,龙州汇越南各水,顺流邕、浔,直达广州,据两粤上游,地位重要,不像江海口岸有各国相互牵制,如果许法国通商,法方无所顾忌,我则难防患于未然;再次,龙州为两粤咽喉,安危所系,不能不争。李在最后强调,入龙通商,有碍边防,危害甚巨。如若同意,无异于纵虎入室,一旦有事,落后边防无法应对。”[39]李秉衡的意见全面、集中反映出两广官员反对广西边境通商的理由。龙州通商前,广西边防压力较小,原有的左江道“历朝南潘向化,自清初至道光、咸丰间,惟于龙(州)凭(祥)营所辖水陆各溢口,以成兵及沿边土司协力防守”[40]。龙州开埠通商后,法国屯兵在中越边境的谅山、高平等地,广西与越南接壤之地皆需设防,边防压力大增。
(二)同意广西边境通商的原因
同意广西边境通商的主要有李鸿章、薛福成、曾纪泽、郭嵩焘等人,他们之所以赞成中法陆路通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通商对边防有利无弊。中法战争爆发前,郭嵩焘认为守护边境的关键是通过法律对边境通商人员加以管理,同时可以通过互市通商来了解西方文明产物,还可以收取经商费用补充边防费用,确实是有利无弊[41]。中法战争后,对于人们担忧的通商影响边防问题,郭嵩焘认为:中国在沿海有通商口岸十三处,长江沿岸通商口有五处,但并没有因开放通商口岸而影响安全。直隶总督李鸿章也用沿海各海口通商并没有给海防带来负面影响的案例来加以说明,认为中法陆路通商于国于民不会带来太大损害[42]。其二,认为通商有利于振兴中国商务。薛福成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知识、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目睹洋货涌进中国城乡后造成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和民族经济凋零,因而他高度重视商品这一“重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及后果。光绪五年(1879年)在薛福成所著的《筹洋刍议》中,他既痛惜地看到洋货进口逐年递增,每年“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43],更从中感悟到发展工商业正是西方国家富强的重要经验。他认识到商品竞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本着“夺外利以润吾民”[44]的宗旨,明确提出通商以振兴中国商务的主张。基于对工商业的认识,中法战争前后,薛福成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或企业家支持中法陆路通商,认为通商不仅不会对中国造成损害,甚至大大有益于边防[45]。其三,避免给法国人以侵略口实。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在巴黎曾向总理衙门陈述筹办越事七条。其中第四条提出:法人常以约中许在红江开埠通商而至今尚未举办以为口实。按法国、越南之约,中国可以不认,越南不能不认,宜劝越南慨然将红江开埠通商,而不可引法、越条约为言。可明告各国,言现遵中国之命,在红江开设通商埠头,允与西洋各国贸易。各国得此消息,既服中国之能调停,又见我与越南情不隔阂,可省无数窥伺之心[46]。可见,曾纪泽同意红河开埠通商是因为越法之间已经签订条约,不希望给法国人以侵略口实。而李鸿章赞成滇桂边境开埠通商,也是基于当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在回复张之洞的信中写道:“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亦未练成,一发难收,则决裂固意中事也。法事与上年俄事又异,俄皇垂毙,持盈保泰,机有可乘;法为德挫十余年,养精蓄锐,欲借孱小以逞强贪利,恐中土未易与争锋。”[47]可见,他认为中国水师未成,难以战胜法国。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分析了李鸿章在越南战场上的消极防御:“李鸿章深知中国无对外作战之能力,滇、粤军尚未尽采新法,军械尤不可精,未必可用;淮军虽早练洋枪,但以朝鲜问题日趋严重,不敢轻调安南。海军方在萌芽,自造之军舰,皆微弱不足道,一旦作战,必遭根本破毁,多年辛苦经营之成果,未免可惜。自始即抱宁弃勿争之政策。”[48]按照这一政策,开埠通商也就不难理解。
综合来看,论者在广西边境通商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多与自身职责、对西方的了解程度有关。极力反对通商者以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巡抚或总督为主,对他们而言,边防安全是首要考量因素。而赞成通商者多有出国考察经历,了解商务对于国家兴盛繁荣的作用,或多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对中国与西方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有较深了解。此外,对自身集团利益的关注也是重要原因。
总之,军事与经济实力是外交的基础。晚清政府在议定广西边境通商问题上之所以左右踌躇、进退失据,固然是因其不谙世界大势,但也受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所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抓住机会,发展自己,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才能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