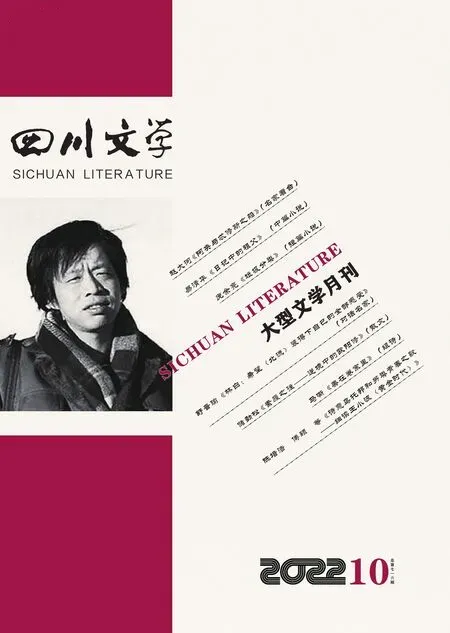此味在人间
□ 文/胡曙霞
一姜知冷暖
厨房角落,若少了姜的身影,便觉得空落落的。烧鱼、熬汤、炖肉,哪一样少得了姜?看其外貌,极是寻常,灰棕表皮,肥厚根茎,拇指般的姜芽严密无缝。若要洗净,非得将姜掰开不可。撕裂的地方,颜色鲜黄,闻一闻,芳香扑鼻,放嘴里舔一舔,辛辣无比。
却是这辛辣,让人欲罢不能。少时,外婆喜欢种姜,狭枝长叶,纷纷披披,仿佛迷你版竹林。一棵拔出,连须带土,乳黄的皮,嫩红的顶,肥硕的躯,拎手中,抖索几下,泥土簌簌,一指连一指,一芽挨一芽,端的是大丰收。掰下茎叶,清理洗净,一块块嫩姜,黄皮红顶,让人一看便溢出口水。或腌,或炒,嫩中带辣,脆中藏香,吃起来停不了口。嫩姜出土的日子,凭空多吃几碗饭,姜炒肉、姜炒豆,无论哪一样,都让人欲罢不能。
小姨父是腌姜能手。嫩姜丰收的时节,他把家中的玻璃罐,一个个洗净。阳光下,一字儿摆开,锃锃发亮。嫩姜洗净,拍裂入盐,捏出水。而后一块块装入玻璃罐,压紧,倒白糖和香醋,密封。一周后开瓶,用干净的筷子夹一小碟,配稀饭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节,你若到姨父家,好客的他非赠你一罐腌姜。回得家中,有事没事,总惦记那姜,仿佛三岁孩童,隔三岔五,便要掀开盖子,用筷子夹一块放入嘴中,且甜、且酸、且辣,脆嫩爽口,别有滋味。吃一块,并不过瘾,过了一会儿,总还要去拿。如此这般,反反复复。
姜是老的辣。老姜一般用于配料,皮成褐黄,皱缩起褶,藏在厨房的边角,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召唤。炒肉、炖鸡、蒸鱼,哪一样少得了姜?入了姜的食材去腥增鲜。这厢的火苗腾腾地烧,那边的黑锅冒出青烟,找一老姜,切半,用手捏着,朝着锅底来回擦。入油,放鱼,煎至七分熟,再拿一块姜,刮皮切丝,撒在鱼身,入水焖一会儿,出锅,味道鲜美。
年少,村庄做喜事,大师傅寻来大姜若干,锃亮的大刀对其嚓嚓切片,雪白锋利的刀从姜的躯上咔咔而落,那姜便成又细又长的丝了。我顶佩服大师傅的刀工,一转眼的工夫,姜块成丝,匀称无二。黄黄的姜丝,落入滚油的大锅,滋滋冒泡,鸡鸭鱼肉,蟹螺虾贝,各式大菜,因了姜的辅佐,灵魂苏醒,活色生香。
冬日,寒雪潇潇。父亲从远方回,须发覆雪,脸色苍白,手脚僵硬。趁父亲拍雪的间隙,母亲嘱我灶中添火,她转身拿姜、捏枣。水烧沸,丢下去核的枣,丢下切片的姜,一碗浓浓的姜汤,递至眼前。汤雾袅袅,一碗滚烫的姜汤落肚,父亲的脸色缓和了不少。他抱我入怀,我依着父亲,淡淡的姜味,喷薄到脸颊,搅出微微的暖。
年关将近,村庄里流行一种糖,美其名曰——姜糖。制糖之人将生姜、红糖等原料兑水放铁锅里熬,熬至糊状,冷却,挂在铁钩上,反反复复地拉扯出一条条糖丝,等到再也拉不动时,便将其切成小块。寒冷的冬天,丢一块姜糖放嘴里,脆香甜辣,绵软滋润,让人温暖又踏实。
长大之后,离开村庄,来到城市,鲜少见到土生土长的姜。城市的菜场也有姜,细细长长,纤维颇多,吃在嘴里总不是家乡的味。有一年,厨房少姜,在拼多多购得黄山老姜一箱,分量足,价格低,足足用了一年还有剩余。来年春天,剩余的老姜冒出芽,吐出叶,一副要开花的模样。然而,姜是极少开花的,即便开花,也只是穗状花序,鳞状苞片,仿若松果。我没见过开花的生姜,却见过白色的野姜花,一朵朵,仿佛展翅的白蝶,那清冷翩跹、山野之姿,与姜的品性,无比契合。
青葱撒佳肴
乡下人家,处处栽葱。门前、屋后、墙脚,破瓮、旧盆、粗罐,哪里都有它。你看它,不挑不拣,不声不响,一把泥,几撮灰,均匀地扭出来,纤纤细细,娉娉婷婷,如同诗经楚辞中走出来的小美女。
古人形容美人的手指喜欢说“指如削葱根”,可见这葱,自有独特的韵味,楚楚之姿,青青之色,一团绿意,惹人欢喜。
《红楼梦》里也写葱。四十九回,贾府一下子来了四位姑娘,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琦。晴雯欢天喜地地说:“大太太的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把美人比作水葱,贴切而巧妙。可见,葱是清秀美好的代名词。青葱婷婷,又齐整,又鲜嫩,可不就是美人儿纤细的身姿吗?
葱的好,不仅仅在于它的美,还在于它的亲切随和。作为食材界的“和事佬”,葱具有去腥、增香的作用,葱叶、葱白,葱实、葱汁皆能入药。从小吃到凉拌再到炒菜,葱味家常菜可谓丰富多样:葱油饼、葱包烩、葱姜炒蟹、葱油拌面、葱爆羊肉,哪一样都让人口舌生津。
葱的种类极多:大葱、楼葱、胡葱、羊角葱、小葱,不一而足。南方人栽葱,大多是小葱。小葱又名香葱,葱叶青翠、葱白纯净,连根拔起,细须沾泥。将葱白外面的薄膜剥掉,洗净,切断,撒上,仿佛一朵朵绿茵茵的小花轻轻绽放。小葱绵软,遇热伏贴,它们闭合葱管,乖乖地贴着菜肴,点缀、调味、增色。
北方人喜食大葱。不同于南方人用小葱当佐料,北方人把大葱当蔬菜。一张烙饼,一簸箕大葱,左手大葱,右手大饼,咔嚓咔嚓地吃起来。那是葱最豪迈的吃法,不烧不煮甚至不用蘸酱,咔嚓几下,大葱就着烙饼入了北方人的胃。南方人若看到,一定会惊诧到张口结舌,南方小葱相较北方大葱实在是婉约细致。
门口一盆葱,做菜不用愁。这厢灶火腾腾,那边豆腐出锅,掐一把绿葱洒上,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色泽先是勾了你的口水,更兼那香,匀称有致,丝丝缕缕,扰了你的齿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莫急,拿稳筷子,夹一块豆腐,小口小口地尝,嫩滑之余,小葱绵绵,香得舌尖打转。
每年4-7月,葱的尖头爆出白色的小花,花儿细细碎碎,聚成一团,绒球一般,远远望去,仿佛绿裳姑娘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风吹花摇,簌簌而摆,甚是有趣。开了花的葱,也结籽,用籽去播种,还会长出新的葱。也有把花掐掉的,那样的葱依然鲜嫩不老。还有人把葱挖出来,球茎的瓣掰开,分开种,每个茎瓣也会长出新的一簇。
小时,家住小镇,晨起读书时都会遇见一卖葱少年。一身蓝裳,一篮小葱,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他也不吆喝,就拎着一篮青葱,静静地站在你家门口。一定会买的,一为少年的青涩懂事,二为香葱的鲜嫩可人。吃完撒了葱花的面条,我便背着书包上学去。还是会遇见那少年,一篮子的小葱已然见底,他沐着金色的朝阳,小鹿一般奔向学校。
搬来城市后,少见了葱。有一天,在小院的角落遇到它,仿佛遇到旧相识。它们站在泡沫箱里,一簇簇,且直,且立,青青碧意,绿到泛白,精神好得很。
“要吗?尽管摘去!掐了又长,长了又掐,多的是!”见我痴痴迷迷的样子,葱的主人——二楼的老太太笑着说。
“谢谢您!这葱栽得真好啊!”我由衷地赞叹。
“葱好种,挪几株给你,烧菜的时候,想掐多少就掐多少,香得很咧!”老太太慈眉善目,仿佛老家的外婆。
没等我拒绝,她弯腰拔葱,一棵棵带着泥留着须的青葱塞到我手心。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一缕缕香,在鼻翼轻手轻脚地溜达。
自此,我家窗台多了一盆葱。它揽住过往的清风,喝着飘落的雨水,自生自长。炖竹笋、炒肉片、蒸黄鱼,都要撒葱花儿。有了百搭调味品——葱,普通的一盘菜立马活色生香。
常常的,家里的那人在厨房挥勺忙碌,忽然,他探出头,喊一声“掐几根葱来!”我便丢下书本,蹦到窗台掐葱,一根,一根,又一根,洗净,切段,撒在菜肴的上方。因为葱,寻常的一顿饭,吃出了不一样的味。
大蒜辛辣香
乡下人家,结蒜成辫;厨房烟火,因蒜生香。蒜衣薄薄,层层剥下,露出洁白的身、鼓圆的腹。蒜瓣轮簇,润洁如玉,凑近细闻,香气扑鼻。然,不喜蒜之人,以为是臭气。
我喜蒜,一丝辛辣,一味香,味觉臣服,肺腑舒畅,多日郁闷一扫而空。一颗蒜,为一道菜肴添加内涵,食之,诸多回味。乌冬菜、空心菜、苋菜,各类蔬菜,以蒜调味,鲜美异常。常常的,这边的锅注入油,那边的蒜拿将出来。油在锅里冒青烟,案板上的刀一横,对着蒜啪啪一拍,薄薄的外衣松了。扯住,抖索,蒜瓣溜出,也不用切,只管拿刀继续横着拍,啪啪两声,蒜瓣扁裂,汁香四溢。将其抓起,丢入热油,香得浓郁之时,将青菜推入,翻炒两下,油亮发绿之际出锅。这入了蒜的青菜,去了土腥味,色香味俱全,三五两下便入了口。
而我对蒜最早的记忆便是儿时在姨娘家吃过的腌蒜。一小罐玻璃瓶,倒入米醋、糖、盐,把洗净的蒜头没入,密封。几天后,姨娘时不时地从玻璃罐里夹几颗腌好的蒜头放在小碟子里。表姐稀罕它,捏一颗入嘴,咔嚓咔嚓地咬起来,微微地闭着眼,直说好吃。我看了,也忍不住尝一尝,浓郁的辛味在口腔打滚,差一点辣得我眼泪掉下来,可不敢轻易尝第二个。表姐又若无其事地嚼起来,咔嚓,咔嚓,清脆动人,一副销魂的样。我忍不住又跟着尝了一颗,可也奇,只觉没有先前的霸道,酸甜爽口,不腻歪。嗯,不错,越吃越上瘾。
原来,有一种味觉,习惯之后,化干戈为玉帛,又以绵绵的温柔,悄无声息地俘获你——蒜便是其中的一种。尝试过它的烈马奔腾,虽然颠簸得让人流泪,却也体验了快意恩仇的刺激!至此,迷上它的辛烈,世间美食,有蒜慰平生。
在河坊街买过一瓶辣酱。尝一口,便中意。辣酱里拌入蒜末,又辣又香,吃得人浑身冒汗,却又欲罢不能。一碗面,加入两勺这样的辣酱,蒜香入汤水,袅袅娜娜,直捣舌尖,神经的细枝末节忽而放大、忽而收缩,如此这般,蒜的香味注入肺腑。一碗汤面落肚,心满意足,直呼过瘾。
取整粒大蒜放入蒜臼中捣碎,用色拉油小火炒熟,炒出香味,便是蒜蓉。细瞧那蒜蓉,细细密密,香香软软,它们大面积地覆盖在金针菇、生蚝、开背虾、烤茄子之上,各式菜肴因了蒜蓉的浇筑,去腥、和味,散发出无法言说的香。入夏的蒜蓉小龙虾便是其中翘楚。蒜蓉半斤,葱少许,啤酒两听,另有胡椒粉、白糖为辅料。小龙虾去线入油锅里炸,捞出,取蒜蓉,一半煸炒,一半增味。一盘红艳香美的龙虾装盘后,嘬一口,蒜香直击味蕾,让人浑身抖机灵。
蒜的辛烈让初尝之人辣得流眼泪。可也奇,它的不羁入了面包、鱼、肉,却又变得柔软芳香。原来,遇到对的食物,蒜也会漾出倾世温柔。这样的互相成就,好比良师、诤友,以及上好的爱情。
《齐民要术》载“八和齑”制作方法,其中重要的一味就是大蒜:“蒜:净剥,掐去强根,不去则苦。尝经渡水者,蒜味甜美,剥即用”。在陕西,面馆里摆放大蒜。客人来了,一碗面,一颗蒜,边剥,边咬,边吃面。如此豪放的吃法,端得适宜蒜的性情,越吃越得劲,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蒜的好处很多,杀菌、排毒、降血糖,是血管清道夫。食蒜之人,久而久之会上瘾,见蒜便漾出口水,溢出欢喜。甚至,遇到烦闷之事,吃一顿入了蒜的食物,也会天高地阔,心境畅快起来。
紫苏慰食客
一场梅雨养肥了楼下的紫苏,一棵棵,一丛丛,高壮繁密,蓬蓬勃勃。
每次下楼,见到它,仿佛久违的老朋友,些许亲切从心里冒出来。
紫苏,紫苏呀,念一念它的名,只觉得好。紫是紫苏的紫,苏是紫苏的苏,紫苏两字合一起如此相宜,诗经里的词句一般,耐人寻味,况味悠长。
况味悠长的,一定还有儿时写作文常用的一个词:“光阴荏苒”。可又有几人真正知道“荏苒”的意思?“荏苒”,古语中指苏子。苏子,又名紫苏。古人用紫苏枯荣轮回的过程,比喻时光流逝。
草木一秋,紫苏枯荣。斗转星移,物转人换。
紫苏年年发芽,年年长叶,细腰身,娉婷姿,一身紫裳香细细。哪里没有它?房前屋后,阶缝墙角,处处都有它。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浑身紫盈盈,有的一面绿一面紫。只需在院子随意走几步,就会碰到它。
谁种的?没印象。似乎从老宅盖起的那一天,紫苏就在。许是风吹来的种子,许是鸟儿衔过来的苗,总之,它们就那样自由自在地长。想在哪里发芽就在哪里发芽,想在哪里开花就在哪里开花。谁会管它?谁也不会管它。紫苏生就一副自在的好模样,想长叶就长叶,想结籽就结籽。
大暑的天,热气腾腾。二叔从溪水里摸来溪螺,青壳,尖尾,隆背,用手抓一抓,沙啦啦响。可不急,清水养,吐净泥,再剪尾。
烧一锅清甜的溪螺汤,是大暑天里美美的盼头。姜切细,蒜拍碎,猪油下锅,盐粒儿蹦跶,一勺溪螺下锅,唰,唰,唰,铲子在铁锅与溪螺间欢快地歌唱,螺尾发亮,螺盖掀开,注入一勺水,慢慢地熬吧。
霞儿,掐一把紫苏来!油烟的香味好闻得紧,奶奶遥遥递一声。我蹦跶着去了,随便一蹲,便瞧见了它,叶团有尖,边缘有齿,卵圆铺排,憨厚可爱。挑那最好的,对准叶柄,轻轻一掐,紫色的叶片,落掌心。
总得掐下四五片,洗净,切细。溪螺汤沸了,撒下紫苏,凛冽甘辛的香,迎面喷涌。加了紫苏的溪螺,清甜醇美,夹一颗,撮嘴吸,鲜嫩的螺肉,在口腔轻歌曼舞。
除了溪螺,紫苏还可与溪鱼、拉面、土豆相佐,整个夏天,我的舌尖与紫苏缠绵,徜徉在紫苏的香里,神清气爽,盘桓不忘。
秋日,清蒸大闸蟹,也少不了紫苏。蟹腹放紫苏,去腥增香,爽口解腻,驱寒暖胃。吃罢螃蟹,手指染腥,不易去。用紫苏叶煮的水洗一洗、闻一闻,香喷喷。
多年以后,知道有一种紫苏叶熬的汤,叫紫苏饮。远在宋朝,人们流行紫苏饮,明代养生书里记载着:“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候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倾去,将泡过的紫苏入壶,倾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
紫苏饮解表散寒、行气和胃,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作家周华诚也喜欢紫苏,用文字夸奖它:“可以去尽腥膻之气、俗世之气、市侩之气、铜臭之气、造作之气,让它的同伴、邻居,都沾染上它的芳香。”这便是紫苏,如兰芝,似涧水,能洗涤,能去污,以一身细香抚慰红尘食客的心。
这样的紫苏岂止在舌尖?我曾用过紫苏面膜,水淋淋、香喷喷,养得皮肤水润洁净;我曾穿过紫苏染过的棉麻裳,一席淡紫如云似雾;我曾欣赏过一束用紫苏成就的插花艺术,紫意盈盈,别具一格……
紫苏,紫苏,只轻轻地喊一喊它的名,便有一股细香在唇齿间蔓延……
香菜意绵绵
居然有一种菜叫香菜。这名儿有意思,一听便记住了。香菜,香菜,该有多少香,从菜中而来。然,说是菜,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和葱花、姜丝、蒜头一样,撒在菜肴之上,起到点缀、提味之用。
香菜又名芫荽,状似芹,茎纤细,叶缺刻,多用于凉拌菜。香菜肉丝、香菜饺子、凉拌香菜、虾皮拌香菜,都是吾乡之人常吃的佳肴。尤其是海蜇头,必有香菜辅佐不可,人们无法想象没有香菜的海蜇头如何上桌,那味道必然大打折扣。你看,晶莹如丝的海蜇头,伴着纤细的香菜,风雅如画,别样风情。再品,脆爽之余,浓郁的香味次第传来,斑斑驳驳,如暗月之花,浮动一片美。
第一次尝香菜,年幼之时。婆婆煮芋头,起锅之际,撒上香菜,入口一尝,一股呛鼻的味,腾挪移闪,熏死个人。一口吐掉,呸!难吃,太难吃!哪来的菜,顶着香的名头,去诓人。简直就是菜中小霸王,浓味儿灌下去,也不管你是否受得了。
哼,再也不碰这玩意儿。
没承想,诚心躲,却总也绕不开。门前、屋后,破缸、旧盆,哪里都是它的家。一丛丛,一簇簇,细细密密,绿色的烟雾一般,弥漫、扩散、氤氲。
吾乡之人喜爱它,顿顿离不了,一边烧菜,一边支使娃娃,去,掐一把香菜来。那娃儿便撒开腿儿欢蹦而去。
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它的?回忆找不出相应的源头,只知,后来的我,觉得香菜浓郁好闻,让人如痴如醉,一盘好菜,非有香菜不可。甚至,我能蘸醋生吃香菜,越嚼越香,香到四肢百骸,香到不能自已。
原来,有一种菜,很耐吃,还能吃上瘾。如同一个人,越相处,越喜欢;越喜欢,越深爱。
我想起我的叔叔了。
叔叔其实不是叔叔,是我的继父。读初中那年,叔叔来到我家。当时的我,满怀戒备,青春期的叛逆如同一株长刺的仙人掌。他呢?呵呵一笑,包容所有,仿佛他的身套着一件软猬甲,刀枪不入。攻击屡屡无效后,我慢慢收敛刻薄与尖锐,缴械投降。
叔叔会种菜,种子随处一撒,豆苗儿争先恐后地蹿出头,同样的四季豆,愣是比别家的肥胖鲜嫩许多,同样的丝瓜也比别家的丰满俊逸。所有的菜蔬里,叔叔最爱香菜。家门口的一小片地,常年种着它。只见他随手撒下香菜的种,不几日,它们便扭着绿色的小身段,娉婷而生。茎儿纤细,叶儿羽状,远远望去,绿意蒙蒙,生机勃勃。
家有香菜,香飘十里。
炒面、蒸鱼、炖汤,哪一样菜肴离得了香菜?叔叔的香菜,让日子逐渐丰盈,仿佛一块棉布绣了朵小花,添了一点点鲜,染了一点点艳,细细品咂,有说不出的好。
傍晚,天边的红云腾腾地燃烧,家里的大锅油烟四溅,“哧溜”一声黄鱼入锅。“霞儿,去门前摘香菜!”叔叔一边用勺子将鱼翻身,一边朝我喊。
“好咧!”我欢蹦而跑。一地的香菜,绿莹莹的春水一般,随手一掐,满手香。两面金黄的鱼儿配上绿绿的香菜,好吃又好看。家人围着,边吃边聊。一顿饭,总要吃到月上柳梢头。
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一直过下去。没承想,五十岁的叔叔,得了癌症。他去的时候,满地的香菜忽然开了花,雪白的小花,喷涌而出,遍地的香,前赴后继,仿佛淡淡的哀伤,缭绕不息……
辣椒烈如火
辣是一种痛觉,而非味觉。辣椒入口,针挑刺戳,灼烧绵密。不会吃辣之人,受了刺激,免不了吐舌喝水、挥手跺脚,嘴里嚷着,再也不吃辣了。可也奇,吃着吃着,也就习惯,甚至无辣不欢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家小女便是其中一个,五六岁之时,面条加辣椒,吃一口面,跑到门口吐一回舌头,再吃一口面,再跑到门口吐一回舌头,一边吃一边大喊:“妈妈,不好啦,嘴巴着火了!”吃着,吃着,也就上瘾了。
家里厨房,辣椒必备。红色的、绿色的,尖的、圆的,新鲜的、罐装的,摆放在伸手可及之处。烧鱼头、炒螺蛳、烤羊排,都需辣椒点缀。这些佳肴,因辣而奔腾,鲜衣怒马,豪爽刚烈。
无辣不欢的城市很多,长沙、贵阳、武汉、重庆、成都、太原……以辣出名的菜肴亦不少,西安的酸辣鸡杂、重庆的辣子肥肠、武汉的麻辣牛肉、成都的麻辣烫、长沙的剁椒鱼头,它们因辣而驰名。辣椒的种类,自然也多,朝天椒、灯笼椒、羊角椒、印度鬼椒、巧克力辣椒等等,因辣椒制作的调料也不尽其数:辣椒油、辣椒酱、剁辣椒等等。
因了小女食辣,我家窗外种满辣椒,叶椭圆,茎较粗,花白色。那花虽小,却也耐看,纯白剔透,细小玲珑。花落,辣椒从花托处扭出来,先是绿的,后转成红的,一个挨一个,喜气洋洋,炮仗一般,甚是可人。家有辣椒,做菜不愁,这厢的鱼刚下锅,那边喊声丫头摘辣椒。鱼焖至七成熟,新鲜的辣椒刚刚剁好,撒进去,遮腥增味,火烧火燎,让人吃了直咂嘴吐舌。
看过一部纪录片,陕北人家的晚饭时光。家穷,无余钱买菜,一大碗手擀面,捞在粗瓷大碗中,剁碎的红辣椒粗粗地泼上去。老子、儿子、妻子,手捧红艳艳的手擀面,蹲在家门口,埋头痛吃,稀里哗啦,大汗淋漓。那样的酣畅,极富感染力,让人不得不相信,这拌了辣椒的手擀面是世上最美的食物。若干年之后,纪录片的内容几近忘却,那户人家吃面的情景却根深蒂固,红红的辣椒、白白的面条,嗦嗦的声音,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辣椒究竟有何神奇,竟为穷苦人家的食物注入光芒?一趟西安之行,让我寻得了谜底。羊肉泡馍、西安凉皮、关中搅团、辣子疙瘩、油泼辣子面、肉丸胡辣汤,西安的每一道美食都离不开辣椒,一座城,因辣生香。即便如此,店家还怕你不够辣,一瓶瓶辣酱桌上供着,凭君任取。品尝西安美食亦是与辣椒较量的过程,辣意纵横,灵魂尖叫,这厢细汗纷纷,那边意犹未尽。辣椒的美意在西安的美食里得以淋漓地展示,仿佛身着红衣的少侠,踏马江湖,快意恩仇。此中意境,灼灼燃烧,热血沸腾,不能与人语。
杭州有一家隐石餐厅,藏在大井巷的深处,此家餐厅有一招牌菜——好吃的羊排。满满的一盘红色尖椒,油亮细长,密密叠叠,好吃的羊排藏匿其间若隐若现,捞一块,尝其味,松脆可口,辣意可人,好吃,果然好吃。这样的一道菜,因了辣椒,色鲜艳,味劲爆,让人难以忘怀。
途经南宋御街,被一家酱铺的香勾住脚,剁椒拌大蒜,红红白白,碎碎密密,一股子辣香满街淌。忍不住地住了脚,忍不住地拿眼直勾勾地看,忍不住地舌尖沁出口水。想着,拿这辣酱拌面条或煮鱼该是何等痛快。哪怕什么也没有,直接拌白米饭,亦是吃得人额头冒汗、舌头打转呀。忍不住买一罐,忍不住用筷子尖蘸一抹,拌菜、拌鱼、拌鸡爪、拌白米饭,一顿饭因了一点点辣酱吃得那叫一个痛快,一忽儿口腔着火,一忽儿蚂蚁啃食,各种滋味,纷沓而来,够味,够狠,够劲。明明辣得说不出话,偏就迷恋那股子劲,舌尖的味蕾,在辣酱的刺激下,暗夜的烟火一般,咻的一声,炸出红的黄的紫的蓝的斑斓。
如今的我,已和女儿结为盟友,共同成为辣椒的忠实粉丝。常常的,我点一盘酸菜鱼,她点一道爆炒牛蛙,一样的香嫩爽口,一样的辣意十足,一样的直呼过瘾。每每这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宋祖英唱过的歌:辣妹子从来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出门怕不辣,抓一把辣椒会说话……
八角茴香醇
南方人的厨房少茴香,除非炖肉、熬猪蹄、煮茶叶蛋,也无须多,就那么几颗,散散地落入食物中。看其外表,顶有趣,八角的星星一般,精美的盘扣似的,它们在熬制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芳香绵绵地释放,为食物注入鲜甜的美味。
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国时期的美女,大乔与小乔是一对姐妹花。茴香也有大小之分,大茴香,小茴香,然,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大茴香,乔木果子,八角形,香料之王,是卤制品、炖焖菜肴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小茴香,伞形科草本植物,可做菜蔬、香料,是煎饼、饺子、团子等馅料的最佳点缀品。
北方人爱吃小茴香,拎一把小茴香于手中,几近染一捧绿雾或绿云,那叠叠的叶,温柔得让人心疼。在小茴香妖娆的姿态、摄人魂魄的气息里,北方人找到了归属感,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小茴香置于馅料、蛋液、面粉中,包饺子、做包子、摊饼子,绿色的小茴香在北方人的舌尖绕出别样芳香。那滋味,深入人心,让人上瘾。
而南方人口中的茴香,自是大茴香。大茴香又名八角,因其能除却肉中臭气,使之添香,故名茴香。大茴香即大料,学名八角茴香。一颗颗八角来自高高的八角树,它们在枝头成熟、老化、掉落。孩子们捡拾林中八角,或捏在指尖,或置于手心,细细观之,辐轮匀称,精美如花。
《本草品汇精要》中对八角如是描绘:“其形大如钱,有八角如辐而锐,赤黑色,每角中有子一枚,如皂荚子小匾而光明可爱,今药多用之。”八角可入药,温阳散寒;亦可入食,增鲜添味。在南方,八角用于食物的概率并不算高,偶尔与之相遇,便被那一丝别样的味觉所牵绊。它们像舞台上的配角,面目模糊,却又在某种菜肴中扮演点睛之笔。添加了八角的食物,味觉丰美,斑斓灿烂,让人品咂不止。八角可调味却不能单吃,若不小心,夹一颗入口,定会被其“怔住”,而后,迅速吐掉。
在广东、广西、云南一带,八角树葱郁茂密,挺拔高耸,倒卵状的叶,层层叠叠,泼油一般。森森八角林,暗香隐秘。风吹树梢,深绿的光泽一片推动另一片,有阳光从叶尖滑落,一滴又一滴。静静地听,慢慢地看,仿佛跌入芳香秘境,直欲寻香而去。
枝头上,深红的八角花,鲜艳欲滴、玲珑别致。是美人额前的朱砂痣,抑或是玲珑别致的红风铃?它们藏在茂密的绿叶间,仿佛深海里的红鱼,摇曳着,闪烁着。风过,雨过,红花结绿果,八角形的绿星星,累累垂枝。
一边开花,一边结果,是八角树的特点。果子沉沉,花儿灼灼。早熟的那果,自然落地;迟一些的,或站着采收;或用小竹钩采摘。因其花果同生,采摘时要格外小心。顺风而落的八角,孩子们欢呼着去捡。他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寻宝一样。
采摘回来的八角摊晾在晒场,果实肥大,颗粒饱满,密密匀铺。热烈的阳光亲吻着八角,在它们身上留下细细的吻痕,只听一阵噼啪作响,八角的芳香破壳而出。它们成群结队,活泼的蝴蝶一般,散入风中,飞入门庭。风化后的八角,成了棕褐色的干果,人们将其卖去,或入了中药房,或入了寻常人家的厨房。
江南的主妇们,拿出八角几颗,制作待客的美食:江南红烧肉、茶叶蛋、盐水毛豆、小鸡炖土豆,都有八角的身影。而卤猪蹄、卤鸡爪、卤鸡翅、卤鸡胗,各式卤味更是非有八角不可。
大姑是制作卤味的高手,她的手常年与八角接触,以至于指尖绕着无法言说的香味。有远客来,大姑洗净双手,准备美食。大锅架好,柴火燃起,加水,入调料:八角、花椒、料酒、姜片、鸡翅……大火将水烧沸,转小火慢卤。时光静静,风儿轻轻,空中弥漫着无法言说的香气,八角、花椒、姜片各种调料相互融合又齐齐作用,翅尖的骨骼滋啦作响,鲜嫩的翅中慢慢收汁。
卤好的鸡翅,冒着热气,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拿一个放嘴里咬一咬,软糯的肉筋、上瘾的酱汁,让人赞不绝口。其间,那一缕八角的香,一牵一扯,若有若无,吃得人欲罢不能,黯然销魂。
八角,茴香,果真是迂迂回回的香、缭绕不绝的味。“草”字下面一个“回”,回的是雨露精华、日月芬芳。它们如散落的八角星星,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忽隐忽现,在平淡的光阴里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