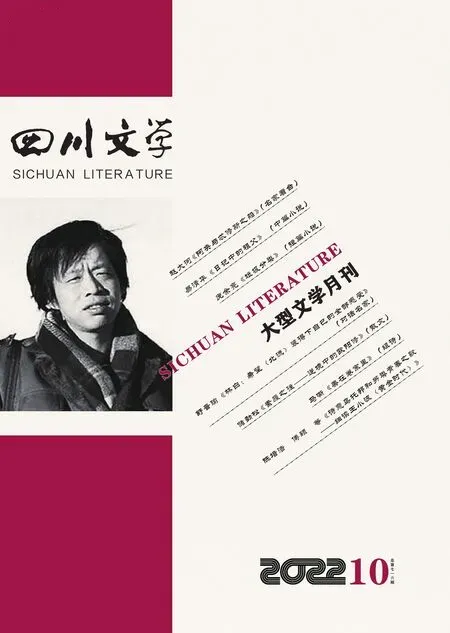垃圾分类
□文/庞余亮
男人四十一枝花,男人五十豆腐渣。这是女领导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快跨入豆腐渣的那年腊月,也就是我四十九岁那个腊月,女领导说得特别多。估计她把我当成孙悟空了,这句话正好是紧箍咒。提醒。警告。潜台词是:快成豆腐渣了,可别再嘚瑟了,可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当然是错误的,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手机也是错误的。拿起拖把拖地“做样子”是错误的,真正拖起地来“存心地滑导致谋害”也是错误的。
我越是不嘚瑟,女领导的脾气反而接近爆表。爆表的程度差不多从三段直接涨到了九段。我是不会上当的,宁愿成为夹着尾巴的豆腐渣。
为了不和女领导发生碰撞,我学会了做一个逃跑主义者。理论根据很多,比如,“豆腐渣”眼不见为净。比如,三十六计,“豆腐渣”走为上策。比如,“豆腐渣”要去外面完成我每天10000步的必修课。
如此甩手逃跑等于变相抗议也是错误的。必须在下楼的时候,还应该时刻把女领导放在心上,主动请缨扔垃圾,把女领导已分好的垃圾一一扔到楼下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里。
“别扔错啦!”
“得令!”
“什么得令不得令?!不能扔错!”
“晓得。”
只有我回答“晓得”这个词的时候,女领导这才放心让我这个“豆腐渣”接过她手中的各类垃圾堆。
“扔完记得洗个手。”
“晓得。”
无论是“晓得”还是“不晓得”,10000步完成之后回家,还要“晓得”洗手。专门讲投降和招安的《水浒传》里的“晓得”这一词是“省得”。省得。晓得。不省得。不晓得。但无论“省得”还是“晓得”,豆腐渣的生活就等同于垃圾。生活。垃圾。过去是往一个垃圾桶里扔垃圾。自从有了垃圾分类,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变成了:生活。垃圾。垃圾分类。往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里扔垃圾。豆腐渣的生活就是这样波澜不惊。
生活波澜不惊并不等于没有波澜。最近的波澜产生于我家女领导和在北京上大学的林公子微信通话之后。开始的时候,女领导并不满足于微信通话,她需要的是和我们家林公子的视频通话。这是她和林公子上大学前的约定:妈妈会很想你,必须保证每天10分钟视频通话。林公子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到了北京,林公子坚决不同意视频通话,他只接受微信通话。林公子的口气很坚决。女领导本来还想坚持,我悄悄暗示她,儿大不由娘,如果再坚持的话。这微信通话的待遇也会取消的。因为人家翅膀硬了。
“什么人家?不是你儿子?如果不是你这个做老子纵容包庇,他哪里会这样不听话?”
我什么也不会说,豆腐渣的命运连臭豆腐的命运都不如。
腊月应该是那个长硬了翅膀的林公子放寒假的日子了。过了腊月十五,女领导就忙好了过年的一切,就等林公子放假回家了。
事情做完了,女领导就不再折腾豆腐渣了,而是会让我这个豆腐渣陪她一边吃零食,一边追看电视剧《人世间》。那个愁眉苦脸的雷佳音,惹我们家女领导哭了好几回。
腊月二十下午,也不知道为什么,抹干眼泪的女领导忽然拿过我的手机。我们家女领导经常检查我的手机,我是一点也不害怕的。没密码,没隐私。但我没想到女领导是用我的手机给林公子打语音电话。还用了免提。过了会儿,那边响起了林公子极其不耐烦的声音。女领导又把手机移动到她的面前,说不许你老爸想你啊。过了会儿,女领导和林公子聊了起来,说了她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时,林公子突然打断女领导,说他准备后年考研冲刺,寒假不回来过年了。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把手机又扔到我面前的女领导慌乱而焦虑,瘫坐在沙发上叹息。
“喜鹊尾巴长一长,娶了媳妇不要娘。”
女领导的情绪立即转移到喜鹊的尾巴上了,对我的安慰不理不睬。林公子那边挂了手机。这个臭小子,捅了一个马蜂窝。我俯身收拾女领导面前的零食壳。这个月的训练,我已知道这些零食壳都叫作“厨余垃圾”。
我还是错了。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枝花,不是所有的零食壳都叫厨余垃圾。花生壳是“厨余垃圾”,开心果的壳就不是“厨余垃圾”,而叫作“其他垃圾”。
再后来,我就属于“其他垃圾”了(本来豆腐渣是属于“厨余垃圾”)。女领导把这件小事迅速扩大了。如果因为这次归类不准确,我们家分类垃圾被社区检查发现,应该得到的1分没得到,那会在我们这个单元拿不到前3名。前3名的奖励是3卷垃圾袋。天啦,就这3卷垃圾袋,我们家女领导把坐在书房里的我数落了整整1个小时。
女领导说不是钱的问题。
我说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女领导说她从来就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女领导说得当然全对。所有的“对”都是她的,所有的“错”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大鱼吃小鱼。在我们家,林公子在北京上大学,家里就两条鱼。女领导当然是大鱼,我必须是心甘情愿被吃的小鱼。当然,我也是那个不到五十岁的豆腐渣。每天必须走10000步的豆腐渣。
今天我不想在马路上完成这10000步了,我想躲到人民公园里完成这10000步的必修课,即使人民公园有为了防疫而需要的烦人的登记手续。
公园里满是中年男人和老年男人。我敢肯定,他们基本都是被脾气大的女领导“赶”出来的豆腐渣。有的豆腐渣和豆腐渣打牌,有的豆腐渣和豆腐渣下棋。这都是自暴自弃的豆腐渣。还有一部分努力想做一枝花的豆腐渣,红红绿绿的运动衣,构成了围着公园中心湖转圈的暴走团。
我无法加入打牌的豆腐渣团队,也不想围观下棋的豆腐渣团队。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尾随着暴走团的尾巴走了一圈。微信的步数顿时上升了2000多步。再想女领导有关“开心果”的训话就没意思了。我想如果跟着他们再走4圈,10000步必修课就完成了。
滥竽充数的人只要心安理得,是很容易混下去的。可我的身体素质的确就像豆腐渣,到了第三圈,我已落后大半圈。到了第五圈,我整整落下一圈,好在我的10000步快完成了。也幸好落后一圈,准备脱离轨道的我就被多年不见的薛师傅逮住了。
平凡的日子被熟人逮住了是有意思的。本来豆腐渣们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即使有林公子不回家过年这样的事情,也不过是微波,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冲击。林公子回家,最高兴的是女领导,她会每天过得特别忙碌而充实,而我则被继续孤立在家,成为大鱼小鱼都不吃的小虾子。我暗暗感谢那些被我误分的“开心果”壳,如果不是那些“开心果”壳,我就不会到大公园来,也不会被薛师傅逮住。
薛师傅是父亲生前非常要好的工友和棋友。薛师傅笑着讲了他的两个孙子是白眼狼的故事。他去南京帮着带大了,进了幼儿园就不要他们了,还嫌弃他不会说普通话。于是薛师傅又回来了。我赶紧也“出卖”了我们家林公子的情况,同样是个白眼狼。
薛师傅感慨地说他们这一辈早翻篇了,比起我去世的父亲,他算是赚大了。为了不让谈话太过于消极,我讲如果不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下岗的事,我极其有可能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也进机械厂,极其有可能成为薛师傅的徒弟。因为父亲说全厂就薛师傅脾气好技术好。薛师傅哈哈大笑,说我父亲是爱屋及乌。论技术,全厂还数我父亲林来根。再后来,薛师傅就说到了高建年。我还一下子想不起来高建年是谁。
“高建年,就是差点成为你的老丈人,那个想招你为驸马的高建年。”
薛师傅又说了一大通我的“老丈人”和我父亲恩恩怨怨的故事,薛师傅说我父亲和他都和这个狗脾气的高建年吵过架喝过酒还断过交。当然后来又和好起来了。
高建年不是我的“老丈人”。我也不能承认这个“老丈人”。要是说给我家女领导听的话,会引起世界大战,甚至宇宙大战。女领导的父亲,也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正和老岳母一起在苏州为我小舅子一家做牛做马呢。
薛师傅说高建年的一生比电视剧好玩,比如打老婆。
“这个老高啊,怎么下得了手的?”
这是父亲常常感慨的话。
“都是黄汤灌进去了呢。”
这是母亲的回答。
他们不说名字,我也知道是那个高建年。高建年除了上班,就是喝酒。如果不让他喝酒,他就打老婆,去妇联检讨。再酗酒,再打老婆,再去妇联检讨。
豆腐渣们的时间也是豆腐渣。薛师傅一边陪我慢慢走着,继续说高建年后半生的事。高建年的第一次离婚是前年的事。68岁的他赌输了家里准备帮女儿女婿买房子的5万块。他老婆坚决离婚。
离婚在如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高建年,如果不喝酒不赌博,还是很有人样的。高建年和发妻离婚后,无法一个人过日子,先后和好几个女人合伙过日子。后来和一个58岁的女老板登记结婚,结婚那天,高建年发了喜帖,去了一部分老工友。薛师傅也去了,没收贺礼,只收了一幅书法作品:
一对老新人,
两台旧机器。
一天动一次,
一动就吭气。
不动不服气,
再动就歇气。
薛师傅说到这里的时候,禁不住大笑起来。可能笑得太厉害了,接着又剧烈咳嗽起来。我估计这是薛师傅写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他们都是大老粗,唯有薛师傅肚子里有墨水。记得薛师傅第一次见到我,就考了我一个问题,一张桌子四个角,用刀切掉一个角,还剩下几个角度。我当然答错了。我说3个,其实是5个。那次薛师傅也是这样哈哈大笑的,只不过,那时他的笑声很年轻。
在父亲那帮老工友中,除了有墨水的薛师傅,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建年了,高建年开口就是满嘴巴像机关枪一样的粗话。很多年之后,我听说外国有个作家写了篇《丈母娘骂人辞典》。如果当时把高建年的粗话收集起来,足可以编一本《高建年粗话辞典》。记得那年机械厂拔河比赛。薛师傅是龙尾,我那矮胖的父亲是龙头,指挥官是穿中山装的高建年。他把粗话说得投入而忘情,气势如虹。对方的指挥官也跟着说,生生把一场拔河赛带成了粗话比赛。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说得气势如虹、响彻云霄的粗话比赛了。
女老板很快和高建年离婚了。高建年现在是一个人过。
“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好名声出去了呢。”
和薛师傅分手回到家,首先按照女领导平时的教育,去卫生间用消毒液洗手。洗完手,女领导停止了在沙发上刷抖音的动作,一脸神秘的微笑看我。
我以为林公子改变主意又回家了。女领导说不是。我心里咯噔一声,不是林公子就是我的事啊。还是科技发达,今天我的微信步数已超过了15000步。这足以证明我没有艳遇女同学,更没有经过什么粉红色的足浴店。
“我没问你这个。”
“你一没钱,二没胆……”
女领导的话中满是鄙视和不屑。我已习惯于这样的鄙视和不屑,这是一种哈巴狗的性格。在女领导的这么多年训练下,她的鄙视和不屑反而让我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赞许和鼓励。哈巴狗可是越鼓励越兴奋的。
于是我就跟女领导汇报公园豆腐渣奇遇记,怎么看到暴走团,怎么跟着滥竽充数,怎么遇到薛师傅,薛师傅照顾孙子之后又怎么回来,还讲到高建年,一个人生活的高建年。
接着,我讲到了拔河比赛,讲到了拔河比赛后,指挥官高建年要认我做干儿子的事,还要把钟山表塞给我做见面礼。
我没说“老丈人”的事,没讲高建年会说粗话,更没讲高建年的赌博、离婚、结婚又离婚的事。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如果讲了这个事,无论我的口气是羡慕或者愤怒,女领导会说高建年就是垃圾。能讲垃圾人的人自己也是垃圾,这位优秀小学教师还会借题发挥,把垃圾人的事设计成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问答题,甚至会做出大论文。在漫长的日子里,女领导会成为诡计多端的考官,让我这个可怜的小学生时时刻刻做、反反复复做。做对了是低分,做错了会是负分。低分和负分的生活待遇都会降级的。
“后来的钟山表呢?”
女领导还是抓到了一个细节。
当然还回去了。
“老丈人”和“干爸爸”的事还是有大区别的。为了确保不露馅,我赶紧祭出薛师傅说他孙子是“白眼狼”的故事,延续到空巢老人和老年化社会的悲凉。
我家女领导果真就中计了,感慨说到了正在北京的那个“白眼狼”,每个“白眼狼”都是微信上专家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是忘恩负义的高手。
“他们……就是我们的明天呢。”
陷入情绪中的女领导所说“他们”肯定包括了薛师傅和高建年两个人。
我似乎有点愧对女领导的信任,赶紧起身做晚饭。
我只会下面条。一碗面条呈现给女领导,女领导竟然狠狠夸奖了我。反复说起一个成语:相濡以沫。
女领导还说这个成语是庄子说的,就是写《逍遥游》的那个庄子。
女领导高估了这碗面条。她不知道我心里的拔河比赛还在进行,高建年率领父亲和薛师傅得到了冠军。是父亲上台领的锦旗,下来台,父亲把锦旗披在我的肩上,穿中山装的高建年摸着我的头说我不错,最适合做他女婿。我当然知道女婿是什么意思,用刚刚学到的粗话回骂了他。高建年哈哈大笑,竟把腕上的钟山表撸了下来,套到我的手腕上,说是给乘龙快婿的定亲礼,他回家就给他宝贝公主高丽丽说,他这个做老子的,给她招到一个好驸马了。
城北是老城,越往北走,童年的记忆就扑面而来,道路是变了,两边都是绿化植物,好在那些刷了新色的老楼群还是原来的轮廓。
薛师傅不肯领我去见高建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他支支吾吾的解释中,我大致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建年见了他还是用粗话骂他,过去在厂里,高建年说粗话,骂所有的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现在他不习惯了,真的不习惯了。他不喜欢别人说粗话,也不喜欢别人骂他粗话。有次他嘴巴里稍微冒出了一句粗话,被他的孙子批评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也这么大年纪了……很不舒服。”
薛师傅还是提供了高建年的手机和住的社区。他的这话其实也是变相地给了我一次心理建设。高建年见到谁都骂,见到我肯定也不例外。
我不知道我怕不怕高建年骂人。人都活成豆腐渣了,还怕几句粗话吗?况且还是熟悉的人。上初中之前,高建年一直叫我女婿。就因为“女婿”这个词,我有点怕见到他。后来我上了高中之后,机械厂彻底解散了,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高建年。再后来,父亲生病去世。听说他很伤心。凌晨父亲火化,他说好来送行的,但由于伤心过度,把自己灌醉了,等他醒来,父亲的葬礼早已结束。薛师傅说,后来高建年在我们家办豆腐宴之前又把自己灌醉了。
靠近社区便民中心是一家馒头店。腊月底的酒酵馒头店特别有烟火气,做馒头的笼屉有好几米高,蒸气翻腾,做馒头的师傅像是出没在仙境里。我买了10个馒头,心想,如果高建年家没有准备过年的馒头,这馒头正好送给他。如果他不要的话,那就带回家,我自己过年吃。况且有了这一袋馒头,我进社区便民中心就比两手空空更加心安理得。
社区便民中心办公的全是女人,叽叽喳喳地讨论垃圾分类的事。很多老人根本不懂垃圾分类,教了好多次,还是不会。实在太麻烦。
垃圾分类的事讨论好了,她们又在谈论年终奖的事。
我插不上嘴,只能听着。过了会儿,有个中年女人看到了我,很警惕地问我从哪里来,有什么事。
这种问法就证明她们是熟识社区居民的。
我直接问起了高建年。中年女人开始没听懂高建年,后来我说了几次,还说到了他喜欢喝酒,中年女人顿时懂了:你说的人是那个高科长。你一开始说找高科长我就知道啦。但我哪里知道高建年叫高科长呢?薛师傅也没有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过高建年是高科长呢。
“这个人麻烦。”
不管麻烦不麻烦,我还是要找到高建年的。按照中年女人提供的地址,我知道了具体的门牌号。转了几个弯,又穿越黑魆魆的楼梯,终于找到了高建年家门口。
我开始敲门,敲了十几下,没有人开门。敲门声引出了对门的老太太。老太太先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远方的侄儿。老太太又打量了我几下,估计是想从我的脸上找到跟高建年相似的部分。后来她示意我拍门,因为这个人说不定在睡觉。喝多了就睡觉。醒来继续喝。
拍门还是没人回应。
“不在屋里,那肯定出去鬼混啦。”
老太太说完,长长叹了一口气。很苍老也很无奈地叹气声。
我回到家,女领导表扬了我,今天的微信步数达到了24000多。她提醒我要注意不要劳累膝盖,有许多散步狂人最后膝盖都出问题了。
到了晚上,我还在想着挂在高建年门上的那袋酒酵馒头。可能是真的走累了,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了机械厂、说粗话的高建年。他还是那样脾气大,把我挂在他门上的馒头都扔在楼梯上了,那些馒头在楼梯上滚个不停。老太太的叹气声依旧在我的耳朵里回荡。我再也睡不着了,扔在地上的馒头,应该属于“厨余垃圾”。
早上起来,我跟女领导说到我梦见了父亲。
女领导说快过年了,要给地下的父亲烧年纸了,所以这才梦见的。
其实我知道,我梦见父亲是因为高建年,他曾经为了父亲反复喝醉,肯定有他的大感情在里面。虽然薛师傅安慰过我,一个人要把自己灌醉,什么理由都可以的。父亲去世后,大家都在忙生活。日子越过越快,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其他人都成了车窗外的雨滴,一晃而过。母亲常说父亲是块石头。父亲在家是沉默的,不说话的,也没有脾气的。但父亲肯定有故事的。薛师傅讲的父亲都是我熟悉的父亲。我很想跟高建年谈谈我不知道的父亲。
我也快到了父亲下岗的那个年纪了。
第三天晚上,我终于遇到了高建年。其实第二天晚上我也摸过去的,明明他家门里的灯亮着,门缝里全是酒气,就是没有人开门。估计又喝多了。这次不用敲门,门没关好,我一推开门就进来了。
高建年比想象中老了许多。
桌上是我的馒头袋,还有一盆看不出是什么肉的砂锅煲。
忽然,他站起来,用筷子指着我,问候了我一大串粗话。喉咙很大,这粗话我是熟悉的,但也和他的衰老一样,粗话里的力道没有了,在腊月夜晚的寒冷中更是可怜。高建年家没有开空调。我找了一圈,没有空调。他看我找空调的样子,以为我是社区的,又问候了我一大串粗话。
等到他的粗话雨下完之后,我向他介绍了我自己。我把父亲的名字说了三遍,他这才好像记起了我是他的老朋友林来根的儿子。
“来盅?”
高建年还用袖子拂了拂身边的凳子,意思我坐下。
我必须坐下,也只得坐下。女领导批评过我的性格,总是缩头缩尾,还多愁善感。是林黛玉与林冲的合体。女领导有所不知,林冲最后上梁山了哇。我今夜好像就是上梁山了,喝酒,吃肉。砂锅里的肉烂乎乎的,放了太多的味精。酒是苏北一家酒厂生产的高度酒,不知道是山芋酿造的,还是小麦酿造的,反正很冲脑子。两杯酒下肚,我有点晕。好在我发现高建年并不计较我喝不喝完杯中的酒,我就开始偷懒。我开始说父亲林来根,但高建年的火车根本开不到我的轨道上来。他骂那女人。我一直不能确定他说的那女人是谁。后来还是听出来了,是他的前妻,也就是高丽丽的妈妈。高建年不是总动手打高丽丽的妈妈吗?为什么还要这么仇恨呢?
高建年的话越来越多。他可能也没人听他说话,他说了他每个月的收入,退休金4000多,宝贝公主偷偷贴他1500。他一个月快6000,全部吃光用光赌光。高建年一点也不忌讳自己的赌博和其他的嗜好,他说他就想哪一天成为路倒,这样那女人就开心了,从年轻的时候,他只要喝醉了,她就骂他去死。高建年越说越糊涂,我还是听出来了,现在他想跟着那女人和高丽丽一起生活,还有个宝贝外孙。但那女人不同意,跟高丽丽说,只要他去,她就立即跳长江。说到这里,他说了句粗话。意思是:人一仰,二十一根指头全朝上。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跳长江谁不会呢?”
好不容易把喝多了的高建年安顿到床上,替他关灯、关门。我赶紧骑小蓝车回家,我还拐弯到了超市买了口香糖,又去外面走了走,这才回家。我家女领导已睡熟了,他又开始忙开了。好在林公子答应回家过年了。女领导说她要争取在林公子回家之前,把书房营造出像大学自修室的氛围。
早上起来,我还是打电话把晚上的情况告诉了薛师傅。薛师傅正在赶往南京家人幸福团聚的车上。他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我知道薛师傅的意思。人生很多时候,就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但谁也不会穿越时空啊。昨天晚上高建年把“跳长江谁不会呢?”先后说了十几遍。他肯定醉了,我想塞给他的1000块红包也没送出去。我怀疑他还是没把我认出来。
林公子提前一天回家打乱我再次去高建年家送红包的计划。这个家伙,总是给我们一惊一乍的享受。林公子一回家,女领导目光就完全在他身上了,但我的目光也在林公子身上啊。女领导是我儿子的女管家,我则是儿子的第一服务员。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总想替他做些跑腿的事,但儿子不让,林公子会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懂,除了替他吃下女领导给他准备的他又不太想吃的各种美食。
女领导也不再为我搞不清垃圾分类而生气了。生活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又是糊涂的。比如我很清晰,我已经变得相当自觉,我已经弄懂了垃圾分类。绿色垃圾桶。红色垃圾桶。灰色垃圾桶。黑色垃圾桶。这是生活的四胞胎呢。社区居委会几乎也不检查垃圾桶里的分类垃圾了,腊月底了,垃圾太多了。都在期待来年,新年来了,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
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我特地当着女领导的面上了体重秤,对着上面的数字夸张叫道,我必须继续我的步行锻炼了。女领导这才发觉我这几天的微信步行数量少得惊人,她恩准我半天时间步行,把前几天欠下的全部补回来。为了保证她和宝贝儿子待在一起的完整时间,女领导竟然把步行太多会伤害膝盖的科学道理给忘记了。
高建年在家。中午肯定喝了酒,我赶紧塞给他红包。他推托了一下就收下了。他以为我是上级来慰问的,说了许多感谢政府的话。
我赶紧说起我父亲的名字林来根,还有薛师傅的名字,他终于想起了我,说了我的父亲林来根很多好话,在他的叙述中,我的父亲从不喊苦喊累,有荣誉也不争,就像是机械厂的雷锋。高建年说他就想和这样的好人做亲家,跟好人学好人呢。还有,到了好人家不吃亏呢。
高建年对我们家的表扬里有那1000元红包的嫌疑,我赶紧转而问他怎么生活。他说他早上从来不吃,只喝水,三大杯水。中午去小饭店代伙,中饭60多元,晚上40多元。一瓶酒正好二顿。有钱打打牌,衣服送到干洗店。现在过年了,小饭店马上就不开伙了,他是买砂锅回家的,一口气订了十五个砂锅,他算了算,一天一只砂锅,正好熬到明年饭店开门。砂锅也不用洗,吃完就扔。
高建年说得很轻松,我似乎听到了每天晚上他往楼下扔砂锅的声音。砂锅破裂,寂静破裂。在众人的诅咒声中他沉沉睡去。
生活,其实就是习惯。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感觉不习惯的话,只要被生活的拳头捶打几下,肯定会习惯的。
我突然感觉后脑勺一阵熟悉的凉风。
回头一看,差点叫出声来,不是社区女领导,是我家的女领导。
女领导的跟踪能力太强了,估计她肯定早怀疑我了。为了掩饰我暂时的短路,我赶紧向女领导介绍高建年,这个老师傅就是我常常跟你说的干爸爸。
“哪里是干爸爸,是老丈人!”
高建年纠正了我。
后来,高建年就不让我说活了。他开始回忆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父亲的青年和中年。我父亲去世后他的痛苦。再后来不说我和父亲了。而说了我和高丽丽的很多事,他说他看中的是我,但他批评我太老实了,根本不主动。他说一直想培养我和高丽丽的感情,但最后还是阴差阳错。
高建年的回忆很深情,就像抒情诗人。
他叙述的话语中竟然没有一句粗话。
我无法也无力阻止这个说个不停的老抒情诗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提前到来。我家女领导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高建年,而是我这个豆腐渣。
女领导的眼睛里全是愤怒和不屑。
重温旧梦。痴心妄想。不自量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这是我代替她骂我的话。
但是我代替不了她。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不再去想我们家即将开始的最最严重的风暴。我的脚边是一只空砂锅。我知道,砂锅的碎片跟开心果的壳一样,都属于“其他垃圾”,必须投进黑色垃圾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