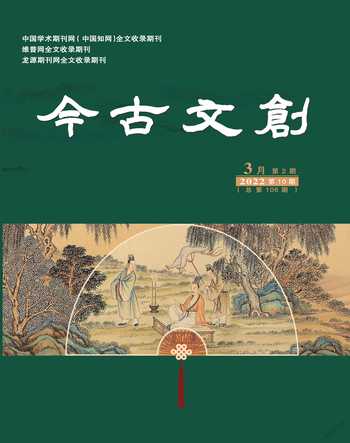花非花, 何以引“胡蝶”
姚鸽
【摘要】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中的高产作家之一,在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创作中贯穿着独特的风格。在创作主题上,《极花》中反映拐卖妇女的社会问题,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经过艺术的加工带给读者思考,扎根土地,关注人物,挖掘人性与社会。擅长使用意象,形成很好的创作意境,使得人物、环境、故事等浑然一体。从“极花”“血葱”“窑洞”等为作品传递出特定意境氛围,更是在叙述中使用地域化特色的方言,让故事和人物更丰满、真切。在这部作品中夹杂着方言,使作品更有真实感和画面感,增强其生动性与表现力。
【关键词】 极花;贾平凹;语言;主题;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2)10-0004-03
基金项目:本文由上海杉达学院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2020年度上海杉达学院科研基金(校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0YB11)。
贾平凹是当代高产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始终追求创新与突破的作家,其作品中呈现出的对陕西故乡的热爱、对故乡人深厚而浓烈的情感抒发让人久久回味。随着阅历增长与创作积累,贾平凹对人性、生命的感悟也如剥洋葱般一层一层的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诠释出来,“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贾平凹《自在独行》)生命的睿智——从容是真,然而命运呢?是否早已注定要孤独地走向未来?2016年贾平凹出版了长篇小说《极花》,这是一部反映拐卖妇女及贫困农村男性婚姻问题的作品。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源自一位老乡的诉苦,其女儿被拐三年后警方将她找回,电视报道英勇解救事迹后人们指指点点,父亲本想让女儿嫁到更远、没人知道此事的地方去,然而她又留了纸条回到了被拐的村子里。《极花》的故事情节与老乡的现实情况相似,但又多了很多创作上的特色,情感上更加感同身受,整部小说更加丰满。
一、主题
贾平凹一直都比较关注“人”,对个体生存的关怀,对个体人生的拷问,都是贾平凹重要的创作主题。无论胡蝶、还是夏自花(《暂坐》),无论是展示人性的淳朴还是揭露人性的异化,都浸透了贾平凹对人性的观察与深入思考,进而传达出对现实的思考。在其作品的各色人物中,他们的精神命运,现实境遇都会启发读者体验并探讨人之为人存在的意义,进而认识自我,探究自我。
贾平凹更善于讲“故事”,在一串串的故事中让人物更加鲜活、更加灵动,仿佛作品中的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极花》中的女主人公胡蝶,贾平凹给女主人公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 :胡蝶。“作者或许是根据《庄子 · 齐物论》中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所起的名字,女主人公在小说中的命运俨如一只茧慢慢蜕变成翩翩飞舞的蝴蝶,她怀揣着对城市的希冀从农村来到城市,后来如做梦一般,清醒之后发现自己被拐卖到了偏僻的农村,痛苦不堪,希望变成了绝望,这是破茧前所经历的苦痛;随着时间的前行,村中人情风物对她的感化、胡蝶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不再挣扎,最终破茧成蝶,在被拐卖的农村中翩翩飞舞,完成了成长与蜕变。”[1]然而这个美好象征意义的名称,其人生经历上却让人唏嘘不已,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虽逐步提高,但始终性别上的差别在社会现象中无处不见。儿童和妇女作为弱势群体,需要被社会关注并给予关爱。胡蝶最终回到了圪梁村,是对现实的妥协还是人性中的不舍我们无从得知,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垒起来,成了兔子……” [2]俨然胡蝶成了丢失翅膀的“蝴蝶”,黑亮始终无法成为她人生中前进的那一道光亮,在圪梁村她是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是毫无尊重可言,所有的核心都指向她无条件的妥协,向黑亮妥协,向命运妥协,向自己妥协。她痛苦的经历了黑暗与折磨,这一人物也塑造的真真切切,仿佛就在读者的身边呼救,贾平凹创作用笔触跟着人物走,是否要给胡蝶一个完美的结局,是否可以用笔改变她的不幸,可是作者要如何去改变,文学作品里改变了,但是现实中呢?因此,贾平凹在后记中也无奈地表达:“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 [3]
“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是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4]作者用故事给了读者思考,社会的现实问题,人在面对现实时的心理变化,进而暴露出的人性问题,这也是文学作品的使命所在。对人的研究和关注,贾平凹创作的主题特色也体现在此,只有足够多的问题暴露凸显,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作家是时代的歌颂者,也是时代的批判者,作家作品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变迁,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冷暖,贾平凹的《极花》与以往写过的乡土文学都有所不同,在作品中希望有精神,能体现人格理想,这也是作家创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二、意象
意象本是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概念。“意象”的“意”是意念,指的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意。“象”是具象,指表现对象的客观物态。意象是主观情感和客观物态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审美契合的产物。[5]在贾平凹的《极花》中也有不少的意象,或者可以说是象征物,它们是无声的存在,但对于整个故事的展开却起到了很大的烘托作用,最为典型的有“极花”“血葱”“窑洞”。
小说以“极花”命名,其中写到的极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它深深的融入整个作品的底蕴当中。“黑亮说,看到那个镜框吗,镜框里的那棵干花就是极花。类似于青海的冬虫夏草,也就是一种虫子,长得和青虫一个模样……当青海那边的冬虫夏草突然成了最高档的滋补珍品,价格飞涨,这里的人说:咱这儿不是也有这种虫草吗……”[6]因此,老老爷起了“极花”这个名字,被城里人发现后,以高价收买,圪梁村的村民为了挖极花甚至荒废了庄稼,后来极花被挖得快绝种,村里人才不得不重拾庄稼。仅剩的极花被人装在相框里,制作标本,挂在窑洞的墙壁上。看似“极花”与人物没有关联,实则这一意象就是胡蝶的写照,胡蝶是寻花的,然而这极花是假的,如今被做成了干花标本,这与胡蝶来到圪梁村的命运是何其的相似:极花是圪梁村男人们生存来源,以胡蝶为代表的女性是男人们的生活伴侣;极花是冒充的冬虫夏草,以胡蝶为代表的女性是被迫拐卖的生活伴侣;极花用尽被制作成标本干花,以胡蝶的代表的被拐卖女性最终也身心俱疲向现实低头。“花”和“蝶”原本寓意着美好,而在作品中的隐喻和象征展现了断翅的胡蝶向着干枯的极花奔赴而去。
如果说“极花”象征农村女性,那小说种还描写到另一种植物:“血葱”即象征农村男性。“……村长说:血葱不是春药,比春药强十倍,又不伤身体,给你说个案子吧,村里有个张老撑,八十二岁那年……” [7]血葱生长于温泉旁,营养价值高,壮阳效果尤为明显。血葱象征着圪梁村男性的现实,当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部分的农村劳力,也夺走了农村的女人,这让还深处农村的男性体会到了深深的不公平。他们守着故土却抵不过城市发展吸引人力的魔性,作品中胡蝶就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典型,要有城市人的形象,不再扎辫子,把长发放下来,染了一绺黄头发,学说普通话,买高跟鞋等等。圪梁村的男性虽不去深挖背后的社会原因,但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贾平凹在后记中提到:“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黑亮爹有石匠的手艺,陆陆续续村里的男人,从张耙子到王保宗,再到腊八兄弟都让他做了一个石头女人放在家门口,村里有几十个石头女人,没娶媳妇的光棍,给石头女人起了名字,慢慢地,石头女人的脸全成了黑色,黑明超亮。贾平凹的叙述与血葱的寓意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悲。
乡村、县城、城市是一个文学空间,不仅提供一种生活,也提供了文学经验与传统,贾平凹的作品也常常放在这一空间进行写作,從乡到城,即使书写城市,但有着乡土的经验与背景,能够关注度更为广泛,时刻保持一种反思的视角,这也是其创作的独特之处。
窑洞,是陕西一带独特的住房,冬暖夏凉,这一意象所产生的效果不留痕迹,但却魔力十足。在《极花》中它是困住胡蝶的地方,也是黑亮挂念的地方,它不仅仅是遮风挡雨那么简单,更是胡蝶精神禁锢之地。
窑洞在圪梁村是男人们温暖的家,然而对于被拐卖妇女而言却是噩梦之地。一开篇就提到胡蝶在窑壁上刻下一百七十八条道儿,每一条道儿看似刻在窑洞墙壁上,更是一道一道划在了胡蝶的心上,每一道儿都是煎熬。胡蝶认为窑是《西游记》里的牛魔王,自己是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有感觉窑洞是一只蚌,自己是被吞进去的一粒沙子。胡蝶狂躁、咆哮,对窑洞外不好奇也没有兴趣,但更远处的远方只能成为一个念想,仅能靠回忆去安抚自己。
此外,还有葫芦、剪纸、井等意象,除了物象,还有潜在的意象,最值得一提的是老老爷,他总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总是在研究星野“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上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星野”,老老爷是胡蝶发现的第一个希望,她捉摸不透老老爷,觉得他跟圪梁村其他人不一样,有文化会帮助自己逃离,又感觉他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这一人物所营造出的意境就像是潘多拉魔盒中的希望,虽然我们的生活充满困难与不幸,但心中总怀有希望。
三、语言
作品渗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与经验,包裹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最终都通过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贾平凹作为陕西人,在每一部作品中几乎都带着陕西的方言,当人物的语言和作者叙述的语言通过土语讲述的时候,这让作品更加鲜活,有画面感,同时也体现着陕西的文化意蕴。比如他的《秦腔》非常丰富地展示了商州地方的风俗和文化底蕴,在作品中也大量地运用了商州地方方言[8],使作品更加有生活气息,这样的语言也使得作品地域化色彩更加浓厚。在当代文学中,有这种语言风格的作家也很多,尤其是经历了“乡——城”的作家群。
《极花》作品中方言的使用更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作品中每一个人物一开口使读者能够感受到胡蝶真真切切的被拐卖到圪梁村了。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象基本都出现在偏远的山村,而这种地方的人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外界的信息隔绝,从语言上来讲基本使用的都是方言,因此,《极花》中方言的使用效果使得故事更为逼真。
“那个傍晚,在窑壁上刻下第一百七十八条道儿,乌鸦叽里咵嚓往下拉屎”中的“叽里咵嚓”在方言中表示的是“毫无顾忌,动作迅速地做一件事”,贾平凹在创作中自然而然的使用也使得作品情感更加顺畅。
“喂,说你哩”,“他说:我骂城市哩”,“我说:你娘会笑哩,我娘正哭哩”,“八斤说:村长,叫你哩。村长说:谁叫哩,就说我忙着哩。”……中的结尾词“哩”,方言词属于助词。相当于“呢(ne)”“啦(la)”,不仅仅在小说中,散文中贾平凹也常常使用这一助词,如《写给母亲》中“母亲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
“黑亮说:听说村长去骚情过訾米”中的“骚情”也是一个典型的陕西方言,在陕西农村中老百姓使用这个词语的频率很高,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中也常常运用此方言。它在方言中有多重含义表达,比如有“过分热情,刻意显摆,嘚瑟而被鄙视”,有“轻佻,发骚”等。
“我又坐到门墩上了,觉得嘴里有些寡,想吃点什么”中的“寡”表示“没有味道,想吃点好吃的”,这个词语在老一辈人口中使用较多。
如此以外,还有“侍弄”“瞎怂”等方言俚语。
对贾平凹创作中语言的使用,他也直言“我不喜欢张牙舞爪的语言,我主张憨一些,朴一些”,[9]也正是这样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对于方言区域内的读者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像是在家门口讲故事,对于方言外的读者而言,更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贾平凹在《说话》中提到自己出门不大说话,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在写文章时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反复推敲,也甚是用心表达。
语言是最能体现作者风格的标志,它决定着作品的基调和被接受度,方言土语的使用也不是越多越好,使用过多难免会产生晦涩之感,影响整个作品的阅读,恰到好处的使用才是如虎添翼。贾平凹在《好的语言是什么》中提到陕西民间散落了上古语言,沦为土语,语言也要向古典和民间学习。
四、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让读者在作品中常常看到乡土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物质、人文、制度、民俗等等层面,不是粗略的体现,而是根深蒂固的渗透,这也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的气质。作家用语言作品去展示这种乡土气息以及乡土与城市之间的碰撞,也显示出中国社会也是具有乡土性的。贾平凹的创作主题一直在变,但乡土的核心线却一直都在。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更多原汁原味的中国社会,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性,这不是惨烈的批判,而是把乡土的思念之情、社会民生的关心以及批判与思考融合了在一起。
贾平凹创作非常注重细节处理,对圪梁村村庄的描写,人物动作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意蕴、景物、日常生活的描写都关乎着细节,增加了空间的协调性与融合性。同时,也增强了故事性,用方言诉说着故乡的故事,对于题材的选择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方式,他认为真正的大题材往往是选择作家的,关注现实生活才可能更本真和灵敏,才能写出情感。文学价值诚然是写人的,要写到人本身的问题,这样更贴近生活,《极花》就是实实在在地来源于生活,立足对女性的关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贾平凹在《稿边笔记》中提到理解的小说就是正常给人说话的一种腔调,一个人的呼吸如何,语言就是如何,在其创作中,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方言使用成为其作为陕西作家的一个符号和特征,语言也是有情绪、有内涵的,在圪梁村方言的使用让作品更加鲜活,它能更准确、更生动地表达喜怒哀乐、人情冷暖。
参考文献:
[1]陈颖.胡蝶,破茧成蝶——分析贾平凹《极花》中的三个隐喻[J].青年文学家,2017,(17):54.
[2]贾平凹.极花·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12.
[3]贾平凹.极花·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12.
[4]贾平凹.极花·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10.
[5]尹相如.写作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41.
[6]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1-22.
[7]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81-82.
[8]陈倩.浅谈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特色——以《秦腔》为例[J].名作欣赏,2019,(17):78-79.
[9]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二卷)——制造地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467501908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