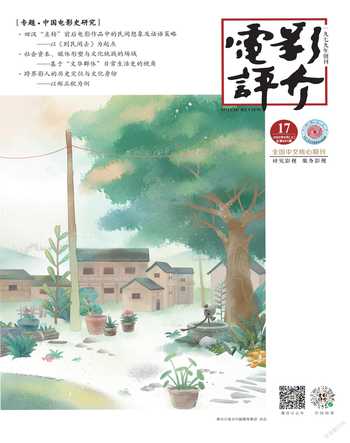叙事四重奏与人物口述史:《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摄制技巧探析
李文慧 何德民
2020年,贾樟柯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成功入围柏林电影节,这部充满文学性与历史特色的纪录片以四位主体人物为叙述视点,勾连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导演通过特有摄制技巧,将学术性的口述史转化为能够为群众接受的纪录片形式。叙述主体之间既有本质的共通之处,又有纵向分列的不同点,同在对故乡土地的眷恋和对苦难的看法,异在其各自所处的时代节点。电影的镜头是多样而游离的,并不完全固定在叙述者处,反而从叙述者的口述内容向外生发,涉及多处外部空间,镜头在内部空间中的位移亦能够减轻观影者的疲劳感。
一、从口述史到纪录片
口述史与纪录片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都以记录真实事件为目标,但口述史追求的是学术目标,纪录片则更多追求大众审美目标。贾樟柯决定拍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起因是2019年的首届吕梁文学季,他看到几十位知名作家齐聚山西的一个小乡村,大家以“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为主题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时候的导演觉得自己可以将这群文艺工作者的激情通过镜头记录下来。其实,从最初构想来看,这部作品似乎更具有口述史的学术特征,然而电影始终是一种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的产物,纪录片显然更适合作为载体。
口述史是史料学的一个门类,它主要通过记录亲历者的话语来形成研究资料。当然,口述史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对谈话内容进行录制,它需要工作者具备相当的历史理论知识与专业素养,在谈话过程中尽量梳理个体经验与宏观背景,使二者在保留真实性的前提下形成平衡。学者周海燕认为,若要真正做好口述史工作,“需要关注个体经验在社会中的关系与位置,需要关注个体叙事的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契合或是断裂,更需要关注个体认知、情感和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1]。归结而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口述史的重中之重,而贾樟柯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个别主体与社会大语境的疏离与交缠,所以他倾向于并且擅长利用口述史形式来拍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具有鲜明的口述史特点——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等都是当代代表作家,他们自己或其亲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建设,岁月赋予他们沉静舒展的气质,他们也为历史添加上小小的注笔;被采访者面对镜头回答问题、剖析自我,没有情节的集中展现,有的只是零散回忆。
这样看来,影片似乎真的可以称作口述史的典范。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贾樟柯是一名导演,而非历史学者,因此口述史在他这里只能作为形式(而且是一种不甚完满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实际上他早已通过特有的摄制技巧将这些口述资料转化为纪录片。那么纪录片是什么?比之口述史,纪录片为什么更符合普通观众的审美品位?
埃尔文·莱塞在论述纪录片时这样说:“较之于‘纪录电影(documentary),我宁可使用‘非虚构电影(non-fiction film)这个词,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这类影片不是人为创作的,剧中人也不是演员装扮的,他们有自己的名字,真实可信。‘非虚构电影的题材不是虚构的,而是一种事实,是一种存在的再现。人们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东西,它被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认为是重要的,而且是作为‘真实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也是摄影机和录音带能够抓取的。对于‘非虚构电影的可能性来说,这意味着一种边界条件的确立,也就是对于表达的适用性的限制。”[2]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真实是纪录片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与口述史的共同点。正是这种亲缘性,使贾樟柯能够灵活地将口述史转化为纪录电影。余华、马烽的女儿、贾平凹、梁鸿的姐姐……这些叙述者都并非虚构,他们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甚至拥有比我们更加丰富的体验,因此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世界,或许会看到这个社会不一样的风景。当然,纪录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前文所说,它“能够被摄影机和录音带抓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抓取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而是有技巧的再现。例如,贾樟柯在对《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叙述主体进行拍摄时,他并没有舍弃主观能动性,完全被动地任由摄影机器记录谈话过程,反而通过使用复杂的镜头语言来将稍显枯燥的历史资料呈现为动态有致的电影。
二、敘述主体的变与不变
对叙述主体的选择和安排是将口述史转化为纪录片的有效技巧之一。贾樟柯的纪录片既保留了口述史对叙述主体陈述内容相关性的传统,又灵活地创新叙述者身份,将他们与时代相联系,形成纵向链条。
相较于规范口述史,贾樟柯的电影在叙述主体方面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口述史中的口述主体往往是唯一的,他与采访者的对话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形成重要历史资料,他们的对话是不被打扰的,而采访者虽然不必具有太强的存在感,但却是有必要出现的。然而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口述主体不再唯一,呈现出四重奏形式——马烽女儿讲述父亲与村庄的故事,她的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对已逝之人的尊敬;贾平凹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坎坷的家世与人生经历;余华用鲜活不羁的语言告诉世人他所寻找的故土灵魂;梁鸿则几度哽咽,谈起亲人们的遭遇与梁庄人的漂泊心境。多重叙事主体给予观众不一样的视点,有效缓和了观影过程中的审美疲劳感,也为更多的内容展现提供了条件。此外,我们应该关注到,导演选择的这四位作家在出生时间点上是不同的,但却形成了微妙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活跃着的马烽不仅着眼写作,而且关注乡民的生活状况;出生于50年代的贾平凹对西安故土有着浓重归属感;60后余华同样忘不了幼年记忆中大海的微黄颜色;70年代出生的梁鸿以敏锐的感知力与细腻的笔触写出家乡与家乡人的故事。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历了从建立新中国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史,因此处于其中的个体必然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通过对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作家的关注,来管窥那个时期的瞬息万变、复杂多样。
当然,影片仍然沿用了口述史的一些优秀传统,例如对一个深刻的、现实的主题的挖掘。从这部影片的原定名称《一个村庄的文学》可以看出,贾樟柯的这部纪录片落脚点仍然在乡村,与文学相关的乡村,是我们平常无法想象到的、作家眼中的故乡。而透过这一现象直视本质,我们应该思考乡村故事意味着什么?其实是一种对根的追寻,不仅是物质之根,也是灵魂之根、文化之根。作为传承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根扎在农村广袤的土壤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一步步消解乡村的形象,然而想要真正形成文化自信,最应该做的便是寻找那个消逝的乡村形象、抓住正在消失的故土记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传统社会,时间和空间深深扎根在地方的背景中;在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失去根基,发生分离。[3]电影所关注的商洛、梁庄、吕梁,其实就是被遗忘的地方,出生于这里的人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不停地涌入一个陌生但繁荣的城市,在新的空间里,他们与过往的时间记忆诀别,于是形成灵魂断裂。《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要做的便是找到断裂口,并将断裂之处弥合。余华选择了极为诗意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弥合,他说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沿着海域游过去,游到书上所说的海水变蓝的地方,海水变蓝之处大概就是故乡重新清晰起来的地方;而对于成长于革命年代的马烽而言,他选择以实干的方式留住乡土记忆,或者说是将乡土推入现代化进程中,既保留故乡的淳朴,又让乡土中的人们大踏步走进新时代;贾平凹在作品中谈秦腔,说自己最痛苦最快乐的时光都在那片热血土地之上,他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陕北高原的粗犷与热情,这又何尝不是在以笨拙的方式寻找梦中的文化之根;梁鸿在镜头前教年幼的儿子河南话,饱含深情地谈起多年前父母的苦难,在作品中为梁庄的家乡人寻找新出路,同样是对家乡呼唤的回应。
当然,在追寻故土之根的主题之外还有个体对苦难的看法,似乎贾樟柯想通过这四位作家传达给观众一个思想,那便是乡土可以成为疗愈伤痛的好地方。贾家庄之于马烽,是奋斗的地方,他带领乡村里的人走向安乐;而贾平凹在镜头中陈述父亲曾经被误会成国民党内部人员的往事时,以一种平静的态度直视对面可能存在的提问者,仿佛他看到的不是人,而是那片最痛苦也最快乐的土地;余华谈到自己幼年时在浙江海盐的经历,居住环境并不舒适,但他却以幽默诙谐的态度谈起年少青春,这也是那片记忆中的乡土给予的宽广胸怀;对比前三者,或许梁鸿的苦难更接近于普通人的苦难,母亲的瘫痪与父亲遭遇的非议都给年幼的她留下了痛苦记忆,甚至一谈到那段时光便泣不成声,然而最终她能够成功释放自己的情感也恰是因为回到河南那片土地上的经历,她看到来来往往的家乡人奔赴城市,揣摩着他们平凡而又充满温情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疗愈自己的伤痛。
三、摄制镜头的游离
口述史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和固定的镜头,然而这样的产物显然不具备趣味性,于是贾樟柯并不多用固定镜头,反而多次让机位从口述的封闭空间中出走,延展至外部的广阔土地,外部画面与口述者的自身经历和所说内容又有一定关联性,从而形成完整关系链条。当然在口述者所处的封闭空间内,鏡头也有轻微位移,从下至上或是从左到右,画面焦点一点点显现,观众也在这种镜头游戏中减轻了观影疲劳感。从电影纪录片创作的角度出发,采用多机位拍摄口述者,不仅可以让观众被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鲜活的讲述内容所吸引,而且能够更加饱满而富有质感地呈现叙述者生存的环境、状态、情绪,在陌生而又新奇的体验之中,走进历史深处。[4]
(一)镜头的“出走”
镜头的“出走”指的是摄影机位从口述者所处空间转向另一个外部空间的拍摄手法,从内而外,不只是镜头发生了转移,导演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引导观众的思考进行转向:从叙述中获得的不应该只有历史,还应当有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过往时光的认知,这种认知或许缺乏客观性与真实性,但却因为两重时空的交汇而显得格外珍贵。
在电影开头,90岁的老人坐在木椅上讲起马烽为贾家庄带来的变化,这时的画面并未固定在此,而是时而展现贾家庄的风景,似乎与当初马烽的努力形成一种对照。同样,导演在拍摄马烽女儿这一片段时,也穿插了许多与口述内容相关的画面。例如,当她谈到父亲高超的版画技术时,一幅木刻版画便缓缓出现在持续几秒的长镜头中;当她谈到贾家庄人民的变化时,曾经的村庄与如今的村庄适时呈现在观众眼前。导演安排人物以口述形式完成影片布局,但却又不完全拘泥于口述史限制,而是在口述之外穿插想象中的画面,这种手法已经突破了学术性的记录目标,走向了大众传媒的审美目标。
在贾平凹这一章节中,他说起自己找工作的困难,最后因为一手好字获得出路时,钢琴声渐渐响起,叙述者退出画面,一幅书法字展现在镜头中央“白眼观世”,接着镜头又缓缓转向外面的马路,各式各样的行人为生活而忙碌,他们的身影与贾平凹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似乎世间所有的苦难都不过如此,世间所有个体都平凡而又特殊。同样的摄制手法也出现在贾平凹谈起自己的经典作品时,摄影机位从叙述空间中游走至戏台上,铿锵有力的秦腔吟唱出作家内心深处的天籁之音。
余华谈到自己被约稿后的兴奋心情时,画面出现一个人缓缓念出他书中的句子:“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叙述者与陌生人物的交接其实是当下现实与书籍的交接,导演通过镜头出走的方式将叙述推往深处,引导观众思考其间联系。在他说到《活着》这本书写完了一个人的一生时,镜头转移到公园——长椅上的年长男人,唱着乐曲的女人一一出现,仿佛正是与那句“一个人的一生”相照应。
(二)镜头的位移
与镜头的“出走”相比,位移式镜头依然在口述空间之内,但机位的变化依然存在,只是被收缩到了内部空间中。从镜头语言的拍摄方式来分,大可分为推、拉、摇、移、跟、升和降几种镜头,每种镜头都有不同的效果与应用环境。[5]
在电影开头那一个长镜头中,九十岁的老人缓缓说起与马烽共事的经历,机位从下向上升起,由地面至矮桌上的红色水壶再到老人的面庞,轻微的变动使画面具有了连贯性,同时又不至于产生一镜到底的生硬感。余华在小饭馆的叙述同样采用了移动的镜头,机位以人物为中心点,从人物的一侧移动至另一侧,画面焦点的暂时变化使得观众得以放松的同时,叙述者的话题也进入新阶段。影片中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叙述者,那便是最后出现的梁鸿之子,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显然并不能作为一个完整口述者出现,但正是他的出现使得背后的提问者得以真正现身。随着梁鸿、提问者与少年的对话出现,镜头从人物的脸庞处移动至河流中央,巨大的黑石与清澈的水流激荡起水花,历史的巨变从镜头语言中展现出来。
影片整体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转场都采用镜头推移的方式进行展现——从叙述者所处空间到宽阔的日常生活空间(无论城市或是乡村),机位的变动是缓慢的,但画面中的内容却又发生本质变化,如此便可以给予观众一定的思考时间。此外,电影最后以余华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镜头随着他的身影在岸边徘徊,似乎真的要走向海的那一头,海水变成蓝色的那一头。
结语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始终坚持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与土地的厚重相融贯,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彰显中华民族扎根黄土的血脉传统。《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口述史的形式建构纪录片框架,将口述的历史感、真实感与电影的观赏性纳入同一线路,令国内外观众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中国心灵史与文化底蕴。
【作者简介】 李文慧,女,山东茌平人,韩国清州大学艺术学院、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影视艺术研究;
何德民,男,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纪录片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齐鲁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编号:20DXWJ01)
阶段性成果、山东省艺术重点课题“网络平台自制纪录片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编号:L2021Q0708016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周海燕.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119-127.
[2][德]埃尔文·莱塞.合法的手段——纪录电影与历史[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聂欣如,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69.
[3][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409.
[4]李坤伦.《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文学名义重回历史现场的影像之思[ J ].美与时代(下),2020(06):94-96.
[5]刘一辰.影视作品中镜头语言分析——基于专业学习的角度[ J ].西部广播电视,2019(02):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