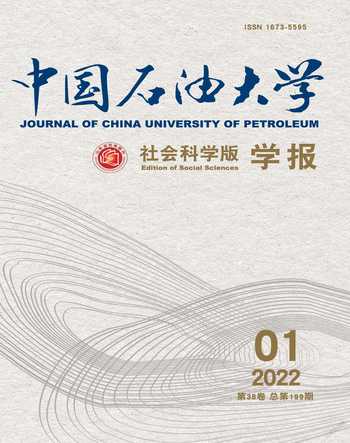从自然审美视角比较“卧游”与“如画”
王晓丽 周思钊


摘要:“卧游”与“如画”作为中西方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主张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之地位比绘画重要,“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自然欣赏的标准,故绘画之地位比自然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欣赏者囿于一室之内,而心游万物,“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旅游者带着猎奇心理与视觉占有欲,身游大自然之中;“卧游”具有畅神与疗疾之功能,“如画”则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心理保护。比较“卧游”与“如画”,可以窥探中西方欣赏自然的差异之处,透视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卧游;如画;自然审美
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1-0099-08
一、引言
“卧游”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美学范畴,最初诞生于画论领域,而后延展到诗文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炳在《画山水序》中率先提出“卧游”范畴:“(宗炳)善书画,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叹曰:‘噫! 老病具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其高清如此。”[1]128-129“卧游”的直接对象是关于自然山水的画作,而非自然山水,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卧游”是一个画论术语,主要探讨山水画的欣赏问题。而后,南宋李氏作《潇湘卧游图卷》,明代沈周作《卧游图册》,清代程正揆作《江山卧游图》,等等。“卧游”成为中国古代画论中一个独特范畴。其实,“卧游”不仅在画论领域盛行,在诗文领域也颇受关注。宋代范成大《初入大峨》中云:“剩作画图归挂壁,他年犹欲卧游之。”宋代汪藻《横山堂》中云:“临赋竟传今日句,卧游安用昔人图。”宋代陆游《小阁纳凉》中云:“莫遣良工更摹写,此诗端是卧游图。”明代吴宽《答济之约游西山不赴》中云:“莫笑晓来风雨阻,卧游诗句也堪誊。”明代陆治在《左虞过访漫答二首》中云:“山水將身隐,图书足卧游。”清代王士禛《初秋索梅耦长画》中云:“诗到无声足卧游,雨窗含墨对清秋。”清代戴亨《题方竹楼画竹》中云:“盛夏摊书作卧游,中有凉飙扫炎热。”由此可以看出,“卧游”从画论拓展到诗文领域,诗文也成为卧游的媒介。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宋代吕祖谦的《卧游录》,这是第一本以“卧游”为题的专著,作者卧游古籍,每遇古人描绘的人境胜处,便记录下来,汇编在一起,形成《卧游录》。
尽管“卧游”的直接对象是画作与诗文,但是这些画作与诗文都是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因此可以说,自然山水是“卧游”的间接对象,从自然审美的视角看,“卧游”具有浓厚的自然美学内涵。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道:“宗炳却发现了山水是神的具象化,这便是所谓‘栖形’;因山水可以入画,故栖息于山水之形里的神,可以感通于绘图之上,在道理上,神即入于作品之中。所以宗炳的画山水,即是他的游山水;此即其所谓卧游。”[2]144诚如徐复观所言,对于宗炳而言,“画山水”即“游山水”,亦即“卧游”,因此,卧游者真正欣赏的则是画作背后所要展现的真实山水之境。因为对于宗炳而言,自然山水并非作为画作的背景,而是画作的主题:“仅以山水作人物画之背景时,不必要求山水之真实性,故亦无此问题。现宗炳所要求者,乃将他所喜爱的真山真水,表现于画面之上……此说明山水画至宗炳而有其严肃性,在此严肃性之下,始能奠定其基础。独立性的山水画,至此而始成立。但他所把握的真山真水,是质而有趣灵的;因之,他所要表现的是由山水之形,以现出山水的‘玄牝之灵’,以与其胸中之灵,融为一体,不可随便以一般的写实主义称之。”[2]143从徐复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宗炳而言,“卧游”的对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山水画、真实的自然山水、山水之灵。山水画虽然是第一层对象,但是山水画只是媒介,卧游者希望通过卧游山水画册,进而抵达第二层对象即真实的自然山水,以便突破时空限制,与自然时时相对,进而上升至第三层对象即自然之灵的境界。由此可见,“卧游”与自然欣赏紧密相关,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审美内涵。
“如画”(picturesque)即“像图画一样”(picture-like),强调按照风景画的方式来欣赏自然,本身就是西方自然美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根据希普尔考察,“picturesque”一词可以追溯至更早的荷兰语“schilderachtig”,此后由该荷兰语而发展成为意大利语pittorésco和法语pittoresque,再进而演化为英语picturesque词汇。[3]185“如画”发展成为西方美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则需要追溯到18世纪后期吉尔平、普赖斯和奈特等人那里。吉尔平使“如画”(the picturesque)获得程式化的美学意义,使之成为一个与“优美”(beautiful)相区分的美学术语。从英语语法来看,“the+adj”表示某一类事物,吉尔平则将“the”与“picturesque”连在一起,反复使用,形成固定表达,用来表示“某一类如画的事物”。这类事物的共同因素就是吉尔平在《论版画》(1768年)中所说的:“一个表达图像中令人愉快的特定之美的术语。”[4]1792年,吉尔平发表《论文三篇》,严肃讨论了“如画”的理论内涵,使之获得程式化意义。吉尔平认为,“如画”(picturesque)是一种不同于优美(beautiful)的美,他称之为 “如画美”(picturesque beauty)。[5]6其实,如画美(picturesque beauty)就是指如画之物(the picturesque)的共同审美要素。吉尔平认为,区分如画美(picturesque beauty)与优美(beautiful)的关键在于粗糙(roughness):“粗糙(roughness)构成了优美(beautiful)与如画(the picturesque)的最本质差别;绘画中对象的具体特性(particular quality)令人愉悦——我用普通的术语粗糙来说明这点;但是粗糙很可能只与事物主体的表面相关:当我们言说其轮廓时,则使用粗犷(ruggedness)这个词。然而,两种观点都进入到如画中。”[5]6-7由此可见,吉尔平借助“粗糙”概念,将“如画”与“优美”区别开来。吉尔平之后,普赖斯进一步明确“如画”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与“优美” “崇高”(sublime)并举的美学范畴。1794年,普赖斯发表《论如画:与崇高和优美进行比较》,提出了“如画性”(picturesqueness)概念,这是一个名词,旨在说明“如画”是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审美特质。在普赖斯看来,“如画”既区别于“优美”,也区别于“崇高”,它所具有的特性是粗糙、突变(sudden variation)和新颖(freshness),这样就比较清晰地规定了“如画”的理论内涵。[6]此后,奈特发表了《景观:三书中的说教诗》和《趣味原则的分析研究》,对如画理论进行了完善。在吉尔平那里,“如画”是形容词,是审美主体(即如画之眼)对于具有如画美的事物的主观描述;在普赖斯那里,“如画”则成为名词,是对外在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审美特性之规定;在奈特看来,“如画”并不在于审美主体,也不在于审美客体,而是在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联想关系上,“如画一词所表达的与绘画的真正联系,是通过联想获得的整体愉快,因此它只能由某些特别的人感觉到,这种人要拥有与之发生关联的相关观念” [7]。在吉尔平、普赖斯和奈特的努力下,“如画”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与优美、崇高并列,成为18世纪英语世界的三大美学范畴之一,如希普尔的书名《十八世纪英国审美理论中的优美、崇高与如画》[3]所揭示的那样。此外,在自然审美实践领域,如画理论颇受大众青睐,比如18世纪欧洲“大旅游”(the Grand Tour)十分流行,许多旅行者带着克劳德镜(Claude glass)以及旅游手册,去自然中寻找如画景色。自从如画理论兴起以后,按照如画的方式欣赏自然,始终是西方世界欣赏自然的重要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卧游”与“如画”所处的文化语境、时代背景不同,但是两者都涉及一个共同问题,即自然审美问题。在如何欣赏自然的问题上,“卧游”与“如画”虽然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画作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又有所不同:“卧游”主张透过山水画去欣赏真实的自然山水,“如画”则主张从真实的自然山水中见出风景画的意味,两者迥然有别。因此,本文试图在自然审美欣赏的视角下,比较“卧游”与“如画”,从而探究中西方自然审美欣赏的差异,并揭示中西方对待自然态度的差别,进而深入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与社会根源,为当代中国自然美学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二、山水畫与风景画:“卧游”与“如画”所借助的绘画之特点不同
“卧游”与“如画”虽然都强调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但是它们所借助的绘画之特点并不相同,这必然使得它们各自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不同。下面,我们选取两幅“卧游”与“如画”的代表图画为案例(见图1,图2),详细分析两者所借助的绘画类型之差异。
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两幅图画的主要要素大体一致,都有山、水、树、船、人;而且画面布局也相似,远景为山,中景为水,近景为树,但是这两幅图给欣赏者带来的审美感受却完全不同。沈周的《秋江钓艇图》所描绘的山水形式巧妙,崇山向远景延伸,一直隐没在淡淡云雾之中,给人以“惟恍惟惚”的神秘之感;人物在船上垂钓,悠悠江面,静哉若斯,颇有天人合一之意境;前景的三株树并立,姿态各异,显然是画家有意经营布置的结果;尤其是沈周于画上自题了一首诗“满池纶竿处处绿,百人同业不同船。江风江水无凭准,相并相开总偶然”,诗与画面相结合,营造出一种超脱与悟道之境。伊贝特森的《从络伍德看朗代尔山峰》所描绘的朗代尔山,湖山相依,山峰倒映在湖里,光线明晰,给人以真实之感;大山向远景延伸,光线变暗,山峰逐渐隐没,给人以荒野之感;船上与岸边的人,在自然中十分愉悦,充满着世俗的欢乐;前景的三棵树挺立着,树下卧着四头牛,不像画家有意营造的,似乎是画家如实描摹风景的结果。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卧游”与“如画”所借助的绘画特点极不相同。张彦远在介绍了宗炳“卧游”思想后,评论道:“且宗公高士也,飘然物外情,不可以俗画传其意旨。”[1]131可见,宗炳卧游所借助的绘画并不是一般的俗画。关于这个问题,清朝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进一步说道:“士大夫之画,所以异于画工者,全在气韵间求之而已……若刻意求工,遗神袭貌,匠门习气,易于沾染。慎之慎之……近日俗画,专尚形模,如小女子描钩花样,一笔不苟。画非不工也,而生气全无,不可复与之论画矣。”[8]由此可知,“卧游”所借助的画是“士大夫之画”,是文人山水画,追求山水之“气韵”,偏重写意。实际上,“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就偏重写实,强调对自然景色进行细致而如实地描绘。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在研究“如画”时指出:“对画境游的游客来说,最主要的激动来自于认出和追溯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相似度……当他们置身北威尔士,瞥见一处美景,观景者就会激活早先的画例,感觉眼前的本地风景简直就是杜埃画作的完美再现。”[9]55对于如画欣赏者而言,他们通常按照景观画去自然中寻找真实的景色,因此“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与真实自然的相似度很高。比如,吉尔平的《1770年夏怀河和部分南威尔士等地见闻,主要和如画美相关》和查尔斯·黑斯的《沿怀河远足,从洛斯到蒙茅斯》,图文并茂,对怀河风景进行了比较真实地描绘,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英国人在怀河河谷地区进行画境游时必备的旅游手册,相当于关于怀河的旅游指南。因此,“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属于重写意的“文人画”,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则更接近于重写实的“画工之画”。
“卧游”与“如画”所借助的绘画类型明显不同,其原因在于,“卧游”与“如画”的审美诉求不一样。如宗炳所言,其卧游是为了“澄怀观道”,盛大士之所以作《溪山卧游录》,也是因为“慕宗少文澄怀观道”[8]。这就意味着,“卧游”所借助的绘画须包含有“道”的意味;然而,“如画”所借助的偏重写实的“画工之画”或者类似旅游指南的风景画并非旨在让欣赏者“澄怀观道”,而是让游客从自然中寻找和绘画极其相似的风景以自娱,换句话说,就是让游客把风景画当作旅游指南来欣赏自然风光。因此“如画”偏爱那些真实描绘自然风光的风景画,包括旅游手册上的图画。
有两则事例,可以明显地展示出“卧游”与“如画”的审美诉求不同。一则是与“卧游”有关。《江山卧游图》的作者程正揆曾说过,卧游图能够“补足迹之不到,或山河阻隔,或时事乖违,或限于资斧,或具无济胜,势不能游,而恣情于笔墨,不必天下之有是境也”[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卧游”而言,卧游图不必完全符合自然环境,甚至是“不必天下之有是境”。另一则是与“如画”有关。19世纪“如画”这种自然审美方式从欧洲传到了北美,北美哈德逊河风景画派开始兴起,其画作被游客们所追捧。“美国买家喜欢那些表现真实场景的绘画,他们希望绘画所表现的细节能够经得起仔细的观察,这种要求迫使科勒去画事物而不是思想。此外,艺术资助人常常希望知道绘画中所画之地的名字和位置,而且他们会去旅行,站在艺术家所站之处,拿绘画与真实的景观进行比较。”[11]因此,对于“如画”的追随者而言,他们更热衷于风景画的真实性。从更深层次上讲,“卧游”与“如画”所借助的绘画类型不同,还在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
三、以形媚道与视觉资源:“卧游”与“如画”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
“卧游”与“如画”都是借助绘画来欣赏自然,但是两者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即两者处理自然与绘画之关系的立场不同。
“卧游”产生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自然山水成为文人画书写的主题。但是画家画自然山水,是为了澄怀味象,畅神以悟道,因此对于“卧游”来说,道的地位重于自然,自然则重于绘画,表现为:道>自然>绘画。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而有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己乎?”[1]129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然山水“质而有趣灵”“以形媚道”,因此在中国山水欣赏传统中,道的地位要比自然山水重要。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还说道:“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1]130在宗炳看来,神或道“栖形感类”,如果欣赏者通过卧游山水画,“应会感神”,体悟到道之后,则不必再去自然中“求幽岩”了。因此,对于宗炳而言,自然山水欣赏的关键是从自然之境中悟道,道是第一位的,相对而言,自然则是第二位的。
关于自然与绘画之关系,“卧游”则强调自然比绘画重要。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讲道:“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1]129-130从这里可以看出,宗炳首先“眷恋”的是自然山水,但是不知觉间“老之将至”,于是不得已才“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因此,对宗炳而言,自然相对于绘画而言是第一位的,绘画只是迫不得已而作之,进而被当作自然山水的替代品。自然山水之所以比画作重要,是因为自然山水“以形媚道”,即其中含有道,而绘画则通过“以形写形,以色貌色”[1]130,领悟自然山水中所含的道。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写道,自然山水“倏忽隐现,并无人先摹稿子,而惟我遇之,遂为独得之秘,岂可觌面失之乎?若一时未得纸笔,亦须以指画肚,务得其意之所在”[12]。可见,画家在面对自然山水时,关键也是要领悟自然山水“意之所在”,即揣摩山水之境背后的道。
综上所述,自然山水“以形媚道”,所以自然山水离道近;而山水画则通过“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经营惨澹,结构自然”[12],来追求自然山水背后的道,因此与道又隔一层。所以说,对于卧游而言,道比自然更重要,自然比绘画更重要。参照“得鱼忘筌”的说法,道就类似于“鱼”,而山水画则类似于“筌”,自然则处于两者之间,山水画只有“以形写形”“结构自然”、富有意境,才能传神达道。其自然欣赏的关键词是“境”,而非“美”,人们是通过山水画所营造的意境,来体悟山水中所含的道。
“如画”产生于西方18世纪,自然风景成为绘画的主题。人们以风景画的形式去探寻自然风景,是为了追寻视觉上的形式美,以达到审美愉悦。对于“如画”来说,形式美的地位重于绘画,而绘画则重于自然,表现为:形式美>绘画>自然。
与“卧游”不同,“如画”追求的是形式美,欣赏者专门欣赏形式优美的自然风景,由于绘画是一门专门研究线条、色彩、形状等形式要素的艺术,因此绘画成为自然审美欣赏的标准。吉尔平认为如画就是“像一幅画”(like picture),也就是说,自然事物如果适合入画,就具有如画美。他在《论如画美》中指出:“一些事物具有某种特质,这种特质可以通过一幅画展示出来,从而愉悦我们的眼睛,它们就是如画的景物。”[5]3对于吉尔平而言,为了把审美对象变得适合入画,不惜主张要对其加以改造,他说:“一座帕拉弟奥式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是优雅的,令人感到愉快。但是如果我们将它引入一幅画中,立即就成为了一个在形式上并不令人愉快的事物。如果我们想给予它如画之美(picturesque beauty), 我们就必须使用棒子而不是凿子:我们必须打倒一半,迫害另一半,并将其残缺的物件堆成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将它从一座平滑的建筑转变成一堆粗糙的废墟。”[13]由此可以看出,对吉尔平而言,自然作為客观实在的审美对象,必须服从一定的绘画标准,达到适合入画,才能具有如画之美。普赖斯虽然不像吉尔平那样亲自拿起“棒子”改造审美对象,使审美对象变得“粗糙”,但是普赖斯也觉得审美对象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符合如画之美的标准。比如普赖斯认为一座表面光滑的神庙或宫殿并不是如画的事物,只有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如风霜雨雪等自然天气的侵蚀,青苔、灌木、藤蔓等入侵,剥蚀掉其齐整的外表与光鲜的色彩,使其呈现出一定的粗糙感和斑驳的色差,才能成为如画的事物。[9]81-82
由此可见,对吉尔平和普赖斯而言,风景画是如画的审美标准,作为审美对象的事物只有符合风景画的标准,才能被视为是如画的。因此,给欣赏者带来视觉愉悦的形式美是最终追求,类似于“鱼”,而自然风景则是“筌”,风景画则介于两者之间,自然风景只有与风景画高度相似,才会给欣赏者带来审美愉悦。因此,对于“如画”而言,其自然欣赏的关键词是“美”,而非“境”,欣赏者通过欣赏具有形式美的自然风景,达到视觉上的愉悦。
“卧游”与“如画”处理自然与绘画之关系的不同立场,透视出东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卧游”认为山水“以形媚道”,欣赏者通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展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尊重与顺服。“如画”则追求自然的形式美,把自然看作视觉资源,如画旅游者带着旅行手册和克劳德镜,在自然中到处寻找如画风景,以满足视觉上的审美愉悦。“如画”展现了18世纪西方社会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的倾向,流露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18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西方人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得到极大提升,同时自然也被纳入到西方工业社会运作当中,被视为工业资源。这种思想折射在自然审美领域中,就表现为人们把自然视为视觉资源,从审美上征服尚未开发的荒野自然,展现人们对大自然的征服。如吉尔平所说:“猎人追逐微不足道的猎物,而有趣味的人追求大自然的美丽,跟随着她,穿过她所有的秘境,当她以某种优雅的姿态掠过身边时,他能一瞥惊鸿,追踪她的足迹,领略各种幽微神秘。”[5]48如画旅行者追逐自然风景,就像猎人捕获猎物一样,可见在吉尔平看来,如画风景就是旅游者的猎物或者战利品。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在论述如画时指出,在如画的帮助下“未被驯服的风景得以控制”[9]94。由此可见,“如画”为18世纪的西方人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驯服那些未被开发的自然风景,提供了美学理论上的支持。“如画”在本质上展示了西方人在审美上对自然的征服,是人化自然的表现。同样都是借助绘画来欣赏自然,“卧游”“澄怀观道”,展现的是天人合一,而“如画”则展现的是人向自然的进军,这也跟“卧游”与“如画”介入自然的方式不同有关。
四、非身体化与身体化:“卧游”与“如画”的审美欣赏方式不同
虽然“卧游”与“如画”都与自然审美欣赏相关,但是从身体维度上看,两者介入自然的方式迥然不同:“卧游”侧重以一种非身体化的方式来体验自然,欣赏者要从“应目”到“会心”,再到“感神”,由外而内,用心领悟自然山水背后的道;“如画”则侧重以一种身体化的方式来体验自然,欣赏者要身临自然,借助克劳德镜和旅游手册等,向外界世界探索,驯服未开发的荒野景色,获得视觉上的愉悦。
从身体所处的空间来看,卧游者囿于一室之内,披图幽对,而心游山川万物;如画欣赏者虽身游于山川万物之中,却囿于眼前之景色。宗炳由于“老病具至”,不得不囿于一室之内,于是将自然山水图之于室,“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1]130。樵甫在《重刻卧游录序》中说:“窃思‘卧游’云者,谓咫尺具有冈峦之势,枕簟有濠、梁之观,不必蹑屐扶筇,梯山钓水也。”[14]由此可知,卧游者从客观上“不得不”囿于一室之内,到“不必要”蹑屐扶筇,梯山钓水,亲临自然。卧游者虽囿于一室之内,足不出户,却可以“坐究四荒”,心驰万里,“独应无人之野”。元代诗人倪瓒的《顾仲贽来闻徐生病差》云:“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入卧游。”万里江山皆可卧而游之。明代章潢在评价吕祖谦的《卧游录》时说道:“矧海宇巨岳,名山足迹弗能遍,幸有先哲图记具在,时时览之,虽不出户,而神之所游,不广且大乎?”[15]可见,卧游的范围“广且大”,完全不受限制。如画欣赏者则向自然进军,在自然风景的驱使下,他们走进群山荒野之中,四处寻找如画之美。这些如画旅游者像猎人一样,“游客夸耀自己如何邂逅那些荒蛮的风景,如同‘捕获’各种狂野的美景,又如何把它们定格成图画战利品”[9]94。由于如画旅游者要站在观景之处,将眼前的自然风景“定格成图画”,所以会囿于眼前之景色,反倒不能如卧游那样“坐究四荒”。
从身体状态来看,“卧游”强调欣赏者要“澄怀”“理气”,排除杂念与欲望;而“如画”则伴随着旅游者强烈的猎奇心理和视觉占有欲。宗炳强调,卧游首先需要“澄怀”“闲居理气”,即欣赏者清理身心杂念,让身心清净,这就类似于“静斋”“坐忘”和“虚静”的状态,强调欣赏者要澄澈胸怀,形成一种淡然、超脱的身心状态。与卧游者不同,如画旅行者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猎奇心理和视觉占有欲,他们在自然中寻找风景,就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一旦寻找到如画风景,他们会利用绘画的构图手法,或者借助克劳德镜,将其定格,仿佛捕获或占有了这一处风景,并向他人炫耀。毫不夸张地讲,在如画旅行者眼里,如画风景犹如一种可以被占有的财富,“如画风景艺术家‘挪用’自然风景,并把它加工成商品。在各种‘必备’(工具)的帮助下,他把自然无法控制的馈赠转换成了可以框定的财富”[9]113。
从感官参与情况来看,“卧游”强调应目会心、澄怀味象;“如画”则将克劳德镜视为眼睛的延伸,用视觉来捕捉自然的形式美。宗炳强调,“澄怀”“理气”之后,卧游者通过眼睛凝视山水画,欣赏山水画中的意境,从而达到心有所感,即“应目会心”,如此这般,才能真正“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1]130,
从而“应会感神,神超理得”[1]130,进而悟道。与“卧游”不同,“如画”把自然看作视觉资源,因此更重视眼睛这一感官器官。“如畫”强调旅游者借助视觉来寻找风景如画的自然景色,并从中获得视觉上的愉悦。为了更方便地从自然中获取如画之美,“如画”主张把克劳德镜视为眼睛的延伸,从而获得更好的视觉体验。克劳德镜可以修改风景,使风景变形,具有理想美的特征。游客常常会在克劳德镜镜面上涂以色彩,这就相当于欣赏者在景物上镀上了色调,实现人们对风景的操控,如“涂成蓝色和灰色的镜片能使色调变暗,可以让一处多变的午后景色沐浴在月光之中;在中午使用黄色或‘日出’镜片观景,轻易就能看到辉煌的黎明景色,而且‘没有晨雾的梦空感’。透过霜白色的镜片,远处的谷垛就会变成雪堆”[9]97-98。
“卧游”与“如画”介入自然的方式不同,“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而“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这必然带来不同的审美效果:“卧游”让欣赏者走向自我的内心世界,超脱世俗;“如画”则让欣赏者走向外在世界,向自然进军。因此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
五、畅神疗疾与心理保护:“卧游”与“如画”的功能不同
“卧游”要求欣赏者在心理上必须“澄怀”“坐忘”,具有明显的去世俗化色彩。这表现在卧游的“畅神”功能上。宗炳在提出“卧游”之后,指出:“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1]130“神”指审美主体的精神状态,“畅神”就是指通过卧游山水画,“应目会心”“澄怀味象”“应会感神”,审美主体感受到自我精神上的自由与愉悦。在畅神中,审美主体不受山水比德思想的约束,也没有个人世俗观念的考虑,“独应无人之野”,直面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没有任何虚伪与夸饰,主体处于自觉自醒的状态。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说:“令人坐对移晷,倾消尘想。”[8]樵甫在《重刻卧游录序》中也说道:“寻绎一过,胸次洒然,如置身于舞雩、沂水间,油然有‘乐与人同’之致,岂惟是怡悦心目云尔哉!”[16]其实,盛大士的“倾消尘想”、樵甫的“胸次洒然”,都是对宗炳“畅神”观点的呼应。由于卧游可以畅神,因此具有疗疾功能。北宋元佑二年,秦观因为精神苦闷,周身不舒,患肠癖病,卧床不起。友人高符仲携带王维的《辋川图》,供他欣赏,告之曰:阅此可以疗疾。秦观便令人“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数日疾良愈”[17]。秦观卧游王维的《辋川图》,洗涤心中忧虑,驱除尘世烦恼,达到畅神境界,脏腑随之调和,身体也恢复健康了,这便是卧游的疗疾功能。
“如画”让欣赏者带着画家的眼睛欣赏自然风景,从自然中获得审美愉悦,这点与卧游类似。但是更重要的是,“如画”通过风景画来实现“人化自然”的目的,为游客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与保护。“如画”为游客控制那些未被驯服的荒野自然景色,提供一种可以操作的技术手段以及心理准备,使得游客不至于迷失在荒野自然当中。
典型的画境游客是一位绅士或淑女,他或她醉心于有节制的审美反应——对一系列新颖而又令人感到恐怖的视觉体验做出有节制的审美反应。游客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却步、常常也使人无所适从的风景,在此情形下,(审美)新词汇、景色的系统分类、能使观景者‘定格’一处风景的素描和绘画技艺的发展,以及纵览风景构图的观景点,都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微妙的心理保护。[9]94
旅游者第一次面对荒野自然时会感到“恐怖”“无所适从”,望而“却步”,这时候旅游者就需要能为他们欣赏荒野自然提供支持的审美理论,而“如画”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让欣赏者按照风景画的方式来欣赏荒野自然,将那些符合绘画构图的景色看成如画美的,而那些不符合绘画特征的事物则被视为非风景优美的(unscenic),从而为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微妙的心理保护”,使之不至于“无所适从”。也就是说,“如画”沟通了荒野自然与风景画,游客通过在荒野自然与风景画之间寻找相似性,从而达到某种熟悉的感觉,才不至于因感到“恐怖”而“却步”。“如画”为18世纪西方人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赫特纳说:“几百年来,阿尔卑斯山只是一个可怖的对象,到18世纪末时才为人们所赞叹。再晚些时候,又揭开了原野和海的美……过去完全不被重视的荒野的自然美却慢慢进入人们的意识中。”[18]
六、结语
在自然审美的视角下,“卧游”与“如画”作为东西方两个独特的美学范畴,虽然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认为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的地位比绘画重要,而“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欣赏自然的标准,故绘画的地位比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更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囿于一室之内,“澄怀”“理气”“应目会心”,心游万物,而“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游客带着强烈的猎奇心理和视觉占有欲,将克劳德镜作为眼睛的延伸,身游于山川万物之中;“卧游”让欣赏者走向自我内心世界,具有“畅神”“疗疾”功能,而“如画”则让欣赏者走向外部世界,借助风景画进行人化自然,甚至操控自然风景,为18世纪西方人在审美上向荒野自然进军提供了理论支持。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尊重自然,认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是人们悟道的一个路径,人们通过欣赏山水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审美欣赏的关键词在于“境”;18世纪的西方文化传统则把自然纳入到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之中,把自然风景看作视觉资源,“如画”成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的理论工具,背后所隐含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其审美关键词是“美”。“卧游”与“如画”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自然审美问题的不同解答,对两者加以比较分析,能够为当代自然美学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尤其是在当今云计算盛行的数字化时代,人们常常足不出户,利用手机、平板等客户端,选择在云端欣赏电子镜头中如画的自然风景,“云游”俨然成为当今自然欣赏的新方式。“卧游”和“如画”理论一个强调“足不出户”,一个强调“风景如画”,能够“为足不出户的云游模式提供了美学理论上的支持与借鉴”[19]。
如何欣赏自然是东西方文化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东西方文化传统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卧游”方式,西方传统文化提出了“如画”方式。然而,这两种话语在自然美学、环境美学领域的影响力却迥然不同:“如画”作为自然审美话语十分流行,一度与“优美”“崇高”并列,成为自然审美的三大范畴之一;然而“卧游”作为自然审美话语仅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盛行,在国内环境美学领域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更何论在国外环境美学领域的传播与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卧游”与“如画”,将二者并置,希望借此引起国内环境美学研究者对于“卧游”这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自然审美范畴的关注,从而着力推动中国自然审美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 John W Hippie. The Beautiful,the Sublime,the Picturesqu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 Theory[M]. Carbondale: Th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7.
[4] Stephanie Ross. The Picturesque: An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87(46): 271-279.
[5] William Gilpin. 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M].London: Thoemmes Press, 2001.
[6] Uvedale Price. An Essay on the Picturesque as Compared with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M].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1:67-84.
[7] Richard P Knight. An Analy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aste[M]. London: T. Payne, 1806:154-155.
[8] 盛大士.溪山臥游录:卷一[M]//安澜.画史丛书.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9]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M].张箭飞,韦照周,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0] 薛峰.简明美术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40.
[11] Eugene Hargrove.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M].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89:97-98.
[12] 盛大士.溪山臥游录:卷二[M]//安澜.画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13] Boudreau Gordon. Thoreau, William Gilpin, and the Metaphysical Ground of the Picturesque[J].American Literature, 1973(45): 357-369.
[14]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6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39.
[15] 章潢.五岳诸名山总序[M]//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6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38.
[16] 樵甫.重刻卧游录序[M]//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6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39.
[17]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20.
[18]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M].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36.
[19] 周思钊.探索环境审美欣赏的云游模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4-20(4).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Mind Travel" and "Picturesque" are two important aesthetic categori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respectively. The common view in these categories is appreciating nature through paintings of nature. However,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landscape paintings of "Mind Travel",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freehand brushwork, while in landscape paintings of "Picturesque"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realism. Mind Travel theory stresses that the landscape approaches Tao through the beauty of its shape, so nature takes a more important status than painting. Picturesque theory pursues the formal beauty, and landscape painting is the standard of natural appreciation, so painting takes a more important status than nature. Mind Travel theory emphasizes the non-physical experience of nature, in which appreciators are confined to one room while the mind tours in all things. However, Picturesque theory stresse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of nature and tourist takes a physical tour of nature with curiosity and visual acquisitiveness. "Mind Travel" has the functions of pleasing spirit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while "Picturesque" provides 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to peoples aesthetic march to nature. The comparison of "Mind Travel" and "Picturesque" can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natural aesthetics, bu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Mind Travel; Picturesque; natural appreciation
2099500783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