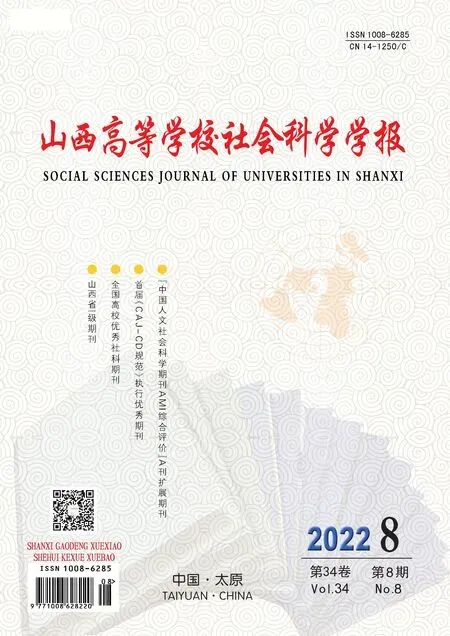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王 健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苏轼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亦是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文学成就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其哲学思想近年来也受到学界关注。刘燕飞整体系统地研究了苏轼的哲学思想;王国炎从反对王安石变法、洛蜀之争与苏轼文学成就三个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不受关注的原因;姜国柱、王水照和杨丽华等学者具体研究了苏轼的人性论思想;耿亮之、徐建芳、高纯林等分析了苏轼的易学思想。无论是在蜀学、苏轼人性论、易学思想还是在苏轼孟学思想以及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中鲜有重视苏轼义利思想的研究。但是研究苏轼的义利思想对分析蜀学思想体系以及研究整个宋学都具有意义,笔者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苏轼义利思想的来源
苏轼义利思想直接继承其父亲苏洵的义利观,同时也受到北宋时期儒者对义利问题认识的间接影响。
1.苏洵义利观对苏轼产生重要影响。苏洵肯定“义”的道德要求,认为“义”是行为规范,并且可以矫正天下人的不正之心。“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1]277苏洵认为,将“义”作为道德标准虽然可以匡正天下人之心,但是只言“义”而没有“利”,就是“徒义”,就成为圣人戕害天下的利器。苏洵以伯夷、叔齐为例,说明“徒义”的危害:“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义也,伯夷、叔齐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1]277“义”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徒义”就是戕害天下的工具。武王伐纣,即使高扬大义但也没有舍弃利。无论是伯夷叔齐守节而死,还是武王行大义诛独夫,都不能以“徒义”加天下。苏洵反对“徒义”,也反对“徒利”,认为“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1]279。没有“义”作为规范的“利”就是“徒利”,苏洵主张将义和利相结合。如果没有义,天下将没有节制,但是没有利,则道难行。所以君子欲行圣人之道,必须将利与义相结合。苏洵认为利与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1]278,义与利互相支撑,彼此结合为“义利”和“利义”,“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1]278。苏洵所著《利者义之和论》是对《周易》“利者,义之和”的解释,他对于义利问题的分析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曾枣庄认为,苏洵的义利思想与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主张大相径庭。
苏洵尚未完成《易传》,就与世长辞,在其临终之时将《易传》的后续完成的重任交给苏轼。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之作了记载,苏洵命苏轼继承遗述其志,苏轼泣而受命,撰成《东坡易传》。苏辙之孙苏籀在其《栾城遗言》中也提到先祖晚年读《周易》,未完成《易传》而长逝,苏轼受其命,遂完成此书。故而,苏轼吸收了苏洵解《易》的方法,并进一步阐发了义利相和的观点。朱熹评价苏轼关于义利关系的解读方法,“‘和’字,也有那老苏所谓‘无利,则义有惨杀而不和’之意”[2]。再次说明,苏轼的义利思想直接继承苏洵的义利观。
2.北宋儒者义利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自中唐以后,官私文献中“孔孟”并称的现象增多,孟子被封上爵号,拥有了进入孔庙的资格,《孟子》一书也跻身儒家经典之列。周予同先生将孟子及《孟子》在唐宋时期的变化称为“孟子升格运动”[3]。随着孟子地位不断提升,在北宋,孟子的道统论、辟异端、谈心性和辨王霸[4]等思想受到儒者关注。“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5]的王霸之辨是北宋儒者研究圣贤思想的主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研究,需要深入分析义利关系。因此,义利之辨也成为北宋儒者关注的问题。基于如此的学术环境,孟子的义利之辨和北宋儒者的义利思想自然对苏轼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孟子义利之辨成为重要论题。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儒者从来没有忽略义利之辨。北宋时期的各学派都重视义利之辨,不论是尊孟派还是疑孟派,都无法回避义利之辨。现在学界认为苏轼虽然不是尊孟派,但是他的本意不是为了非难孟子,而是希望通过孟子能够通达孔子的思想。所以,苏轼能够自觉地吸收孟子义利思想。其次,欧阳修、王安石、程颐等人尊崇孟子,此数子在思想领域居于重要地位,苏轼自然无法忽视他们的学术思想,苏轼的义利思想同样受到他们的影响。欧阳修注重礼义廉耻,认为儒家稳定社会、维系人心的主要理论就在于礼义廉耻。孟子主张的羞恶之心,即义之端,也是欧阳修极为重视的。他在史学的著述中,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史著,使不忠不义之人受到谴责。陈寅恪先生评价道:“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6]苏轼与欧阳修有师徒之情,欧阳修的道德做人主张,不可能不对苏轼产生影响。王安石尊崇孟子,将孟子的义利之辨思想运用到政治改革中,其变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义利思想,明确主张理财便是义。苏轼虽反对新法中的一些措施,但二人的义利观在理论上大致相同。程颐强调重义轻利,从义利之辨分析理欲之争,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截然对立。苏轼在与欧阳修、王安石、程颐等的交往中,互相不断争论,在往往复复的辩驳中,思想的碰撞使苏轼对义利观产生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
二、苏轼义利思想的理论基础
自然人性论是苏轼义利思想的理论基础。苏轼认为:“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7]60文中的“后之儒者”是指理学家,苏轼认为当时的理学家没有真正理会圣人之道。针对程颐等理学家的人性论,苏轼阐发了自己对“性”和“情”的理解,认为性、情无善恶之分,肯定了人的欲望是自然而来的。
1.苏轼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是与后之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相异的。对于人的本性与天地之性苏轼未作区分,认为人之性是同于天地之性的,“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8]258。苏轼的意思是,以往圣人作《易》,用阴阳来喻天之道,以柔刚来比地之道,把仁义视作人之道,这样天地之道与人之道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别,苏轼就将人的“性”扩展到道的本性。在人之性与天地之性一致的基础上,苏轼围绕“性”展开了论述。“圣人既得性命之理,则顺而下之,以极其变。率一物而两之,以开生生之门,所谓因贰以齐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设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纷然相错。尽八物之变,而邪正吉凶、悔吝忧虞、进退得失之情,不可穷尽也。”[8]10苏轼论“性”主要是在人的领域进行的,他认为贤者对于“性”有所理解而不知用,愚者有所用而不知道“性”的真实含义。
苏轼将人的欲望视为人本性的一部分,认为欲望与道德没有关系。从情感来讲,人的本性可以归纳为追求自己所乐之事,如君子向往孔颜之乐,小人则以一己之利作为乐处所在,如此看来,性与道不无关系[9]。性,不论贤者还是愚者都具有。仁义礼智都是从人的本性演绎而来,这样的本性每个人都具有,是不因尧舜桀纣存亡的。理学家主张用善恶规定“性”,苏轼反驳这种“性”有善恶的观点。他认为“性”是最根本的,“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阴阳交而生万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故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8]174-175。“性”是决定物成之为物的根本因素,性与善不是同一个概念,圣人用仁义礼智命名善,混淆了性和善的关系,因此苏轼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于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8]175-176苏轼用火来比喻性,用火之效指代善。如果没有性就无法产生善,将人之性提高到了高于善的地位,也表明苏轼坚持性无善恶的观点。苏轼分析了“性”与“道”的关系,将道作为解释性的媒介,“敢问性与道之辨,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则闻也。有声而后有闻邪?有闻而后有声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8]175-176。用“声”和“闻”来描述“道”和“性”的关系,性和道具有一致性,将性放在道德层面,他认为“性”存在于道德领域,同时又不限于道德领域,善是由性所引发。苏轼认为性是无善无恶的,这是对理学家所坚持的性善思想的反驳。
2.苏轼尊重人情,对人欲予以肯定。这是苏轼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苏轼主张性情合一,认为“道”要符合人情。“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7]49不仅“道”要顺应人情,而且“礼”要随情而变,不违逆人情是礼的原则。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7]114-115苏轼认为理学家将性情分开不符合圣人之道。苏轼主张性无善恶之别,性与情是统一的,情是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认为性动而生情,性与情没有善恶之分。正是出于自然人性论,他主张性情统一,肯定人欲,因而不反对利,强调义利相和。
三、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
苏轼继承其父苏洵的义利观,吸收了先秦儒家与北宋儒者的义利思想,在道德价值层面上注重“义”的作用,强调要自觉积极地遵守“义”,明确提出了“以义正身”的主张。
宋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社会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构建,作为人臣要尽己之力引导君主恢复三代之隆,希望能与君主共治天下,所以作为人臣,就要肩负起政治责任与政治使命。苏轼给出了大臣的定义,“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7]125。苏轼主张大臣要用“义”辅佐君主,规范君主的行为,端正君主的动机,使其不要做出危害国家的行为。若想用义正君,大臣必须将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遵守义的标准,做到身正心正。忠义之臣不仅要以义正身,当国家没有明主在位时,还要敢于为天下之事对抗小人。“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7]125苏轼认为“义”“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怀义,小人无义而以利居之。“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7]127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解释“‘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时说道:“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则畏,动则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内‘直’,推其直于物,故外‘方’。直在其内,方在其外。隐然如名师良友之在吾侧也,是以独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8]123君子以义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义正身,能够将义视为良师益友陪伴在自己身边,时刻监督审视自己的行为,怀义而立身则人不孤,不会像小人那般迟疑畏惧。
苏轼强调为学的方法须要先怀仁义之道,主张学习应当以自己的志向为准绳,立志于仁则学到的内容是仁,立志于义则学到的内容是义,如果以功利为志,则所学到的内容就是功利。苏轼强调要立志于仁义,将仁义之道作为求学之法、求学之目标,那样才能所学有成。苏轼重视“义”的道德标准,在自我的道德修养上,坚持以仁义为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慎独。《中庸》要求君子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内圣外王,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宣扬儒家思想匡扶社稷,希望君行道,民行善。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人民安康,达到夏商周三代之治。宋代儒者主张修身,即追求内圣的功夫,己身正方可正他人。苏轼也注重内圣自修,强调要把义作为内在修养的道德标准。
苏轼申述当儒者位极人臣时,不仅要能够做到以义正身,而且要以义正君。“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7]125君子以义为心,小人怀利相接,君子有匡扶天下之志,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决心。但是君子要想诛灭小人,则需要君子怀义相交。“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7]127小人急于争利,经常为了避患而失去彼此之间的信任,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互相欺诈。因此,苏轼强调以义正身,遵守义的道德规范。
苏轼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明确“利”的作用,强调“利以安身”。从情的理路出发,肯定人欲,在解释“保合太和乃利贞”一句时表明了情无善恶,情以为利的思想。“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夫刚健中正纯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则爻也。’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各正性命为贞,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贞者,性情也’,言其变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8]13-15以“情”释“利”,性与情无善恶之分,只是性发散而为情,所以利也没有善恶的性质,是人性的一部分。苏轼对“利”予以肯定的评价。《乾卦·彖传》记载“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苏轼认为这句话解释了利的含义,“此所以为利也,生而成之,乾之始终也,成物之谓利矣”[8]10。利可以成物,如果没有利则物不成、身不安。
《东坡易传》中对“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句作注云:“精义者,穷理也;入神者,尽性以至于命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岂徒然哉?将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尽水之变而皆有以应之,精义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与之为一,不知其为水,入神者也。与水为一,不知其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谓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闲,其体舒。是何故?则用利而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则物莫吾测而德崇矣。”[8]227-228苏轼用水作比,喻指精义、入神、致用的含义。知道水既能浮,又能沉,尽晓水的变化就是精义,即穷理;明白水有浮沉的作用,而能与水为一,就是入神,即尽性致命;善于游泳的人可以操舟而行可谓致用,操舟而行,心中闲适而不惊,身体舒缓而不累,究其原因是可以用利安身。苏轼虽然强调要“义以为心”,但是不能只讲义,不讲利,要将利作为百姓安身立命的工具。利本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所应该批判的是“徒利”,即没有义作为支撑的利。以利安身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人崇尚德行,追寻仁义,更好地遵守义的道德标准。
苏轼对义与利关系的认知直接承继于苏洵,苏轼的义利思想与苏洵相一致。苏洵在《义利相和论》表明义有“拂天下之心”的性质,正因这一性质,义便有所“不和”(即有违人心),因此义需要“即于利”才能“和”(即不违背人心)。所谓的“义利”“利义”就是“合义之利”“有利之义”。在苏洵“义利相和论”的影响下,苏轼既肯定义的规范性,也认识到利的作用,明确了利对义的补充作用。他不仅将义利视作行为标准,还将利看作百姓生存的物质条件。为了不拂天下之心,遂将利引入义之中,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主张“义利相和”。
首先,苏轼肯定利的作用,认为在义与利之间,利是对义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苏轼分析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的关系,认为民生得到保障才能使人的品行道德端正,只有用利才能使人民懂礼节。粮仓充实才有向人民讲授道德伦理的可能,百姓丰衣足食就可以自觉地确立荣辱观。用利就是厚生,是注重民生问题,要用利先安身。如果不注重民生,黎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薄弱,无法使百姓有稳定的生活,最终结果就会导致黎民犯上作乱,危害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统一。讲利而使黎民生活富庶、饱食暖衣,这样才可以对黎民进行道德伦理的教化,匡正人们的道德行为,宣扬仁义的思想。如果抛弃利而单纯讲义,人们不会听从道德的约束,正德的目标也将是黄粱美梦。用利安身才能使得德正,注重厚民生才能使百姓崇尚正确的道德标准,苏轼强调的“用利安身”目的是为了崇德。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利,而没有义的约束,就会带来灾难。仁义之心是内在于人的,必须要将仁义之心作为道德思想的核心,否则独言其利,天下则会有大难。苏轼进一步阐说,圣人君子所反对的是没有义作为支撑的利,认为这样的利会带来灾难,使个人、社会、国家都处于危亡之际。
其次,苏轼强调义的规范性,利的实现要在义的规范下进行。利必须要以义为核心,用利可安身,但是安身还不够,还必须要能够以义正身。如果不以“义”规范“利”,就会导致上下交征利,以利为心,人人只求其利,招致大难,使得国家危亡、社会动荡。苏轼用“义利相和”诠释义利关系,其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用利来解决民生的问题,使得民众的生活有所保障;另一方面是为了规范民众的行为,将义作为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只为利而不求义的动机、想法、行为。
最后,苏轼表明义与利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存在。苏轼主张将义与利相结合,即义不能缺少利的补充,利不能失去义的约束。苏轼对义与利的概念内涵有独特认识,分析了彼此的道德价值地位,受苏洵的影响,反对“徒义”,批判“徒利”,提出“义利相和”的观点。《东坡易传》中解释“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时提出“礼非亨,则偏滞而不合;利非义,则惨洌而不和”[8]17。这一解释非常明显地表明是对苏洵义利观的继承。苏轼认为“礼”如果没有“亨”,即长人嘉会则会偏滞而难以相合,如果义没有利作为补充就会“惨洌”相杀。利要和于义,而义必须也要以利和。如果义没有利,则民众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是对百姓的一种残害,也就无法宣扬义。在解释《豫卦》“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簮。象曰:由豫有得。志大行也”时说道:“盍,何不也。簮,固结也。五阴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贞,三豫易怀,而二贞难致。难至者疑之,则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来者、去者、观望而不至者,举勿疑之,则吾朋何有不固者乎?”[8]22即是说,人所附者以利和,以利散,围绕利则吾朋固矣。简而言之,在苏轼看来,义与利之间是“相和”的内在关系。
总而言之,苏轼的义利思想有其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其父苏洵的义利观对其义利思想产生直接影响,北宋儒者的义利思想为苏轼义利思想形成提供了间接资源。“义利相和”的理念体现了苏轼义利思想的本质。苏轼的义利思想影响其政治主张,对其民本思想影响尤重,从而肯定民是天下之本,认为君主只不过是负责天下之事而已。依托其义利思想,苏轼形成了与王安石不同的政治主张,重视民众的物质利益,注重民生,强调从百姓生存的物质条件看待利,以利补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