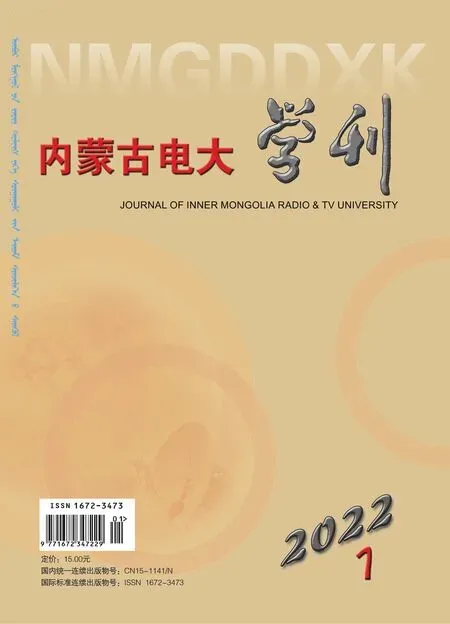基于《小城畸人》两译本对比浅析重译的必要性
陈亚杰,舒鑫钰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Winesburg,Ohio(《小城畸人》)于1919年出版,全文140,000字,由二十五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故事组成。故事以安德森的故乡俄亥俄州温士堡镇为背景,勾勒出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怪”,反映出工业化时期美国生活的现实情况,并再现了工业化的转变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这部小说不仅影响了后来的一代美国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也对现代美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作用。该小说在中国的首次译介由吴岩先生完成于1983年,当时作品的译名为《温士堡,俄亥俄》,后于2008年重译,将小说题目改为《小城畸人》。2020年9月,刘士聪先生重译的《小城畸人》出版,为此本小说增加新译,对该小说做出了时隔二十余年的不同解读。
提及“重译”,就需要对其意义有所了解,它一般指“对自己旧译的修正润色”[1]P29,学界中还流行“复译”一说,即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出另外的译本。但学者林煌天说过:“复译和重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2]P219针对重译的必要性,鲁迅先生指出:“翻译地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3]P243文学作品重译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王振平指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译本,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翻译中对意义内容的歪曲和形式韵味的丢失总是难以避免的。[4]P20另有学者孙致礼提出,在知识结构和翻译理念存在欠缺的情况下,翻译中难免出现理解或有偏差、表达或失严谨等现象,[5]P44他还指出,翻译应该是永无止境的。[6]P9
本文选取的《小城畸人》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两个版本的翻译时间跨度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根据中国知网(CNKI)搜索关键词“《小城畸人》”(截至2020年11月10日)得出以下内容:张晨阳从成长小说视角分析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7]P1,黄煜菲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作品中的女性畸人形象[8]P8等,大多针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具体意象。搜索“《小城畸人》翻译”“《小城畸人》译本”等关键词,只呈现出从文学层面分析的研究论文。此篇论文将刘士聪新译(2020年)的《小城畸人》及吴岩十多年前(2008年)的译本为语料进行对比分析,考察新译和旧译的异同同时,研究新译本中对旧译本出现的疏漏或误译、语言陈旧、生硬拗口等问题的修正,并探讨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
一、作品作者及《小城畸人》简介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是20世纪初期的一位美国作家。他在短篇小说领域颇有建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传统文学形式对美国短篇小说影响的局面,使美国短篇小说能够取得独立的发展。与此同时,安德森是最早关注人们内心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对后世作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威廉·福克纳称其为“作家的作家”。然而,安德森的大多数作品没有获得人们的关注。作为安德森最杰出的代表作,《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的发表,奠定了安德森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小城畸人》发表于1919年,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被称为描写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小镇生活的经典著作。该小说以安德森的家乡温士堡为背景,描写了美国处于工业转型时期,小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塑造了一群既传统又受到现实功利主义影响而扭曲,渴望爱与自由又疏于交流的 “小城畸人”。全文共二十五篇,以小男孩乔治·威拉德为线索,其成长与小镇发展及小镇人民紧密相连。以威拉德的成长轨迹贯穿全文,将每一篇小故事中的人物紧密联系起来,这一设定体现了作者在作品中隐含的深意。
二、文学作品重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学作品重译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常见。受到时代、文化、语言表达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针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时代的译者会给出不一样的理解和表达。因此,任何译作都不可能拥有永久的生命力,[9]P39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英国翻译家Postgate, J.P认为,不存在最终定本,译文会随着时间而老化。[10]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也提出,即使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也是有年限的。
国内学者对于重译重要性的阐述,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关于佛经的翻译。现代学者也对文学作品的重译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翁显良先生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原作,译文要与时俱进,过了一定时期又得把译过的作品再译。[11]P7许钧先生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可能一次就被彻底认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一部译作只是对原作的一种阐释和理解,因此重译是对源文本意义的更深层次挖掘。[12]P2许渊冲先生在1996年就重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重译”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译过的作品, 重新译一次;二是别人译过的作品, 自己重复译一遍。[13]P56由此,重译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小城畸人》,首次译介于1983年完成,吴岩于二十五年后(2008年)对自己的初译本进行了二次修改和完善,正如他自己在译本序中写的那样,1983年的译文是年轻时的旧译,有些错、漏的地方。修订本在旧译和旧作的基础上做了修改,想必仍有错误和不贴切的地方。[14]P10十二年后,刘士聪对该小说进行重译,重译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在旧译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和改进”,[15]P45对之前译本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并查漏补缺,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致于此。
三、从两个译本对比看重译
(一)从疏漏或误译现象看重译
译者在翻译英文作品过程中,无法保证每一个字句都精准无误。面对文化差异和各式作家的独特写作方式,出现理解错误或误译在所难免。因此,重译中的一大重点就是对旧版本中的疏漏或误译现象进行查漏补缺,使得译文更加贴合原文。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例1. With a kind of religious fervor he had managed to go through the pitfalls of his youth and to remain virginal until after his marriage.[16]P91
吴岩译(下文简称“吴译”):他用一种宗教式的热情,设法经过他那青春的陷阱,保持童真,直到他结婚的时候。[14]P85
刘士聪译(下文简称“刘译”):他怀着一种宗教似的热情经受着青春时期的一个个挫折,直到婚后他仍然保持着节操。[17]P103
对于原文中“to remain virginal until after his marriage”的表述,两位译者分别译作“保持童真,直到结婚的时候”和“直到婚后仍然保持着节操”,这是两种状态描述,本句原文作者用“until after marriage”,结合下文中作者对电报员与妻子关系的描写,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婚后仍然保持这种状态,而非在结婚后结束了这种状态,所以吴岩对于此句的翻译属于误译。
例2. (he said,)looking with bleary eyes at the men who walked along the station platform past the telegraph office.[16]P88
吴译:一面用他的烂眼睛望着沿车站月台行走的人们经过电报局门口。[14]P82
刘译:(他说,)用朦胧惺忪的眼睛看着沿站台月台走来从电报局门口经过的人们。[17]P100
“bleary”一词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为“(of eyes)not able to see clearly,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tired”,由此得知,此处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主人公睡眼惺忪,因疲惫睁不开眼睛。对比两位译者给出的不同译法,刘士聪译为“朦胧惺忪的眼睛”,更为贴切,而吴岩此处将其翻译为“烂眼睛”,则误解了原作者的意思,属于误译现象。
例3.Wash Williams’ voice rose to a half scream.[16]P92
吴译:沃许·威廉的声音提高,几乎成为绝叫了。[14]P85
刘译:沃什·威廉斯抬高嗓门,快要喊起来了。[17]P104
对比两个译者的译文,对“rose to a half scream”刘士聪的译文“快要喊起来了”很贴切,表达出了主人公当时的激动心情。吴岩在译文中使用的“绝叫”一词,无法在汉语词典中查询到用法和释义,反而在日语中较为常见,写作“絶叫”,意为“大声疾呼,尖叫”[18]。就语法而言,“几乎成为”不能用来修饰动词“尖叫、喊叫”;从语言层面来看,在汉译本中出现日语词,不但会造成读者的困惑,而且不符合目标语的使用习惯。因此,吴岩此处对译文的处理属于误译。
(二)从语言的时代性看重译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使用的语言不断更替。旧译本中的语言较为符合译者所处时代的风格习惯,可能会与当今的语言习惯不符,略显陈旧。重译能够修正这一缺陷,使得译作更加符合当代读者的语言使用和阅读习惯。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例4. Thoughtful books will have to be written and thoughtful lives lived by people about them.[16]P62
吴译:她们左右的人得写上几本深思熟虑的书,而且还得过着深思熟虑的生活。[14]P53
刘译:她们周围的人得写出经过周密思考的书,得过精心计划的生活。[17]P64
对原文中的“lived by people about them”,两位译者分别用了“左右”和“周围”一词。“左右”在汉语词典中有八个意思:一是指左边和右边(例如:主席台左右,红旗迎风飘扬);二是指附近(如《送东阳马生序》中的“余立侍左右”);三是指称跟从的侍者(如《三国演义·第三回》:至嘉德殿门,张让、段珪迎出,左右围住,进大惊);四是指书札中常用的称谓敬辞(如《史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五是指帮助、辅助的意思(如《诗经·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六是指控制、指挥的意思(例如:他的行动为她所左右);七是“反正”的意思(比如我左右闲着没事,就陪你走一趟吧);八是指上下、光景,多放在数量词后,表示约略之数(如:六点左右到的家)等等。虽然“左右”有身边、附近之意,但现在人们更习惯把“左右”用在数量词之后表约略的数字,或者使用其名词之意“左边和右边”和其动词之意“控制、指挥”等,人们更倾向于用“周围”表达“身旁、附近”之意。因此,就两位译者各处的时代而言,译法均无错误,但就语言的时代性而言,刘士聪翻译为“周围”,更符合现今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
例5. (……) and in his own household he drove his family distracted by his constant harping on the subject.[16]P62
吴译:他尽弹这个老调,弄得全家都不耐烦。[14]P54
刘译:他老谈这件事,弄得家人不耐烦。[17]P65
“harp on something”作为动词词组意思是“to keep talking about sth in a boring or annoying way”,对应的中文释义为“喋喋不休地谈论;唠叨”。两位译者分别译为“尽弹这个老调”和“老谈这件事”,意义上相差无几,但在词语表达上大相径庭。“老调”在汉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已说过多次令人厌烦的论调,通常表达为“老调重弹”;二是指流行地区以河北保定为中心的戏曲剧种,称为“老调梆子”。但此处“尽弹老调”的用法较为陈旧,与当今时代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有些差异,阅读起来也缺少流畅感。原作者在此处想要强调主人公一直重复谈论一件事,用“老谈这件事”的表达方法,既简洁又符合言语使用习惯。
例6. (……,) giving and taking friendship and affection as one takes the feel of a wind on the cheek.[16]P62
吴译:友谊和爱情之间的给与受,一如人们领受清风在面颊上的轻浮。[14]P54
刘译:相互之间的友谊和感情有如来自河岸的清风,煦煦拂面。[17]P65
依据原文的“giving and taking”吴岩进行了准确的翻译,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确是“给和受”,即给予和接受。但就语言的时代性来说,“给与受”词组的使用频率在当今时代较少出现,搜索关键词也无法得出相关内容。刘士聪译为“相互之间的友谊和感情”,既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也更符合当今时代人们的言语习惯。
(三) 从言语生硬或拗口现象看重译
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原文表达和句法结构的影响, 译出生硬、拗口的语句来。此种译文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会使原文的美感大打折扣。因此,在重译的作品中重新润色生硬拗口的译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流畅且舒适的阅读体验。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例7. He was dirty. 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unclean.[16]P88
吴译:他很龌龊,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不洁的。[14]P81
刘译:他很脏,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17]P100
对比两个译例,“dirty”作为形容词,在英文中的意思有“not clean;dishonest;connected with sex in an offensive way;dull”,对应的中文意思即“不洁的;不诚实或卑鄙的;猥亵的;暗淡的”。这段人物刻画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报员——沃什·威廉斯,联系上下文可知,这里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这位电报员除了一双手,其他身体部分不太注意是否整洁,因为下文中提到“Not everything about Wash was un-clean. He took care of his hands”。“龌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不干净;脏。一般用来形容人品恶劣,思想不纯正;或形容人气量狭小,拘于小节”[19]P1378。虽然,释义中有“不干净;脏”之意,但从目前汉语使用习惯看,提到“龌龊”一词,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形容人的品质低劣”,容易先入为主,对人物的形象产生误解。因此,在这里直接译为“脏”,更符合当前的汉语使用习惯。
例8.He was not then known as Wing Biddlebaum, but went by the less euphonic name of Adolph Myers.[16]P18
吴译:那时他不叫飞翼比德尔鲍姆,却以音调较差的阿道夫·迈尔斯为姓名。[14]P7
刘译:那时他不叫飞翅比德尔鲍姆,他用的是一个不太悦耳的名字,阿道夫·迈尔斯。[17]P9
对词组“less euphonic”的处理,吴岩译为“音调较差”,刘士聪译为“不太悦耳”。“euphonic”在《英汉大词典》中的释义为“声音悦耳的、变音的”[20]P637,译为“音调较差”意思上固然没错,但阅读起来显得尤为生硬,而且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的发音习惯不同,目标语受众无法感知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音调较差”差在哪里。刘士聪将其译为“不太悦耳”,就显得顺畅流利许多。
例9. (……), don’t think of himself as in any way a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town (where he had lived for twenty years).[16]P15
吴译:却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不是这小城生活的一部分。[14]P4
刘译:却不把自己看成小镇生活的一部分。[17]P5
对比两个译者的译文,吴岩按照原句的顺序完全直译,“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不是”读起来既不通顺又生硬拗口。虽然两位译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者的表达方式不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刘士聪译为“却不把自己看成……”则更为通顺,也获得了与原文异曲同工的效果。
四、结语
通过上文中的分析,重译文学作品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通过重译,能够对旧版本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错译或漏译、语言过时、语言生硬拗口等问题进行修正,也能够更加贴合原文,为大众读者提供忠实性高、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重译通过仔细研读前人译本和原文本,能够为社会和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译作。重译并不是完全推翻前人的译本,而是在社会时代不断发展的浪潮中,让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得到更好的延续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