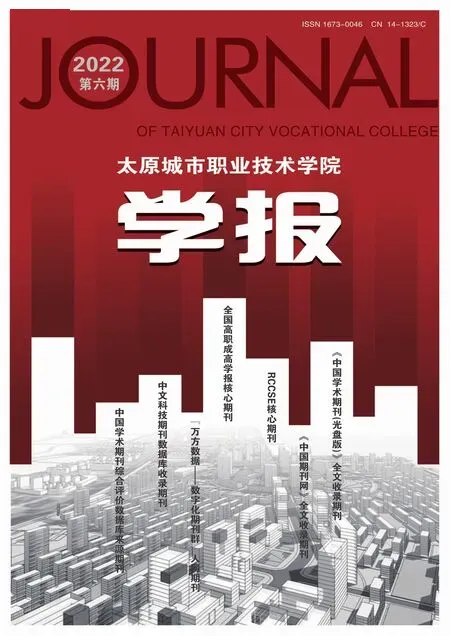增能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建构
■康蔚林,罗 丹
(1.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100;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一、研究缘起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迅猛,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达到1.9亿,占总人口的13.5%,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空巢独居老人近一个亿,高龄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加。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胜利、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农村空巢老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保障,但是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往往被忽视,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日益凸显。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2018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国老年人中有36.6%的人感到孤独,其中43.9%为农村老年人。西部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家中老人沦为空巢老人,独自生活、艰难自理。精神赡养缺失造成了空巢老人的“空心”问题,由此引发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疾病,这严重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老人精神生活的满足程度不仅关系到老人晚年生活状况,还关系到家庭生活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序幕的拉开,实现农村有效养老,解决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刻不容缓。
现阶段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相关研究较少,偶尔会在研究中提及精神慰藉或者情感支持等相关概念,但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基于此,本文以一个典型的“空巢老人”村落四川中部X村为例,探讨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的现状及建构路径。X村是位于四川中部乐山市的一个山村,该村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727人,占比约60.7%,其中空巢老人数量为603位,占比约83%。该村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高,是西南地区一个典型的空巢村。通过选取10位空巢老人与2名村干部进行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的方式,多方面、多维度了解当地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现状、老年人相关工作的开展等情况,期冀为探讨构建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方向。
二、精神赡养与增能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精神赡养
精神赡养是影响老人晚年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精神赡养”这一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学者穆光宗认为精神赡养包括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1]。学者莫医铭指出精神赡养是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家庭中的子辈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健康,使老年人获得人格尊重和情感慰藉,从而幸福、安然地度过晚年[2]。综合学者们的定义,本文将“精神赡养”定义为: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以自身为基础,通过获取、整合家人、同辈群体及社会给予的支持与资源,为自己提供精神支持,以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获得良好的精神生活。
(二)增能理论
增能理论作为现代社会工作的一个基础理论。增能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体能力,强调挖掘或激发服务对象的潜能,帮助自我实现或增强影响[3]。增能理论认为,应相信和认同个体有能力在与他人及环境在积极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本文探讨从不同层面挖掘农村空巢老人获取精神需求的内在潜力,恢复其因空巢造成的孤独感,帮助其实现社会的再融入。
三、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困境
(一)空巢老人自我支持的精神赡养意识缺乏
一是农村空巢老人普遍缺乏精神赡养的观念与精神养老的积极意识。她们将赡养简单等同于物质赡养,认为只要有吃有喝,子女所给付的费用能维持基本生活就是尽到了赡养义务。空巢老人缺乏主动改善精神生活状态的意识,即使是子女未尽到赡养义务,也会碍于面子或顾及到“家丑不可外扬”,不会采用法律手段维权。二是农村空巢老人对他人或相关组织给予的精神赡养方面的资源,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访谈中发现,农村空巢老人不主动寻求子女的关心。她们表示由于怕打扰子女的工作和生活,一般不会主动跟他们打电话,更不会主动向他们倾诉不愉快的事情。
(二)家庭的代际支持功能孱弱,精神赡养的供养主体缺位
一是承担精神赡养义务的供养主体缺位,给予老人的情感慰藉不足。X村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回家频率为一年一次,均在过年期间,在家停留时间约为15天;有少数人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回家一次。子女与老人的长期隔离,导致老人内心孤寂,同时遇到困难也无处倾诉。访谈中,有两位老人明确表示时常感觉一个人生活很无趣——“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我说话,无聊得很”。这种长期的分离状态导致他们对子女的思念增加,从而更进一步加深老人的孤独感,电话成为父母与子女之间联络情感的主要方式,但并不能成为情感互动的有效途径。这使得老人在子辈中获得的精神慰藉逐渐减弱。
二是代际间的情感支持功能弱化,呈现出“去情化”特征。访谈发现,子女多通过给老人金钱、物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关心,言语上的情感互动较少。大部分老人与子女的通话频率在一周一次甚至更长,老人与子女的聊天内容没有实质性内容,均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并不能为老人提供情感上的精神慰藉。正如一老人所言:“就问吃饭没有,最近在干啥子,身体好不好之类的。我有啥子不高兴的事情,也不得跟他们讲,他们工作忙又累,跟他们讲干啥嘛。”还有一些老人表示一旦自己遇到困难,不到万不得已,子女根本不会亲力亲为地帮助自己,顶多给自己一些钱让自己去解决,让不少老人感到心寒。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在现代化冲击之下出现了“孝道异化”现象。
(三)社区及社会组织支持的精神赡养资源鲜少
第一,农村社区的服务能力较弱。一是乡村社区的基础服务设施相对落后,不能满足老人的精神娱乐需求。X村仅一处健身场地、一个图书阅览室和棋牌室,活动室设备老旧、数量少,且活动场所距离较远(需步行15~20分钟才能到达)。二是针对老年人举办的精神文化活动很少。访谈中一位村干部谈到:“我们这村没有什么日常活动,主要是经费不够、人手不足,也没有合适的场地,活动办不起来。就算办起来了,也没有多少人来看。就每年有一次老年协会的活动,附近的老人去吃个中午饭,一起聊聊天就回家了。”
第二,缺乏提供为老服务的专业社会组织。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在当地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提供渠道中,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较小。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医院、社区服务机构等养老服务机构在X村尚未建立起来。
(四)政府在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领域支持力度尚显不足
一是政府在老人赡养方面侧重提供物质支持,忽略了精神赡养方面。当地政府将大部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对拓展社区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对精神养老的专项资金支持匮乏。通过与当地老人交流得知,当地政府针对老人的工作集中在满足其物质需求和关注其身体健康方面,如组织一年一度的下乡体检、对贫困空巢老人进行节日慰问等,对精神需求的回应较少。二是政府支持精神赡养的机构建设尚不完善,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缺乏制度保障。三是政府未能有效动员和配置社会力量,满足老年人的情感慰藉需求。
四、增能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理路
增能理论视角为我们建构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了新思路。首先从空巢老人家庭入手,积极挖掘空巢老人家庭内部所拥有的能力。其次利用乡土资源,改善空巢老人的外部环境条件。具体而言,可以从个人增能、家庭增能、人际增能、社区增能、环境增能五个层面出发,不断完善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一)个人增能:提高空巢老人精神养老自我效能
个人层面的增能,即发掘积极的自我意识和创造力。精神赡养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以老人为中心”。站在内因角度来讲,老年人自我封闭、消极厌世的悲观情绪是空巢老人获取精神幸福的主要障碍。因此,老年人要转变观念,通过“精神自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老年人可以用丰富的经验来发挥余热,培养兴趣爱好来充实生活,提升老有所为的价值感。农村资源有限,可以就地取材,发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如对花草感兴趣的老人可以种花种草、善于编制东西的老人可以培养编手工品的爱好、利用宽阔的场地和其他老人一起做一些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更多可以消遣时间、娱乐身心、排解心理压力的方式,并通过新的兴趣爱好,加强社会参与,获得成就感,缓解消极心理。
(二)家庭增能:加强家庭精神赡养代际支持功能
家庭层面的增能,即调动家庭成员的内部能力资源,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实现家庭成员良好的社会互动。第一,增进配偶在生活照护场景中精神慰藉功能。夫妻两人间相互扶持,互相照顾,成为彼此重要的精神支柱。两人之间围绕生活琐事进行日常交流可以有效缓解苦闷的情绪。访谈中发现,老人们均提到来自配偶的关心、陪伴是让他们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对于丧偶的老人可以通过重组家庭解决丧偶老人孤独和照料问题,“搭伴养老”应得到社会认可与法律保护。第二,承担老人精神赡养主体责任的子代应当加强子女对老人的关心,重视老人的精神需求。首先子代应采用多种方式提高与老人互动的频率,想方设法“常回家看看”,给予老人更多的情感支持,让父母快乐。其次,女子行孝要注重老人的内在需求,子女应学会换位思考,尽力缩短代沟距离,如对父辈进行有必要的文化反哺,促进代际的良性支持。
(三)人际增能:拓展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人际网络
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旨在帮助弱势群体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通过个人与他人的合作来培养一种集体意识,拓宽解决问题的途径[4]。亲友邻居成为空巢老人获得精神慰藉与情感支持的有益补充。首先,亲友邻居是农村空巢老人日常交流群体之一。在走访中发现,该村大多数老人都喜欢在公路旁或者是在田间地头与其他人聊天,聊天内容多为生活琐事或者当地的新鲜事。其次,亲友邻居还是空巢老人遇到个体困境时获得救助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位老人说道:“前几年我被狗咬了,就是我们这周围的人帮我处理的,带我去医院,给我办各种手续,还帮我照料家里。后来我那些兄弟姐妹来看我,每个人还带东西、拿钱给我,其实他们来陪我说说话我就很高兴了。”中国有句古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因此,增强亲友、邻居间的联系,强化双方的关系,进行恰当的思想引导,鼓励空巢老人之间“抱团取暖”,以此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
(四)社区增能:强化社区及社会组织的养老服务水平
社区层面的增能,即依托社区自治的软硬件资源,整合社区的空间资源,组织居民参与,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完善社区的服务,实现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应完善社区治理,着力提升社区的互助功能。为缓解空巢老人精神的“疏离感”“无力感”,可以建立农村社区空巢老人养老互助体系,建设精神养老服务场所,如老年活动中心、兴趣小组等。有条件的社区还可以组建老人精神养老服务队伍,鼓励社区的年轻人加入队伍,使得社区老人有一个大家庭,改善老人的精神困扰和生活困难。同时,通过增加支持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老人加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去,进一步发挥社区的善治功能。
第二,发挥社会组织及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在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多样化情感需求中的作用,如发展志愿者协会、老年机构等。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助力为老服务,如可以组织当地镇上的小学生、初中生定期为农村空巢老人开展“下乡入户”志愿服务活动、“结对子”志愿服务等。同时积极探索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农村空巢老人关爱服务,通过设立社会工作站点、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空巢老人精神慰藉提供专业、有效的服务。
(五)环境增能:创设支持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环境
环境层面的增能,旨在改善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创设有利于实现自助的规则与制度,帮助个体提升获取外在环境资源的能力。
第一,政府积极创建支持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文化环境。通过弘扬“孝道”文化,形成“爱老”“尊老”“敬老”良好风气。针对社会大众对精神赡养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政府应面向社会大众,广泛开展正确赡养观念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民众树立精神赡养的意识。对“孝老”“敬老”优秀模范家庭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以此形成良好的风气。同时发挥乡土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不尽精神赡养义务的赡养人进行道德谴责。以X村为例,可以借助一年一度的李花节或者年末的篝火晚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和模范家庭表彰活动,在当地树立典范,从而为提升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水平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政府积极创建支持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政策环境。一方面,实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学生回乡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对回乡创业的务工人员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提供资金支持、适当放宽一些政策门槛,借此吸引更多青年可以在家发展,还可以照料家中老人,使农村老人不再“空巢”。另一方面,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基础,完善养老保障相关的政策体系。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开展有关老年人赡养的政策建设工作,提供物质帮扶,使政策能够真正“为老所用”。
五、结语
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是老人主体性失能、家庭资本衰落、社区服务效能不足、社会资本微弱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挖掘空巢老人家庭内部的资源,提高家庭成员代内与代际间的精神支持功能,实现家庭内部的增能,从而为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提供内生动力。同时,需要挖掘家庭外部资源(友邻、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互助网络,为空巢老人获取精神慰藉提供支持。通过社会支持各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内外联动,共同增能,推动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工作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