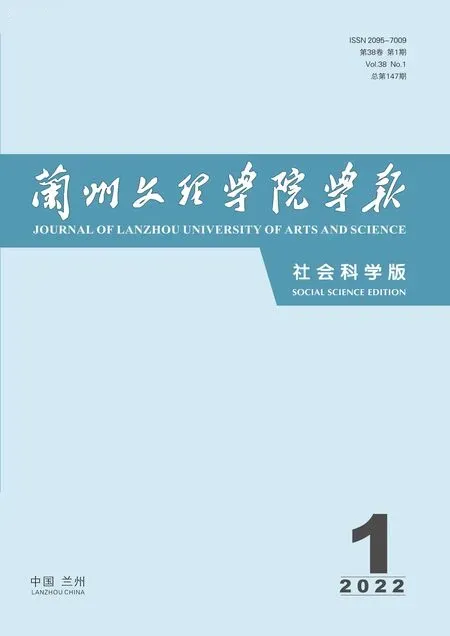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松鸣岩花儿探源
徐 凤
(兰州文理学院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花儿,又称“少年”,因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从流传的区域来说,花儿是一种跨省区、跨国度的民间音乐艺术,流传在我国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和中亚一带;从传唱的民族来看,它是一种多民族民歌,流传在汉、回、藏、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蒙古等多个民族中,其流传地域南起甘肃省宕昌县,北抵宁夏贺兰山,西自青海日月山,东接六盘山,外加两个“飞地”(东部天山下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和西部天山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聚居区)[1],约40个县(区、市),近20万平方公里,其流传时间之久、流布区域之广、地域流派之多,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中国民歌史上一支非常艳丽的花朵,学界对其起源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如下观点:《诗经》说,代表学者有黄荣恩、赵存禄、李文实等;西晋说,代表学者是包孝祖;唐代说,代表学者是张亚雄;元代说,代表学者有孙殊青、刘凯;明代说,代表学者有顾颉刚、柯杨、宋志贤、封尘等;藏风说,代表学者有张亚雄、王沛等;《阿干歌》说,代表学者有赵仁魁、包孝祖等;民族融合说,代表学者有张亚雄、王沛、郭正清等。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探究了花儿的起源,为进一步认识花儿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学术依据,但是不可否认,这一课题还有继续探究的空间。
通常情况下,学界把花儿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体系。比较而言,河州花儿曲令多(目前记录出来的曲令有150多首)、传唱民族多、流布区域广;洮岷花儿曲令少、传唱民族少、流布区域小,尤其是它们曲令调风差别非常大,所以探究其起源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区别对待,本文旨在探究河州花儿的代表松鸣岩花儿的起源问题。
柯杨教授说:“要研究花儿,首先应当考证花儿的作者及演唱者——洮、岷、河、湟一带汉、回等族人民的来历。如果不对这一地区之所以形成多民族交叉聚居的历史原因来一番探讨,恐怕就无法真正了解多民族人民用汉语所创造的独特民歌——花儿的来源。”[2]这一观点有其深刻的道理。和政县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县人口约20.81万,有汉、回、土、藏、东乡、保安、撒拉、蒙古等多个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融合过程,对花儿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秦汉时期古羌人民歌是花儿形成的母体
据史料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和政一带为羌戎之地。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阔、影响深远的大部族,古羌人特别喜爱音乐,也发明了多种乐器,广受民众喜爱的羌笛就是其中的一件。早期的羌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作了民歌,演唱时以羌笛伴奏,音调高亢、粗犷、嘹亮,他们或用来缓解生产时的疲劳,或传达对恋人的爱慕之情,或宣泄心中的不快,且情歌居多,自古就留下了“歌舞不停,酒不休”、“沙朗不歇,羌歌不断,月亮不落,星星不睡”的音乐盛况,至今还有酒歌、节日歌、民俗歌、婚嫁歌、仪式歌、劳动歌、沙朗歌等多种民歌形式。
早在秦王朝刚刚建立之初,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不断入境掠夺中原人民的财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朝廷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奔西北伐匈奴、修长城、设郡县,并“徙罪人以居之”,把中原少数汉人迁入了古河州。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羌人常常威胁中原,汉廷又迁关中汉人到古河州充实边塞。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义渠安国率兵进攻羌人部落,激起羌人强烈反抗,义渠安国败回令居(今永登西北)。同年四月,汉宣帝派赵充国领兵击羌。赵充国为天水人,深知羌情,他先集中兵力打击掀起事端的先零羌,后招抚其它部族,为稳定湟水流域的羌族社会,他留下步兵屯田,使河湟一带的汉族人口大大增加,这里的农业生产也得以迅速发展,从此古河州成了羌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地区,随之羌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兴盛起来,羌人嘹亮优美的民歌曲调被汉人模仿传唱,汉人丰富流畅的语言也被羌人引入了他们的演唱。
关于羌族民歌与花儿之间的联系,民族音乐学者杜亚雄认为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在调式、音调、旋律等方面有同源关系,两者均继承了古代羌族音乐的传统[3];年轻学者朱婷通过分析自己收集的1000余首羌族民歌和200余首西北花儿,认为羌族民歌与花儿在音乐形态(音阶调式、节奏节拍、旋律手法、曲式结构)、歌词内容、演唱方式等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4]。尤其是朱婷,她在研究中所列举的花儿代表曲令《河州大令》《二梅花令》《尕妹妹令》《二啦啦令》《水红花令》《山丹花令》《三闪直令》等都是松鸣岩花儿的代表曲令,从这个角度来说,羌族民歌就是松鸣岩花儿的母体。
另外,清道光年间河州诗人张和在《松鸣叠翠》一诗中云:“叠嶂层峦看不明,万松积翠锁峥嵘。楼台偶露林间影,风雨时听树杪声。羌笛遥传边曲古,雪山寒接暮云横。登临应有孙登啸,半岭斜阳鸾凤鸣”,其中的“羌笛”实为当地的“咪咪”(或“筚筚”)。咪咪用细毛竹做成,长约15厘米,竹身钻有4个发音孔,一端装有用柳枝或白杨、毛刺、麦秆等嫩皮做成的哨子。当地人说咪咪原为单管吹奏,后来模仿羌笛改为双管。咪咪与花儿相伴相生,长期共存,均为五声音阶,2009年和政“咪咪”被列入临夏回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笛是我国古老的气鸣乐器,已有2000多年历史,流行在四川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居住地。羌笛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竹节长、管身较细,双管并排用线缠绕连结在一起,全长13-19厘米,管口直径2厘米左右,笛管上端装有4厘米长的竹制吹嘴。据史料记载,西汉前羌笛上有四个孔,公元1世纪由京房加了一个高音按孔成了五孔,东汉马融在《长笛赋》中就有“近世双笛从羌起”的记载。据史料记载,四川阿坝州羌族的先祖在东汉时期就生活在甘肃古河州,由此足以说明,和政“咪咪”与羌笛同根同源,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羌族音乐与花儿的密切关系。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和匈奴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鲜卑族原为东胡的一支,属于游牧民族。西汉时,因匈奴势力强大,鲜卑族被阻隔在辽东塞外。东汉时,匈奴转衰,鲜卑族自塞南渐居漠北。东汉末年,他们经河西散居于甘、青、宁部分地区。从晋明帝太宁元年到西秦永弘元年,约百年时间里河州一带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鲜卑、匈奴、羯氐诸族同羌族、汉族形成空前复杂的政治局面,这既是河州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杂居时期,也是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
宋元嘉八年(431),夏灭西秦,吐谷浑灭夏,西秦和夏的治地尽为吐谷浑所占,至此吐谷浑统治地区东西约3000里,囊括今甘、青、宁全部地区,吐谷浑进入鼎盛时期。隋大业五年(609),炀帝率军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唐龙朔三年(663)兴起于西藏的又一个游牧民族吐蕃攻打吐谷浑,吐谷浑败降,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和王后弘化逃到凉州,吐蕃尽占吐谷浑领地,吐谷浑灭亡。从建国到败亡,吐谷浑在甘青宁统治长达350年。
《魏书》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涉归之存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5]吐谷浑毅然率部沿着阴山山脉向西而行,到达甘肃后在今兰州附近过黄河在临洮北界白兰镇立足,后来逐渐扩大地盘,占有今临夏、夏河、川西松潘及青海南部地区。“阿干”在鲜卑语里是“哥哥”的意思,《阿干歌》事件说明当时鲜卑族音乐已经相当成熟。据说,《阿干歌》西传后影响很大,白兰镇因此被改为“阿干镇”。虽然《阿干歌》原歌已经失传,但清乾隆年间陇上诗人吴镇根据传闻和史料补写了《阿干歌》,清人李霁园评价其“十分朴挚,声泪迸,当有意摹古者难能。”因此,有学者认为传统花儿充满忧伤、沉痛,如泣如诉的哭腔和它高亢、粗犷、婉转、悠长而又尾音急转直下的基调和主旋律与当年传唱在西北高原上的《阿干歌》一脉相承[6]。至此,鲜卑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就可见一斑。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男子从小就练习骑射,他们平日放牧牲畜,一遇战争即刻投入战斗,生存和战斗能力都很强,经常向中原发动掠夺性战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兵驱赶。西汉时期,武帝也先后多次派大将征讨,战败的匈奴大量内迁,他们散居于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南北朝时期慢慢活跃起来,先后建立了前赵、北凉、夏三个政权。北魏泰常六年(421),北凉王沮渠蒙逊攻灭西凉,旋据西平,“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北魏太延五年(439)九月,魏主拓拔焘亲自率兵攻打北凉,北凉国亡,失散的匈奴人少部分融入鲜卑,大部分融入汉族。
匈奴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民族,《后汉书》中记载了一首《匈奴歌》,其歌词几乎妇孺皆知:“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四字,却生动地表达了匈奴人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和亡国失地的悲愤之情。既然匈奴歌能在河西唱,也就能在河州唱,其对河州花儿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匈奴歌》中的哀婉之调与河州花儿有同工异曲之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与松鸣岩花儿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唐宋时期吐蕃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吐蕃,是生息于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唐贞观十三年(638),吐蕃赞善松赞干布向唐求娶公主被拒后,发兵北上攻入今宁夏北部和甘肃南部的吐谷浑及党项境内。高宗显庆五年(660),吐蕃继续攻打吐谷浑,攻占了青海大部分地区,其势力对唐朝造成了极大威胁,同年唐高宗派薛仁贵、郭子仪率兵10万攻打吐蕃,大非川一战唐军失利。仪凤元年(676),吐蕃军进入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同仁、化隆西一带)、河(今临夏及青海民和、循化一带)、芳(今迭部)诸州,征服了这里的汉、羌、鲜卑等民族,并将许多吐蕃部落迁入这些地方。神龙二年(706),唐蕃会盟。开元二十二年(734),唐蕃以赤岭为界,并在甘松岭(今四川松潘镇)互市。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原驻守在洮东的防御吐蕃的哥舒翰部15万大军被调入陕西潼关平乱,吐蕃趁机攻唐,于至德二年(757)攻陷鄯、武(今武都)、叠(今迭部)、宕(今舟曲)诸地。宝应元年(762),吐蕃攻陷秦(今天水)、渭(今陇西东南)、洮(今临潭)、成(今礼县南)诸地。定应二年(763),吐蕃攻陷河(今临夏东北)、兰(今皋兰)、岷(今岷县)、廓、临(临洮)、原(今宁夏固原)等地,基本将原吐谷浑的辖地尽纳吐蕃统治范围,直到大中五年(851)河西张议潮收复河陇,吐蕃统治古河州近200年。在这一段时间,吐蕃实行严厉的同化政策,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如汉人、羌人、鲜卑人等)都要说蕃语、穿蕃服、吃蕃食、从事放牧,即使汉人之间偷偷说汉语,也习惯按蕃人的语调说,久而久之在吐蕃统治区内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汉语方言,即宾语在前、主谓语在后,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语言,这就是今天的河州话。
吐蕃政权被瓦解之后,除少数贵族退回西藏外,大部分部落留居甘青宁地区,并在宋代建立了藏族唃厮啰政权。唃厮啰是吐蕃赞普的后裔,受到甘青宁藏族的拥戴,到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聚众数十万人,在河、洮、湟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地方封建政权,所辖区域“在黄河之曲,直西成都数千里,占河、湟间二千余里”[7],由于它一直臣服于宋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宋治平二年(1065),唃厮啰死。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宋朝派王韶将军发动“熙河之役”,收复熙(今临洮)、河、湟、岷、宕(今宕昌)、迭(今迭部)、亹(今青海门源)等地,唃厮啰政权转移至以青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湟水流域,结束了吐蕃对甘肃境内河湟一带的统治。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藏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民族,藏文文献记载,古代藏族人民的交流常用民歌来表达。今天,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藏族人民悠扬的歌声,能看到他们拉起手、踢起腿翩翩起舞的场景。在藏族民歌中,情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多为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歌声,这种声音在底层劳动人民和上层统治阶级中都能听到,17世纪六世达赖仓央加措的“情歌”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作者是宗教领袖,但他敢于突破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写出人的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向往,不但思想内容是积极进步的,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仓央嘉措情歌》多取比兴,直抒胸臆,结构上采取了谐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八句外,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节奏明快,语言通俗易唱,其中多取比兴和每首四句的特点就与松鸣岩花儿相一致。
关于藏族民歌对花儿的影响,已被多个学者所关注,如《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说:花儿“这种山歌,名曰‘花儿’,亦曰‘少年’……歌唱近于藏人的风格,以高而长的音调为其特色”[8];花儿研究者张亚雄说:“所谓‘花儿’者,实际上等于汉语的藏歌,是接近蒙、藏部落所开创,仿藏歌音节,制汉语山歌”[2]100,另有谈士杰[9]、陶柯[10]、刘凯[11]等学者都撰文阐述了藏族民歌对花儿的影响。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藏族民歌与花儿有如下相似之处:音调相似,都高亢、响亮、悠长,有震颤;结构大体相同,河州花儿多由四句构成,尽管句式不整齐,但一、三句结构对称,二、四句结构对称,奇句每句四个节奏,偶句每句三个节奏,而藏族谐体民歌也多为四句,其中一、三句对称,二、四句对称,只是节奏比花儿更自由一些;比兴手法相同,清初临洮诗人吴镇有“花儿饶比兴,藏女亦风流”的诗句,河州花儿几乎每首都用比兴,而藏族民歌也擅长比兴;表情达意都直抒胸臆,且情歌居多;语法上都采用藏语语法。由此可见,藏族民歌与花儿之间的确存在密切关系。
四、元明时期蒙古族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南宋开禧元年(1205),成吉思汗第一次率兵攻打西夏,宝庆三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病故于六盘山清水县(今清水县),临终前遗言秘不发丧以待西夏国主献城投降,一个月后西夏国主南平王投降,西夏灭亡,西至敦煌、东到黄河两岸的西夏故地尽为蒙古军所占。南宋绍定二年(1229),窝阔台继承汗位开始伐金,蒙古军先后攻破临洮、洮州(今临潭县)及西宁等府州,最后攻破甘青交界的积石州,唃厮啰政权归顺蒙古军。宋端平元年(1234)正月初九,金哀宗传位于宗室完颜承麟,初十宋军先破蔡州南门,随后蒙古军入城,金哀宗自缢身亡,完颜承麟为蒙古军所杀,金朝灭亡,至此西夏、金朝、唃厮啰政权分立割据的甘青宁地区统一于蒙古政权。南宋景定元年(1260)三月二十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北)即汗位,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十八日,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发布大元诏,标志元朝建立。南宋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蒙古军的猛烈进攻下,宋军崩溃,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投海身亡,南宋彻底灭亡,忽必烈统一全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置甘肃行省,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今甘肃省所辖的东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分属于陕西行省和宣政院所属的河州路、脱思麻路管辖,其中河州隶属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许多蒙古族部落迁入甘青宁地区放牧,有花儿唱道:
阴山阳山是倒对山,鞑子占的是草山。尕妹出来门前站,好像是才开的牡丹[8]189。
蒙古部落并非只有蒙古族人,其构成比较复杂。早在宋嘉定十一年(1218),成吉思汗派往西域的商队在花刺子模被守将所杀,为了报仇成吉思汗于次年亲率蒙古军队西征。随着蒙古军的进攻,将俘获的工匠和青壮年编入“西域签军”和“各色技术营”,因这些人有着西域种族特征,史书称“西域色目人”。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大明,建元洪武。同年八月,明军逼至通州,元顺帝带后妃、太子及朝臣百官弃大都城(今北京市)北走,元朝宣告覆灭。北走的元顺帝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境内)重建王廷,史称北元。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大将邓愈攻克河州,明太祖赐原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锁南普何姓,设河州卫。明朝政府规定:“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婚嫁”[7],其目的是加强民族同化减少民族矛盾,从而形成了甘青宁地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也奠定了甘肃现有民族的基本格局。
蒙古族也是一个自古就擅长歌舞的民族,其民歌不仅数量多,形式也非常多样。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固步自封的,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尤其是身处多民族聚居之地时,其文化融合就更为明显,花儿研究者牙含章、张亚雄、郭正清就认为蒙古族民歌与花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较二者,它们的相似之处主要有:
(1)结构相似
下面是两首蒙古族民歌歌词:
威风矫健的小红马哟,结队行军骑上它哟。今夜宿营莫沉睡哟,清早日出齐出发哟[12]。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13]!
下面是两首松鸣岩花儿歌词:
黄河沿上牛吃水,牛鼻圈吊给者水哩;端起个饭碗想起你,面叶儿捞不到嘴哩[14]。
太子山上的松柏树,四季里长青者哩;双脚踏的是五彩路,越走时越宽敞哩[15]。
可以看出,不管是蒙古族民歌还是花儿,它们的歌词都是每首四句,两句为一段,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抒情,只是蒙古族民歌多用形容词,而花儿是直接写景或抒情,字数比蒙古族民歌少。
(2)曲调都以高亢悠扬为特点。
(3)内容都非常丰富,既有赞美山川河流的,又有歌颂爱情的;既有控诉剥削阶级的,又有歌颂劳动人民的;既有赞美英雄的,又有诅咒恶霸的;既有描绘美好风光的,又有倾诉相思之苦的,几乎是无事不唱、无人不唱、无情不唱。
明代中叶时,花儿已经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传唱的民间音乐艺术,歌词中经常出现的“十三省”(如“十三省的家什找完了,找不见菊花的碗了;清茶哈熬成个牛血了,茶叶哈滚成个纸了;双手拉端上者不接了,阿塔些得罪下你了。”[16])就被多位学者认为是明代花儿的印记。在目前整理出来的花儿曲令中,“汉族花儿常引用《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包公案》《杨家将》等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作为起兴的内容”[17],保安族有《保安令》,东乡族有《东乡令》,撒拉族有《撒拉令》,土族有《土族令》,回族花儿歌词中多穿插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8],藏族花儿歌词中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古藏语倒装句。
综上所述,花儿是多民族民歌融合的产物,具体来说,羌族民歌是其母体,古鲜卑人民歌、匈奴人民歌、吐蕃人民歌和蒙古族民歌都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它是多民族民歌联姻的“混血儿”,正因为这样,花儿才既有忧伤凄婉之风,又有欢快明朗之调,才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广泛流传。如果要从时间上做一界定的话,那么秦汉时期是花儿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至元代是其发展期,明代是其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