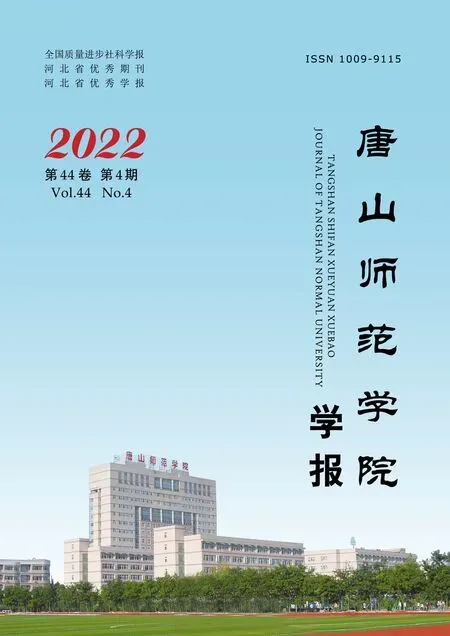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关系辨析
廖华力
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关系辨析
廖华力
(南宁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晨报》副刊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过辉煌成绩。这是包括主编李大钊和鲁迅等众多撰稿人共谋合力的结果。作为五四新文化战线的“战友”,李大钊在大刀阔斧改革《晨报》副刊的同时,成功接引鲁迅登堂入室地“走进”《晨报》副刊,并迎来鲁迅文学生涯中一段非常难得的“黄金时期”。李大钊与鲁迅相互成全的互动关系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晨报》副刊;李大钊;鲁迅;文学场;相互成全
一、《晨报》副刊简史与李大钊的选择
1918年12月1日创刊的《晨报》副刊被历史地认定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首。它在第七版(或第五版)刊登文学艺术类作品,称为《晨报》“学术栏”或“学术版”;1921年10月12日《晨报》“学术版”改出四版单张,定名为《晨报副镌》和《晨报附刊》,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1925年4月1日《晨报副镌》又更名为《晨报副刊》,直至1928年6月停刊。本文使用“《晨报》副刊”时,特指1919年春至1920年6月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学术版”。
《晨报》副刊在五四时期成为鲁迅开展文学活动的一块非常难得的“场域”,但它并不是天生就成为鲁迅的“文学活动场域”,它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系机关刊物《晨报》的副刊,它最开始是外在于鲁迅而独立发展的。只有在研究系内部,《晨报》主编蒲伯英、《晨报》的精神领袖梁启超等主要人物积极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晨报》副刊选择一条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道路,并奠定《晨报》副刊相对独立批判与宽容自由精神空间的情况下,鲁迅选择“进入”并改造《晨报》副刊,成为他的“文学活动场域”才拥有理论的可能性。同时,随着《新青年》阵营的逐渐分化与解体,仍然高举思想启蒙旗帜,渴望坚守思想启蒙阵地的鲁迅,不得不面临重新寻找与开辟“文学活动场域”的无奈命运。作为新文化运动“战友”的李大钊,由于自身具有的个人特质与先天资源优势,被历史幸运地选中充任《晨报》副刊主编。他对于《晨报》副刊的苦心经营与改革创新,成功接引鲁迅登堂入室地“走进”《晨报》副刊。鲁迅与《晨报》副刊由此开启一段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辉煌历史。
早在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就参与创刊作为《晨报》前身的《晨钟报》,并担任过20多天的编辑主任[1]。《晨钟报》1918年9月被段祺瑞政府勒令查封。1918年12月1日《晨钟报》复刊,改名《晨报》。蒲伯英任总编辑。李大钊由于从前就在《晨钟报》担任编辑主任,所以蒲伯英再次聘请他协助编辑《晨报》,主持《晨报》“学术版”。
1919年左右的李大钊,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会成员兼轮值主编,同时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等学科的教授,《新潮》社与《国民杂志》社的顾问与指导教师,而且已经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享有相当的威望与影响力。但是,相较于蒲伯英、梁启超、《晨报》社长刘崇佑等人,李大钊的政治资历与社会影响力毕竟尚浅,在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权威也是相形见绌。章士钊曾说“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2]。因此,在蒲伯英出任总编辑的情况下,李大钊对《晨报》的言论指向与根本性质的掌控,就会受到极大局限与规约。接引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源头活水的重要园地只能策略性投注到《晨报》副刊,而不是“正刊”。
为什么李大钊愿意屈就《晨报》“学术版”,在一向边缘化的“副刊”闹腾?这是不是意味着李大钊甘心大材小用,冲着“学术版”的“安全”而来,怕闹出麻烦?答案是否定的。这次李大钊本着“学术版”而来,有其更远大、更深沉的抱负。报纸副刊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但是报纸副刊作为肥沃的文化园地,并没有生长出茂盛的精神庄稼。《晨报》“学术版”相对影响巨大的《晨报》而言,尤为如此。这是十分可惜的。李大钊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抓住再次进入《晨报》的有利时机,迅速成为“学术版”的主编。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攻城掠地的时候,高瞻远瞩,把目光转移到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移,为新文化运动开拓出全新的渠道和平台,增添了强劲的薪火。同时也体现出李大钊卓越的战略眼光。
二、李大钊改革后的《晨报》副刊
李大钊主编《晨报》“学术版”后,“学术版”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先锋气息非常浓厚。
第一,李大钊协助《晨报》“学术版”增设“自由论坛”栏。1919年1月31日《晨报》刊登的“启事”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它为后来《晨报》副刊重大成就的取得立下开创之功。
首先,它预示《晨报》“学术版”即将迎来旧有面貌的巨大改变。《晨报》创刊时“学术版”沿袭《晨钟报》“学术栏”的旧有风格,主要栏目设置有:专载、文苑、小说等,内容虽然没有陷入当时市场一般“副刊”的黄色低级趣味,但是作为消闲读物的性质,以及反映旧派文人名士趣味的特征,使它仍未脱离旧式报纸副刊的窠臼。自由论坛栏目的创设立即使这一版变成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
其次,它树立《晨报》“学术版”开放办刊的良好形象与姿态。作为当时在社会政治形象欠佳、社会声誉为人诟病的研究系机关刊物的《晨报》,吸收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之一的李大钊参与编辑工作,本身就很好地表明《晨报》办刊姿态的重大改变。在旧派知识分子看来它依然是旧有的传统色彩占据主导,却能够接受一定新兴分子的介入;在新派知识分子看来它却充满新鲜的时代气息,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所占据,它为改变新派知识分子对《晨报》旧有的不良印象,笼络新、旧两派知识分子共同在这一传播平台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创造条件。“‘欢迎社外投稿’,‘无论文言或白话皆所欢迎’等措辞与态度,也是《晨报》主动打破自身原有的封闭状态,在更加开放的办刊方针指导下,构建内容质量过硬、作者群体多样化、受众满意度提升的一种表示与愿景。”[3]
再次,它塑造《晨报》“学术版”精英化与高尚化的特色。从此以后“学术版”的深度与高度一直维持在极高的水平。这些栏目的创设、改良,对建构“学术版”严肃而高尚的刊物面貌与传媒形象至为重要。
“自由论坛”增设后经常刊发论述新思潮及评论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文章。在五四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夜,作为给予革命青年指导方向的重要体现之一,李大钊适时反映并回应新、旧思潮的激战,亦即民主与科学同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与交锋。在1919年2、3月间,正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攻击《新青年》—北大派最为猛烈的时候,李大钊适时地把文化斗争的阵地扩大到《晨报》“学术版”的文化空间与版面空间。在3月4、5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进一步揭发顽固守旧人群妄想铲除思想萌芽新机的图谋。他用俄国的实例警告守旧派说:“新的思潮和新的革命精神,是任何暴政都摧残不了的。……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4]无情的揭露与警告,给予守旧反动势力以迎头痛击,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传播保驾护航。
第二,李大钊协助《晨报》“学术版”开辟“劳动节专号”与“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表明劳动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李大钊在1919年2月14、15日的“学术版”发表《劳动教育问题》,抨击现存“不良社会制度”,指出“一个人汗血滴滴的终日劳作……牛马一般”[5]291,“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同时指出:“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经渐渐觉醒。”关心劳动问题、社会教育的人们一定要注意“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5]293。李大钊真诚地相信俄国十月革命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是人类社会的彻底改革。在李大钊的强烈影响与帮助下,1919年5月1日《晨报》“学术版”刊出“劳动节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李大钊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扼要说明“五一节”的由来,提道:“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6]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此。1919年5月5日,“学术版”开始出现“马克思研究”专栏,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一回的诞生纪念日,兹篇系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简洁明瞭,颇有价值。”[6]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术版”频繁刊载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一系列马克思研究专论,包括马克思生平与著作介绍。“劳动神圣”“社会改造”等口号与思想一时成为新闻舆论宣传的中心议题。“学术版”积极而富有革命性的思想文化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重大作用。而李大钊正是这些举措与效果的主导者,具有深厚研究系背景的《晨报》及其副刊也因此产生令人诧异的先进性与革命性。
第三,李大钊把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步实绩及时引入《晨报》“学术版”,使“学术版”成为传播与实验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晨报》副刊日后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在北方的堡垒”[7]奠定厚重的基石,同时开启《晨报》副刊作为鲁迅新的“文学活动场域”的序幕。
三、主编《晨报》副刊的李大钊与鲁迅的关系
1919年3月11日至14日,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学术版”从《新青年》第4卷第5号转载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为鲁迅与《晨报》副刊发生关系的开始。
《狂人日记》因深刻暴露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弊害的主题思想,“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8]等卓异风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主题深刻,形式特别,影响深远,在东方文学大地破土而出,拔地而起,宣告中国一代新文学的诞生,揭开中国文学史新的序章。阿英在1930年曾说过:“《狂人日记》的发表,正不亚于对当时的封建势力投下了一颗极猛烈的炸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于封建势力抗战最初的以及最后的宣言。”[9]190阿英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徐中玉在《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意义时也说:“《狂人日记》不但是鲁迅用新的特别格式进行创作的第一次试验,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有机地吸取外国近代文学形式的最初试验。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而且它造就成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树立一个极好的榜样,为后来的创作开辟一条康庄大道。”[9]192李希凡在《〈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中指出:“《狂人日记》可以称得起是‘五四’文化革命运动最鲜明的反封建宣言书。……《狂人日记》是《呐喊》《彷徨》反封建主题的纲领和序言。”[9]194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作品,研究者过去仅把目光盯在首发刊物《新青年》上,把《狂人日记》与《新青年》紧密联结在一起,却很少注意《晨报》“学术版”转载的《狂人日记》。从鲁迅作品的传播流程考量,人们往往习惯关注源头,而不甚在意传播流程。《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影响与它在《晨报》“学术版”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新青年》是月刊、精英杂志,发行量有限,而《晨报》是日刊、大众传媒,从传播范围看,《晨报》“学术版”的读者覆盖面要比《新青年》大得多。有了《晨报》“学术版”的拓展传播,《狂人日记》才能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篇白话小说。大凡论述鲁迅小说的论著,几乎没有不论及《狂人日记》的。研究者对鲁迅小说的评论之多,大约除了《阿Q正传》,就属《狂人日记》。但是,《狂人日记》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时,虽然在部分知识青年中产生强烈影响,却“未曾能邀得国粹家之一斥”[10]。像《狂人日记》这样的反封建杰作的出现,按理应该像丢在封建大家庭后院的一颗重磅炸弹,必定引起身心发霉的封建卫道者“惊恐万状”才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就连作为作者的鲁迅也不得不无奈地在1918年8月20日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感慨道:《狂人日记》是“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0]。从信中不难看出鲁迅当时的寂寞心境。“鲁迅提倡读史,目的还是为了现在。因为现在的情形与历史上某些时候非常相似。”[11]茅盾后来曾指出:“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未曾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显著的风波。”[8]这种类似刀子扎在身上而几无反应的脱出常轨现象,其原因恐怕不单是《新青年》“无句不怪,有字皆狂”,也还部分因为国粹家的麻木不仁。林纾所谓让其“自生自灭可耳”的夜郎自大,严复“贾政”式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其实是精神极度麻木的僵尸的乐观。“前无古人”的作品就这样“悄悄地闪了过去”,岂不是太可惜。因此,借着《晨报》“学术版”大刀阔斧改革的东风以及新、旧思潮正在热烈交战的历史契机,作为对封建顽固势力集体示威的重要武器,李大钊又一次把《狂人日记》这颗“炸弹”引爆在《晨报》“学术版”,知识青年读者对鲁迅小说的最初反响随后逐渐增多起来。
1919年12月1日,《晨报》刊出《周年纪念增刊》,鲁迅应邀发表《一件小事》。作为鲁迅所有33篇小说中篇幅最为短小的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与李大钊和《晨报》有着莫大的关联。
首先,它是李大钊约稿的结果。研究系多年的政治作为与意欲,身为教育部佥事兼科长的鲁迅是有所耳闻目睹的,他对研究系的性质也有清醒的判断。他清楚地知道“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作为作者如果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还有什么话可说呢”[13]。后来他主编《语丝》周刊时还曾说过:“给《晨报副刊》投稿的人,我这里是不登的。”[12]这都说明研究系及其传播媒介的所作所为曾经给鲁迅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如果不是作为《新青年》同人的李大钊在主持“学术版”,向鲁迅约稿,鲁迅的作品要想破天荒地在《晨报》出现,那是极难想象的。
其次,小说的主题应和当时“劳工神圣”的口号。这是鲁迅小说唯一一篇以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品,这在一向主要以刻画农民与知识分子见长的鲁迅来说,极为罕见,也是极为难得的。当时“劳工神圣”的口号在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风行一时,这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革命潮流影响下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崭新认识。在五四运动以前,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理解还是比较抽象模糊的。他们说的“劳工”并不是严格地特指工人阶级,而是包括各个阶级、知识分子在内。在一向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传统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李大钊即这一口号的积极鼓吹者与支持者。《晨报》也早在1919年5月1日由于李大钊的热情帮助而率先刊出“劳动节纪念”专号,积极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鲁迅应李大钊约稿而创作的短篇小说,即通过一个人力车夫表现劳动人民高贵的精神品质。然而鲁迅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人一样高喊空洞的口号与陈词滥调,而是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描写了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
再次,《晨报》的传媒特性规约小说的艺术特色。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认为:“《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9]335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亦说《一件小事》:“因为故事太简单……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9]335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却说:“《一件小事》,实在说,是简劲而有寓意的素写,是一篇结构美丽的象征诗。”[9]336他们都一致指向小说篇幅过于短小,结构过于简单的艺术特色。
为什么会出现既是小说,又是随笔,甚至是杂文、诗歌的体裁界定难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晨报》的大众传媒特性。《晨报》是日刊,篇幅有限,这对小说字数的多寡提出相应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体现鲁迅高超的技艺?鲁迅并没有孤立描写劳动人民的品质,而是以极简省的笔墨,通过抒情的方法反映故事的发生环境,这在文章开头与结尾都得以深刻地体现出来。鲁迅还把“我”与车夫的思想矛盾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重要线索,从中刻画两个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与人物对话的应用,鲁迅总是力求精炼,严格服从主题思想的特殊需要。例如,他每次写到“风”,只不过短短的一句话,但或烘托人物性格,或衬托人物形象,或给人物的心理活动创作一个适宜的背景环境,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键与补充,都是如此的自然而且丝丝入扣。鲁迅真正实现了短篇小说“借一斑而窥全豹”的创作目的。
鲁迅与李大钊最初在《新青年》的集会上认识,陈独秀是牵线人,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同人。李大钊给鲁迅的初次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13]538。“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13]538但是,即使是《新青年》时代,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但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鲁迅与李大钊的交往还不是太过紧密,鲁迅想法是“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13]540。因此,李大钊主编《晨报》“学术版”时期,鲁迅与《晨报》“学术版”的互动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除了答应李大钊的邀请发表文章外,再无更多的关联。李大钊的主要贡献是把鲁迅的名字与文学作品创造性地拓展到《晨报》“学术版”的舆论宣传阵地,并成功地改革《晨报》“学术版”,为鲁迅在孙伏园主编时期真正昂首阔步地“进入”与建构《晨报》副刊作为重要的“文学活动场域”开辟道路。
[1] 李大钊.新现象[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7.
[2] 章士钊.序[M]//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 1951:1.
[3] 廖华力.蒲殿俊与《晨报》副刊[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06-112.
[4]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3.
[5]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李大钊.“五一节”(May Day)杂感[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5.
[7]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69.
[8] 茅盾.读《呐喊》[M]//查国华,杨美兰,编.茅盾论鲁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3.
[9] 李煜昆.鲁迅小说研究述评[M].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
[10] 鲁迅.致许寿裳[M]//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5.
[11] 王吉鹏,韩瑞玲.鲁迅与《国民新报副刊》[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6):1-4.
[12]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M]//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8-169.
[13]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M]//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the Supplement ofEdited by Li Dazhao
LIAO Hua-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The supplement of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ideology, culture,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 of many writers including editor-in-chief Li Dazhao and Lu Xun. As a “comrade-in-arms”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Front, Li Dazhao, while radically reforming thesupplement, successfully invited Lu Xun to “enter” thesupplement, and ushered in a very rare “golden period” in Lu Xun’s literary caree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Dazhao and Lu Xun should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he supplement of; Li Dazhao; Lu Xun; literature field; mutual fulfillment
I210.6
A
1009-9115(2022)04-0017-05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4.004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FXW001),南宁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19KYQD155)
2021-09-28
2022-02-28
廖华力(1986-),男,壮族,广西凭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