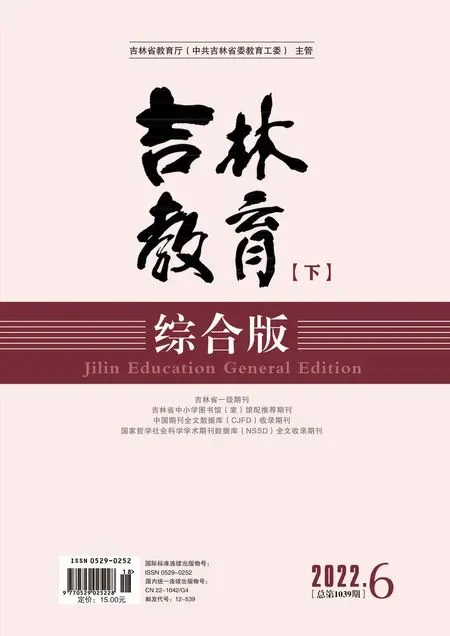窥一斑而见豹之全貌 读史传以品叙事艺术
——以《屈原列传》《苏武传》为例探究群文阅读策略
刘 玮
在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三单元的单元导语中提出“鉴赏作品的叙事艺术”,单元研习任务中也强调:“优秀的史传文学,往往围绕历史人物,选取恰切的历史事实……同时将史家对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的态度蕴含其中。”[1]在单篇文章的教学中,难以让学生直观地体会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艺术,更难体会史家曲笔。然而通过群文阅读的方式,对多篇文章进行对比、总结,既可以驱动学生增大阅读量,又能够提升思考质量,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思维发展与提升的要求。学生可以通过语言获得形象思维,并发展逻辑思维以及辩证思维。
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 中曾经消解了文学的概念,认为“文学是什么”这个概念丝毫不重要,文学和历史并无区别,因为:“既然理论本身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理论家们为什么还要劳神看他们解读的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呢?”[2]“史学家只说明一件事如何导致另一件事,说明因何发生,而不能说明为什么发生。历史解释的模式也是故事发展逻辑的原理,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与西方文学理论家的理论不同,在我们的文学理论中,不仅没有消解文学这个概念,相反地,我们将优质的史传纳入文学这一概念之中。钱钟书先生认为“古史即诗”,“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3]这一观点合理地阐释了史学和文学的共生性。史官虽秉笔直书又占有大量的实录材料,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如何选取材料编写史书,如何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则是史传作者的个人发挥空间。否则,同样记载西汉历史,司马迁和班固自应毫无区别,司马光也无须耗时十九年编纂《资治通鉴》。因此我们认为,优秀的史传是文学,对历史的解读中蕴含着史学家的匠心。
史学家在写作史传时,一大难点就是材料的缺失,这一空白部分自然也必然地需要由史学家发挥补充。例如蜀汉终其一国并无史官,因此《蜀书》粗疏。陈寿四十八岁开始编撰《三国志》,距离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首次提出三分天下的战略主张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在《隆中对》 中,只有“凡三往,乃见”有历史材料,即《出师表》 中“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二人相见之后,即“因屏人曰”,整个对话过程并无第三人在场,对话之后又并无文字记录,因此我们不难得知,所谓“三顾茅庐天下计”并非诸葛亮之计,而是陈寿在看到蜀国的立国战略之后,反推当时之计,这个计策既要与实际相符,又要能打动刘备,可以说陈寿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另外,陈寿非常注重驾驭语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相同句式形成排山倒海指点江山的气势,动词意义相同却加以变化,造就了经典句式。王勃在写作《滕王阁序》 中,“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 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俱是与陈寿一脉相承,这种从局部着眼,睥睨天下的气势也尽得陈寿之精髓。陈寿所处的年代,骈文并不是主流文学样式,陈寿如此驾驭语言自有其目的,诸葛亮未出茅庐而评说天下大势之时只有二十几岁,这种以运天下于股掌中的语言,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年轻谋士的自信和雄心。因此,他认为“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要知道,在陈寿合理虚构这段话时,事实已经证明了诸葛亮的计谋失败,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而陈寿仍然把这段有些浪漫主义的话写进《隆中对》,则体现出年轻的诸葛亮眼光独到,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浪漫和天真。陈寿为诸葛亮设计的这句对荆州地缘的评说,一方面体现诸葛亮的气势,另一方面也为蜀汉的悲剧结局蓄势,以春秋笔法,隐含对诸葛亮军事才能平平的批评。由此可见,史学家高度关注史传中的语言和修辞,做到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体现出史学家的文心。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三单元中两篇文章《屈原列传》 《苏武传》 分别选自《史记》 《汉书》。这两部著作兼有文学史学双重意义。班、马二人为后世史学著作的写作设定了范本,这个范本不仅是史传文章的文学体例,还有史官对人物的史学评价和对历史品评的态度,以及这种评价和态度的表现方法。单篇文章可以夯实学生的文言文基础,然而当我们要去探究其中共性特征时,多篇文章的比较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例如学生在只读了香菱写的前两首诗的时候,都认为香菱写得不错,而当又读完最后一首之后,便觉得高下立见。因此想对教材中的史传文学作品做深入的叙事艺术分析,则万不可僵化,满足于现成文本。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拓展篇目或者将教材中删节的文本还原至全文中,相同传主不同史学家的记录、同一母题归类、原生文本还原等诸多方式选取群文,在对比中自然发现其中的差异甚至矛盾,分析才能有的放矢,更具有针对性。用学生发现的差异和困惑,或者教师合理设计的问题,来撬动学生对史传文学的深入研究,让学生体会到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
一、通过准确剪裁史料,突出传主精神品质
《屈原列传》 节选的结尾部分几乎直接选用了楚辞《渔父》 的内容,只是删掉了《渔父》 中的最后一段渔父的语言。所以可以设置这样的问题:“从情节安排和主次人物两个角度,思考为什么司马迁要删掉《渔父》 的最后一段?”学生发现二人的对话无关对错,是以身殉道和明哲保身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屈原列传》 中,屈原感慨“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之后,只有删掉渔父的人生观表达,才能使屈原的人物语言和“遂自投汨罗以死”的行为二者联系紧密,体现出“言为心声”的特点。还有的学生发现两篇文章虽然体裁不同,但皆以主人公为题目,楚辞《渔父》 的主人公是渔父,“莞尔”的神情,“乃去,不复与言”的动作,都在刻画一个精神自由、超脱旷达的智者形象。除去以直钩钓鱼引来周文王的姜太公外,庄子笔下的渔父和楚辞中的渔父几乎同时出现,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旷达超脱、精神自由的渔父形象。而《屈原列传》 的主人公则是传主屈原,隐去《渔父》的最后一段,以屈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结尾,凸显出屈原宁折不弯的高洁品性和为国牺牲的爱国主义热情。
二、运用多种记叙手法,塑造圆形人物形象
在《苏武传》 中,班固通过卫律劝降、幽置大窖、迁于北海的情节设置,塑造了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流落敌国十九年而仍不辱汉节的英雄形象。由于课文较长,学生或多或少觉得疲惫,于是在分析了苏武形象之后,笔者安排了一段“彩蛋”,即苏武的独子苏元因参与上官桀等人谋反之事而被武帝处死后,苏武在武帝垂询时才透露自己在匈奴有一幼子,武帝命其将此子赎回的片段。读罢,学生大呼意外,原本肃穆得有些沉闷的课堂顿时活跃起来,笔者趁机问:“班固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意外,又为什么不按时间顺序叙述,要用补叙的方式将这个意外安排在返回汉朝之后?”学生马上表示,这个情节的设置非常巧妙,苏武在匈奴十九年,从生活逻辑上说,应该是千头万绪,大事小情不计其数,司马迁只选取了几件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情组织材料撰写《苏武传》,自然最能凸显出苏武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丈夫风范,然而通过结尾补叙,让我们看见苏武十九年来在匈奴生活的细节,非常真实动人,将苏武从一个扁平人物变为一个圆形人物,使得人物有血有肉,更加丰满。还有学生表示,这个情节作为补叙在全文结尾出现,前面出使匈奴、羁留匈奴和智离匈奴的情节才完整流畅,凸显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学生认为,苏武在匈奴有妻有子,却一有机会马上回归汉朝,舍弃小家奔赴国家,不仅无损于苏武的英雄形象,反倒更加突出了他一直心系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作为文章次要人物的汉武帝,在李陵的叙述中刻薄寡恩、年老智昏,然而在苏武独子死后关心苏武是否还有儿子,并允许苏武将胡汉混血儿子接回来团聚,又以此子为郎,使得汉武帝也立体化,由刻薄寡恩的帝王形象变成一个颇有人情味的老者形象。
课文的选本固然能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形象,而读过《苏武传》 的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充分尊重史实、不随意删减的同时,也是有着巨大的主观能动性的,选择记叙材料,调整叙事顺序,看似是在情节安排上下功夫,其实在传主和相关人物的形象刻画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里形式不仅和内容统一,还有助于内容的完善。
三、外显的合传安排,内隐的作者态度
教材中的书下注释已经表明《苏武传》 是附在其父苏建之后,而这篇合传中除了苏家父子,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广及其孙子李陵,为何要将这两家三代四人置于一篇传记中,学生自然能想到李陵被迫投降和苏武宁死不降的对比,进而提出李广和苏建为何放在同一篇传记中的问题。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抓住这个困惑我给学生展示苏建和李广的传记,引导学生关注二人的仕途爵位。学生对于“李广难封”早就有了了解,而战斗力、领导力远远不如李广的苏建却可以“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让学生颇感惊讶。通过对二者封侯与否章节的对比,有的学生体会到苏建作为卫青的校尉,分享卫青军功就能封侯,而李广一直战斗在胡汉交战的第一线而未能封侯,甚至是因为由李广牵制住匈奴主力,卫青才能大获全胜取得军功,二者对比体现出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有的学生认为李广不能取得战功是因为其有“飞将军”之名,一直和匈奴的主力精英部队对抗,以强克强,功劳甚大而不得军功,体现出“军功爵制”的不合理性,这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李广的命运悲剧。
《李广苏建传》 中李广难封和苏建获封二者对比,李陵降于匈奴和苏武宁死不降都可以形成对比,在这种对比之下,对于历史功业的评说,对于人物人生选择的臧否,都已经不言自明,教师不必大力渲染苏武的坚贞不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章自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对学生产生思想上的教育和熏陶。
学生在课后通过自行阅读《霍光金日磾传》,发现二者为官行事都非常小心谨慎,也都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而家族结果大不相同,霍光死后三年身死族灭,金日磾却以外族身份在汉朝获封秺侯,家族“七世内侍”。其中相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家族命运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学生在作业中反馈,发现霍家的衰亡在霍光身死之后,而霍光的审慎只止于自身;金日磾却家风甚严格,其母对其兄弟二人的教导严格,后因儿子与宫人调笑竟然手刃亲生儿子。看到二人不同的结局,学生感叹“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合传中人物的结构安排自有其用意,仅仅通过二位传主相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家族命运,就体现出其中原因,通过这种对比,学生对“春秋笔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史传文学的篇目中,当然要落实文言知识,也可以通过图表的方式对文章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教学还可以继续拓展广度和深度。依托教材文本,选择相关文本进行对比阅读和拓展阅读。文本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唯一性,无论是删减部分文本或者节选原文,不同的剪裁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通过群文对比阅读,以比较的方式提高文本分析的有效性。在我国史学历史上,史官记史,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载,更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史传文学作家,尤其是前三史的作者,往往在记录史实的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史识。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高超巧妙叙事艺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真正地“成一家之言”。通过群文阅读,探究叙事背后的艺术,使得文言文的讲授教学不仅仅止步于“文言”,由言入文,用文学的眼光审视似冷峻的史传,自然能看出史传中文学以文载道和含蓄抒情的特点,体现出史传文学审美和审智的共生性,不仅激发了学生求知求真的兴趣和热情,更启迪学生审美的能力,在提升学生阅读质量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