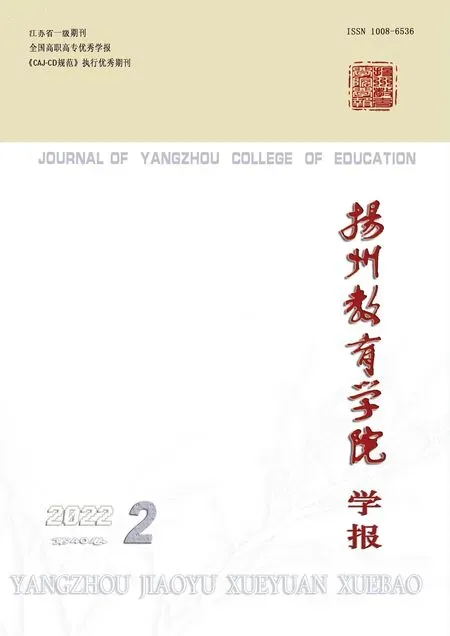论毕飞宇小说中的身体叙事
郁 果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身体不仅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肉体,还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精神灵魂。在当今消费社会的文化背景之下,身体越来越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关注的焦点。海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1]文学的问题也是如此,文学与身体密不可分,没有身体的文学只是抽象、空洞的说教,是概念的堆砌,有了身体的参与,文学才是形象、丰满的。毕飞宇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身体方面的叙事,本文着重从压抑的身体、越轨的身体、异化的身体三个方面来分析毕飞宇小说中的身体叙事。
一、压抑的身体
纵观中国历史,传统社会倡导对身体的压抑,如“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妇女裹脚缠足的封建陋习,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禁锢、压迫。中国儒家文化,一直提倡克制自己的欲望,如儒家强调的“克己复礼为仁”,儒家认为只有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有礼,才能称为“仁”。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中,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存在于复杂的伦理关系中,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身体,都要遭到排挤与唾弃。可是,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过分地压抑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欲与性欲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不管你怎样与它们进行抗争,它始终在你的心里,影响着你的行为。可是在毕飞宇的笔下,多处体现权力对身体的压迫,让人感到身体在权力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微不足道。毕飞宇小说《平原》中,下乡知青吴蔓玲因为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随口的一句“前途无量”,迷陷于权力的漩涡无法自拔,成为权力玩弄的对象。充满斗志的吴蔓玲刚到王家庄就喊出了要做乡下人不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的口号,作为村支书,吴蔓玲处处争先,看到混世魔王开始积极工作,她为了表现自己的先进性,工作得比他更积极,进行恶性竞争。明明可以吃饭,坚持不吃,明明能睡觉,坚持不睡,充分体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达到一种“非我”的状态。尽管吴蔓玲将自己比作男人,处处和男人比,和男人争,可是吴蔓玲毕竟还是女人,她也会想男人,面对情欲的焦虑和困惑,吴蔓玲无处排解,竟然将自己的宠物狗当成自己的性幻想对象,自慰并高潮。面对灵肉冲突,吴蔓玲将自己的情欲发泄到动物身上来自我满足。作者用犀利、冷酷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情欲迷狂的身体。吴蔓玲作为妇女解放的典范,用实际行动向男权社会发起抗争,她成功地掌握了权力,可是作为女人她却是失败的,她始终没能体会到被爱的滋味。毕飞宇通过塑造吴蔓玲这个人物形象向我们传递出:在男权社会的女性虽然女权意识觉醒,但是终究敌不过女性与生俱来需要被呵护被爱的天性。
《哺乳期的女人》作为毕飞宇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了没有吃过母乳的留守儿童旺旺看见年轻母亲惠嫂给孩子喂奶,抑制不住内心对母乳的好奇、渴望,咬了惠嫂的乳房,由此遭到村里人的非议和爷爷的打骂的故事。小说中的旺旺虽然表面看上去衣食无忧,顿顿有蛋有肉,长得结结实实,可是七岁的旺旺从来没有吃过母乳。父母为了赚钱离家去跑运输,每年只有短暂的相聚时间。父母对于旺旺而言只是汇款单上那冰冷的一行字,在物质方面旺旺是富足的,可是在精神和情感方面,旺旺是贫乏的。虽然每天都能吃一包旺旺饼干,可是这也弥补不了父母之爱缺失的遗憾,工业化生产的营养品始终没法取代自然、安全、温暖的母乳。因此在惠嫂喂奶时,旺旺被奶香吸引,对他而言那是母亲的味道,是没有“尝”过的味道。旺旺咬惠嫂乳房是出于孩童本能对母亲、对母爱的渴望,但是这却遭到了断桥镇村民的戏谑和非议,他们一致认为旺旺耍流氓,将孩童单纯本能对母爱的渴望说成是“吃豆腐”。面对舆论的压制,旺旺的爷爷羞得无地自容,对旺旺一阵痛打,限制旺旺和惠嫂的接触。爷爷作为旺旺最亲近的人,也把他当作了“小流氓”。不管是村民还是爷爷都没能理解旺旺的行为,他们认为旺旺并不缺奶水,并不约而同地将旺旺这样的行为和性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不知道旺旺缺的是母爱的呵护和滋润。断桥镇村民残忍地将自己龌龊的思想强加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作者给镇子取名断桥镇不仅是说镇子在地理上被河水阻断,更是寓意小镇人在思想上与外面现代文明的隔断。“断桥镇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在这条水面上开始他们的人生航程的。他们不喜欢断桥镇上的石头与水的反光,一到岁数便向着远方世界蜂拥而去。断桥镇的年轻人沿着水路消逝得无影无踪,都来不及在水面上留下背影。”[2]留在断桥镇的多是一些老年人,虽然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但是思想上依然封建保守,他们以阴暗猥琐的思想揣度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简单淳朴的愿望。唯一一个真正理解旺旺的是年轻的母亲惠嫂,透过旺旺忧伤的眼睛,她看到了旺旺对母爱的渴望,以及被人误解的惶恐和委屈,这触发了惠嫂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激发了她的母性关怀,于是在一个午后,趁着爷爷午睡,惠嫂带着旺旺来到杂货铺后院要给旺旺喂奶,可是却遭到了拒绝,旺旺带着哭腔说这不是自己母亲的乳汁。旺旺幼小的心灵因为断桥镇村民的恶意揣测已经受到了伤害,他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为了符合所谓的道德准则,压抑住内心对母爱的渴望。旺旺对惠嫂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坐在门栏上看惠嫂,到躲在门缝后面看惠嫂,再到拒绝惠嫂,毕飞宇通过对旺旺前后身体动作变化的叙述,体现了旺旺对自我的压抑和逐渐关闭的心灵之门,表达了对人性险恶阴暗和人与人之间心灵隔膜的批判,以及对孩童幼小心灵遭到伤害的痛心。
二、越轨的身体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随着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女性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解放。波伏娃曾指出:“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了贞操;它多少有点公开地承认男性拥有性的自由权利,却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性行为,若未经习俗、圣典认可,对于她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种弱点。她应当捍卫自己的贞操、自己的荣誉。要是她屈从,要是她堕落,她就会遭到歧视。”[3]430在毕飞宇的小说《林红的假日》中,主人公林红是一个年轻、漂亮、事业有成的杂志社主编,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好姑娘”“好女人”。但是一天,自己的手下,文艺部的记者青果的一句:“林总,你这样活着累不累?”一语惊醒梦中人,林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累”是她对现在生活的整体评价,在内心深处林红其实早已厌倦每天繁琐、“意义重大”的事务,林红决定找个地方放纵一次,做一天“坏女人”。林红决定通过出游来放松心情。以往林红的头发都是盘着的,这次林红将头发披了下来,以往林红出门从来不化妆,这次“恶狠狠地”化了一次,林红还穿上了以往从来不敢穿的短裤和背心。毕飞宇通过林红着装打扮上的变化,暗示了林红这次彻头彻尾的改变,摘掉面具做回自己。林红释放出身体深处常年压抑的激情和欲望,和兄弟报社的张国劲来了一次刺激的“婚外恋”,林红真实地做了一次自己,逃脱社会话语的规训,遵循自己的内心。可是身体的越轨并没有给林红带来快乐,“林红的身子空掉了,脑子也空掉了,一股说不出的难受突然就把她的身躯贮满了。沉重消失了,一身的‘轻’反而让她一下子无所适从”。毕飞宇通过林红身体前后的变化意在说明,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包含了复杂的伦理、道德、文化、政治内涵,一味地追求随心所欲,最后只会适得其反,因此最后林红才会尖声叫道:“我就是喜欢这样,我就是想弄得一身脏。”[4]自始至终,林红都处在社会话语的规训之中,虽然看似通过婚外情,林红的身体得到了“释放”,可是一声尖叫将她“拉回现实”,在林红的内心深处,她难以接受那个越轨的自己,她终究没有逃出社会话语体系的牢笼。波伏娃曾经提出过“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的论断,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标上温柔、贤惠、依赖、顺从的标签,这些都是强加给女性的社会属性而非女性的自然属性,女性的自我认同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也深受父权社会男性话语的影响。毕飞宇通过身体叙事揭示肉欲与理性,自然与规训之间的矛盾。
《青衣》作为毕飞宇小说创作的转折点,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主人公筱燕秋本是青衣名角,可伴随着名气的增长,筱燕秋的心气也在增长,一次她竟然因嫉妒自己的恩师李雪芬,将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到恩师脸上,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自此陨落。二十年后,一次机缘巧合,在烟厂老板的资金资助下,筱燕秋有了重新登台的机会,可是岁月无情,年龄始终是演员无法迈过的一道坎,筱燕秋被后来居上年轻貌美的春来取代。烟厂老板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资助《奔月》剧组,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征服欲,在得到筱燕秋的身体后,老板转头就向更加年轻、漂亮的春来伸出了橄榄枝。在所有人心中,筱燕秋就是那个天宫中清高、不食人间烟火的嫦娥,可是“嫦娥”竟然为了圆自己的戏剧梦出卖身体,卑劣轻贱地去讨好老板,可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嫦娥”也不得不低下她高傲的头颅,从天宫坠入凡尘。毕飞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出的《青衣》,当时正值中国经济腾飞之时,社会充斥着对金钱的盲目崇拜,资本成为权力的象征,高回报率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对纯粹艺术的追求显得难能可贵,但也注定是个悲剧。小说中不管是烟厂老板还是剧团团长乔炳璋,他们都不是为了艺术让筱燕秋重返舞台。烟厂老板是为了满足自己儿时占有筱燕秋身体的梦,而乔炳璋是为了满足金主爸爸的要求,筱燕秋对艺术的一厢情愿与这个现实、功利的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注定会以悲剧收尾。“身体是人类永远走不出的牢狱,又是人类永远的乐园”[5],毕飞宇在安排筱燕秋的命运时,将她的命运沉浮和身体的变化捆绑在了一起,起初筱燕秋凭借身体优势成为《奔月》剧组嫦娥第一人选,后来筱燕秋因为“嫉妒”烫伤恩师离开舞台,接着烟厂老板出现,筱燕秋通过出卖身体得以重回舞台,最终筱燕秋怀孕流产,一代青衣正式谢幕。毕飞宇通过对筱燕秋身体前后变化的书写,揭示了人的命运被经济价值衡量、主宰,传统文化遭到资本吞噬、操控的悲剧。
三、异化的身体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人格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本我、自我、超我。在正常的人格中,这三个部分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维持着平衡状态,而一旦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就会带来人格的异化,外在表现为身体的异化。
在小说《雨天的棉花糖》中,毕飞宇塑造了一位有着女性气质的男生红豆,因为父亲的军人情结而被迫参军,在战场上因被俘而误认为牺牲,成为烈士。但是伴随红豆突然的回归,迎来的却是大家的排斥,对于红豆家而言,烈士带来的是荣耀,而被释战俘带来的却是耻辱,在舆论的重压下,红豆精神错乱以致最终死亡。红豆从小就像女孩子一样,爱脸红、爱忸怩,被人称为假丫头片子,他虽然有着男儿身,却长着一颗女儿心。红豆从小就不喜欢木制手枪、弹弓等普通男孩喜欢的玩具,他喜欢二胡、喜欢音乐,这些在传统观念里带有女性意味的爱好。红豆生在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能长成一个英姿飒爽、高大威武的男子汉,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气概的合格军人,可是红豆却偏偏希望成为一个干干净净、安安稳稳的女孩子,这也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应该是血性、阳刚、力量的代名词,阴柔、娇羞的“娘炮儿”形象在父权制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对于男性的要求,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因此红豆总是难以真正融入社会,不管是儿时在厕所里遭到凌辱,还是长大后因为没有成为烈士遭到家里人的嫌弃。明明可以做男人却偏要做女人,明明可以做烈士却偏要做战俘,红豆没有按照社会给他的“剧本”演戏,跳出了社会为他框定的模式,那是不能被接受的,是要遭到唾弃的。身份认同的危机一步步将红豆推入深渊,绝望的红豆最终精神失常,只希望能通过杀掉过去那个不被社会接纳的自己来“重生”。相较于政治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文化对身体的影响则更加隐蔽,身体处在文化环境中,自然形成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生活习惯,毕飞宇通过对红豆身体异化过程的书写,表现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对人个性的禁锢,以及个体在面对传统伦理道德对身体的规训时的毫无招架之力,体现身体在权威话语体系下的疼痛、臣服、扭曲与异化。
人的身体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权力通过对身体的征服、规训从而达到对人的统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面对权力的操控压迫,身体只能屈从于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中,“性”和“权力”是小说主要探讨的两个主题,小说中王连方通过权力来满足自己对性的需求,玉米则是利用性来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性面前,男女本是平等的,可是在传统封建观念里,女性的身体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自古就有“母凭子贵”的说法,母亲的个人价值需要凭借儿子才能显现。小说《玉米》中,施桂芳为王连方一连生下了七个丫头,这伤了王连方的自尊,因为他听说“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7],为了证明自己,挽回男人的尊严,王连方拼了命要生男孩。为了保持女人的矜持,不被男人“看轻了”“看贱了”,施桂芳在进行房事时都是夹着、捂着,可是这却遭来了王连方的两记耳光,王连方大声呵斥到:“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天两碗饭的。”[3]3在王连方心中,妻子的任务和价值就是传宗接代,如果没有生到男孩就是失职,因此在生活中应该如履薄冰,对丈夫应该是有求必应,而施桂芳居然每天还有脸吃两碗饭,对于丈夫的需求还躲躲闪闪,真是该打。在王连方眼里,女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没有生出儿子的女人更是没有话语权,可悲的是,这一点也得到了施桂芳的认同,面对王连方,她言听计从,甚至到了害怕的地步。由此女人的身体异化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延续香火的工具。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大多是以悲剧收场,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女性没有办法“做自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她们始终是男人的附庸,即便是获得了权力,也必须借男人之手获得。权力总是在不平等关系的状态下运作的,在小说《玉米》中,玉米和彭国梁虽然爱得火热,难舍难分,可是在节骨眼上,玉米还是把住了最后一道关口,她要让彭国梁留些念想,这时的玉米还十分珍视自己的身体,想要将自己美好的处女之身留到洞房花烛夜。可是情况在村支书父亲王连方乱搞男女关系东窗事发后急转直下,王连方的“下台”让王家乱成了一锅粥,玉米与飞行员的婚事告吹,妹妹玉秀和玉叶遭到村民轮奸,家里的变故让玉米认清了“形势”,她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她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嫁出去来重振王家门楣,对于结婚对象玉米只有一个要求,手里有权就行。玉米如愿以偿作了五十多岁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的填房,用自己年轻的身体换取权力与地位。玉米心甘情愿成为权力的奴隶,权力主宰了她的行为和思想。女性的身体是她们与父权社会交易的资本,玉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她选择通过嫁给权力来带领家庭走出困境,玉米对权力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盲从和执着,她想要做人上人,想要拥有身份、地位,只有权力能带给她这些。玉米自幼生活在权力的庇护之下,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优越感,从小玉米就展现出对权力的极度渴求,母亲施桂芳在生完小八子后越发懒了,不愿过问家里的事情,玉米主动接过了持家的权力,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玉米享受着权力带给自己的话语权,她不能忍受没有权力的生活,只能通过身体与权力进行交易,哪怕失去尊严与爱情也在所不惜,玉米的身体在此时已经完全异化为一个毫无灵魂的权力的牺牲品。
四、结语
毕飞宇在小说中通过对身体的书写,揭露人物的潜意识,暗示人物的命运,表现人与时代的矛盾、冲突,表达对时代发展的反思,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事实表明,“我们的身体在长期以来被实践理性所驯服了,道德化的身体使我们丧失了对身体的支配权”[8]。毕飞宇通过身体写作,塑造出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揭露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小说中的身体具有一定的隐喻性,涵盖了他对生命的反思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