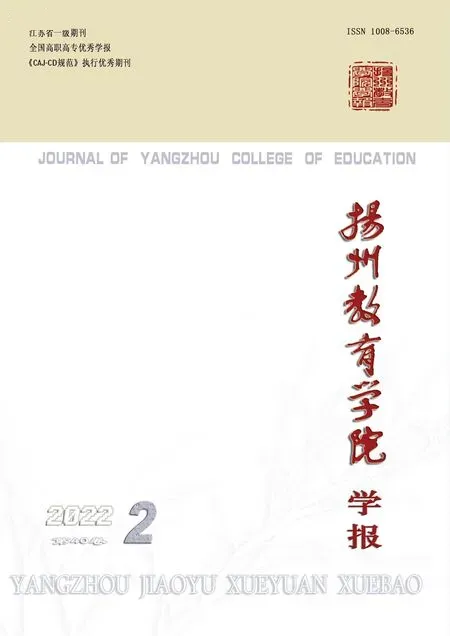徐灿与秋瑾爱国词之比较
李 爽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女性诗词作家之中,有两颗明星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就是明末清初的徐灿和清末民初的秋瑾。前者历经朝代更迭的耻辱,金戈铁马的动荡;后者则生于内忧外患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面对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她们突破了性别的局限,把视角放在了对家国情怀的抒写之上,以刀笔为武器,化文字为力量,于剪红刻翠的女性词坛中各显身手,各标风韵。
一、爱国词产生之背景
徐灿(1628—1680),字湘蘋,号深明,为光禄丞徐子懋的次女,海宁大学士陈之遴的继室。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家文化的诗礼熏陶,著有《拙政园诗集》二卷、《拙政园诗余》三卷,凡诗词246首,今皆存。她是“蕉园五子”之一,素有“闺阁弁冕”之称,是一个典型的名门闺秀。据《拙政园诗集》卷首所收其侄陈元龙撰写的《家传》云,她“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1]3,为徐子懋“所钟爱”。对于徐灿的才情与身世,晚清词人朱孝臧评其为“词是易安人道韫”[2],陈维崧评其“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秀,一人而已”[3],陈廷焯亦称之 “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黤,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 徐之亚”[4]133,由此可见,她在中国女性词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
徐灿一生的身世际遇,可以用“早历欢愉,晚经叵测”八字来概括。出身于书香世家,受尽父母宠爱,青年嫁得如意郎君,情投意合,这种近似完美的生活却随着清兵入关而付之东流。丈夫陈之遴因其父的失职而成为明王朝“永不叙用”之人;随着明王朝的覆灭,丈夫又结识新贵,迎降清军,接连升任……在正统儒家文化洗礼之下成长起来的徐灿,自然是看不惯丈夫的屈尊折节,虽说是夫贵妻荣,但这种仕途上的顺遂却并没有让徐灿得到应有的欢喜和畅意。好景不长,陈之遴先后经历了得罪谴戍、连坐结党、发配盛京、剥夺命官、籍没家产,徐灿虽然没有像男子一般遭遇杀戮、灭族的直接危险,但也深感官场政坛的波诡云谲。这种饱经沧桑巨变和忧生患世的情感幻化成文字,就成了浸染血色的爱国词。
秋瑾(1877—1907),字璿卿,别署鉴湖女侠, 出生于浙江绍兴,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秋家四代“均登贤书,乃为越中右族矣”[5]113。父秋寿官至湖南桂阳州知州,母亲单氏知书达理且深明大义。母亲谆谆教诲,父亲也在闲暇之余教其作诗,常“亲为指点讲解,偶成小诗,即呈堂上润饰,以是进境甚速”[5]143。如此浓厚的诗学氛围为她的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瑾秉性聪慧,有“过目成诵”之誉,常醉心于古典诗词,尤喜杜甫、辛弃疾、陆游等名家作品。她性格坚强豪爽,常以英雌花木兰、秦良玉自况[6]2。同时,她喜读经史,曾说过:“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7]108她的主要作品收集在《秋瑾诗文集》中,就其诗词,何震评论:“读其诗词,多慷慨之音。凡叹欢愉忧愤之情,身世家国之感,一寄之吟咏。思有所寄,援笔直摅,而生平志节,又隐约于意言之表。”[8]248梁乙真评其:“诗笔磊落有英气,直陈其性情矣。”[8]251
秋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腐败黑暗、帝国主义对华鲸吞蚕食的时代,同时也是新旧思想冲突,爱国志士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时代。秋瑾很快加入到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革命热潮中来,她抛下牢笼般的家庭,赴日留学,奔走呼号,以民主斗士的形象活跃于社会。为了抒发爱国热情与宣传革命思想,爱国词作应运而生。
处于硝烟弥漫时期的徐灿与秋瑾,看似生不逢时,但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特殊的历史环境成就了她们在文学上的地位与价值。她们在词作中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感。究其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两人都生长于官宦之家,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次,两人都经历了黍离麦秀之悲,也目睹了铜驼荆棘之惨。第三,两人深处于易代变革时期,思想相对比较活跃,随着女性意识的萌发与觉醒,她们打破了对啼红怨绿和融脂腻粉的描写,开始用女性固有的情思来书写浓厚的家国情怀。
二、爱国情感在词作中的具体表现
爱国情感在两位女史笔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主要包涵以下两个层次的意义:一种是面对异族的侵凌所导致的山河易主的局面,对于自己民族的政体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归宿性热情或感伤性余痛。第二种是超越对于腐败政体的愚忠式的归心,表现为对于自己置身于其中整个民族“存亡与发展”的忧患,以及救亡图存的热情行动[9]。很显然,徐灿属于第一种单纯的遗民感伤故土式的爱国,而秋瑾则属于后一种勇士奋起抗争般的爱国。
徐灿作为由明入清的女词人,她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朝代变迁,又目睹了丈夫的“屈尊失节”,她在词作中将这种独特的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主要表现在乡关之思、亡国之痛这两个方面。
乡关之思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一斛珠·有怀故园》:
恁般便过,元宵了踏歌声杳。二月燕台犹白草。风雨寒闺,何处邀春好。
吴侬只合江南老,雪里枝枝红意早。窗俯碧河云半袅。绣幕才揽,一枕梅香绕。[1]52
这首词是徐灿随丈夫在燕京怀念江南故乡时所作,词的上片主要写北国元宵已过,燕京早春二月却并没有让人感到一丝暖意,相反却是一片凄风苦雨的败落景象。下片主要是追忆江南的美好,“吴侬只合江南老”乃是化用了韦庄《菩萨蛮》中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早春的红梅凌枝傲雪,梅花的清香在揽起帘幕的那一刻涌入闺中,沁人心脾。一切景语皆情语,南北早春的景象判若冰火,两种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徐灿关于亡国之痛的词作有很多,这里以比较有影响的《踏莎行·初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1]78
这看似是一首普通的伤春怀旧词,但难能可贵的是词中所流露的是颇为沉痛的家国兴亡之感。阳春三月,本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但词人毫无赏春的兴致,愁绪绵绵不绝。接着写到晶帘寂然空垂,黄莺空枝独唱,这些景象暗含着千丝万缕之愁绪。然春愁何在?下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想回归故国,奈何不见踪迹,只见落日残照和流不尽的一江之水。层层碧云映现着昔日秀美的河山,更令人徒增伤悲。最后一句可谓达到了情感的高潮:词人祈求天边的明月,不要将光亮照到河山深处,以免戳人痛处,因为自己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家国之思所带来的苦痛了,这是绝望之后的清吟低唱。清朝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中评其:“既超诣,又和雅,笔意在五代、北宋之间。”[4]133今人钱仲联更是评其:“于念旧伤离之中,寄沧桑变革之叹。”[10]37
秋瑾的爱国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出国前和赴日留学期间。
先看出国前写的《满江红·小住京华》: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娥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6]80
这首词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词人随夫北上寓居京城期间。上片简单交代时间和地点,很快笔锋转向分析当时国家危如累卵的形势,由此引发强烈的思乡之情。“殊未屑”三个字表明了词人与传统女子贵妇形象作出的了断,在当时那个封建时代,这是何等的英勇与决绝。下片开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是为自己堪比男儿的雄心而自豪,为自己忠肝义胆的“因人常热”而自期。这种胸襟气度,当时的凡夫俗子中是不能引起强烈共鸣的,面对此种情形,她一方面自我调节,安慰自己英雄末路必当荆棘丛生,但同时也因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革命而黯然神伤。
留日期间,秋瑾也创作出了很多爱国词作,强烈地表达出她甘赴国难的雄心和不辞万里东渡的壮志。下面这首《鹧鸪天》就是典型的一首: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牺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6]97
这首词作于赴日后不久,语言浅显,明白如话,上片写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充满了担心,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满腔热血。下片写出她历经艰难险阻,孤独飘零海外。“休言女子非英物”再一次表明女子奋勇向前不甘示弱的雄心壮志,甚至托情于宝剑,这既有壮志未酬的苦闷,也有救民于水火的急切。
纵观徐灿和秋瑾的爱国词作,同是抒写忧生患世的爱国情怀,但两者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前者是雨打春残子规啼的哀怨缠绵,后者却犹如惊天响亮的闪电横空出世。前者将情感寄于景物,深隐幽咽,后者则直抒胸臆,明快洒脱。前者属于单纯思想上的爱国,写词无非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后者则不单单是为了抒写个人的豪情壮志,而是将这种爱国情感付诸实践。前者虽然与古代其他女性词人相比,走出了闺阁,格局放宽,将着眼点投入到家国兴衰之中,但在男权社会中仍属于附庸,内心的苦痛不便甚至不敢畅言直说,把词作当成排遣情绪的最佳载体。后者则不同,她将女性词史中暗含的“男性至尊”的传统完全打破,不仅提倡民主精神和人格平等,而且通过彰显女性纯粹的精神追求来反照男性的不足,与传统女性的形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三、爱国情怀的不同表现风格
徐灿和秋瑾在词作中虽然都流露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思,但在表现风格上却自成一家,各有千秋。
(一)徐灿词作“精秀渊雅”
徐灿是端庄娴雅的大家闺秀,她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深受儒家礼乐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塑造了她温文尔雅的性格。这种性格为她今后精秀渊雅的词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秀”源于她造词用语的精绝灵秀。徐灿有着十分细腻的心思和过人的才情,遣词造句不在话下。清陈廷焯评其为:“国朝闺秀工词者,自以徐湘蘋为第一。”[4]133秉性偏于柔静内敛的她在进行词的创作时,看似摒弃浮华,自然天成,毫无雕琢造作之态,实际只是不露痕迹,技法高超,她在进行语料加工时绝不是信马由缰不着边际,而是仔细斟酌详加考量。比如《苏幕遮·秋老》“故园烟芜昏復晓。尚有青山,强向江城绕”[1]105,故乡云烟迷蒙,或明或暗,时昏时晓。接着笔锋一转,这种情景之下,“尚”有青山环绕江城,“强”字传达出一种不可阻挡之势,打破固有的沉寂和压抑,一种生机活力扑面而来,给人带来希望和期盼。比如“今春何事待将休,丝雨柳梢头。恁般心绪撩乱,还要替花愁”[1]70,虽然第一句只是为了简单表达春天将要逝去这件事,但一个“休”字就吐尽了词人内心的凄凉与无奈;作者将自身与落花自比,一个“替”字就将自己感叹芳华易逝的自伤自愁充裕其中, 内心无法言说的苦痛通过文字的传递得以抒发和彰显。既有灵犀一点的词心,又有驾轻就熟的技法,同时兼备女性对于语言和构思的独特感悟,这就造就了徐灿词的精绝灵秀。
她的“渊雅”源于她取境的深幽纯雅。徐灿虽是大家闺秀,但毕竟是锁在深闺中的女子,无论眼界还是见识都会受到时代和家庭的局限,这种局限使得她在词境的选取上不可能宏广博大,加之时代的变革、家庭的际遇使她日坐愁城,内心怅触多端的苦痛如鲠在喉,于是她便把这种情感深深地掩藏在词作之中,这使她的词在抒情上显得幽远凄迷。比如“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1]98,面对故土难回,远谪他乡,内心的悲痛无法排遣,只能在梦里悲泪横流。钱仲联先生评其为:“声泪俱下,尺幅有千里之势。”[10]38比如“销魂不待君先说,悽悽似痛还如咽。还如咽。旧恩新宠,晓云流月”[1]64,悲痛无以言说,心气郁结,萦绕胸膛,无法排遣,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丈夫屈尊新贵,忘掉旧恩,美好的过去犹如“晓云流月”转瞬即逝。
(二)秋瑾词作“豪爽明快”
秋瑾是一位集爽气、豪气、霸气于一身的女侠。她不像锁在深闺的女子,少年时便喜欢舞枪弄剑,这种刚烈直爽的个性促使她在词作上完全脱去了女性固有的脂粉气,更多显露出一个革命者叱咤风云的气度。豪爽明快的词风在这种独特个性的影响下悄然形成。
她的“豪爽”源于她取境的广博和秉性的直率。不满于闺阁对女子的束缚,她赴日留学,这使得她的视野较传统女性开阔,加之她个性爽快豪放,这必然在她的词作中有所体现。比如“仗粲花莲舌,启聩振聋。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7]95,她劝勉好友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使出浑身解数来“唤起大千姊妹”,目的是迎接男女平等的曙光。“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牺身”[7]97,秋瑾为祖国的命运殚精竭虑,甚至做好了牺牲奉献的准备。这种女性少有的豪迈之气被徐蕴华评其:“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11]
她的“明快”源于她用语的明白畅快。秋瑾爱国词的创作是她革命激情的真实流露,是为配合政治斗争所写下的艺术宣传品,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所以,秋瑾词质朴浅显,明白如话,读之使人有种爽如哀梨、快如并剪之感。秋宗章曾这样评价:“姊天性伉爽,诗词多为兴到之作,别有意境。弗加雕琢,恍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非若寻常腐儒之沾沾于格律声调。”[5]151比如,“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每个英雄作主”[7]96,对当时局势分析得可谓犀利深刻,一针见血。又如,“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7]94,劝同辈努力洗刷前耻。由于语言太过浅显直白,打破了诗显词隐的创作规律,这使得她的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弊端:急就之章,语言不够成熟,稍显粗糙,伤其真美。
四、结语
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徐灿和秋瑾虽然所处的时代、所拥有的性格特征、所表达的词作思想以及词作风格上都呈现了不同的色彩,但她们都拥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她们以各自的聪慧、各自的才情抒发自己的爱国情志,彰显了女性特有的人性光辉,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