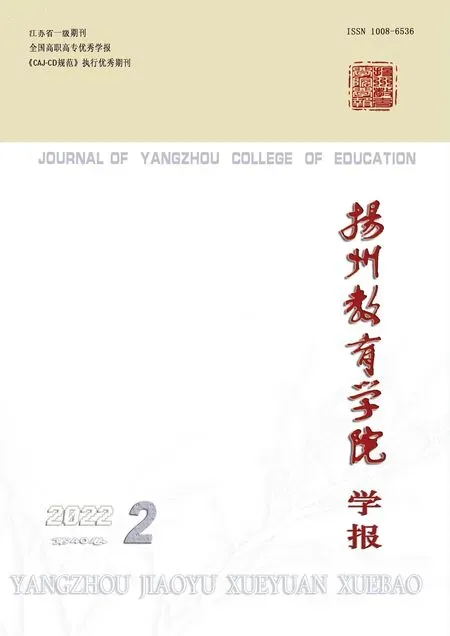论唐代禁毁淫祠运动中的官员角色
——以对伍子胥庙的管理为中心
庄 冰 莹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淫祠,是学界研究民间信仰的重要课题。淫祠,是指不在祀典之上的地方祠庙。对淫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和政权与地方祠祀之间的互动。
目前有关唐代淫祠的研究,有些整体分析“淫祠”的特点、祠庙分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措施;有些集中分析某个神祇或某个重要事件;有些揭示佛道二教与地方祠祀的关系;有些分析地方官员心态的;在也有些探讨唐代中央是如何管理地方祠庙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伍子胥庙作为切入点,以中央和地方两个视角,详尽地分析子胥庙在唐代祭祀体系中的发展变化,以期展现在以伍子胥庙为代表的地方祠庙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对抗和唐代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的践行。
一、唐朝江南伍子胥庙的分布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父亲为楚平王太子太傅伍奢。在父亲被诬陷后,伍子胥一路逃窜至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破楚国,掘墓鞭尸为父报仇;后吴王儿子夫差即位,在美人计和奸人离间之下,他赐死伍子胥,伍子胥的尸体被抛进今钱塘江中。伍子胥被杀后不久,吴人便为他在江边立庙加以祭祀,“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1]。伍子胥投江之际,钱塘江形成了巨大的潮涌,民众便将潮涌和伍子胥被冤杀联系起来,认为潮涌是伍子胥死不瞑目的表现,由此才为他设立祠堂。[2]34自春秋战国始,伍子胥一直被视为“凶神”,也就是说,此时为伍子胥立祠,不是为了祠祀忠贤,而是祀厉除灾,东汉王充认为他“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但与此同时,伍子胥庙仍遍布“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3]等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伍子胥形象渐趋正面,经由儒家发展和士人塑造,子胥神的形象已由“凶神”转化成符合儒家理想体系的“忠孝”,并一度作为国家正祀之江渎的陪祀。[2]38南朝梁元帝还曾作有《祀伍相庙诗》,至唐朝,伍子胥信仰进一步发展。现将史料所见伍子胥庙的情况见表1:

表1 唐以前至唐伍子胥庙分布情况
上表所举共23例,从名称上来看,祭祀伍子胥的祠庙名称有“伍子胥庙”“伍员庙”“伍相祠”“江水祠”“胥山祠”等等,还有称之为“五髭须”者,“五髭须”是伍子胥的谐音。从祭祀方式上看,“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每年祭祀三次,堪比五岳。从祭祀缘由来看,王充认为祭祀伍子胥是为了“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通过材料可以发现,唐以前就有地方长官禁止祭祀伍子胥庙:南朝的范缜由于“不信鬼神”下令停止祭祀包括伍子胥庙在内的多个祠庙,隋代开皇年间高励也以祭祀伍子胥神浪费民力上谕停止祭祀。
表1基本能反映伍子胥庙的分布和发展情况。从时间上来看,有唐一代都存在伍子胥庙,且经久不衰。从地域上来看,伍子胥庙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如江都、会稽、钱塘、苏州、楚州、杭州等地,剩下的主要分布在楚地,如荆州、江陵、澧州等。吴、楚两地是伍子胥生前活动的主要地方,子胥庙也集中分布在这两个地区。
江南地区作为伍子胥历史传说的主要历史舞台,是伍子胥信仰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有唐一代,杭州伍子胥庙的地位格外突出。据日本学者水越知研究,这与杭州在江南地区的地位提升息息相关。[4]伍子胥庙集中分布在江南地区,而江南正是唐朝清除淫祠运动的重地。下文将从中央和地方两个视角分析伍子胥庙在唐朝祭祀体系中的位置。
二、唐朝江南禁毁淫祠运动与伍子庙的“正统化”
唐人是这样定义淫祠的:“若妖神淫祠,无名而设。……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祠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祠也。”[5]子胥庙既不在国家祀典上,又鞭杀楚国旧君尸体,横死钱塘江,当属无功德节行,根据这个定义,应是“淫祠”一类。据蔡宗宪的研究,“淫祠”一词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淫祀”为同义词,随着地方神祠的发展而分化,在唐朝成为偏指祠庙的词类,人们对“淫祀”风俗逐渐聚焦于祠庙。[6]淫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地方民众是不会将自己祭拜的祠庙认定为淫祠的。
唐初,中央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对待淫祠。武德九年(626)九月,“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7]31。《隋书·地理志》载:“(江南)俗信鬼神,好淫祠。”[8]江南地区神祠众多,因此对该地区的淫祠管控尤为严格。武则天时,江南巡抚使狄仁杰痛感“吴、楚之俗多淫祠”,奏毁淫祠“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7]2887。《隋唐嘉话》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一千)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庙存焉。”[9]其中“一千”二字脱落。
这次淫祠运动清除了包括楚王项羽、越王勾践、赵佗、马援在内的一大批祠庙,保留了夏禹、吴太伯、季札庙和伍子胥庙。戴孚《广异记》所载是对此次运动的补充:“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10]这则故事显示了此次打击淫祠的力度之大,使用大火焚烧且以死刑立威,并且在获得敕牒后才得以焚烧端州蛮神庙,旨在展示此次打击淫祠运动的巨大功效,突出了中央的威力,即皇帝和官员地位要比民间所信仰的神祇高,在他们的敕牒面前,民间祠庙不存在反抗的力量。
与这次淫祠运动相关的地方祠庙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祠祭对象上,都为人格神,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死后成神,这些人都是生前有功德或者符合儒家传统理想形象的,有些是正常死亡,有些是横死,如项羽自刎乌江,子胥尸沉大江;其二,从祠祭地域上来说,这些人都是与江南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人物。材料所限,无法进一步判断狄仁杰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庙和伍子胥四庙的依据。
在保留的四神中,夏禹、太伯、季札属于儒家观念中的圣贤:夏禹是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贤王;吴太伯,因其三让天下的美德,被尊称为“三让王”;而季札,太伯的后人,也被公认为贤者。至唐朝,伍子胥形象虽已向忠孝靠拢,只是其祠庙的地位始终比较模糊。
伍子胥庙为什么被保留?狄仁杰此次禁毁江南淫祠运动,时间上在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叛乱后,地点在徐敬业作乱的长江流域,且武则天一直怀疑徐敬业的真实下落,《檄告西楚霸王文》明显有指责徐敬业“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11]的意图。这次保留子胥庙,可能是武则天掌权时期有意淡化“从一而终”忠君思想,强调良臣应像伍子胥择主而事。
伍子胥庙的保留并不代表着就此受到国家认可。毕竟在“(毁淫祠)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的语境中,伍子胥庙是被判定为淫祠的,颇有“此次不清理,暂且留着,下次清理”的潜藏意思。玄宗年间开出的地方祠庙保护名单就是一个例证,因为伍子胥庙并没有在这个名单上。
天宝七载(748)五月十五日,政府开列出一张地方祭祀的保护名单,上包括帝王(配享将相)、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12]。从禁毁淫祠到认定部分地方祠祭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意识深入地方社会的努力。国家权力对祭祀合法性的垄断,“促进了中央、都市、上层文明的传播与扩张”[13]258。在这份名单上,狄仁杰在禁毁淫祠运动中所保留的“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庙,夏禹属帝王一类,吴太伯(吴郡)、季札(丹阳郡)属义士一类,唯独伍子胥庙不在名单上,子胥并没有进入忠臣一类,这再次论证子胥庙在中央依然属于有待清除的“淫祠”,处于被毁灭的边缘。
相较于中央直接把子胥庙归为“淫祠”一类,在地方官眼中,此庙的位置就比较模糊了。贞元十年(794),苏州刺史于頔“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庙等三数庙存焉”[7]4129。伍子胥庙被保留,或许是武则天时期狄仁杰保留子胥庙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
唐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江南已经成为唐中央的财赋重地。为了加深对江南地区的掌控,中央又再次在此地进行大规模的禁毁淫祠运动。穆宗长庆二年(822),李德裕在浙江观察使任上时,上奏汇报清除状况:“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7]4511这里表明祠庙保存的标准是“按方志”,表明了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尊重。在这里,伍子胥庙是否被保留并无直接体现,但是禁毁淫祠运动前后,即长庆二年七月,杭州刺史白居易曾向伍子胥求雨,并在任职杭州时有相关诗作留下:一是《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中所记“伍相庙边繁似雪, 孤山园里丽如妆”,一是《杭州春望》中所载“涛声夜入伍员庙, 柳色春藏苏小家”[14]522。由此可见,子胥庙并没有被清除,而是保留了的。
不仅如此,唐代的地方官员反而积极地修缮残破的伍子胥庙宇,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伍子胥信仰的发展。元和十年(815),杭州刺史卢元辅修缮胥山祠,其《胥山祠铭(并序)》说:“千五百年,庙貌不改。汉史迁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谬也。”[15]7137指明伍子胥庙的沿革,认为杭州的胥山祠就是《史记》所载吴人所修的胥山祠:“投于水滨,愤悱鼓怒,配涛作神,其神迄今。”[15]7137以及铭文里的“投於河上,自统波涛”,论述了伍子胥的忠孝特点和潮神形象,为修缮祭拜伍子胥庙寻找到了依据;铭文最后“虽非命祀,不让渎齐。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说明了伍子胥庙此时依然没有进入国家正式的祭祀系统,但作为地方官的卢元辅认可其合理性。
半个世纪以后,景福二年(893),钱镠请求赐封伍子胥,两年后(895),吴山伍子胥庙获封为惠应候,中央正式肯定了伍子胥信仰的合法性;乾宁三年(896),杨行密派安仁义沿“沙路”袭击湖州,钱镠“乃祭江而祷胥山祠”,潮水冲毁沙路组织杨行密一军,钱镠“感其灵贶,请而封之”,唐中央政府遂“敕封吴山惠应侯为吴安王”[16],伍子胥庙由此获得国家赐号。
另外,伍子胥能否血食于楚的情况也值得被研究,其实质是儒家伦理与地方性崇拜的冲突。面对叛楚成为吴国将军的伍子胥,楚人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刘蜕《谕江陵耆老书》写道:“子胥何为飨人之食,而江陵何为事仇人之神乎?”[17]乾宁、光化年间,澧州太守李善夷想重修澧江边上残破的伍相庙[15]8743,“里人”就表示了强烈地反对:“不可也,员,楚之仇。鞭我死君,其过也。”“员,孝父者,其庙废之,则不以旌其孝,建之则不以劝其忠。”[15]8743楚人赞扬伍子胥为父报仇是孝,可鞭杀国君是为不忠,忠孝在这里产生了割裂和对立。伍子胥是否能血食于楚,折射的是时人对“忠”的理解。那么,以谁为君就至关重要了。陈淳认为:“伍子胥应该血食于吴,不该血食于楚。”[18]这里是以楚王为君;李善夷提出,春秋时期,伍子胥是周天子之臣,引吴灭楚是对周天子的忠诚,“当平王之时,君上乃周景王也”。这个观点保持了整体的天下观念,超越吴、楚地方意识。李善夷,时调谪澧州的唐朝官员,这个观点折射出他对唐中央和藩镇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忠”的对象应该是唐天子。这种“大局”观念在藩镇割据、起义不断的唐末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得以顺利重修澧州的子胥庙并立碑示人。此外,这时江南伍子胥庙已获得国家赐号,应该也对此次重修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官员对伍子胥庙命运的影响
分析唐代的材料可以看出,伍子胥庙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地方官。蒲慕州曾论述汉代的知识分子在民间信仰中大概扮演三种角色:批评者、改革者与参与者。唐代官员在地方祠庙前所扮演的角色也大概可分为这三种:参与者、改革者和清除者。本文所论及的官员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地方长官刺史;一类是由中央派出到地方的使官。
第一种角色是地方官作为参与者,认同地方民众的信仰,成为祭祀活动的一员。参与到祭祀活动中的官员,有的是认同地方祠庙的合理性,有的是为了安抚受灾的地方民众。面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出于收买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去祭拜人们所信仰的地方祠庙,包括未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地方官员做祭神文祈雨求晴是一种政治性表演,灵验事迹可以转换成他在任期间的突出贡献,如果不灵验,恰恰能够说明淫祠存在的不合理性。杭州刺史白居易作祭神文:“一昨祷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有应,雨未霑足。是用择日一作撰词祗事,改请于神。”[14]900-901祈求子胥、城隍神降雨,祈佑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还有杭州刺史卢元辅修缮伍子胥庙,所作《胥山祠铭》铭文就表示他完全认可伍子胥庙的合理性地位和神异力量。
第二种地方官所扮演的角色是改革者,在面对地方祠庙时,他们多采取温和的教化措施。这类官员认为民众祭拜地方祠庙是鬼神观念作祟,一遇疾病灾疫就向神明祈祐,荒废民力。因此会采取相应的对治政策:兴办学校,开启民智;劝农务桑,以正本业;增设医药,以除疫疾等等。有些地方官为了引导祭祀风俗,则主动树立可供祭祀的典范。如高宗时建州“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7]2816,刺史张文琮下教书:“春秋二社,盖本为农,惟独此州,废而不立。礼典既缺,风俗何观?近年已来,田多不熟,抑不祭先农所致乎!神在于敬,何以邀福?”[7]2816建立社稷的场所,引导民众祭祀。开元中,房州刺史“州带山谷,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又通狭路,幷造传馆,行旅甚以为便”[7]4798。在肃宗、代宗年间,庐州刺史罗饷,目睹了当地“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祠”的状况,下令禁止淫祠祭祀,修建学校以启发民智。
第三种是清除者,即不认可祠庙的合理性以强硬态度清除,如狄仁杰和李德裕清除江南淫祠运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狄仁杰和李德裕的特殊身份,他们清除淫祠时的身份分别是江南道巡抚大使和浙西(道)观察使。在唐朝,道由监察区向准行政区过渡,其法律地位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巡抚大史和观察使作为使官,在管理派出地地方事务时集中体现着中央的意志,对江南地区的淫祠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表明中央控制地方的强烈意愿。“社区神祇与国家神祇、官方宗教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19]狄仁杰强力清除江南淫祠保留了子胥庙,这为伍子胥庙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从此江南地方官员保留伍子胥庙都能以此为历史依据。李德裕清除淫祠运动中,其清除的标准是“依照地志”,而《册府元龟》所载长庆四年诏令“所在淫祀不合礼经者,并委长吏禁断”[20],说明管内各州地方官员对此也拥有很大自主权。
总的来说,面对地方祠庙,地方官员如刺史都比较温和,而由中央派出的使官通常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不过其具体推进工作往往下发至管内各州。地方官员作为当地父母官,最直接的管理者,在执行中央命令时往往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以保证地方社会的稳定,获得民众认可。他们处于中央与民众之间的“过渡带”,既执行中央命令反映中央意愿,又确保政令推行稳健。刺史作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在州级行政中的地位最高。因此,地方长官面对地方祠祭的态度,对地方祠庙性质的判定,往往能决定祠庙的命运。伍子胥庙也不例外。伍子胥,从吴人变成吴地守护神,江南地区对伍子胥的信仰深具地方特色;在发展演变中,伍子胥形象的儒学色彩浓厚,突出了其忠孝形象,符合地方官的选择标准;至唐朝,子胥庙的潮神司职能力得到极大强化,是民众希冀风调雨顺等美好心愿的集中投射,因此地方官不会将伍子胥庙认定为“淫祠”,子胥庙便在历次清除淫祠运动中得以幸存。可以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与民众的“过渡带”,为伍子胥等一众地方祠庙提供了生存空间,才有唐末伍子胥庙获得中央赐封,被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命运。此后,赐封赐额成为中央管理地方祠庙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祀与淫祀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即权力对祭祀合法性的垄断。”[13]258中央对地方祠庙的管理,无论是“禁毁祀典之外的祠庙”,“承认部分地方祠祭准许祭拜”还是“赐封赐号灵验的神祠”,其实质都是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不同的是,赐号赐封将主要的认定权力收归中央,而地方官转而与地方力量结合在一起,争取获得中央赐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