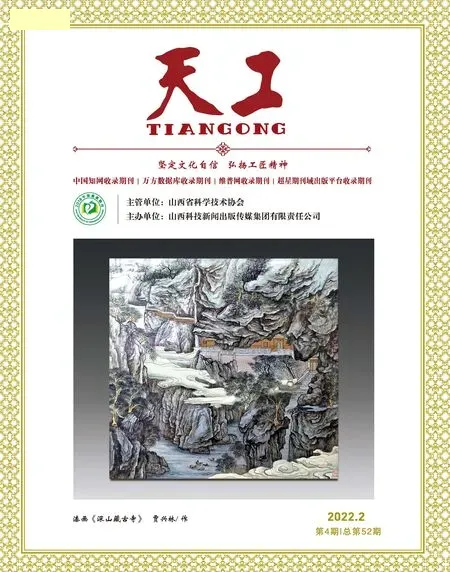偏差与纠偏:对回归“堆花艺术”研究的思考
韩志强 王潆梅
1.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2.山西大学新闻学院
一、研究缘起
笔者在《“花”“锦”之辨与为“堆花艺术”正名》①《天工》2021年第4期,第18-22页。一文中提到,现在存在“堆花”与“堆锦”概念交叉引起的人们认知模糊的现象,在论文中笔者重新思考了两者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技艺差异,认为堆花包含堆锦,堆锦包含不了堆花,堆锦也等同不了堆花,应该站在尊重历史与艺术的角度为“堆花艺术” 进行正名。为了进一步了解近年来学界对“堆花艺术”的研究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堆花”“长治堆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找到了一些关于“宜兴均陶堆花”“堆花米酒”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未找到“长治堆花”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笔者发现,“长治堆花”的叫法多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改名之前的一些史料与文献之中。比如1915 年,李治清带领儿子李模、李楷及其长孙李时忠祖孙三代制作出多幅精美的堆花作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春夏秋冬》四条屏获银奖。更名以后,学术界大多转向了对“堆锦”的研究。为什么对“堆花艺术”的关注较少?目前学术界对于“堆锦艺术”的研究情况究竟怎样?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基于此,笔者采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选取2000年至2021年10月期间国内的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对国内“堆锦艺术”这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作者机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进一步倡议学术界要回归对“堆花艺术”的研究。
二、文献来源与特征分析
(一)文献来源
本文以“堆锦”“堆花”“长治堆锦”“上党堆锦”等为检索词对CNKI数据库进行组配检索获取文献,再对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会议、采访、新闻、卷首语、图片等不相关的结果,并以文献的引文为线索进行二次检索,以最大限度保证文献的全面性。最终确定36篇相关文献,并对其发表年度、作者机构、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了解国内关于“堆锦艺术”研究的文献分布状况。
(二)特征分析
通过对文献发布时间进行统计,发现2000—2021年间对“堆锦艺术”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少,一共有35篇相关文献。发文数量较多的是2013年,论文数量为5篇,其次为2010年和2019年,发文数量均为4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堆锦艺术”给予的关注度不高。
从发文作者所在机构来看,长治学院发文量有5篇,太原理工大学有4篇,山西大学和山西师范大学各发2篇,中北大学1篇。由此可见,“堆花(锦)”艺术发源地山西的高校师生对“堆花(锦)”艺术更为关注。
三、研究内容分析
35篇相关文献所研究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艺术概念的界定
关于“长治堆锦”艺术的概念,几乎大家都是这样写的:“上党堆锦俗称‘长治堆花’,是上党地区特有的地域性民间传统手工艺品。”“长治堆锦又称堆花……”笔者发现了传播过程中,“堆花”与“堆锦”概念交叉引起的人们认知模糊的现象,通过重新思考两者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技艺差异,认为堆花包含堆锦,堆锦包含不了堆花,是“花中锦”而非“锦中花”。
(二)艺术特征的分析
丙宸(2013)对上党堆锦的工艺特征与制作工序进行了阐述,归纳总结了堆锦制作的十道工序,主要有描样、剪裁、贴“飞边”、拨、捏褶、堆粘、彩绘、装饰、底板呈现、嵌框。王玥(2017)在其硕士论文《山西长治堆锦的演变及艺术特色》中,对不同历史时期“长治堆锦”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介绍:清末民国时期端庄典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质朴纯真、改革开放初清新别致、21世纪以来多彩纷呈。郝沛沛(2018)从“堆”“锦”两方面入手分析了“长治堆锦”的艺术特征,并对“长治堆锦”的传承提出了两点思考,一是要与现实生活相交融,二是要参与体验设计。李婷(2019)从题词、造型、构图、色彩、材质五个方面对“长治堆锦”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她认为“长治堆锦”主要以趋吉辟邪和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运用了散点式、分割式、截取式和动态式四种构图方式,其背景色偏冷,主体物艳丽,整体色调和谐,造型写实,通过丝绸材质凸显画面生动逼真的立体效果。除此之外,“长治堆锦”也具有审美意蕴和社会生活功用,这也是“长治堆锦”作为“贵族工艺”的原因和“百变不衰”的因素。
(三) 艺术发展的历史溯源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界对“长治堆锦”艺术产生于何时,主要有三种争论。有学者认为产生于隋唐、唐宋时期。王欣在《中华一绝——上党堆锦文化艺术》(2006)一文中认为上党堆锦产生于唐朝时期,并讨论了上党堆锦的发展历程。涂必成也认为上党堆锦起源于唐代,是唐玄宗在长治做潞州别驾时从宫廷中带到上党地区的。有学者认为产生于明代。闫德明(2010)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才四个方面论证了“长治堆锦”形成约在明代的中晚期。张环也在其硕士论文《浅析上党堆锦的文化生成及演变》(2010)中,通过叙述上党地区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物质条件、工艺基础和时代背景,论述了上党堆锦产生于明代初期。也有学者认为“长治堆锦”产生于清光绪年间。主要代表人物是岳续明,其在《“长治堆锦”名闻天下》(2001)中认为,堆锦产生于清光绪年间,并阐述了“长治堆锦”艺术自清产生至19世纪80年代的发展情况。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长治堆锦”的发展基本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明清时期李模的出现使“长治堆锦”艺术名声大震,堆锦作品荣获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质奖。清末到民国时期,上党堆锦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治堆锦”艺术重整旗鼓,并开始制作以现实题材为内容的作品。21世纪初,涂必成重振堆锦艺术,上党堆锦艺术不仅频频在全国性工艺美展上亮相,屡屡获奖,更重要的是在以佛教、西方文明经典题材为代表的题材开拓上,有了重大的扩展。如今,“长治堆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遇到瓶颈,需要我们探索发展传承之路。
(四)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从目前研究来看,学术界对“长治堆锦”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的研究较多。曾圣舒在其硕士论文《“长治堆锦”研究》(2010)一文中认为“长治堆锦”艺术在实践中出现了绘画与制作的关系“倒位”的现象。他认为,这种“倒位”现象阻碍了“长治堆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种对绘画技巧的过度依赖,不仅不利于丝绸质感的充分发挥,同时也限制了制作技巧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因此,他提出关于“长治堆锦”艺术的发展思考 :(1)必须处理好观念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首先要在堆锦画稿的“原创性”上下功夫,其次要突破堆锦绘画性的“禁区”,实现观念更新。(2)“长治堆锦”艺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3)把握好堆锦艺术的“高端”和“底线”,建立良性发展模式。对于堆锦作品来说,材料精美、工艺地道、格调高雅的堆锦才是凝聚堆锦艺术精华的作品,才是传承发展的要害所在。堆锦作品如果越出了艺术底线,创新也就失去了意义。马丽美在其硕士论文《试论上党堆锦艺术的保护与发展》(2010)中对山西上党堆锦艺术的工艺特点进行了阐述,在了解上党堆锦保护与传承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发展思路,提出了关于上党堆锦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她认为“长治堆锦”艺术的问题是:堆锦研究人员稀缺、堆锦缺少一个适应环境的生存空间、伪劣产品的充斥,基于此她提出了四点措施:借助群体活动弘扬上党堆锦艺术、加强与相关科研机构或专家合作研究、上党堆锦与现代美术教育相结合、加大上党堆锦培训广度,培养工艺传人。刘磊(2011)通过分析“长治堆锦”的现状与困境提出了重振堆锦的四个方案: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堆锦产品市场和“与时俱进”,使传统与现代结合。郝沛沛(2017)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上党堆锦手工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上党堆锦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两极分化的双轨制研究思路。王璐(2019)以长治地区的堆锦状况和艺术价值为基点,分析探求传承和发展堆锦艺术的新思路、新方法:(1)重视传承主体的培养;(2)不断创新再创造,与时俱进改进原料和工艺流程,通过“长治堆锦”与家居装饰品、旅游纪念品、服装设计的融合来提升“长治堆锦”的价值;(3)加大宣传力度,推广品牌文化,打造堆锦品牌,并且学会利用新媒体,创新销售平台,提升市场空间。
李靖萌和曹勇都对“长治堆锦”艺术的展学馆进行设计与研究,从而使“长治堆锦”艺术得到推广与保护。李靖萌(2019)通过资料分析、周边地区探访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对“长治堆锦”艺术展学馆的选址地——山西省长治市的区位特征、历史价值、手工艺发展现状等进行了剖析与阐述,本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从建筑形态、内部功能、空间环境以及多元化发展等多方面出发,进行“上党堆锦”展学馆的空间设计。曹勇(2021)通过分析“长治堆锦”技艺特点、传承人、工艺制作方式和流程,对“长治堆锦”技艺的展示空间进行设计研究,为堆锦工艺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值得借鉴的展示方式。
此外,贾峰从堆锦艺术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层面探讨堆锦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以山西长治地区的上党堆锦为实证研究对象,从个人购买偏好入手,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对部分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分析归纳了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上党堆锦工艺品设计开发的策略。
邢淑萍从网络营销层面探讨堆锦艺术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梳理“长治堆锦”的产销现状,提出自建网站实现在线订购、借助名网搭建淘宝商店、借助网络媒介线上藏品营销、网上造势线下体验四种堆锦网络营销模式。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学界认为“长治堆锦”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方式大体有四点:(1)注重传承人才的培养;(2)进行堆锦艺术的创新;(3)加大宣传力度,打造“长治堆锦”品牌;(4)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营销。在传承人才培养层面,牛晶晶从人类学视角,对山西上党堆锦的传承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选取了上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堆锦艺术家涂必成和弓春香老师,着重研究他们的堆锦创作成果,目的是从它的历史中来把握堆锦艺术家的创作发展脉络。通过分析前人的创作经验与风格特色,为堆锦艺人的创作发展提供借鉴。牛晶晶认为上党堆锦的发展需要“人”来支撑,后辈应该担起保护和传承上党堆锦的重任,不断扩散上党堆锦的艺术影响力。
除此之外,将堆锦艺术与美术教育相结合也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之一。刘磊章(2012)以“长治堆锦”为例,分析了如何利用当地的历史、经济、文化资源,使“长治堆锦”这样的传统工艺美术找到属于它们自身的地位和生存空间。田伟(2018)结合校本课程开发的方法步骤,提出将“长治堆锦”这一民间艺术融合到初中美术课堂,让学生认识、了解堆锦的文化历史,掌握堆锦的制作工艺,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培养对民间艺术传承的责任感。
四、讨论与展望
(一)目前研究的重点与不足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目前“长治堆锦”艺术引起了艺术理论与设计、美术人类学、民俗学、市场营销等不同学科的关注,主要集中探讨关于“长治堆锦”的艺术特征、起源与发展、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超出了“堆锦”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学界目前是把“堆锦艺术”与“堆花艺术”当成一回事来进行研究的,这可能的原因大概就是“长治堆花”于20世纪60年代改名为“堆锦”之后,大家将“堆花”和“堆锦”的概念等同,并基于此进行研究与传播。
“堆花”与“堆锦”的概念模糊导致了“堆花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传播偏差现象,且长时间的传播必然会使对“堆锦”艺术的研究成为对“堆花”艺术研究的制约瓶颈,缩小了“堆花艺术”固有所包含的其他丰富的材料使用与特殊技艺的内容,而非仅仅停留在锦缎材质的使用上。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传播偏差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信息失真现象。具体来说,它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发生了非主观的再次编码和解码,使得传播偏离了传播者的原有意图,没有达到预期传播效果而导致了其他非预期的结果。这种信息失真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在传播环节发生的,也可能是在接收环节发生的。①李璐玚,闫名驰:《传播偏差在大众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产生原因》,《新闻知识》,2012年第6期,第40-42页。
首先,当时的保护工作者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只看了由丝绸锦缎堆砌的作品,没有看到更多其他材质堆砌的堆花作品,由此产生了认知误差,故将“堆花”更名为“堆锦”。这其实模糊了“堆花”和“堆锦”的概念,在传播源头产生偏误。
其次,之后的相关研究者与传播者没有进行深度思考,均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将“堆花”等同于“堆锦”进行研究与传播。由于这样的信息偏差一直存在,影响着后来人们的认知,逐渐使“堆花艺术”的价值在“误传播”中大打折扣,传承与传播受到阻碍。例如,在“长治堆锦艺术的起源与发展”这一主题下,研究者均将“堆花”的历史等同于“堆锦”的历史,并基于此对“长治堆锦”艺术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梳理。这就导致“堆花艺术”的研究范围被缩小,艺术传承价值被忽略。
(二)未来研究展望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长治堆锦”艺术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影响面还不够大,如果在及时厘清“堆花”“堆锦”概念的基础上,既保持对“堆锦”的研究,又回归到对“堆花”艺术的研究,在今后的传播与传承道路上会产生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价值。
笔者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并投入研究。
首先,进一步厘清“堆花”与“堆锦”的概念,重新思考两者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技艺差异,为“堆花”艺术正名,同时也为“堆锦”艺术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真正研究“堆锦”。其次,应回归对“堆花艺术”的研究,这需要对其艺术特征、起源与发展、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丰富其知识体系,建构其传承谱系,挖掘除堆锦之外“堆花艺术”中其他材质使用的技艺传承内容。再次,以堆花之名研究并传播“堆花艺术”,实现“堆花艺术”的名词普及,这是“堆花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前提,只有为“堆花”正名,才能切实发掘“堆花艺术”的真正价值,为之后的研究打好基础,让更多的人研究、关注、保护、发展该艺术。
因误会而产生偏差,也要因理性而在纠偏中实现回归。回归对“堆花艺术”的研究,既是对历史与艺术的尊重,也体现了对艺术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希望之后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发掘“堆花艺术”的价值,让“堆花艺术”重新焕发生机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