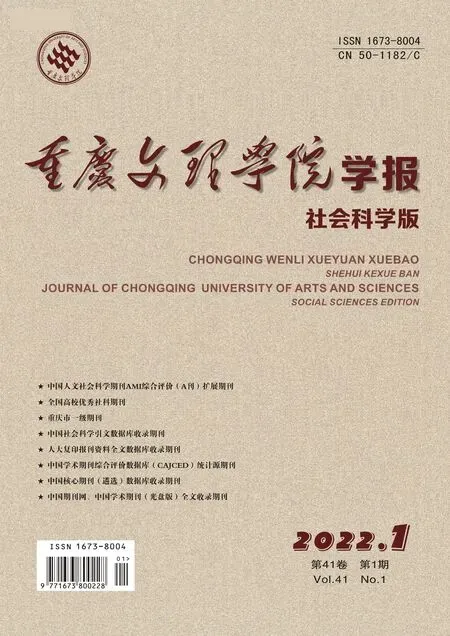表征与抵抗:青年群体的时代焦虑
——以“躺平”现象为例
辜慧英,侯凡跃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网络流行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与文化潮流,也与青年群体的心理变化、现实状况有紧密联系。近期,网络流行语“躺平”成了青年群体中的一股时尚——年轻人不再沉迷于“丧”情绪,不再追求什么都不干的“佛系”,而是选择策略性的“躺平”:即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只管做好自己的事,降低对生活的要求,保持低欲望,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躺平”作为一种青年网络现象,已逐渐成为以9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的泛圈层文化符码。
对于青年网络现象,现有研究主要从青年亚文化的理论视域进行探索。如吴茜从青年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佛系青年如何通过象征叙事、网络部族及其社会表征来进行身份的实践[1]。对于以“躺平”“佛系”为代表的网络现象的研究,既有消极意义叙事,也有正面话语解读。例如,一部分人认为,在就业环境、生活成本、人际关系的碾压之下,年轻人疲于竞争,选择“躺平”是“内卷”失败后的退路。令小雄、李春丽从社会结构性的视角出发,认为“躺平”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义”,其实质是用一种戏谑的叙事方式来掩饰自身竞争力和能力的不足[2]。而“躺平”的现象表征也与“佛系”青年存在共通之处,如李东坡、牛娜认为佛系青年的本质是青年群体陷入了信仰危机,通过淡漠主流信仰来逃避压力剧增的社会现实[3]。对于“躺平”现象背后的“低欲望”心理症候,张志坚则认为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固化导致了青年的低欲望心态[4]。也有观点认为“躺平”现象是社会结构性变化导致的,青年人选择用自身行动对外界规训和变化做出回应。伯明翰学派将青年亚文化视为社会结构矛盾化的产物,其行为表现是为了抵抗阶级霸权并解决父辈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遗留问题[5]。就其具体社会现象而言,蒋建国认为“丧”“佛系”等自我贬抑式的话语表达,是网民进行自我身份定位而实施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6]。“躺平青年”主动选择改变赚钱买房、升职加班的传统路径,用自己的方式抵抗外在环境的强势规训,其本质是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后,以一种软性抵抗的态度做出的人生选择。
可见,以“躺平”回应“内卷”,更像是新一代年轻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躺平”在形式上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却不是绝望的代名词[7]。因此,本文通过对“躺平”现象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行分析,以期探寻一条规避其消极影响、促进青年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一、青年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躺平”现象
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也是一定时代演化的产物。“躺平”作为一种青年社会现象,可以将其视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可以在分析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对“躺平”的原因进行结构性审视。
(一)“躺平”的理论视域:青年亚文化的解读视角
对于作为青年现象的“躺平”,学界主要从青年亚文化和后亚文化两种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一方面,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从抵抗、风格、收编的三个方面,将青年视为一种与主流社会的群体身份相区隔的群体,他们对主流文化和固有阶层秩序进行抵抗,并努力建构自身的群体秩序与亚群体认同[8],通过这种抵抗构建身份识别的文化符码。青年亚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文化形成的社会共识;而主流文化通常以收编或直接禁止的方式对亚文化群体进行管控,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之中,以瓦解青年亚文化群体带来的消极抵抗性与批判性。青年亚文化研究视域之下的“躺平”是青年群体对阶层秩序的一种抵抗形式,在社会竞争加剧的当下,青年群体以传统的学业和就业等方式实现阶层跨越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在媒体对“中产阶级”的房车等物质化配置的过度渲染中,高物价、高房价与低工资的社会现实不断冲击着成长中的青年群体,使其产生逃避的倾向,索性选择主动退出竞争的“躺平”姿态,逃避跃升中产阶级的困难。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产生了理论嬗变,后亚文化研究兴起,更关注技术与符号消费之下的青年亚文化行为。学者从生活方式、新部族、亚文化资本等角度,进行青年亚文化的理论再造和创新[9]。后亚文化理论尝试摆脱社会结构中的阶级捆绑,从个体化视角解读青年行为。其所关注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不再具有强烈的阶层反抗色彩,更强调对现代化都市中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行重新解读,而生活方式就是个体进行自我定义的重要途径。现代青年群体通过生活方式的展演来进行身份定义,打造亚文化资本,这种“生活的展演”往往表征为一定的媒介符号。从后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将青年的“躺平”行为视为是对现代生活“庸俗化”和“程式化”进行抵抗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实现与主流共同体之间的区隔。
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研究视角下的青年群体以亚文化资本抗争阶层秩序,但在新媒体技术语境之下缺乏相关的实践研究。而后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躺平”则是青年个体生活方式、亚文化资本的“展演”,与阶层秩序无关。两种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需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对我国社会语境下的“躺平”现象进行分析,通过探究“躺平”现象的媒介社会表征及其自我实践,剖析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躺平”的,进而为时代焦虑下的青年群体指明前进方向。
(二)“躺平”的社会背景:“内卷化”话语变迁
从当前的社会背景来看,“内卷化”成为主流的社会语境。由竞争到“躺平”的话语变迁过程,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卷化”。“内卷化”(involution)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指的是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只能通过内部的复杂化而继续下去。一般用于形容某个领域或系统中发生过度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10]。将“内卷化”研究提升到社会结构层面的是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他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11]。中国学者黄宗智是最早将“内卷化”概念用于中国社会现象的分析,将中国与英美的基本治理哲学进行对比,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12]。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内卷化”的阵痛,当社会整体创新不足时,无意义的精益求精、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消磨了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青年群体在互联网上对内卷化进行了热烈讨论,主要围绕就业、工资、购房、物价、情感等话题展开,其基调以焦虑、消极等负面情绪为主。在内卷环境之下,青年群体面临的竞争压力激增,只能不断地努力以避免被淘汰的可能,但付出与收获之间往往不成正比,于是“躺平”“佛系”等现象在青年群体的话语场域中盛行起来。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将目光局限于这种“原地踏步”式的竞争,无益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大多数青年群体正处在由大学校园向职场跨越的新阶段,他们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跃升,实现对“白领-中产阶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C·莱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所言,新中产阶级被看作整个现代社会的征兆或象征[13]。但新中产阶级无法从工作中获取他们内在的意义,不能自主掌控工作行为,而是习惯于听从指令,甚至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兴趣[14]。青年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时,自身的社会结构位置和对自我的社会期望也在不断调整,对于中产阶层的认知难以达成共识,也难以在“中间”概念上建立共同的标准。因此,在丧失自身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内卷环境下,青年群体对于自身阶级地位的社会认同诉求则更加激烈,而阶层跃升不畅带来的阻碍使其对于自身的话语呈现和身份构建出现了社会性转变,“躺平”现象背后是青年群体对阶层跃升的焦虑和恐惧。
二、“躺平”的符号意涵:“自嘲”与“低欲望”的风格传达
英国伯明翰学派使用“风格”一词对亚文化进行研究,风格被视为亚文化的“图腾”和“第二层肌肤”[8],青年亚文化通过形成风格化的仪式抵抗成为一股强势的社会力量[15]。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理论认为风格由形象、品行和行话三个要素组成[8]。形象包括服装、发型、装饰物等,品行即行为、仪态等,行话则由言语、词语等构成,由此构建了青年亚文化的“图腾”。“躺平”现象是一场由具有网络叙事能力的边缘青年群体掀起的对“内卷化”进行软性反抗的青年亚文化运动,其所倡导的“躺平主义”以追求自我真实的先锋实验的形象,跨越了消费主义和科技主义的束缚,追求回归自我本真的简朴主义;并以“自嘲”的话语风格在网络上以文字、图片、视频等生产象征叙事,通过在线的仪式展演构建“躺平青年”群体的认同实践,进而形成了一种“低欲望”的文化风格。
(一)“躺平”的消极抵抗:“自嘲式”的话语风格
自嘲即自我嘲解,是一种进行自我反讽的策略,也是一种进行表演和社交的手段。随着网络交往的扩散,自嘲网络热词引发了一场青年群体的狂欢热潮。以2021年的网络流行语为例,如“夺笋呐”“普却信”“鸡娃”等,“躺平”更是以其独特的价值意蕴出圈,其话语表现更侧重于自我排解式的消遣和嘲讽,带有一定的娱乐消遣色彩,以集体狂欢的形式消解了主流的严肃话语。
一方面,“躺平青年”的自嘲是社会阶层固化和自我价值迷失之下的压力排解。青年群体的自我嘲讽,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进行的一场“情感宣泄式”解压,也是对强势话语体系的解构。网络自嘲的话语形式,既是网民自我展演的新渠道,又是当下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反映。网络的发达使得许多草根自媒体“一炮而红”,而大多数普通青年难以凭借在网络上的社交行为和自我展演实现自身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由此,媒介实践与生活实践之间有着极大的反差,青年群体在面临现实生活各种压力冲击的同时,意识到自身向上流动的“阶级跃升”难以轻易实现,其自身尊严感不断降低,对于自我在网络社会中的“数字劳工”身份也感到价值的丧失,进而产生身份焦虑。而自嘲作为青年群体自我表达的方式,能够通过轻松的话语和戏谑的语言使他们感到愉快,适当释放压力,因而,当追求自我舒适的“躺平”话语一出现,便极大地迎合了青年群体的需求,他们借以“自况”,制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躺平”文化奇观。
另一方面,“躺平”式的自嘲也是在为自身的消极逃避寻找借口,通过低成本的“口嗨”表达内心的不满。“躺平”式的自嘲并非只是外在的自我矮化,其深层心理机制是对社会的失望以及对未来和人生整体性的否定。他们以身份降格和拒绝“内卷”的姿态来消解主流话语的规训,在拉低自我期待的同时,达到舒缓压力的目的。归根到底,“且躺且珍惜”的价值取向源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不满,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消极暗示的不断强化、自卑情绪的蔓延和各种不良心态的生成。由此,青年群体的自身主体积极性在“躺平”热潮中不断消解。青年群体承受着时代演化的压力,其自嘲式的话语狂欢呈现出一种自我审视的娱乐精神,传达出对社会阶层分化甚至阶层固化的结构性矛盾的“软性抵抗”。但若将纯粹的“躺平”口号演化为行动上的“放弃”和不思进取则让青年丧失了对自身生命价值进行思考的能力,更容易导致其价值追求的偏离。
(二)“躺平”的符号表征:“低欲望”的外化机制
青年群体的“自嘲”是一种自我调侃的话语,也是“低欲望”文化风格的外在表现。“低欲望”最初由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提出,描述的是日本新一代青年不愿重复父辈的生活,追求自我个性发展,因此选择不婚不育、不买房的低欲望生活[16]。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英国的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美国的归巢族(Boomerang Kids)等都与“躺平”思潮不谋而合,可见追求舒适的“躺平”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其根本思维是一种保持“低欲望”特质的自我满足主义。
在价值色彩上,“躺平”现象被认为是青年在表达“低欲望”的叙事意义上对抗内卷社会的方式。面临强度高、时间长、薪酬低的工作压力,房价飞涨、存钱困难的置业压力,以及养老负担重、育孩成本高的社会压力,青年人选择性地消极懈怠,以一种“卷不动”的姿态,不再执着于“跑着”向上的人生,而是选择“躺着”,呈现出人生目标的“低欲望”的特质;甚至在面对外界的激励政策时,不反抗、不回应,安于自己平稳的生活。正如《现代性之隐忧》一书所提及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权利以他人不可能驾驭的整套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形态[17]。简言之,“躺平”现象是年轻人以一种更舒适的姿态,与自我和生活达成的和解,是对自我现状感到满意的“低欲望”状态。然而,纯粹消极意义上的“躺平”带有一定“文化虚无主义”和“价值虚空主义”的色彩,对其带来的青年亚文化的无意义泛滥和青年的自我放逐需要更加警惕。
在意指实践上,“躺平”现象的亚文化特征如同拉康“滑动的所指”,投射在青年群体“能指”的空间扩展中。“躺平青年”因其“不争、不抢”的外在表现,呈现出一种“低欲望”的气质,投射在主流文化中则被认为是自甘堕落的选择。但于他们而言,经过自我反思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这种“躺平主义”的语义所指并非外界所描绘的单向度的静态呈现,对于“躺平”的意指存在多元维度解读,可以是纯粹表达“不想努力了”,抑或是“不按照大众所要求的方向去努力了”。后者的意指在青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接受共鸣”,这种社会心理意识所具备的“去中心化”特质,带有一种对抗主流规训的亚文化形态意味。在话语能指层面看似代表了青年人的消极、悲观态度,但就其本身的意指实践而言,仅仅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焦虑和迷茫。因此,“躺平主义”在意指层面代表了年轻人对世俗规训的低欲望,其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消极意义并不高。
(三)“躺平”的新部族叙事:自我认同的身份抗争
“新部族”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新部族主义”假定当代人类已发展成部族式的社会、而非大规模式的社会,因此人类的社会网络将形成独特的“部族”[18]。传统社会的文化群体对应着当代现实社会的群体部落,其交往形式以身体在场为基础。但青年群体在后现代的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性增强,形成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社会,青年亚文化群体以网络为链接、以新媒体为集体模具,根据气氛、共通的精神状态形成集体情感,此时,该亚文化群体也同时具备了流动性和碎片化特征。
在部族的身份认同上,“我是谁”是流动的不确定社会中注定没有答案的宿命追问,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对身份的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19]青年生活在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媒体和消费已经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20]。“躺平青年”以文字、图片等为符号表征,以新媒体为传播载体,以“躺平”为群体认同的情感召唤和情绪感染,通过打造自我风格的“躺平”标签,实现群体身份区隔,完成追寻身份认同的集体话语叙事。霍尔提出年轻人对风格的追求实质上是对生活模式的认同追求的一部分[21],在追寻部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们也找到了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模式。
在反内卷抗争的形式上,“躺平青年”以形式上的不抵抗形成非传统意义上的抵抗,由此形成“不抵抗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抵抗”。当主流规训限定了“阶层”的解释框架,“躺平青年”内心隐藏着对阶层跃迁的焦虑和对生存矛盾的恐惧。在虚拟语境中的“躺平主义”话语,承载了青年群体对房价飙升、996工作压力等方面的负面情绪,他们以形式上的“躺平即正义”将自我从紧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以自我选择的低欲望生活方式代替社会结构的模式化行动,进而减轻社会内卷化带来的焦虑和恐惧。通过这种对抵抗意识的挪用构筑自我生活方式,表达自身态度,显示了其对主流文化的消解。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言,这种文化资本包含了支配者的意义与快乐,且以抵制性力量的姿态出现[22]。
三、“躺平”的软性抗争:“反消费主义”的自我实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助推,消费主义(Consumerism)对人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渗透之势,正如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23]在后现代语境中,整个社会异化成了一个物品皆为符号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所构建的符号成了一种“获得愉悦的活动形式”。而青年群体厌倦了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满足和表面愉悦,以其特有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反消费主义”的软性抵抗浪潮。他们在互联网上自发形成了“反消费主义”的共同体,如以“抠门”为主题的“消费主义逆行者”豆瓣小组和以“极简”为追求的“极简生活”小组。青年群体在主流消费文化的羁绊中,秉持着自我调侃式的抵抗特质,对主流结构的权威进行解构与重塑,解决了媒介实践与生活实践的矛盾,并弥补了社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迷失,实现了价值的重塑,构建出新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图景。
(一)“躺平”的消费观念:消费主义的理性解构
面对工业社会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冲击,青年人的生命共同体意识空前加强,更看重身心的整体健康,企图改变被工作和生活压力驱赶的焦虑状态。他们的“躺平”理念,是一种自我的理性回归和自我价值的重新审视。对于工作,他们不再盲目自我透支,对于生活,则不再热衷于成为消费主义的附庸,而是选择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生存。这并非代表“躺平青年”追求真正无欲无求的生活,而是表明他们拒绝被物质化,拒绝通过物质的消费获得自我价值存在的确证。
在现实逻辑上,反消费主义实际上是“躺平青年”的被动话术。正如鲍德里亚所言:“鉴于物的物质性的存在,它首先应该具有持久性的功能,具有‘持久地’表征社会地位的功能。……在其限度内,也是一种既得的、永久的社会地位。”[24]青年群体对反消费主义的追求正是由此种社会现实所致,大部分青年群体面临工作收入低、生活成本高、购房门槛高等社会现实,他们被媒介营造的美好物质符号世界所吸引,但大多超出自身实际能力而无力承担。因此,为了降低媒介实践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差距,反消费主义成为他们化解焦虑和压力的新路径,是青年群体对消费主义的有效抵抗。
在消费观念上,“躺平”是青年群体在认清社会现实后对消费主义话术进行的理性解构。他们不再刻意追求物质主义带来的身份消费,践行实用消费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的物化社会助推了拜物教的盛行和人的异化,青年群体厌倦了消费主义和盲目物质追求带来的自我满足和身份伪饰,拒绝通过名牌、价格来达到自我身份标榜,认为其实质是阶层恐惧和自我异化的身份焦虑,追求舒适、真实的自我表达。因此,他们秉持“断舍离”的人生信条,以此抵抗消费主义的裹挟,选择简单的品牌、舒适的生活,“躺平”既是其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真实自我的呈现。
(二)“躺平”的自我实践:极简主义的模式借鉴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当今社会已经从崇尚时尚、奢侈品,经历注重质量和舒适度,进而过渡到回归内心的满足感、平和感,进入了“第四消费时代”,“躺平”现象正反映了“第四消费时代”下青年群体追求简约舒适的消费实践。
在模式参照上,“躺平主义”与日本社会的极简主义存在底层共通的逻辑链条。日本低欲望社会中的青年追求“无印良品”,即“无品牌的好东西”,极力淡化品牌意识;厌倦了消费主义的青年群体则对品牌的热衷进行解构,奢侈品并不能为他们带来自我满足感和刺激感。他们贯彻“简单实用”的理念,崇尚简约化、精神化消费,力求达到内心平和的自我满足状态,形成趋于自然、简约、质朴、共享的消费观。“躺平青年”用简化的消费美学对抗固化的社会阶层消费,展开软性抵抗的叙事表达,在消费和生活模式上践行极简主义的人生逻辑,形成了具有共同认知的群体,如豆瓣“极简生活”“极简主义”等小组。
在自我实践上,“躺平青年”对自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实践都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他们洞悉智能化推送机制,极力规避互联网精准打造的“物质囚徒困境”。在大数据背景下,根据用户画像打造的“欲望推送机制”强力捆绑消费者的购物选择,推送各种适合人们综合需求的商品。“躺平青年”能够树立工具理性,洞悉这套推送机制的逻辑陷阱,购买刚需物品,避免“被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在消费实践上,他们对于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物品保持淡然态度。过度物质化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物化攀比,进而强化消费“鄙视链”,他们选择践行非功利的朴素主义,拒绝消费主义的裹挟。
四、“躺平”现象的研究结论及反思
从实际现象来看,“躺平”正成为青年群体时代焦虑的情绪宣泄阀门,但现实中对其贯彻到底的可能性极低。事实上,极少数人能做到真正的“躺平”,大多数人无法跨越横亘在“躺平”与奋斗之间的矛盾鸿沟。“躺平”不仅是青年进行理性自我构建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脱嵌”的叙事症候,其行为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弥漫着负面的避世情绪和消极的精神取向。为避免个体“社会脱嵌”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危机,需要防范其负面的社会影响,消解其中的消极意义,引导其向主流文化靠拢,“脱嵌”是为了更好地“嵌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理解青年所思所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瀚天空,也要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地走上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当青年思想认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字路口时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25]因此,对于“躺平主义”中的消极话语抵抗,需要在充分发挥主流话语作用的基础上,激活青年群体自身的积极性,规避其消极性。
(一)发挥主流文化价值引领作用
在“躺平主义”的话语实践中,要进行积极的话语介入,进行正面价值引领,避免“躺平主义”话语中的消极因素进一步扩散。青年选择暂时性“躺平”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难以对其实现全方位的逆转。从“躺平”到“站起来”,是一个内在的自我反思、自我觉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主流价值的引领也十分重要,正如灯塔之于海上迷途之舟。因此,对于“躺平青年”,外部激励是极为有效的,如在主流宣传中,将“躺平主义”的亚文化与主流话语相“接合”,使其具有我国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色。可以将“四史教育”和“爱国教育”引入“躺平”的青年亚文化领域,将青年不争不抢、淡泊名利的追求与道家“无为而为”的思想相结合,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转变“躺平主义”的消极话语。
(二)提升媒介价值塑造的社会功能
应发挥媒介的引领作用,传播正向、积极的价值观。在对“躺平”现象的社会症候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疏通阶层跃升的渠道,淡化盲目的阶层追求热潮。媒介对于“一套及以上中高档住房、一辆及以上中高档私人轿车以及过着体面的生活,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标准”[26]的普遍化、庸俗化、单一化的“中产阶层”叙事,使青年群体逐渐沦为物质的奴隶。因此,在进行主流文化的媒体报道时,要避免媒体报道中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和渲染,缓解“物化社会”的拟态环境带来的时代焦虑,同时也要增强对青年群体积极行为的曝光,提升青年的自我效能感,塑造积极的情感认同。
(三)青年群体自身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人不仅是社会意义的结构性产物,更是有能力进行社会建构的主体。面对消费主义和物质欲望的捆绑,日本青年采取“断舍离”的方式追求“小确幸”式的简单生活,我国青年群体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也应结合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辩证的视角审视自身欲望和物质实际之间的距离,做出符合历史价值观和哲学辩证观的方法应对和选择,使自身既具有纵深的历史视野,又能在反观现实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人生态度和路径,做到知行合一。
对“躺平”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青年群体以“躺平”自嘲,解构主流文化的强势规训,并通过建构新部族找到自我价值认同的确证,进而建立缓解自身焦虑的新生活方式;此外,他们通过参与青年群体共同构建的“躺平主义”话语叙事,抵抗消费主义的诱惑,从而践行“极简主义”的新消费模式。可以看到,其社会存在是由主客观双重因素所致。在客观层面,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内卷化”症候致使年轻人的自身奋斗变得异常艰难,他们面临着时代焦虑的裹挟;在主观层面,年轻人在面临困境和竞争时选择“他强任他强”的“躺平”心态,通过自主淡化竞争,降低自身的焦虑和困窘。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我的生活方式,但也要规避“躺平”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因此,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充分利用媒介的优势,塑造青年群体正确的价值观念,构建清朗的网络环境,以此提升青年群体对自身生活和能力的清醒认识,最终促成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为国家发展培养坚实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