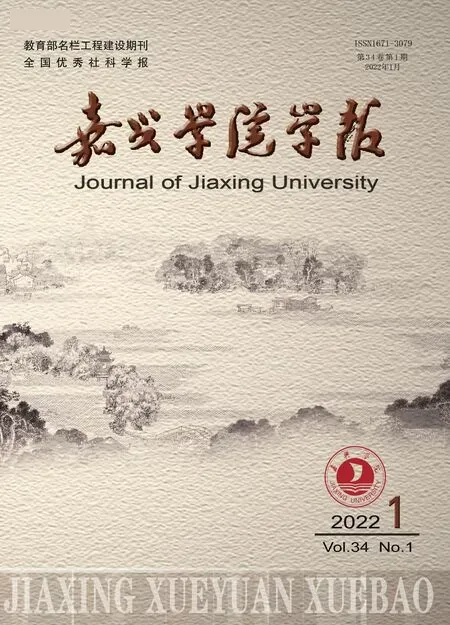根植诗教传统,熔铸红色基因
——论革命家诗词教育与高校课程思政的融合
马腾飞,洪 坚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我国是诗之大国,有着历史悠久的“诗教”传统,儒家的“诗教”侧重强调诗歌和政治道德、社会伦理的关系,为后世历代所宗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优秀的遗存,以诗歌承担文学审美、道德感召的思想教育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在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诗教可为当下的高校人文教育、思政教育提供深厚滋养。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文学经典与心史华章,革命家诗词在高校课程思政中有着极大的文化资源优势,特别是在德育、美育、“四史”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内均大有可为。将革命家诗词融入高校课堂,能够助推当代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铭记革命初心、明确奋斗方向,从而更好地完成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一、 现代“诗教”精神内核与高校课程思政的契合
“诗教”即以“诗”为教,是古代中国绵亘两千余年的文学理论与教育传统。孔子曾提出了包括“思无邪”在内的一系列诗学主张, 其“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诗学理论为后世所熟知。自春秋以来,中国传统诗教的教育文本、教育方法均经历了漫长演变,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早期诗教所采用的教育文本是《诗经》。从《论语》中相关篇章可知,儒家理念是通过诗教培育出“温柔敦厚”“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博雅君子。秦汉以降,以孔子解诗思想为原则,经过历代经学大儒的阐释提倡,诗教内涵日益丰富。唐宋之后,诗教的含义进一步泛化,其“诗”不单可指《诗经》,进而可泛指所有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诗歌作品。学者方长安指出:“凡是以诗歌作品为底本对人进行教育,传扬‘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观念,以礼义规范人的言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使社会机体得以有序运行的行为,都属于诗教。”[2]理应承认,诗教传统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挥了维持国家正统思想、宣扬儒家道德、培育君子典型人格的教育功用。
自明清以来,随着思想理念的停滞与僵化,集权统治下的诗教已经充斥着衰朽落后的封建内容,扼制了文人士子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和“文以载道”观的命运类似,传统诗教观在现代文人群体中饱受质疑与挑战,甚至一度被贴上了“封建残余”“旧文化”等负面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新派文人虽猛烈批判儒家传统,可他们重开启民智的教育导向与古代先贤“重教化”是一脉相承的。龙泉明认为:“‘重教化’所包含的实用功能观念仍存留于现代诗人的意识之中,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3]从立身为人来看,现代作家、教育者对民族、大义的自觉担当,与古典诗教的精神内核确实具有一定共通性:梁启超文学启蒙的精神资源,依然源于古典诗教的“教化”传统;[4]陶行知的诗歌教育“充分吸收传统教育中诗教的精华,取其神明,光耀现实”[5]。与此类似,朱自清、顾随、闻一多等大批文人、教育家兼具新、旧文化的涵养,他们能够挖掘传统诗教中注重讽谏、关注民生之进步观,又能以宏通的文化视野融合现代思潮,在“诗教”的阐释与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民国以来,诸多教育大家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诗教传统在新时期同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必须经过现代意义的“转型”,才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
“国学热”虽然已经持续多年, 但在“数据至上”“流量为王”等观念席卷全球的当下,浮光掠影的快餐文化日渐侵蚀着当代高校校园。在多媒体文化的冲击下,各专业学生对文学经典的深度阅读与思考能力实则大不如前,“诗和远方”日渐成为了大众心目中无比向往的精神奢侈品,这使得人文素质教育的推进变得困难重重。不难看到,部分高校校园的人文生态有恶化的趋势,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气质有待提升。在部分高校学生群体中,价值观紊乱,缺乏爱国热情与社会良知、以“佛系”“躺平”为借口的消极处世、逃避责任担当等不良现象时而得见。针对以上诸多问题,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要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可以看到,上述《纲要》正是把握住了传统儒家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文化主脉,并将其转换为符合当下新时期要求的精神风貌和话语体系。
自2006年“诗教”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古典诗词的文化普及和教育有了长足进展。近年来,央视《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热播,也充分说明了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现代诗教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温儒敏先生提倡把“诗教”传统和现在的语文教育打通,并指出:“诗教毫无疑问就是培养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以及完成审美教育最好的方式之一。”[6]然而,在中小学阶段,本应大力深化、推广的诗教却举步维艰,很难落实。一方面,由于年龄原因,中小学生涉世未深,相应的文学、史学等知识面有限,他们对诗歌的艺术品位、人生感发很难进行深层次的体验;另一方面,在应试教育阶段,诗教也往往变异为强制性地背诵古典诗词名篇以及陷入默写、鉴赏古典诗词的题海。进入高校后,大学生正处于人格、思想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均亟待开展。因此,应将“诗教”融于高校课堂思政,建构富有中华文化气质的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体系,从而实现传统诗教文化精髓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古今”融通。
高校人才培养是育德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古代诗教,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是维护时代需求的道德伦理秩序,鼓励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培养文质彬彬、进德修身的君子人格。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应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优化课程思政的内容供给。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7]作为一种教育传统,诗教的文化内涵可以对以上内容进行多方位的对接,同时也不难转换成新时代、新社会所需要的诗性文化品格。现代诗教的精神内核应当是以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教育范畴,以促进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为目标,积极鼓励其发扬和增加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担当意识,由此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根脉所在,建构具备现代意义的诗教,诗词文化在当今高校课程思政教育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革命家诗词在高校课程思政教育中的文化资源优势
与诗教跌宕起伏的命运相似,作为传统文体的旧体诗词在20世纪同样坎坷多艰、几经沉浮。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作为传统文学主要载体的旧体诗词曾经被视为落后、僵化的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界曾对其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纵观民国以来的中国诗坛,尽管旧体诗词依然有着极为强大的创作阵容与海量作品,但在以白话文学为主要论述对象的现代文学史视野中,20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大都处于被悬置、忽略的状态。[8]尽管如此,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背后,旧体诗词创作和诗教依然有着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民国时期的文人大多有着深厚的旧学传统,不少作家均保留着写作旧体诗词的习惯。即便是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臧克家等现代文坛主将,也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始终未能“忘情”。另一大显著的文化现象是,20世纪的革命家群体中涌现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创作者,他们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20世纪的文化史、革命史留下了诸多经典诗篇。
应该承认,旧体诗词是最富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20世纪老一辈革命家身处新旧之交,大多有着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其诗词创作蔚为大观。这一创作群体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为代表,也包括陈毅、叶剑英、董必武、刘伯承等开国元勋。毛泽东《沁园春·雪》《七律·长征》、陈毅《梅岭三章》等革命家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语文教材,为广大师生所熟知。但如果立足“20世纪革命家”这一范围,除革命领袖外,这一写作群体也应当包括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邓恩铭、叶挺等有少数旧体诗作存世的革命先烈。他们是历史大潮、革命伟业的见证者与亲历者,其一生奋斗包含着九死未悔的奉献精神与革命意志,其诗词是革命历程的血泪心声,值得后人铭记。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20世纪革命家诗词的编集、研究有了长足进展。类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学习资料》《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鉴赏辞典》的革命家诗词选本、资料汇编已有多部问世,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革命领袖的诗词别集、诗歌选本也得到了很好的整理。在学术研究领域,革命家诗词的相关研究虽然稍显滞后,但近年来也涌现了诸多可喜之作,如方竹的《老革命家法治诗词》(2016),韩晓青的《老一辈革命家诗词中的革命精神》(2017),程国君、李继凯的《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及诗史价值》(2020),肖百容、张宁的《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形象塑造》(2021)等。这些成果足以为当下革命家诗词的文学性、革命性、思想性探讨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为高校的课程思政教育提供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并能够开发利用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与高校思政课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9]作为闪耀着“红色基因”的文化资源,革命家诗词作品有无以替代的重大优势。
首先,革命家诗词承载了革命者对伟大思想、崇高理念的坚定信仰,可以为当代师生筑牢信仰之基。在兵燹纷乱的战争年代,面对家国之危局,无数革命者始终坚守信念,坚持革命初心,甚至不惜舍生取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诗词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学表达。夏明翰在英勇就义前高呼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义诗》),一直以来鼓舞着诸多仁人志士。除此之外,革命者还有诸多修辞立诚的瑰玮诗篇,如刘伯承《出益州》有诗句云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10]252邓中夏《过洞庭》云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10]258、朱德《赠友人》云“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10]104等,这些诗作或作于山水登临之时,或作于战事危急之秋,革命家在古典诗词中融入“共和”“共产”“红旗”等革命意象,寄托了他们在至暗时刻伟大、光明的信仰,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可为读者唤醒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
其次,革命家诗词昭示着革命者对家国、民族命运的使命担当,可为当代师生注入奋斗之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画卷,革命家诗词是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诗史”,生动再现了峥嵘岁月中革命家的艰苦奋斗,也寄托了革命家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北洋时期,李大钊在《太平洋舟中咏感》中写下了“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10]244鼓舞吾国少年,匡时救弊;举国危难的抗战时期,陶铸在《大洪山打游击》中疾呼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10]430,朱德在《太行春感》中则高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10]93稍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谢觉哉在《夜起偶书》中呼吁“一贯仁勇智,三头笔锄戈。要将涓滴献,助彼海天波”[10]162。这类诗词用精练的语言,生动诠释了革命家胸怀家国、心忧天下的担当精神与奉献精神。在“躺平”心态日渐流播的当下,革命家诗词可以鼓舞奋斗之魂,恢弘志士之气,是高校理想信念教育、责任担当意识教育的强心剂。
其三,革命家诗词凸显了革命家对党性品格至纯至萃的不懈追求,可为当代师生指明修身之径。20世纪以来,革命家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终身,历尽磨难而九死未悔。诗为心声,方可言志,革命家诗词中的许多篇章凸显了艰难时期老一辈革命家的党性品格,闪耀着烈火真金般的革命精神。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诗中称赞朱德“欲挽狂澜于即倒,不随流俗与同沦”“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10]185,点明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直节风骨,堪称是朱德同志人格、党性最为精当的概括。陈毅《题西山红叶》诗云:“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10]384全诗以西山红叶为礼赞对象,立意高远,体现了革命者勇于奋斗、不畏风霜的高洁品质,闪耀着久经考验、泥而不滓的党性品格。无论是大暗弥天的旧时代还是激情澎湃的新时代,这些诗句中闪耀的党性品格理应成为全体党员的道德风范与党性操守。
古典诗词言志、抒情,其简洁、凝练、隽永的语言美感在文学、审美教育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功用。当下的“现代诗教”应当通过文学教育,让学生树立崇高的奋斗理念与精神信仰,培育其对家国、民族命运的使命感、责任感,指引学生锤炼高尚、纯粹的道德品性。由于特殊的历史年代及特定的文化内容,革命家诗词结合文学性、历史性和思政性于一体,在课程思政中比古代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有更为显著的优势。可以说,革命家诗词作品既是建构“现代诗教”传统的宝贵财富,也是课程思政教育中重要的文化资源。重视革命家诗词在高校的传播、教育,正是以其中的红色基因填补传统诗教在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落差,对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有着重要的建设意义。
三、基于“诗教”的实践:革命家诗词融入大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方法路径探索
革命精神和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教育感染性和历史继承性,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主要创作形式的革命家诗词兼具这两大特征,理应在课程思政教育中得到有效发挥和及时运用。将革命家诗词教育融入大学课程思政教育,可以高效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逐渐在高校范围内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诗教传统”,对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修养的涵化、引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历史等课程的“引诗为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课程是高校思政课程的重心所在,引导革命家诗词进入思政类课堂,旨在拓宽学生的人文视野,加强师生间的共鸣,并进一步考察学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能力。20世纪革命家群体中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诗词洋溢着哲人般的学理生趣,在课堂上引入这类诗词,有助于学生对基本哲学原理的深入理解。周恩来《七绝》中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0]80,“面壁”用禅宗初祖达摩苦修之典,“破壁”用张僧繇画龙点睛之典,很好地阐释了哲学意义上的“量变与质变”。毛泽东《送瘟神》颈联云“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10]55,气象雄大,想象瑰奇,生动诠释了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在教学中可将这些革命家诗词作为典型案例,采用问答或者其他互动方式增加教学趣味性。
历史意义、奋斗精神是革命家诗词的两大特色。革命家诗词作为近现代历史文献的一部分,对近现代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进行了及时书写或重要关联。“近现代史纲要”课堂理论讲授中,可以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丰富教学场景,巧妙利用革命家诗词进行发散思维而展开诗教。如在抗战史的讲授中,可举朱德的《寄语蜀中父老》为例:“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10]95此诗作于1939年冬,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该诗前半写冬景,后半写时事,描绘了我军战士衣裳单薄但热血满腔,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奋勇杀敌。无论是文学性或是革命思想性,该诗堪称杰作。再如,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毅赋《七大开幕》一诗云:“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11]所谓“百年积弱”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到1945年约百年光景。“八载干戈”指的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该诗首先回顾了近现代百年屈辱史,点明抗战之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的伟大功绩,继而热烈歌颂了指引中国未来前进方向的延安精神。教师将这一类诗词作为文化背景在近现代史课堂上进行穿插讲授,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识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点,并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效果。
(二)文学课堂上的案例举隅
革命家诗词的本质是文学作品,虽然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作品是非“科班出身人员”所写就,但革命家诗词中富有文学性、艺术性的经典作品不在少数。身处新旧时期交汇点的20世纪革命家,其诗词亦古亦今,亦旧亦新,可以成为高校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课堂中文学文本的重要案例。
毛泽东同志尤长于词,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佳作迭出,不少篇章已经在中小学阶段编入教材,成为师生所共知的诗词文本。在文学鉴赏和诗词格律的讲授中,这些词作完全可以成为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典型材料和文学分析样本。以毛词名篇而论,《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早已广为人知,对二者进行句法对举、字数统计,可引导学生深入领会“词牌”“长调”的定义。再如,讲授“词牌”和“小令”时,现今学界公认的最短词牌当属《十六字令》,遗憾的是古人未见经典之作,而毛词中恰好有3首名作可以列举,其中第一首最为脍炙人口:“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10]29此词虽为小令,却博大雄浑,足以使学生进一步领略革命家宏伟的襟怀和抱负。
在部分词牌的作品中,毛词往往能一骑偏师,与古人争胜,在讲授古代文学史时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材料补充进去,拓展学生理论视野。如清代邓廷桢《双砚斋词话》曾云“词有不可填之调”,并进一步指出:“词调合小令慢词计之,不下六百有奇,无不可填。然亦有断不可填者,如太白《忆秦娥》……已成千古绝调,虽有健者,未许摩垒。”[12]前人认为部分词牌有着特定情境内容,后人无法还原,因此,千百年来作者虽众,却罕见佳作。然而,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雄浑悲壮,风格劲健,力破古人藩篱,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早已成为革命者的奋斗宣言,其气势、意境均不输于李白原作。再如,毛词《卜算子·咏梅》是对南宋诗人陆游咏梅词的“反其意而用之”,一改原作的孤高、衰飒,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家的斗争豪情和奉献精神,将二者在课堂上进行对举,可以比较古今异同,帮助学生精准领会文学发展中“继承”与“求变”相统一的创新精神。
(三)其他课程中的穿插点染
诗教是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其应用范围不应止步于文、史、哲等人文专业课堂。高校中的诗教实践,理应脱离中小学阶段的讲授背诵、默写鉴赏的固化模式,而应采用潜移默化、涵润滋养的方法。因此,革命家诗词教育进课程思政课堂,需要积极和其他文化课程结合,在不同学科领域探索融合模式,力求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这里试以高校的书画课和旅游文化课作为案例。
传统书画与古典诗词同属艺术领域,可以适当打破学科壁垒,与革命家诗词互为融通。书法、绘画的理论课、实践课均可适当注入革命家诗词的文化元素。如在建党节、国庆节或其他重要纪念节日前后,可引导、鼓励学生以革命家诗词为内容进行书法创作,或将革命家诗词的诗意、诗境作为山水画、油画的摹写素材,在活动期间选择佳作展览。在书法、绘画理论课上,林散之、启功、傅抱石、石鲁等现当代名家有着大量以革命家诗词为内容、主题的书画作品,可以选择其经典之作进行集体观摩和专题讨论,并间接介绍、解读相对应的革命家诗词内容和革命历史时代背景,讨论诗情与书法、画意的融合。
再如,在旅游文化专业课上,革命家诗词同样是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渠道。革命家足迹遍天下,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诸多诗篇,如李大钊的《咏玉泉》,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水调歌头·游泳》,朱德的《太行春感》《游七星岩》,董必武的《三台即景》《游镜泊湖》,谢觉哉的《重游华清池》,林伯渠的《游爱晚亭》《偕友游吉林龙潭山》《西湖纪游》,邓中夏的《过洞庭》,叶挺的《过黄山》,陈毅的《登大庾岭》《淮河远眺》《过洪泽湖》《莫干山纪游词》,叶剑英的《长江大桥》《蝶恋花·海南岛》《游肇庆七星岩》,等等。林伯渠的《游爱晚亭》有云“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10]207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担当与忧国意识;谢觉哉的《重游华清池》有云“春秋浴泳多佳日,从此骊山不帝王”[10]165,展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帝制一去不返的新时期新气象。
总之,革命家诗词是值得精读精讲的作品,在课上穿插讲授,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也可以将其作为旅游胜迹的诠释词进行诵读与识记。
四、余论
为确保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深远性,课程思政教育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手段和内容范式。革命家诗词是我国近现代革命进程中一大显著、独特的文化现象,其生成机理、流播过程、思想内涵均有待学界深入探讨。从教育功能来看,革命家诗词文化对当代高校师生的审美能力培育、理想信念教育、价值观塑造、党性指引等多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引导革命家诗词进入思政课堂,不仅是对现代诗教进行理论尝试,同时也对新时代教材的编撰和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与挑战。
在教材编撰上,如何针对专业课程进行革命家诗词的遴选收录,选择哪些教育性强的诗词作为范例,是在教材主体或是注释、插图中体现,还是在课后习题、期末考查中作为引文材料,均是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对于教师而言,特别是对党员教师而言,在平时的党史学习中,更需要广开视野,选择相应的革命家诗词读本进行精读与学习。只有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与革命家诗词储备,更好地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教育上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做到德育、智育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