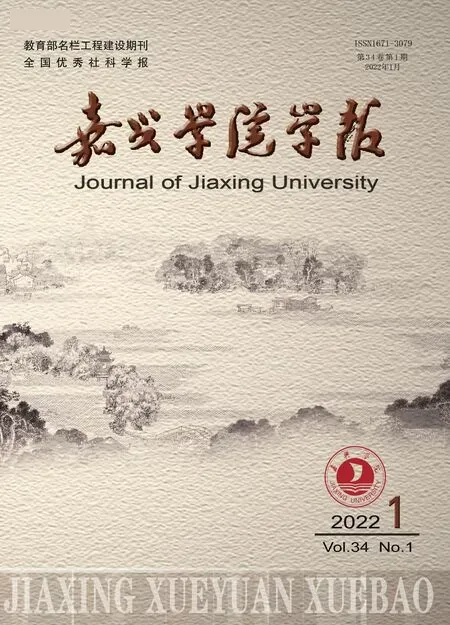近20年“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综述
彭瑞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是一场发生于1922至1927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以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成立为起点,由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反对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在社会蔓延的思想论战,逐步发展为包括收回教育权、反对不平等条约,交织着五卅运动、国民革命的反帝爱国性质的政治运动。在“非基运动”中,主要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国家主义派分别依据不同理论,与自由主义及基督教相对垒;而基督教徒中又分化出部分人士,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反对外国传教差会,掀起“本色教会运动”。1927年,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内政治形势急转而下,“非基运动”也偃旗息鼓。
20世纪,学界曾对“非基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影响作了简单的梳理和解读。得益于更多历史资料的发掘利用,尤其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相关档案文献的翻译及出版,近20年来学界对“非基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当前,学界对“非基运动”爆发的原因、领导力量及其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对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团体及政党的研究也有了较大拓展。如杨天宏的《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成为“非基运动”研究的重要著作,唐晓峰所编的《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2]则为“非基运动”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希望对既往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评析,以期对更进一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非基运动”爆发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如基督教在华活动激化了国内的“非基”情绪、新思想的传播为“非基运动”提供了内在动力、民族主义的生长成为“非基运动”发生的社会基础。[3]
孙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非基运动”的政治、文化、社会及伦理背景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认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及教会学校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是导致“非基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4]“非基运动”的序曲和导火索即1920年前后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的争论以及1922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文献[5]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历史回顾,使得“非基运动”爆发的背景更加清晰、立体。文献[6]从意识形态的观察视角出发,认为“非基运动”源于“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革命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意识形态争夺大众,其发生并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非基运动”的新角度。
陶飞亚关注“非基运动”爆发的政党因素,依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披露的共产国际代表信件和报告,提出共产国际直接催生了“非基运动”,中共则在合法组织如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掩护下领导了这场运动。[7]对此,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存在明显悖于史实的地方,而中共领导“非基运动”的说法则更是夸大其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所能影响的小范围之内组织、领导、参与了“非基运动”。[8]也有研究者指出,要注意到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非基运动”爆发所起到的引导作用。[9]薛晓建调和了以上观点后提出,政党对于“非基运动”蓬勃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只是在“非基运动”初期,国共两党著名人物参与其中,仅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共双方才有意识地以政党的名义领导运动。[10]学者们对共产国际及政党在“非基运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观点及相互辩驳,既体现出学界对“非基运动”保持着一定的关注热情,也反映出这一问题依然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二、“非基督教运动”的阶段划分
“非基运动”历时五年有余,并非始终情绪高亢,而是处于阶段性的起伏之中。刘心勇的《非基督教运动述评》是对“非基运动”阶段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在文中以1924年8月重建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和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界,将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1]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针对阶段划分提出不同看法。
周兴梁以国共合作的建立和五卅运动的爆发为界,将“非基运动”分成兴起、发展、高潮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特点分别为运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至全社会、掀起向教会收回教育权的风潮和反帝斗争全面高涨以至于部分基督徒参与“非基运动”。[12]此说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对“非基运动”第二阶段的起点,学人则稍有分歧。如文献[13-17]认为,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的学潮拉开了“非基运动”的第二幕。文献[18-19]则将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重建视为第二阶段的起点。各学者对“非基运动”阶段的划分均有其道理和依据,显示出“非基运动”本身的波澜与绵长。
另外,还有人将“非基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如郭若平以民族主义在运动中话语权的分量为标准,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指出这两个时期之间其实并无泾渭分明的鸿沟。[20]这样更像是将“非基运动”的演进视为一个不断昂扬的整体。
三、“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的具体化
20世纪学界对“非基运动”的研究为我们勾勒出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历史影响,让我们能够基本了解其前因后果,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不足。21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大大弥补了这一缺憾,开始对“非基运动”中的具体活动主体及运动的边缘地区进行研究。
其中,对于“非基”人物的研究集中于陈独秀、鲁迅、李璜、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刘廷芳等人。文献[21]考察了陈独秀在“非基运动”前后宗教观的转变,指出正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陈独秀对基督教态度由肯定转向否定。文献[22]认为,鲁迅虽没参与“非基运动”,但运动对鲁迅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影响到其之后的文学创作方向。文献[23]肯定了李璜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对收回教育权的积极作用。文献[24]认为,李大钊参与“非基运动”,他不仅推动了“非基运动”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也为批判宗教信仰提供了思想武器。对“护教”代表如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刘廷芳等的研究也不乏案例。郭若平认为,周作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与陈独秀就科学与自由进行辩论,体现出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者在政治文化上的分歧日渐明朗。[25]该成果对研究“后五四时代”学人的分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学者认为,钱玄同从保护思想和信仰自由出发反对“非基运动”,并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尊”“专制”的思想方式进行反思,体现出科学理性的精神。[26]有研究者考察了基督徒知识分子马相伯在“非基运动”中的反应,马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反驳了“科学万能论”“宗教束缚论”等观点,从政治的角度指出“非基运动”的实质是以反基督教为“宣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的符号对象”。[27]吴昶兴对刘廷芳这一兼具中国知识分子和基督徒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复杂人物作了细致的考据,描绘其参与社会改造和寻求身份认同的历程,肯定了刘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出谋划策作出的努力。[28]上述研究也体现出“非基运动”研究重点的游离与转移。
同时,对“非基运动”中各政党、团体的研究有所深入。袁蓉认为,国民党内部对“非基运动”的态度也有左派、中派、右派之分:右派如蒋介石等表面上高喊激进口号,实则对基督教并无反感;中派如孙中山表明了自己反帝但不反基督教的立场;左派如廖仲恺则站在“非基运动”的前沿。[29]有研究者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非基运动”的关系,认为青年团并未发起运动,对运动的领导也是在青年团的“一大”之后逐步实现的。[30]有学者将“非基运动”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考察了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在课程结构及教学目标上的变化,认为其逐渐有了世俗化、中国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向。[31]还有人对秉持文化保守的学衡派反对“非基运动”的观点进行解读,肯定其冷静说理、客观平和的态度,认为其“应将教会与宗教区分对待”,而“教会在中国近代发展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观点有其历史客观性。[32]
另外,对“非基运动”研究的地域视野也从策源地扩展至四川、广东、江苏、湖南、山东等地。文献[33]从传教士的视野出发,考察了四川“非基运动”的背景、经过以及传教士的回应与心理感悟,具有研究对象及视角的创新性。文献[34]展示了汕头各教会学校在“非基运动”尤其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转型。文献[17]描绘了江苏省尤其是苏州、徐州、扬州、南京等地“非基运动”的开展情况,认为不同于其他地区,江苏省的“非基运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文献[35]在延续前人的“非基运动”整体叙述结构基础上,对湖南“非基运动”的背景、过程、特点及影响作了专门研究。文献[18]分析了山东“非基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如组织活动不力、人手不足、生存环境恶劣等,并指出这些问题在早期中共组织的活动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整体地解读这一历史事件。
四、“非基督教运动”的性质
在传统意义上,“非基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但也有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乃至尖锐的观点。
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是肯定“非基运动”的进步性。例如,有学者指出“非基运动”是“国民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延伸和反映”[12],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30],是“以知识界和学生为主体的一场针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运动”[36],“非基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同样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37]
也有学者强调,“非基运动”兼具政治、文化双重属性。“非基运动”是一场“政治与文化互动的运动”[38]。在初期具有学术讨论性质,而后将其作为政治解放的工具。[39]还有学者认为,“非基运动”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与崇尚知识的双向维度,是中华民族在寻求解决中国问题之路上的一次探索。[40]对“非基运动”性质认识的发展,来自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史观加持下更具体的研究,日后“非基运动”或许还会被冠以新的属性。
同时,宗教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如吴茂华认为,“非基运动”是一场非难、谬责乃至妖魔化基督教,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带向“极端主义威权专制道路的运动”。[41]有学者从近代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特点出发,强调“非基运动”思想论战的性质,提出“非基运动”是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流行的社会思想如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新儒家等之间的互动,其结果却是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融合至今仍未能实现。[42]另有研究者依据运动中正反两方对耶稣神格及人格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民国成立十余年中“毁神、造神和输送神话的思潮涌动”[43]。
五、对“非基督教运动”影响及评价的观点
日本学者山本条太郎提出,“非基运动”是一场与义和团运动并称的反基督教运动。[44]
有学者提出,中共成立后相继领导了“纪念李卜克内西被害、支援香港罢工、上海新年宣传、非基督教运动”四大斗争,而“非基运动”使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受了第一次斗争的洗礼,并在斗争中形成统一组织,也使得中共摆脱了注重自修理论而忽视实践的色彩。[45]牟德刚对“非基运动”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认为共产党人在运动中正确处理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对基督教的关系,初步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把近代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阶段。[15]有学者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论证了“非基运动”的进程,不断强化并构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20]还有研究者提出,“非基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中国基督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本色化”运动,而“本色化”的讨论又反过来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46]这一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对“非基运动”的负面评价亦不在少数。有学者认为,“非基运动”少有理性的对话和深入的思考,在思想史上留下“一页败笔”。[36]吴茂华指出,“非基运动”严重违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是一种极左政治的幼稚病,暴露出中国知识阶级精神文化上的弱点。[41]周伟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非基运动”“看似反帝国主义的理性山峰,其基座却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感”。[47]这些学者多从启蒙主义的关键词出发,反思“非基运动”在思想领域的缺憾。另有学者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非基运动”进行点评,认为“非基运动”改变了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新文学远离英美方向走向俄苏方向且日益政治化的重要一环,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48]由上可见一有趣现象,即对“非基运动”持有非议的多非史家。
六、“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展望
从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当前学界对“非基运动”的研究长于抽象的理论探讨,在历史重建方面则“不甚措意”[49],尤其缺少对整个“非基运动”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的全面、立体梳理。
一方面,“非基运动”的进程仍值得再作深入探讨。尽管“非基运动”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明显的高低起伏,各阶段之间也各自有鲜明的特征,但它有着一以贯之的主线和诉求,即反基督教本身及其背后的反对外国侵略,因此需要关注运动各阶段之间的连贯性。对于“非基运动”是如何结束的,现有研究也大都一笔带过。事实上,运动的终结并非一夜之间戛然,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熄火的过程。对此,应该对整个“非基运动”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动力作更具体的探讨。
另一方面,“非基运动”的研究视角有较大的转换空间。“非基运动”由青年学生引起,挑动众多名士学者卷入其中,但其影响范围并未仅限于狭小的知识界,特别是在其发展到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更是带有相当的群众性。同样,基督教的信仰者上至名流,下及黎庶,在政要、学者、商贾、工农中都不乏信徒,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因此,仅从通电宣言、笔战文章的你来我往或文人墨客、宗教领袖的亲身经历出发,恐难展现“非基运动”的完整面貌。对此,可以将研究的视线投射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大众对“非基运动”的反应上,将研究的对象转换到北京、广州、武汉、南京乃至外国政府对运动的不同态度上,使这段历史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