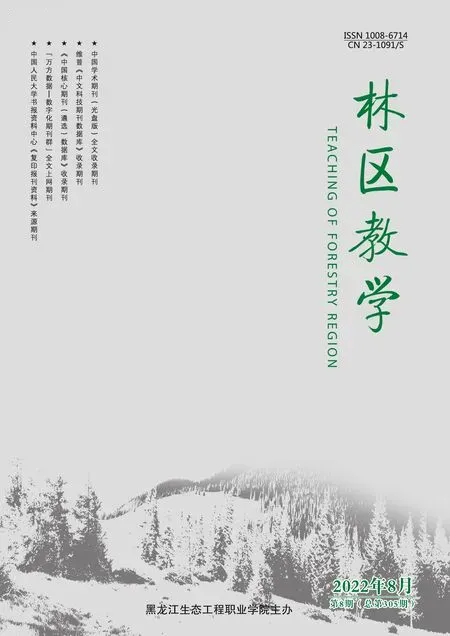因“体”施教:基于文体意识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探究
金文忆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福州 350108)
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着文体意识淡薄、教学方式单一的现象,这使得教师教学、学生阅读陷入了格式化的困境。2017年全国“小语会”陈先云理事长在《增强六个意识,教好部编小学语文教材》培训会主题讲话中指出,教好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需要教师增强包含“文体意识”在内的六大意识,并强调“文体意识淡薄,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而造成不管是什么文体,基本上按照记叙文的方法进行教学,内容是否真实与虚构往往分不清”[1]。不同的文体有其独特的写作特点与语言特色,对学习目标、学习方法要求不一,相对应的教学方法也有所变化。自2016年起,在全国中小学使用的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形成了“单元”为线索,“文体”为主线的双线组元编排[2]。小学语文教学开始强化文体意识,注重因“体”施教。
一、“文体”与“文体意识”的内涵
谈及“文体”,陈先云先生认为,文体是文章的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文本的规格和模式,也是文章存在的基本要素。有研究则认为:“体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文体,不仅指“体裁”,而是由体裁、语体、风格三大要素综合而成的“集”[3]。前者从教材角度出发阐明文体在课程、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后者则站在文章学立场阐释了“文体”一词的内涵。本文综合2022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以上观点,认为文体是文章的体裁,是文章作品在结构和语言运用上所呈现的具体样式或类别。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正是由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与应用文四类实用文体组成,其中囊括“诗歌、散文、小说与戏曲”。在语文实际阅读教学过程中,文章文体不同,对文体教学目标、文体知识、文体要素、文体特征与文体结构的关注大不一样,把握文体开展教学是提升阅读教学质量的关键。
文体意识一词,并非固有概念,而是一个组合名词,学者对“文体意识”的定义不尽相同。较普遍的看法是将文体意识定义为对文体的自觉,表现为应对不同文体的文章时,能够自觉地辨体识文——主动应用对应文体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与逻辑方法把握文章主次[4]。本文将普遍认可的概念具体化,认为文体意识是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构建的关于文体结构、文体要素及文体特征的思维认知。面向教师,强化文体意识要求教学立足于文本优秀选文,紧扣文体特点,做到因“体”而教,选择适切的教学策略让学习生动起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效果。面向学生,强化文体意识就是要求学生增强对文体的敏感程度,在独立阅读过程中掌握文体知识,自主建构文体认知结构,把握阅读重点。
一线教师虽有意识提高自身文体意识,立足文体开展教学,但教学效果并不佳。可见,分析现今教学中存在的文体意识缺乏、淡化的表现,对于优化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仍有重要价值。
二、语文阅读教学文体意识缺乏的表现
1.文体教学目标与单元阅读目标割裂
教学目标是与具体情境相结合并希望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即强调在具体情境下学生行为变化的结果,它是教学活动选择的依据[5]。在阅读教学中,目标既包括文体目标,又指单元目标,前者凸显同一类文体或同一文体不同篇目的独特教学要求,后者体现同一单元下目标的一致性,单元目标寓于文体目标之中。在实际阅读教学过程中,文体教学目标往往自成一体,甚至与单元目标割裂。如,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在单元介绍中点明本单元主旨: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可见,本单元教学主旨在于“观察”二字,即培养学生记录并观察事实的能力。倘若文体教学目标游离于本单元主旨,局限于文言字词的学习、作者情感的挖掘,则错失了利用例文景物描写培养儿童“观察能力”的大好机会。各类文体在教材单元中交替编排,表明选文既有各自特色,也与单元主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6]。因此,目标偏差会导致教学内容缺失,阅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从课堂教学实践来看,教师在面对文体复杂的单元选文教学时,容易陷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教学困境。即只教本篇本文,忽视篇章与单元内其他文章的内在联系,进而使学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难以发掘文体之间的横向联系。教师在教学目标的确立中尚且难以系统归纳不同文体间的异同,又怎能期望学生在自主阅读不同文体文章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阅读相关材料。因此,教师在设置文体目标的过程中,既要关注文体类篇章的特殊性与内容的特殊性,更要始终围绕单元目标这条主线。
2.文体类型定位轻率,阅读教学重点模糊
有的教师对文体类型定位有偏差,即对小学学段中最常见的“小说、戏剧、散文与诗歌”四类文体辨识不清,混淆寓言、童话与神话[7]。具体表现为两类:一是文体把握错误。把诗歌当成散文来教,把寓言当成童话来学,现代诗与古体诗区别混乱。二是文章重点模糊,虚实不分。如对小说《桥》、记实作品《狼牙山五壮士》的主人公与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中“火”的来源就存在虚与实混乱问题[1],导致神话课上成感悟课、童话课上成环保课的教学偏差,这样不仅没有达到学科知识横向融合的教学期待,更是将语文泛化。
教学重点模糊还表现为对文体分布规律、文体特征认识不全面。如忽视教材围绕四类典型文体中“小学低段以极具想象力的童话、诗歌为主,在高段突出具有文学意味的小说与散文”的分布规律。语言风格上,童话为了符合儿童智力发展水平,惯用“重复情节、重复语句”的方式;小说言辞平实;说明文用词严谨;寓言简洁精练。表现手法上,童话、寓言与小说都重视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三者亦有贯通之处,无论是故事的铺陈还是人物的刻画都借助夸张、想象的写作手法。因此实际教学中,既要突出文体的各方面特色,也要避免特征混淆。
3.教师对文体特征感悟较浅,阅读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
在语文教学中,以“读、教、做、写、练”这套普适性的教学方式应对各类文体的现象仍大量存在[2]。这种记叙文式教学方式弱化了教学具有独特性的意识。在学习过程中,“读”分为朗读、阅读、诵读等,各式文体对“读”的要求程度各异。诗歌融情与景于一体,偏重借助抑扬顿挫的、能感受韵律节奏的诵读;小说采用叙述性语言描述故事情节,读的作用为突出情节跌宕,体会故事细节意蕴;记叙文侧重阅读与写作并用,可采用默读[8]。诗对读的要求最高,如古诗《绝句》与诗歌《咏柳》,朗读时要抓住诗歌每一联的语调起伏,前者重在读出平仄押韵,后者侧重读出格律与律动。文体决定阅读内容的呈现样态,教师教学文体更需对文体特征有切身的感悟。
使用盲目的、单一的教学方式,易产生阅读教学错觉:“淡化文体”等同于无需文体知识,或认为学生只需机械记忆文体知识,无需实践训练。结果是学生对各类文体辨识能力不强,加之课堂内外缺乏充足的文笔训练机会,大部分学生的作文读写效果不尽如人意——记叙文写作缺乏关键要素,说明文阅读难以做到明白清楚,散文阅读更是不着边际。教师教学与学生阅读都陷入尴尬状态。
三、强化文体意识,促进语文阅读教学的优化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为使教学更加系统,应从语文核心素养视角析出文体语言、文体审美、文体思维与文体文化四个维度。借助对各类文体典型文章的剖析,引导学生在字词句段的语言学习中把握行文思路,体味情感深浅。教师利用读写结合增强学生文体思维,促进阅读方法内化,落实因“体”施教。
1.由字及类,在建构与运用中把握文体语言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核心素养最核心的部分,是其他要素的基础,这里指的是汉语言文字的建构与运用[9]。文体语言是指在阅读不同类文体时运用的一套独特话语体系,包括汉语言材料、汉语言形式与汉语言结构等。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建构文体语言是促使学生完成赋予言语字词以个人意义的过程。
文章语言风格与用词因文体而异,要抓住关键字词,深化“篇”的认知。语言学习在于字词的品味,为了促进学生对文体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我们要常对关键字、词进行比较推敲、品味涵咏[10]。标题是文章的关键词之一,起到点明文体类型、指示语言风格的作用,如《寓言二则》《古诗二首》。除标题之外,文中亦有凸显语言特点的其他用词,这类用词或以人物描写出现,或借情节虚实彰显。以《去年的树》与《枫桥夜泊》为例,两文都强调情感。但前者以物拟人,鸟树友谊具有鲜明的虚构色彩,主人公动作、神态的语段描写跳脱自由,想象大胆;后者则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以景物载情,展现作者孤寂的心理活动,用词严谨客观。在语言表达上,前者采用简明对话式,直接表现童话故事灵动的语言风格;后者则借用看、听等感官动词与自然景物结合的独白方式表达愁苦,此两种文体的语言差异十分显著——古诗悠远绵长,童话活泼跳动。要达到深化“篇”的理解,应抓住篇章中人物情绪过渡的关键词与起转折作用的过渡语句等,在彰显语言风格的同时唤起学生的情绪起伏,把握“一切景语皆情语”,紧扣“无眠、愁眠”人物状态词与“月落、乌啼、渔火与钟声”等自然景物,联结儿童对“无眠”的个人经验,将孤寂冷清的愁苦推向高潮,学生对“篇”的理解将进一步深化。
文章字词多元组合带动构建多样结构形态,因此要抓住文体结构,强化“类”的意识。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指出:“文辞以体制为先”,对文体、文体结构都有着明确的要求。楚辞、唐诗与宋词虽统称为古诗词,但诗体典雅庄重,词体柔媚艳雅,辞体不羁自由。且诗词赋文体依据字数划分类型,每联四字为四言诗,五字成一联则为五言诗[11]。此外,诗又分为古体诗、现代诗:古体诗讲究对仗工整,现代诗则形式灵活;古体诗言辞严谨,现代诗则灵活跳脱。仅从“诗”这一脉便生发出如此精深的结构与内容。小学阶段的阅读教学虽不讲究精深学问,但也需树立大致的结构意识,从古体诗与现代诗的结构、语言风格、诗体用意几个维度入手,树立“类”的意识,掌握不同类文体的阅读关键[12]。
2.范例延伸,在读写训练中增强文体思维
思维发展基于阅读素材的训练,文体思维是应对不同字词篇章的阅读知识与阅读方法的综合体。换言之,文体思维是学生在自主阅读不同体裁文章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序的、深刻的、具有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掌握阅读各类文体文章的程序性知识是培养文体思维的重要内容,形成文体思维的过程也是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综合运用与不断强化的过程[13]。没有一个有计划的教学过程可以穷尽整个精神世界,没有人能够毫无缺漏地掌握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全部知识与能力,因此文体思维的强化需要发挥范例的中介作用,沟通知识方法与思维,沟通学生主观世界与文章客观世界[14]。
明晰文章间的异同点是寻找范例、锻炼文体思维的重要前提。小说强调人物形象,形象的具体要素包括环境、场面、情节等,富含“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形象思维。阅读说明文围绕这几个要素梳理,才能认识到篇章的核心,说明文强调严谨与逻辑,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以清晰地阐明事物为主要目的。若脱离说明方法来解读说明文,则会使人不知所云。可见,不同文体有其特定的阅读角度和赏析视角,盲目使用则会阻碍阅读能力的提升。
思维的培养在于知识积累与方法凝练,范例是重点的知识内容。范例是个别的但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的,每个作为范例的个别都是反映整体的一面镜子[14]。有效的范例一是来源于课堂中的课文选文,二是以精美课文选文为生长点的课外阅读延伸。因此应当紧扣文体,课堂中深析文体例文以掌握阅读方法,在课后自主阅读范例中复现阅读方法、再造自己的阅读习惯、阅读风格。在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每一章节结尾处“语文园地”模块,都提供了同质文体阅读素材;在实践过程中,也可引用异质文体作为阅读素材,帮助学生形成刺激强化。不论课堂范例精读还是课外范例自主阅读,其目的都是帮助学生形成“类”的文体思维。
3.观照语境,在想象中感受文体审美
审美鉴赏与创造以思维能力为核心,以语言建构为根基。文体审美素养的形成同样需要借助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且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经典文体例文以祖国汉语言文字为语言工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15]。文体审美,就是学生能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运用已建构的语言体系、发挥思维的批判作用,在不同文体文章的阅读中发现母语文字的美、品鉴出语文文体(小说、说明文、诗歌与戏剧等)在语言文字运用上体现出的文字美、意蕴美、意象美的感性美与说事明理的理性美,审美能力的最终去处是审美创造。
作为以文学作品鉴赏为主、以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为目的的主要科目,语文具有特有的文字魅力。首先表现为语文文字的一词多义、意形结合的文字美,如“行”这个多音字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进行转化,又如汉语言文字的演变以象形字为始,虽演变至今很多字得到了简化,然而仍能从字的结构中解构出其内涵。其次是汉语言文字特有的言简意赅、意犹未尽的意蕴美,如大多以文言文字词为主的寓言阅读,以鞭辟入里的小故事揭示人生哲学道理。再次是文字组合形成的意象美,使人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枫桥夜泊》一文中,作者用寥寥几笔“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就将那个难眠的、孤寂的夜晚景色勾勒得淋漓尽致,充分营造了一种冷清、悲凉的环境。最后是文字表现手法复杂多样的理性美,如夸张、拟人、比喻与排比等对人事物的细腻描写,增添文章的趣味性。
语文又与美学相通,具有美学特点与显著的感性特质,甚至以违背语用学逻辑、数理逻辑的表达方式彰显文章的气势与论辩力度。所谓的语用学逻辑,就是语言学与逻辑学的交叉,是从语用维度来研究推理或论证的分析、评价甚至建构的逻辑学分支[16]。在某些情境中,正是因为作者违背了语用学的准则,所以才产生了文学艺术的美感。但语文课并非完全不讲究逻辑顺序,小说文体中典型的说明手法与语文教材中的思辨类文章便严格遵循数理推理的周密性与严谨性。语文中的美恰恰是以文学性话语进行言说时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科学、理性、实用的逻辑产生的“错位”的审美价值[9]。
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揭示语文的审美性质,培养学生的文体审美素养,认识到客体(文体课文)在审美鉴赏中是依赖主体(学生)的。没有主体能动的审美与主体良好的审美态度和审美心境,客体就失去了审美价值”[17]。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教科书中一篇篇文质兼美的课文时,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主体充分发挥联想、想象与比较等方法,能动地感受作者为读者创设的文学艺术环境与情感体验。正如教育家石中英认为的:“任何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实践、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的。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境域,既不存在任何知识,也不存在任何认识主体和认识行为。”[18]尤其是对尚未形成完善的抽象逻辑的小学生而言,有效的情境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去直观地知觉文本内容。因此,良好的教学情境有利于想象与联想的发挥,尤其在故事性强、情感深厚的课文教学时。想要深刻体会文学作品的美,则需要做到经验、想象与情境的统一。
培养文体审美的目的是提升审美的创造能力,深化人们对文化作品的创造性理解。任何文体都蕴含美的因子,虽各有侧重,但都需要学生透过富有张力的语言,借着想象的桥梁与作者对话、与文本对话。只有通过切身体会感受到的美,才能内化为个人认知结构,才更有利于创造美。
4.类篇对比,在理解与借鉴中传承文体文化
文体文化源自于语文核心素养对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作出的要求,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以语言能力与审美能力为基础,以思维能力为核心,传承文体文化是形成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重要路径。语文核心素养将文化学习分成了两个层次:文化理解与文化传承。文化理解与文化继承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是相互促进、不断循环的过程,只有理解了本国文化才能理解包容他国文化。文体文化就是在树立不同文体类型的意识前提下,发掘不同文体中的文化因素,增强对文化理解的全面性与深刻性,增加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9]。
发展文化认识能力的同时应意识到不同文体展现文化内容的方式有异。如一年级“金木水火土”一篇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崇尚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三年级选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日》《清明》三首古诗介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节日,《纸的发明》与《赵州桥》两篇记事的记叙文介绍祖先们精湛的创造发明。两种文体都对民族文化起到解释与介绍的作用,但古诗抒情笔墨较重且较为直接,记叙文较为含蓄,诸如敬仰之情则多以学生的体会为主。
在类篇对比中感受经典作品的人文精神,批判性学习文体文化、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在部编版教材中收录了大量同一文体下的国内外不同文学作品,其文学写作内容、写作方法与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以小说文体为例,中国小说《桥》与外国小说《穷人》两篇小说文化背景、写作内容与写作方法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中国传统自然村落为故事发生地点;后者正值俄国历史上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阶段——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在写作内容上,前者以群体经历为故事内容,后者以个体家庭经历为载体。都是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彰显“以小见大”的魅力。前者故事的发展以群体的对话为主,后者故事大量采用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且在结尾处各有设计,前者特意在结尾处道明老人与小伙子的关系,给迷蒙的故事一个令人悲痛的结局;后者则直至结尾未阐明神秘人到底是谁,给足留白空间。其实两篇文章的设置皆有深意,《桥》一文尽显中华民族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穷人》一文除了让我们看到穷人身上的质朴纯真品质之外,还以留白的方式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期望着有转折。在中华文化的对照中学习不同文化,在体悟我国文化精神的内核中领略外国文化的风光。
文体文化传承离不开实践,学习过程本质上是“认识—实践—再实践”的历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机会,在表达中深化文体文化认识、锻炼文体文化运用能力。
文体意识对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教师在教学中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体”施教将文体知识、文体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在小学阶段,帮助学生树立强烈的文体意识、积累一定的文体知识、产生浓厚的文体学习兴趣是小学文体教学的重要目标。强化教师文体意识、重视因“体”施教,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