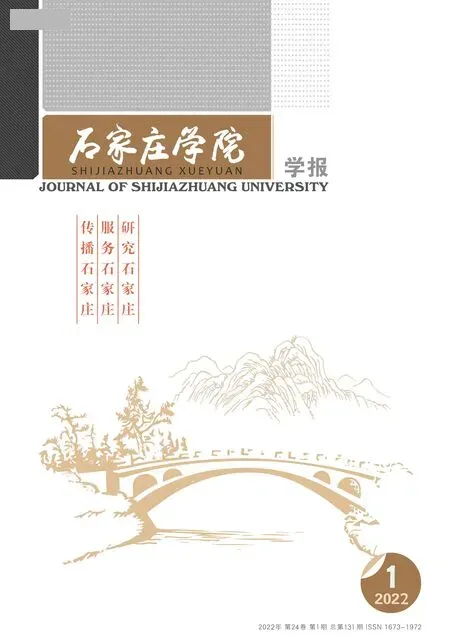艺术批评对象的转变:从“四要素”到“艺术界”
王天歌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的《镜与灯》可认为是现代文学理论的扛鼎之作,它不仅在浪漫主义文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影响了整个20 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艺学研究。在模仿说雄霸西方美学、艺术理论两千年的环境下,艾布拉姆斯提出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简便而又灵活的参考系……可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艺术理论的特征利用起来,然后慎重地使用这个分析图,随时准备将一切有助于眼下目的的特征收纳进来”[1]4的观点,强调艺术批评的一种共同走向。
一、对浪漫主义的回望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 世纪末,盛于19 世纪中叶,与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在对法国新古典主义所宣扬的“庄严和伟大”思想失望的背景下,浪漫主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并且开创了19 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思想洪流冲击了欧洲甚至更多国家,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了浪漫主义。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政治主张,同时还有新的文化、思想。旧秩序的毁灭必然带来新秩序的诞生,封建秩序的腐土已经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破土而出,贵族们的反抗被时代的车轮碾过,新兴的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博爱”之大旗,成为在政治社会中角逐的主角。
谈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它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就不得不谈到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华兹华斯是“湖畔诗人”的领袖,其思想由初期对法国大革命热情洋溢的歌颂变成了后来遁迹于山水的自然崇拜。他在诗歌风格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以至于有人称他为第一个现代诗人。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诗必须含有强烈的情感,这就排除了一切应景、游戏之作”[2]132,摒弃那些“诗歌词藻”与“陈言套语”。其与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作的《抒情歌谣集序》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
康德(Immanuel Kant)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中,对自然界的“本体”和“现象”进行区分,指出“我们必须要把经验的自然界法则同纯粹的或普遍的自然界法则区别开来”[2]92。他在谈及“我们在感性直观的对象里所发现的法则”[2]93之时,也在试图调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理性主义与培根(Francis Bacon)的经验主义。但这种调和是在资产阶级统治逐渐建立之后,在阶级矛盾复杂、贫富现象加剧的状况下并未给予“感性”以合理位置。人们对“理性的把握”失望透顶,整个欧洲弥漫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如是说到:“和启蒙主义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4]5随着康德哲学从客观转向主观,人主观精神的创造和反映、塑造的能力得到进一步肯定,浪漫主义思想得以进一步稳固。事实上,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对生命、生活的理想甚至虚幻的向往的表现。浪漫主义的文学试图用文字给人类展现出一幅理想的细密画,通过心灵的光韵塑造理想来抚摸世间的伤痛。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曾说:“浪漫主义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对于理想的真实的追求。”[5]59在充满颠覆与变革的20 世纪现代思潮中,最后的浪漫主义所坚持的理想之“真”存在极度欲望与极度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随关俄国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Vassilievitch Rachmaninoff)的离去,浪漫主义所憧憬的理想终结了。
浪漫主义理想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思的停止。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对浪漫主义之后的现代主义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引用的德国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一句话,清晰地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索:‘我们应不断尝试将各门艺术紧密地融为一体,探索一门艺术转换为另一门艺术’”[6]。在《新拉奥孔》中,白壁德(Irving Babbitt)以浪漫主义运动为范例,指出了各门艺术出现的“浪漫混合”趋势,主张“应努力重新把握过去文明的内在道德品质”[6]。这种趋势,直击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新古典时期奉为圭臬的“模仿”原则。所以,浪漫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非完全反对古典主义所坚持的“模仿”原则,而是更加强调艺术的自发性、互通性和表现性。
二、“四要素”——作为艺术学范畴的批评模型
“四要素”的分析体系把解释艺术作品的性质和价值的所有尝试分为四大类,即模仿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理论、本体论批评。模仿理论主要讨论的是作品与宇宙的关系,艺术作品对自然的模仿;实用主义主要讨论作品与接受者、欣赏者的关系,从艺术的功能、用途加以概括;表现理论主要讨论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表现艺术家的情感、个性、精神世界以及潜意识等方面;本体论批评,抑或称之为“新批评派”,在20 世三四十年代之后,切断了作品与其他三大要素的关联,把艺术作品视为独立客观的对象加以考察。
“模仿说”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19 世纪初一直是艺术发生学中的主流说法之一。“艺术的目的是模仿自然”在这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定理。之后,逐渐发展为两个指向,一种是“模仿自然”,另一种是“模仿作家”,前者在康德理论体系中被称之为“艺术家天才的创造”,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经验主义。
“实用说”是以欣赏者为中心的批评。古希腊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在《诗艺》中也指出:“诗应当寓教于乐,即劝诫读者,又使其喜爱,才能符合众望。”[7]3诗歌模仿自然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则是引发读者必要的反应,以及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实用说”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以伊丽莎白时代的悉尼(Sydney)爵士为首的批评家们所发扬。悉尼曾指出:“模仿的目的要给人以愉悦和教导……把握住善,而没有愉悦,人们就像躲避陌路人一样离善而去”[1]13,要将道德感化作用作为艺术最终的落脚点。事实上,“实用说”所强调的艺术的功能——感动欣赏者,即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中所谈的“卡塔西斯”。另外,“实用说”为重视心灵表现和天才创造的“表现说”作了铺垫,因此也必须考虑艺术家的才能智慧。就作品与接受者的关系而言,在当代文论中还出现了解释学的美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等不同流派。
“表现说”是在“实用说”基础上的再发展。如前文所谈,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提出“诗是强烈的情感流露”[2]19。实用主义理论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目标都指向了快感和美感。因此,批评家们逐渐强调诗人的天赋、价值判断、自然灵感、创造性想象和再造性想象的能力。从朗基努斯(Cassius Longinus)《论崇高》中可见,其认为“崇高”应该优先考虑情感,并且转向作者能力、思想、心境、情感的形成过程。其树立的批评榜样并未立竿见影地起效,直到英国的邓尼斯阐述了从朗基努斯那里推演出来的概念。这种倾向表明,批评的对象从艺术作品转向了艺术家,文学的探索走向了分析艺术家的心理或个性的道路。事实上,在文学表达中,有很大一部分表达为作者提供了情感宣泄的机会。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早就承认其《新爱洛琦丝》是因为爱情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自己的感情而做的“白日梦”。此外,一些批评家认为,诗所表现的对象不仅反映了外在物象,还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所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诗与真》中也坦率地承认,年轻时所经历的失意和绝望,促使他写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可以二分为表现客观世界的真实和头脑中的真实。这两种真实是相连接的,一旦外部条件出发了感觉经验,便能触发情感。这种观点也为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等符号学美学家所主张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用“寓情于景”和“借景抒情”来对应这两种真实,前者更偏重于把“景”表现得更加真实,后者更注重“情”是否得到张扬。在当代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看来,真正优秀的艺术,再现与表现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客观说”强调艺术作品内部形式,以艺术作品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为中心,探讨形式内部的各种元素所构成的意义与关系。“客观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本体批评的表现。本体批评是自律性的批评,如果失去了本体批评,就会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但是,本体批评需要辩证对待,若将其与艺术家、作品和宇宙割裂开,则会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地。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客观说”全面在艺术批评领域铺开,将诗歌看作“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诚然,一些批评家搬出了康德“美是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的论断,强调他主张的“不存私心也无关实用的概念”[1]25。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康德在谈论具有审美性的作品时特别考虑到其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心理能力[1]25,也就间接导致了19 世纪后期具有后浪漫主义特征的“唯美主义”的兴起,将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
三、“艺术界”——作为社会学范畴的批评对象
艺术的概念在欧洲渐渐通过对宗教的结合及取代,走向了自身的独立。艺术家由工匠转变为天才,艺术品由人工制品转变为膜拜对象,艺术生产转变为创造,艺术欣赏由一般消费转变为鉴赏。在宗教神祇衰落之后,艺术被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奉为神明。[4]199
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模型,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划分,而是一种人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所使用的简便方法。但是,在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反思艺术中的“创造”问题。从现代派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开始,后现代艺术实践则全面地挑战着人类延续两千余年对艺术的认知。当代艺术概念与资本市场、大众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艺术消费的阶层扩大,艺术家不再受制于固定的委托而转向了自由创作。诚然,这种创作带来的是一种意义的隐晦和形式的抽象——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批评的阐释才能得到具体、准确的解释,而不再单纯依靠欣赏者的审美体验。
美国艺术批评家、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在1964 年发表了《艺术界》一文。其明确提出“艺术界”并不是一个审美世界,而是由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在艺术作品的外围所构成的一种“理论氛围”。而这种理论氛围的建立,直接攻击了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合理性。艺术作品不再作为连接艺术家、观众和宇宙的中间环节,“理论解释取代了艺术创造成为艺术中的决定因素”[8]。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在丹托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指出“艺术界是一个由艺术家、批评家、公众、艺术机构、新闻媒体等等构成的社会或圈子,因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5]22。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在其《艺术界》一书中解释:“所有的艺术工作,就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通常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活动……我们最终看到或听到的艺术品的形成并且延续下去。”[9]11贝克尔定义的“艺术界”概念是在现代主义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概念,并且更加侧重艺术创作在社会网络之中的能动性、程序性和时效性。这种“社会网络”的优势在于其范围“可大可小”,相比于迪基的“社会学概念”更有弹性。贝克尔通过观察各种各样的“合作网络”(艺术界),逐渐消解了艺术家、艺术品、观众、宇宙所构成的模型,将它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并将其一一拆开,分析其各自内部的局限与优势。因此,艺术批评的对象彻底泛化,艺术家不再特殊,而艺术品也不再神秘,艺术活动中的其他环节得到了承认。葛瑞斯伍德(Wendy Griseold)在此之上又进一步演绎,得出了“文化菱形”理论。他指出,尽管“艺术界”或松散,或紧密,由各种复杂的元素构成,但重要元素只有四个,即艺术产品、艺术创作者、艺术消费者和更广阔的社会。若想理解艺术品与所处的时代、社会,就必须在“文化菱形”理论的中央,再加入一个“艺术分配者”,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当代艺术必须经过传播才能获得观众,艺术本体与接受者之间的联系仿佛拉得更远了。
20 世纪,社会学科介入艺术领域,让艺术显形为寻常物,而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的“能动性”理论将艺术品彻底视为具有能动力量的对象。盖尔将艺术的要素划分为四种,即艺术家、象征物、原型、观众,而这四个要素又分别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重关系。其中,“当“原型”作为能动者的时候,艺术家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而是需要按照“一定之规”被动地实现象征物的形貌”[10],这就是写实艺术。“原型”在受动时,则是艺术家想象的产物。一定程度上,盖尔的模型与“四要素”中的“表现理论”有类似之处——无论是写实艺术还是想象艺术,都是呈现艺术家如何实现对客观对象、客观世界的“心灵的映照”,只不过“映照”或显或隐。盖尔的落脚点在于对艺术的研究如何去除其“神秘化”,是进一步祛魅的过程。但是,其“能动性”的理论过于强调艺术活动过程的结构性,从而忽略了艺术品作为人主观创造产品的特殊性,也忽略了这种结构主义哲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他在祛除艺术魅惑的同时,又为其笼罩上了哲学的面纱。
自18 世纪末,艺术家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走上了神坛,通过对宗教的结合和对宗教的取代,现代美学完成了对艺术的赋魅。自此之后,就如同康德将创作的标准交给天才的艺术家一样,休谟(David Hume)也将艺术欣赏的趣味标准交给了批评家。浪漫主义并非是要“造神”,而是要拨开“心灵感知”的那一层迷雾,使得心灵的能动性与世界的变化相脉动,让艺术品获得灵韵。
四、“反映”世界与“照亮”世界
浪漫主义并不是一味地宣扬情感至上,它将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本体价值观、宇宙观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具有相似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辉煌的形式。浪漫主义更加偏向个体情感力量的彰显,古典主义偏重庄严伟大崇高的塑造。因此,在一些浪漫主义理论家的诗文中,既有一些模仿论的影子,又有些许表现论的冲动。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既坚持柏拉图式的“理性”,认为艺术是第二重的模仿,但是又强调,“作为一个诗人,就得领会人世间的真与美”[1]153。所以,雪莱在一般意义上把诗歌解释为一种“想象的表现”,是内外协调的产物,能够反映心灵之灯。在柏拉图主义和心理经验主义之间、模仿与表现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对立统一,可见当时文论家和艺术家的观点的基础是建立在心理经验上的。由此观之,在整个浪漫主义思潮下,德国的诗歌、音乐,英国的小说、诗歌、风景画,法国的雕刻和绘画,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在此时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斑斓色彩。
再现是“镜”,反映这个世界;表现是“灯”,照亮这个世界。“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学家一直喜欢求助于镜子来表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本质。”[1]24但是,浪漫主义时代穿梭着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很难用清晰的词语将其准确表达。“情感”与“模仿”、“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之间的映照,想象的整体性再次得到自由的生发。“镜”寓意着模仿,无论是有机还是无机,其功能总是要再现客观现实。而“灯”寓意着表现,不仅表现客观社会中的趋势,还从对世界和事物的关注转向了心灵的补偿。“浪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个时代文学主体性和人性的张扬。“镜与灯”这一对满含隐喻的词语,可能本身就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诠释——镜中实物,灯下光影。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 世纪末期,艺术在经历了宗教、神学和政治的束缚之后,扩大了心灵深处的情感活动范围,达到了主观精神与时代理想的统一。这一时期的艺术批评所勾勒出来的形象并非像现今的“艺术界”一样,具有“程序”或“分类”的价值,而是显映一群在理想与现实相悖离的境地、陷入自我分裂但依然坚持理想信念而饱受痛苦的灵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越来越深入。艺术的生产、叙事和流通也随着时代而变化,“艺术”内在的、固有的价值在不断运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分解成为一个个孤岛,逐渐被象征符号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