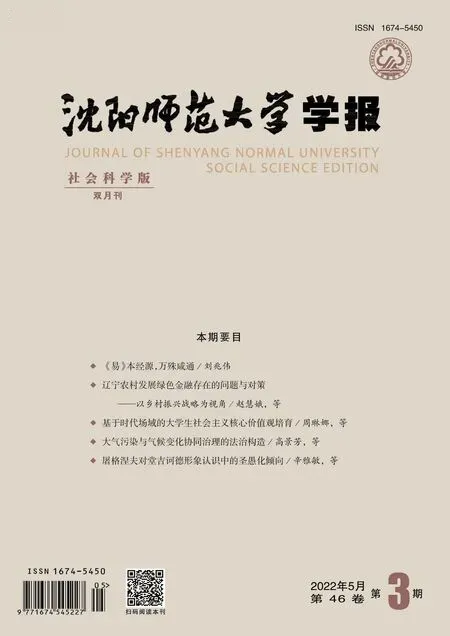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形象认识中的圣愚化倾向
辛雅敏,孙爱迪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世界对于堂吉诃德的形象解读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状态,自《堂吉诃德》传入俄国后,俄国评论界对其解读体现出了不同于世界同时代评论家的特点。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与俄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一、19 世纪俄国对堂吉诃德形象的阐释
加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个文化历史语境传到另一个文化历史语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抽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作者预见到[1]75。自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起,堂吉诃德的形象在其流传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起初它作为一本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读物被西班牙人民接受。为此,纳博科夫在《〈堂吉诃德〉讲稿》中说,这部书从本质上仍属于原始小说的形式,属于结构松散、杂乱无章、光怪陆离的流浪汉和无赖冒险故事一类,而且最初的读者就是把它当作这样的故事来接受、来欣赏的[2]16。在整个16 世纪末17 世纪初西班牙的大环境下,《堂吉诃德》绝非一部严肃作品,它包含大量西班牙的俚语、传说、低俗笑话,更多地被评论家视为喜剧作品。因此,当时的文学界对待《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主要以反面评价为主,并没有认可其价值。罗德里格斯·马林曾经考证在《堂吉诃德》诞生之初的西班牙,那时在西班牙的很多城市出现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人们视其为喜庆的标志——“堂吉诃德和桑丘、杜尔西内娅一起,出现在众多的民间喜庆节目中,被人当作逗乐的小丑到处演示”[3]6。同时,因为堂吉诃德的高知名度和其喜剧表现性,17 世纪就已经有不少戏剧作者不同程度地将堂吉诃德搬上舞台。洛佩·德·维加虽然鄙视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更是贬低,但反过来无意中扩大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影响。作为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文坛泰斗和戏剧至尊,洛佩在其喜剧《傻夫人》中把女主人公傻夫人比作堂吉诃德,并借人物奥克塔维奥之口评价其只会逗世人发笑[3]8。
相较于16、17、18 世纪的诸多反对声音,自19 世纪浪漫主义以来,对堂吉诃德形象的描述开始发生了转变。如大诗人海涅就认为,《堂吉诃德》是崇高与滑稽的完美统一。虽然出现了这样一些对于堂吉诃德的肯定,但在欧洲堂吉诃德的整体形象依然以滑稽和愚蠢为主。随着堂吉诃德形象不断向东传播,到了19 世纪的俄国,诸多俄国评论家对堂吉诃德形象进行了令之升华的高度评价。从别林斯基开始,俄国对于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解读就富有着不同于时代大潮的气质。
别林斯基在其有关堂吉诃德的文章中提到,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一部没有国界和时间的小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堂吉诃德,但成为堂吉诃德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想象力、充满爱心的人和一个高尚的人。的确,堂吉诃德只有在杰出的人中才能找到。但重要的是,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始终,根据一个世纪或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特点,体现在数千种不同的类型和形式中。”[4]137这一想法表明,别林斯基阅读、评论和诠释堂吉诃德的方式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认为堂吉诃德不仅仅是一个喜剧人物,更像是一个小丑的文学评论家是不同的[5]。
继别林斯基之后,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成为堂吉诃德形象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海涅的评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样,通过屠格涅夫的评价,堂吉诃德的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的升华。屠格涅夫在演讲中说:“我们应当承认堂吉诃德精神里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滑稽的一面罢了。”[6]181堂吉诃德可笑的举动不再是疯子的异常行为,反而成为带有崇高牺牲精神的故作滑稽。“他整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为了别人……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请珍视这个词!——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返顾。因此,他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满足于吃最粗劣的饭食和穿最寒酸的衣服,因为他顾不上这些。他心地温顺,但精神上伟大而勇敢;他息事宁人的虔诚没有对他的自由形成限制;他虽无虚荣心,但他不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怀疑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百折不回的意志。一心追求同一个目标,使得他的思想有些单调,思维方式有些片面;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他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为了什么活在世上,这就是主要的知识。”[6]183屠格涅夫的这一观点得到当时世界上很多评论家的高度认可。福楼拜在1869 年致友人信中说:“每到周末,我总是钟情于《堂吉诃德》;在它面前我们几乎全都是矮子。哦上帝,我们觉得自己好渺小!”[3]76席勒在1781年《〈强盗〉序言》中评价,堂吉诃德是“我们所厌弃而喜爱、所惊讶而怜悯的”[7]3。这些评论进一步确立了《堂吉诃德》几乎无与伦比的经典地位。
总而言之,在屠格涅夫解读《堂吉诃德》之前,评论界对堂吉诃德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在屠格涅夫解读后,19 世纪的评论界对其观点和声不断,整体对堂吉诃德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圣伯夫称《堂吉诃德》为“人性的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评价《堂吉诃德》时说:“全世界没有比这更崇高和强大的小说了。迄今为止,他是人类思想的最高表征,是人类所能企及的最苦涩的自嘲。”[3]76堂吉诃德俨然成为人类最崇高精神的一种代表,整个世界在重新阅读和领悟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对骑士道的疯狂迷恋和求而不得被隐喻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悲剧。通过这一系列的转变,我们不难发现,屠格涅夫在堂吉诃德的形象批评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什么原因促使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形象得出与之前研究主流相左的全新阐释呢?这显然与俄国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屠格涅夫等俄国评论家之所以对堂吉诃德另眼相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阅读《堂吉诃德》时所带入的视角不同。这一视角的代入,受到俄国传统圣愚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堂吉诃德的形象在屠格涅夫等俄国评论家眼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被抬高美化,甚至赋予圣性。屠格涅夫在评价堂吉诃德这一形象过程中所产生的全新感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俄国传统圣愚形象的影响,更因为堂吉诃德的形象本身就与圣愚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才使得其在俄国评论界获得高度赞扬。
二、屠格涅夫对于堂吉诃德形象的再认识
屠格涅夫于1860 年1 月在为清贫文学家和学者赈济会集资而举办的公开讲座上,发表了上述名为《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讲。在这一次的演讲中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形象所作出的新的解释是在他与赫尔岑的论战中产生的。赫尔岑在《来自彼岸》一书中回忆1848年垮台的革命的活动家时,将他们讽刺为可笑的堂吉诃德。屠格涅夫认为,赫尔岑贬低了堂吉诃德的形象,因此撰写这篇演讲稿并在其中强调堂吉诃德的英雄主义因素,把堂吉诃德看成是一个战士和革命者。
屠格涅夫在整篇演讲中,对堂吉诃德的形象进行了新的界定,他提出:“堂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6]182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对待其信仰的态度是义无反顾且坚信不疑的,“他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满足于吃最粗劣的饭食和穿最寒酸的衣服,因为他顾不上这些……他的道德观念的坚固性(请注意,这个发疯的游侠骑士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使得他的所有见解和言论,使得他整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显得特别有气魄,虽然他不断地陷入滑稽可笑和受屈辱的境况之中”[6]183。这些解读都跳出了传统评论家对于堂吉诃德形象的固化认识,堂吉诃德不再仅仅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丑角骑士,所收到的也不再是人们的可怜和同情。屠格涅夫使堂吉诃德成为了一面精神上的旗帜,他对骑士道的痴迷也逐渐被提升为对信仰的笃信和执着。
同为俄国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认同屠格涅夫那篇演讲稿(即《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文中的理念在他本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痕迹,也体现在他将自我牺牲的堂吉诃德式形象投射到梅什金公爵身上。屠格涅夫的名作被证明是对堂吉诃德这个有信仰之人的颂歌,并且堂吉诃德被一个超过他自身能力的理想所鼓舞(即便可笑地受到欺骗)。为了不让自己的分类所暗示的东西留下任何疑问,屠格涅夫提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把他作为堂吉诃德类型的例证[8]323-325。这充分表明,正如俄国传统圣愚们做出种种怪异的举动以求精神上的自我提升一样,堂吉诃德似乎也在荒诞怪异的举动中向世人宣扬着他的骑士道。由此可见,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别样解读并不是空穴来风。
欧洲传统文化对待疯癫者并不持一种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疯癫是一种理性的缺失,是一种脱离上帝的行为。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的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9]3欧洲一些国家自中世纪起就开始兴建精神病院,失去理性者被剥夺社会权利、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受到讨伐。而俄国对于愚者和疯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对这些难以琢磨的对象怀有高度的敬重心理,认为这些愚者的举动是对世俗肉身的贬斥,是追求高度精神境界的途径,认为这些人是靠近于上帝的圣者。堂吉诃德在欧洲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一个疯子或小丑,这一先决视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很多欧洲的评论家无法将堂吉诃德与自我牺牲从而献身信仰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当堂吉诃德传入俄国后,他所谓的疯狂举动恰恰符合俄国对于圣愚的传统肯定,触动了俄国作家评论家对于疯癫这一概念的敏感性,这也就导致了俄国评论家对于堂吉诃德的同情与赞美。
屠格涅夫作为俄国作家,虽然自称无神论者,但其却创作出了许多“神秘小说”,如《奇怪的故事》中本身就塑造了带有圣愚和圣徒意味的人物,代表作《罗亭》中对于罗亭的塑造也富有传统圣愚的漂泊无根性,而罗亭本身就被称为“俄国的堂吉诃德”。这足见圣愚传统对于屠格涅夫的深刻影响,同时其也乐于用圣愚这一文化形象对文学人物进行创作和理解。
因此,屠格涅夫在反对他人对堂吉诃德形象进行传统界定时引入圣愚性的解读并不意外。当认真解读屠格涅夫对于堂吉诃德的整体理解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的丰富圣愚因素。屠格涅夫在解读堂吉诃德时认为,堂吉诃德本身首先表现的就是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一句话,对那种处于个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6]182。屠格涅夫之前的评论家对堂吉诃德的赞美多集中于对骑士道的坚定追求,并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哪怕是别林斯基也仍旧是从骑士道的角度对堂吉诃德进行解读的。“别林斯基开创了俄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认为堂吉诃德主要是一个骑士的思想,俄国文学评论家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堂吉诃德。”[5]但是,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解读显然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他认为堂吉诃德的牺牲精神是一种“为它(真理)服务时持之以恒并且做出大的牺牲”[6]182,将自我的牺牲归结到“为了信仰和真理的付出”上去,是符合俄国对于圣愚定义的。
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并非真的疯子,只是看起来让人觉得他是疯子而已。其与世人之间的鸿沟主要在于,世人对其行为的难以理解,以至于他的行为被世人怪化为疯子行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堂吉诃德却保持着难得的坚定和不可动摇——“他不大容易产生共鸣,也不大会进行欣赏;但是他像一棵千年的古树,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既不能改变自己的信念,又不能把思想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6]183。这种饱藏于疯狂外在下的虔诚,也与圣愚不谋而合。
屠格涅夫对于堂吉诃德形象的分析,获得了很多与他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下的俄国作家、评论家的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受堂吉诃德影响创作出了白痴——梅什金这一富有极其典型圣愚气质的文学形象。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长篇小说(指《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中,堂吉诃德是最完整的一个。但他之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时滑稽又可笑。”[10]188这些对于堂吉诃德的进一步理解和塑造,表明了堂吉诃德在屠格涅夫等俄国文学家视角里的群体想象。他的疯狂行径和他因此承受的苦痛,以及他坚定不改的追寻之心,深深地打动了俄国学者,并使他们将其与本国的圣愚形象逐渐联系起来。
堂吉诃德之所以在俄国得到迥异于欧洲的解读与发展,并不仅仅因为俄国评论家对于疯癫者这一形象的敏感性,更因为堂吉诃德与俄国传统圣愚形象本身就具有很多相似性。
三、俄国传统圣愚形象与堂吉诃德的相似性
圣愚是俄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译为“为了基督的痴愚”。本质上是东正教背景下一种特殊的苦修者,大多是一些行为怪异、疯疯癫癫、满口胡话的乞丐或是流浪汉。与传统基督教对待疯子的态度不同,俄国从上层贵族到下层农民都对这些怪异者异常尊敬,认为他们超脱肉体的痛苦而锤炼自我的精神,奉他们说的话为预言,甚至在俄国有过多次大型的圣愚封圣活动。
圣愚之所以在俄国备受尊崇,与其传统影响密不可分,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提出:“在俄国圣愚现象中,有两种传统汇合为一:异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从而大大促成了俄国的双重信仰。圣愚的某些传统特征来源于基督教,另外一些特征来源于萨满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教会对于区分两种来源的意识逐渐消失,但是这样一种现象却保存了下来。”[11]22
俄国传统文化中的圣愚形象随着年代的不同曾多次发生细小的转变,但是其主体形象依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外在形象主要表现为对肉体的摒弃和自我折磨,一些圣愚会在身上佩戴沉重的铁器,并且故意做出引人发笑的举动,甚至主动惹怒他人对自己进行侮辱和迫害。而其内在则表现为对于信仰的绝对尊崇。从这些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堂吉诃德与圣愚形象之间有着极多的相似性,因此才会被俄国评论家以一种近似圣愚的角度进行解读。
首先,堂吉诃德的精神状态与圣愚们多有相似。堂吉诃德一直被称为“癫狂的骑士”,在塞万提斯笔下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被骑士道迷昏了头的怪人。他怀揣着不合时宜的梦想,喊着陈旧的口号,衣着打扮也十分稀奇古怪,迥异于常人。他身材消瘦、高个子,身着一件破烂盔甲,手执一柄长矛,骑一匹驽马,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旁观者可能一开始会因其怪异而略感恐惧,不过很快就会对他的痴愚大肆嘲笑和捉弄,把他当成一个傻子。
然而,实际上的堂吉诃德不止一次在书中的片段描述里展现出他过人的智慧和见解。“他穿着绿色羊毛背心,戴着托莱多式的红色睡帽,又干又瘦,坐在床上活像一个木乃伊。他向两人表示了欢迎,两人问他身体如何,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和身体,思路清晰言辞文雅。闲聊之际,三人谈起国内时政和治国之道,什么弊端应该谴责和革除,什么风气应该改革和取消,俨然成了新上任的立法官,当代的来古格士,再世的梭伦……在谈到的所有问题上堂吉诃德都谈得合情合理,切中要害。”[12]1这样的堂吉诃德让人不由得怀疑,他在外旅行时的一言一行是否是一种伪装,而非其本来面目。堂吉诃德似乎在病弱的学者和疯狂的骑士病患者间反复跳跃,这种表现令人迷惑。
堂吉诃德这种时而清醒、时而昏聩的形象与圣愚如出一辙,我们不难发现,其所作所为看似痴傻可笑,但却无一不是在维护他所笃信和渴望恢复的骑士道。他呵斥鞭打男孩的农夫,释放被押送的犯人,为多洛苔娅小姐报仇等行为,虽然多以可笑的结局收场,但其出发点确实符合堂吉诃德口中的真正的骑士行径,这也恰恰证实了堂吉诃德的正道性。这种对骑士道的内在信仰和其自身荒诞不羁的外在表现与圣愚高度相似。
其次,堂吉诃德的外在打扮和行为举止,符合俄国传统文化对圣愚的界定。俄国圣愚会在身上披挂一些破铜烂铁,早期圣愚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到了中晚期,圣愚虽然会穿一些破衣烂衫,但大多衣不蔽体,尽力使自己的穿着打扮异于众人。堂吉诃德的骑士装扮明显与他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戴着借来的头盔,穿着生锈的盔甲,骑着驽马。无论怎样也不能将其与光辉的骑士联系在一起,但是他确实是全书中最富有骑士精神的人。外在形象的落魄却无法掩饰他内心对骑士道的纯澈追求,也契合俄国那些看起来疯癫痴狂却永远心怀上帝的圣愚形象。
同时,堂吉诃德的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符合圣愚所谓的“第二视力”。“第二视力”是指圣愚们可以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事物,他们会因此说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语言,但这也恰恰是他们高于常人的证明。堂吉诃德冲进山羊群、与风车搏斗、劈砍酒袋,最终的结局是头破血流,毫无收获。这些看起来出自一个疯狂者的举动也被赋予了另一种解读方式,“没有人认可一个疯子的思想,大家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赤裸裸的现实。这个世界没有魔鬼,只有风车;这个世界没有强盗,只有羊群;这个世界没有城堡,只有旅店;第一视力成为人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可怜堂吉诃德至死才明白这个道理,原来他只不过是个疯子”[13]。堂吉诃德以悲剧收场的壮举恰如圣愚们降格生而为人的尊严来接近上帝却不被他人所理解的行为。
正是由于堂吉诃德身上这些让人很容易就与圣愚联系起来的特质,他在屠格涅夫等俄国评论家的观念里才不再止步于单纯的疯子形象。如果将堂吉诃德疯疯癫癫的举止理解为其故意为之,且目的是为了正道,那么他的确可以被勾画为一个胸怀大道、警醒世人之人,也正是这种理解的产生让堂吉诃德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四、结语
19 世纪堂吉诃德形象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巨大的转变,与俄国评论家们对其形象的全新解读密不可分。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俄国评论家更是将堂吉诃德的形象提升到信仰追求者的高度。这一形象的解读实际上充分受到俄国东正教传统的影响,俄国评论家对疯癫的敏感和不同于欧洲的别样理解,促使他们将堂吉诃德与本国传统形象——圣愚逐渐联系在一起。自屠格涅夫解读堂吉诃德伊始,其对堂吉诃德的认识中便富有俄国圣愚特性,而堂吉诃德自身的行为举动,也与圣愚有诸多相似之处。两相结合之下,诞生了对于堂吉诃德的全新解读,推动了《堂吉诃德》的经典化进程,进而影响了世界对堂吉诃德形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