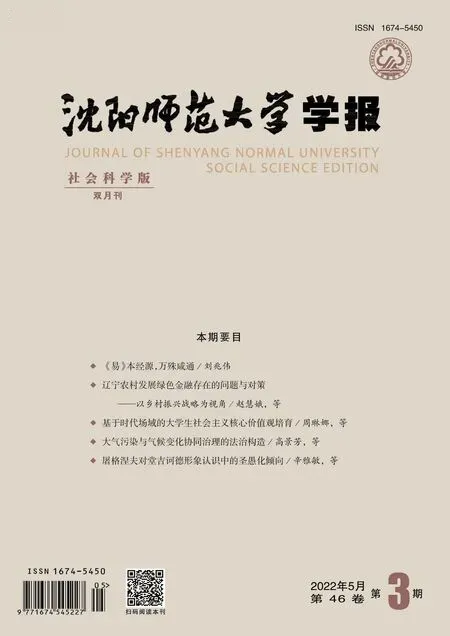家族小说伦理叙事基本属性及其与现实伦理关系
于 巍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家族小说主要是指以家族兴衰和家族人物生活为描写对象,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人情世态与时代特征的小说类型,其主要特征是具有情感体验上的人伦亲情性,对社会透视的家国同构性,宏阔的时间跨度和历史感,并能为人们提供价值精神或价值关系的伦理道德指引。在中国文学史上,家族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母题,有关家族的言说绵密繁复、不绝于耳。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莫言、张炜、陈忠实等一大批中国作家将创作的视点转向家族题材,构成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丰富面向,也由此形成了家族小说集簇的独特创作现象。家族小说伦理叙事研究在文学伦理学的滋养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的研究多从具体作品分析视角对家族小说进行社会学、伦理学审视,在基本概念的厘清方面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家族小说伦理叙事相较于一般伦理而言具有独特的品性,其与一般现实伦理既关联,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它一方面是现实伦理的反映,受到现实伦理语境的规约和激荡;另一方面,它又归属于文学,具有对现实伦理的超越性。对家族小说伦理叙事特性进行梳理与辨析有益于丰富文学伦理学的理论视域,同时可以扩展家族小说研究的纵深。
一、家族小说叙事的伦理视域
家族小说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叙事的基点和描述的中心,伦理成为家族小说创作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可以说,伦理为家族小说叙事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内在语境,它构成了家族小说创作、接受的整个环境。伦理关系与家族小说创作形成了互构关系,一方面,伦理成为家族小说创作的背景和反映的内容;另一方面,家族小说也成为伦理建构的本身,体现伦理并重构时代伦理。就新时期以来家族小说叙事的伦理视域而言,它本身是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融合,具有传承性与多元性,这其中既有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也有西方伦理观念的影响,同时更表现出一种社会转型期的伦理情绪与冲动。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构成了新时期家族小说叙事的底色。在古代中国,伦理即是人伦之理、做人之理,“伦理者,犹言人人当守其为人之规则,而各遵其秩序耳。盖人与人相接,伦理始生。”[1]128人伦之理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原则和规范,伦理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中国的伦理观念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五伦”为典范的伦理观念,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在中国传统中,人伦关系建基于家族伦理关系之上,在“五伦”中家族伦理是构成的基础,君臣、朋友关系的实质也是家族关系的外化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伦理就是经儒家思想演化的家族伦理,是一种血缘亲情伦理的关系。“发端于‘孝悌’这种基本的人伦感情”[2],首先把仁爱施予有血缘有关系的人,继而才能把“仁”推及他人、社会和国家之上。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很自然地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成为文学作品伦理叙事的基础生发点。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尊崇基本伦理的规约,开展创作活动,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限定,如传统小说的“内圣外王”“男尊女卑”观念,“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现实教化意图等,均出于此。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逐渐引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伦理观逐渐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互碰撞、融合,家族小说的伦理环境也因之而发生变化,不断展现着中西伦理观念交融的过程。逐渐地,西方的个体本位主义与中国传统家庭(族)本位之间的冲突,激荡着思想文化及家族小说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思潮,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家族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和沿袭,对高老太爷、蒋捷山、黄俭之等封建家长形象的塑造就是这种伦理批判的艺术实践。与此同时,作家们在创作中常面临情与理、形象描绘与思想批判间的矛盾和冲突,“理智上,他们觉悟到对代表封建父权、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必须展开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在情感上,他们对现实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又不无依恋;在思想批判的意义上,作家们可以对观念上的、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父亲展开猛烈轰击;在文学描绘的意义上,作家却难以对具体的、以个体形象出现的父亲妄加褒贬判断。因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对子女的正常的必要的严与教,同代表封建父权的严酷与专横之间的界限,本就难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这在客观上就给作家们的文学描绘设置了一道颇费踌躇、难于妄加判断的难题。”[3]伦理语境的冲突,表现在家族小说中即是创作心态和叙事表现上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至21 世纪以来伦理思想的转型,为家族小说伦理叙事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伦理叙事语境。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伦理经历了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它一方面转化传统伦理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吸收借鉴西方伦理资源,集合了自身发展、历史传承、吸收借鉴于一身,形成了变动的、多元的、发展的社会伦理氛围。在家族小说创作上,催生出一大批具有本土性、时代性伦理意味的家族小说作品。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这些作品的伦理冲突不再囿于“父子”文化符号的历史隐喻,也不局限于“审父”“弑父”的西方主题模式,而是为文学史提供了众多丰满、多面的人物形象,他们在传统中挣扎,在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中焦虑,在时代伦理中徘徊。
二、伦理作为家族小说的母题特征
家族小说是叙事伦理学重要的文学样式,它是社会伦理向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自然延伸,中国十分重视亲善伦理,家族小说也自然成为承载伦理的重要叙事文体。基于中国文化的伦理特质而言,家族小说的伦理问题构成了家族小说叙事的母题特征,表现和描写伦理成为家族小说的重要特点,就内容而言家族小说以叙述家族在社会文化转型与冲突过程中父子、兄弟、夫妻、亲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重点,充分展现家庭、个人、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它勾连的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复杂的因素和问题导致了各种伦理问题的扭结和生发。因此,伦理内容成为家族小说表述的重要内容。
从主题学研究视角看,家族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在世界各国的经典小说作品中,家族小说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家族小说主要通过对家族代际之间的故事叙述折射出家族中人与人之间、家族与社会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家族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承续与绵延,诸如中国较早出现的《金瓶梅》《红楼梦》这样典型的家族小说。进入20 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家族叙事倾向,如1949 年之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四世同堂》(老舍)、《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等,之后的如《红旗谱》(梁斌)、《三家巷》(欧阳山)、《古船》、《家族》(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笨花》(铁凝)、《秦腔》(贾平凹)等,都以家族为集中叙事的主题,这些小说充分彰显了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揭示20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以及生命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梁鸿说得较为恰切:“‘家族主题’对于揭示中国20 世纪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广的意义和可探索性,它所蕴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20 世纪的作家无法忽略掉的文学命题。”[4]在西方,描写大家族生活的叙事作品众多,对家族小说的认知也是从小说主题类型上进行区分,把家族小说看作是“它应该指描写一个或几个家庭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关系的散文叙事作品——既写两代人以上的家族本身及生活,甚至追溯家族的历史,也涉及同代人中几个成员和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5]。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华克家族传说为原型,描写两个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及爱情与复仇故事。自《呼啸山庄》之后西方的家族小说不断丰富,蔚为大观,早期的创作有左拉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史》(1871—1893)、萨克雷的长篇《纽可漠一家》(1851—1853)等,托·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1906—1922)、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1922—1940)、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基伦斯的《扬布拉德一家》(1954)、阿·哈利的《根》(1976)等。
从母题的特性看,“作为文学史研究术语的‘母题’,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事件、场面、意象、观念、情绪等。具体说来,就是某类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或题材。如战争、爱情、悲秋、别离、思乡、流浪等母题。所谓情节母题,是文学作品中起主干作用的事件、场面、意象(这些事件、场面、意象当然也往往包含了某些观念、情绪),它往往是某类文学创作的标志,是显示某类文学创作特点的内容”[6]。中国家族小说的母题特性重要的表现方式和形态正是通过对伦理的表达来实现的,其涉猎的伦理问题具有特指性。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加以体现的,宗法血缘关系是家族的核心。在中国强调宗法等级秩序的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等级秩序便体现在家族中。为保障社会的稳定,制定相应的伦理纲常对家族成员进行尊卑有序的伦理制约,并强调“礼治德化”加以道德约束。随着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种旨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家族伦理遭到重创,但蕴含于伦理道德意识之中的道德精神却还在延续,并经由家族成员间伦理关系的变化得以体现。
三、家族小说伦理叙事与现实伦理的扭结
在中国,家族自身就是重要的伦理表征,而以家族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家族小说又是讲述伦理故事最为集中和最为传统的文体之一。伦理内容是家族小说伦理叙事的重点和核心,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等在家族小说中都有重要的映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族小说与伦理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不同之处或者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小说中所反映的伦理内容和伦理关系与现实伦理关系密切但并非完全的对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家族小说伦理叙事与现实伦理的扭结
家族小说是以文学叙事为载体对现实伦理关系的反映,家族小说中所呈现的伦理内容和现实伦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中国家族小说一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文体风格,但作为文学文本,它的实质也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原型,通过艺术加工而成的精神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考察文学艺术特征时,对文艺属性作出的重要总结。意识形态被马克思创造性地引入,在解决唯心主义与旧的唯物主义中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等对立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后来理论家认识世界与社会的重要支撑。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权利话语体系,是“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则的表征体系”,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但意识形态并不表达人们的真实生活,而只是人们借以体验现实世界的“想象方式”[7]201-203。在《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中,他把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有四个过程:第一,社会把个人当做主体来召唤;第二,个人接受召唤,把社会当做承认欲望的对象,并向它屈从;第三,主体同社会主体互相识别,主体间相互识别,主体对自己识别;第四,把想象的状况当做实际状况,主体承认自己是什么,并照此去行动。这实际上表达了在意识形态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人的限制,同时也体现出现实与意识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这种对人的限制和不对等关系表现在艺术当中,就赋予艺术以特殊的意味,艺术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8]520-521。艺术作品具有独立艺术特质,它具有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艺术的这种属性不但区隔了艺术本身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且改变着和创生着它们的关系。就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来看,艺术赋予叙事干预现实与虚构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如马舍雷所说,文学的“虚构欺骗了我们,它确实是想象中的秩序;但它的本意不在欺骗,因为它通过显露自身的欺骗性揭示了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更大的欺骗性,帮助我们摆脱它”[9]456。这种疏离无疑造成了艺术作品及叙事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脱离和纠缠关系。
就家族小说伦理叙事而言,作为叙事艺术,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可避免,其与现实伦理的关系也正构成了叙事艺术意识形态属性与现实之间的疏离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非但无法一一对应,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决定与被决定、把控与逃逸、扭结与疏离的张力关系。这导致家族小说伦理叙事与现实伦理之间不是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复杂的纠合,这也决定了在审视家族小说中表现的伦理内容时不能简单地与现实伦理相对应,尽管他们之间是互文性的依存关系。同时,家族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也决定了家族小说中的伦理对现实伦理的反思和增殖。
(二)家族小说伦理叙事与现实伦理之间的错位
不单是小说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叙事本身的特征也决定了家族小说呈现的伦理内容与现实伦理之间的错位。当我们在探讨描述发生过程中的一件事和现实中事实本身的关系时,就会进入对叙事与纯粹现实关系问题的思考之中。当事实被叙述后它将以“叙事”的面貌出现,那么“叙事”与现实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华莱士·马丁曾有这样的一段论述: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一切(事)在尚未被人形诸语言之前,是按照“本来”面貌存在着的。但这样的事件不是narrative(叙事),而是story,即故事。当这种意义上的故事被特定语言表述之后,所得的结果才是narrative,即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以一定方式结构起来的、并由一位叙述者由特定角度传达给读者(听众)的一系列事件。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参考框架和描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10]323-324。
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错位直接区分了叙事与现实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叙事终究与现实不是一回事,因此在了解“叙事”(narrative)的基本概念时,可以发现“叙事”概念本身有其复杂性和与现实的错位关系。“叙事”的希腊词语是“diefesis”,在英语中的形式为“diegedis”,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便开始使用这一词语,以表达这个证人在法庭上陈述证词的行为。柏拉图在《理想国》第3 卷中也提到这一词,是与模仿相对的概念,意为“纯粹的叙述”。发展到今天,“叙事”的客观性意指已经变得松动,一般指“详细叙述一系列事实或事件并确定和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11]172。热拉尔·热奈特重新发现了“叙事”的古老意义,将其分为三层:第一,指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即故事(story);第二,指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不同的关系,即叙事(narrative);第三,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的事件,即叙述(narrating)[12]6。这种对“叙事”的划分和理解自有其混乱性的同时,也见出“叙事”本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们紧密相连但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叙事”在事实和故事之间游移,它经过叙述者的加工,以一种别样的“话语”方式被认知,或以全新的面貌和意图被公诸于世,这样看来“叙事”已经逃逸出现实事件本身。由“叙事”而展现出的伦理,它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关系也便是错位的、扭结的。在家族小说中讲述的伦理故事及发生方式与现实伦理从叙事本质来看是错位的。
(三)家族小说伦理叙事方式的多样性
从叙事的方式和功能上看,叙事的方式和模式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与现实相比,叙事的多元化超越了现实事实发展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具体到家族小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家族小说伦理的表达途径是多样的,它对现实伦理的发展具有超越性。
如前面提到的热拉尔·热奈特等人对“叙事”的理解,其实包含了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即讲故事的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从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可以将叙事理解为具体的“话语”形式。所谓“话语”(discourse),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术语,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一般理解为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后来扩展为语言在具体语境中所运用的形式,即具体的说话行为和方式,在文学叙事中指文本中的语言即其构成,相当于热拉尔·热奈特所说的“叙述”,“亦即确定以何种方式向听众叙述事件”[11]172。在现代文化、哲学、文学研究领域对“话语”的理解一直在扩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为“话语”注入了新的内涵,他将其界定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历史文化即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构成。各话语类别有其独立存在,同时也共同组成文化的整体内涵,文学叙事话语也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现象,由此提出了话语力量。其中,福柯提出了“话语形构”(discourseformation)。在他看来“话语形构”由各式各样的“陈述”(statememt)组成,支配“陈述”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利”(power),权利对话语进行支配关系[13]。在巴赫金那里,“话语”既是口头的也是书面的,它是两者的统称,又是语言交际的现实单位。在福柯和巴赫金那里作为“叙事”的“话语”显然已经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跳脱而出,已经加入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载体功能,话语表述的技巧、形式也因此变得多元而有意义,不再是单一的语言表意符号。
很显然,叙事的多元化功能赋予了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叙事本身已经不是单纯的语意表达,其自身承载着信息交流、意识形态属性及世界建构等功能,为了达到复杂的建构目的,叙事方式也就是多元的,具有差异化的表达。在家族小说叙事中,其叙述方式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一方面,它承载着复杂的建构内容和意义,其中包括对伦理、思想、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建构与表达;另一方面,它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的展现充分实现着不同的艺术追求。为此,很自然地,家族小说叙事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就有了巨大的差异,家族小说通过叙事通达伦理的追求和意图,它采取的路径是多元的,所揭示出的伦理内涵也是多元而丰富的,它跳脱出历史必然性,以更为广阔的方式观照社会伦理、现实伦理,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伦理本身,更是伦理的可能性。
概言之,家族小说中“伦理叙事”指涉伦理与叙事两个范畴,其既关注文学背后的伦理内容,又关注讲述伦理的技巧,既承认伦理与叙事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又强调伦理叙事对现实伦理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