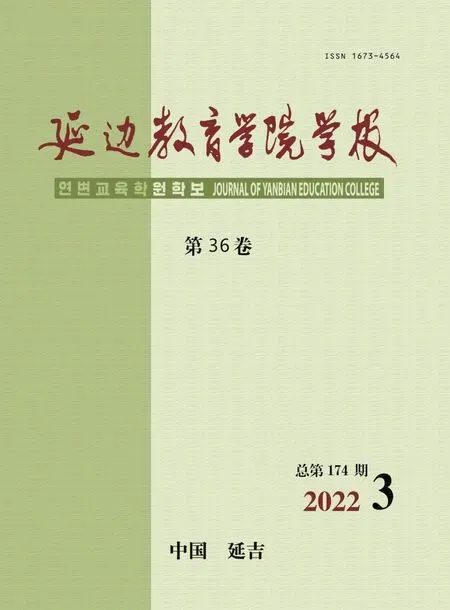纵贯一生的追寻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自由观
安亮帆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一、格罗斯曼其人的文学创作与军旅生涯
(一)格罗斯曼与其早期文学创作概述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于1905 年12月12 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基辅省的别尔基切夫。其本名约瑟夫(Иосиф)继承自其具有犹太血统的父亲所罗门·约瑟夫维奇·格罗斯曼(Соломон Иоси ф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其父辈一支皆是在乌克兰敖德萨省的基利亚(Килия)地区世代经商的富庶望族。[1]
格罗斯曼的文学创作生涯起始于19 世纪20 年代末[2]。在《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创造力与命运》一书中,作者写道:大学时期的格罗斯曼一边在莫斯科当家庭教师,一边从事业余的写作。[3]影响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契机发生在1934 年,这一年格罗斯曼发表的小说《格卢考夫的故事》(《Глюкауф》)得到了高尔基的高度赞扬与肯定,这一作品的成功坚定了格罗斯曼彻底转型成为职业作家的想法。
(二)格罗斯曼的军人经历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941 年,格罗斯曼被派往苏德战争前线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至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地区担任战地记者一职。同年6 月,他的亲人被苏联政府紧急疏散到塔什干地区。9月,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别尔基切夫,并进行了针对的犹太人种族屠杀。他的母亲在这次屠杀中因民族身份而惨遭德军枪毙。[4]
这段军旅生涯把稚嫩且激进的青年格罗斯曼磨砺成为拥有敏锐感知、心怀苏联人民群众命运前途的伟大作家,五年的战争前线经历与记者工作造就了格罗斯曼冷峻写实的文风以及他继承自契诃夫、托尔斯泰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5]
二、格罗斯曼创作生涯中自由观的转变
(一)《人民是不朽的》中所蕴含的自由观雏形
茅盾在1945 年发表的文章《关于<人民是不朽的>》中写道:“苏联人民民族自尊心以及自信力并不是单单从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上的光荣中来的,而是用自己的劳动建立幸福,自己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的人民从现实基础之上养育的。”[6]《人民是不朽的》是格罗斯曼担任战地记者后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品刻画了营地委员包加列夫、营长巴巴姜梁、少校团长迈尔采洛夫以及普通士兵伊格纳底耶夫等一众鲜活的苏联红军战士形象。小说描写了苏德战场前线的苏联士兵经历城市被德军轰炸后奋勇反攻,收复故土的经历。
在《人民是不朽的》中,格罗斯曼着墨最多的人物就是营地委员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包加列夫。包加列夫在战争爆发前是莫斯科某大学的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本来与妻子丽莎过着平静的生活,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征召入伍并担任政治部对敌工作课的代理课长。格罗斯曼在小说中说:“千千万万的人民为了自由而毅然舍生忘死,正像他们曾经毅然担起了工作的重担。在广阔的疆场上这样崇高、朴质、严肃而成仁,成为这样的人民真正是伟大的。”[7]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包加列夫这样的愿意付出一切追求建立自由国家的苏联人民,他的国家才因此伟大,人民也才因此不朽。人民何以是不朽的?——人民因为自由献身而不朽。
母亲离世给格罗斯曼带来的痛苦则通过在小说中描绘浸润鲜血的乌克兰大地体现了出来,伊格纳底耶夫看见德军士兵在自己的故土上过着他们曾经所拥有的幸福生活,认清了他必须将侵略者驱赶出苏联的每一寸国土。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格罗斯曼本人对于法西斯侵略者的态度。
(二)《生活与命运》中不断发展成熟自由观
《生活与命运》是格罗斯曼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小说通过刻画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无数亲人好友的回忆,回答了战争中人的“生活”以及“命运”。格罗斯曼在这部作品中将自己的视角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微观的人的层面上。
在《生活与命运》中,苏联国家机器在一切日常生活中都是个无形的存在,每一次的谈话和思考中苏联都作为一个隐藏的第三方嵌入着。对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讽刺和对压迫人自由的苏联极端政治环境的批判都体现出了作家本身的自由观念。格罗斯曼笔下的人物,都会试图在密不透风的极端政治环境中寻求一丝喘息的机会,无论这时间多么地短暂、影响多么地微弱。吉迪恩·海格教授认为格罗斯曼试图在通过这种描写手法来表达:“整个俄罗斯民族都处在对于自由的无意识交谈之中”。[8]
(三)《一切都在流动》中对斯拉夫民族自由问题的终极发问
《一切都在流动》是作家生前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作家透过小说主人公伊凡的视角,对国家机器无情蹂躏人的自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究竟是什么在流动?”在小说结尾处,伊凡独自一人面对大海,感叹荒谬的时间在无情地流动着。苏联人民一方面麻木地沉浸在国家在工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斯拉夫民族惯有顺服性跪倒在国家机器的面前,甚至甘愿舍弃自己的自由。
格罗斯曼对于斯拉夫民族所处的这种困境并没有报以失望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革命后的俄罗斯在斯大林身上认清了自己”。这个民族惯有的顺服性和麻木性让这片土地诞生了数不尽的残暴政权,但是无论何时,斯拉夫民族总能在寒冷坚硬的土壤上寻求那一点点微弱的自由。自由不会因为斯大林的出现而消亡,斯大林走后,他的事业也不会就此终结,自由的生命力就像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一样:无论前路多凶险,它总会绝地求生并永远存在、不断壮大下去。再强大的力量最后都会在时间的流动中消散而去。“在历史的这条长河中,不灭的永远是人对自由的渴望。”[9]
三、苏联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格罗斯曼的自由观
(一)苏联高压政治环境下格罗斯曼小说出版的坎坷历程
1949 年,《为了正义的事业》正式完稿交付出版,该作于1952 年被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起初,小说受到了苏联作家界的一致好评,但仅仅几个月后,斯大林就在苏联掀起了新一波的反犹浪潮,身为犹太人作家的格罗斯曼在此时遭到布宾诺夫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批评文章而成为众矢之的,该事件的影响直到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解冻时期”才得以平息。[10]
早在1960 年,小说《生活与命运》就得以定稿,格罗斯曼最早将作品原稿交付给了《旗》杂志,但杂志社却始终未给格罗斯曼本人任何关于该书出版的答复。同年11月《旗》杂志编辑部邀请格罗斯曼参加编辑部扩大会议,格罗斯曼本人意识到事态已经急转直下,便以身体生病不适为由拒绝出席会议。[11]1961 年,《旗》编辑部正式通知作家本人,该小说不能发表。不久,《生活与命运》的两份手稿被苏联军方查收。此后,格罗斯曼上信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并收到了广为流传的“该小说至少两三百年后才有机会出版”的回信。[12]受到巨大打击的格罗斯曼因心力交瘁以及饱受癌症折磨很快于1964 年病逝。一直到1980 年,以幸存下来的本书微缩胶片原稿为基础的俄文版单行本才在瑞士首次与世人见面。苏联更是到1988 年“文学回归潮”时期才得以在格罗斯曼自己的祖国出版。
弥留之际的格罗斯曼对好友利普京坦言:“我希望小说可以出版,哪怕是国外也行”。[13]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关心小说的出版事宜,即便遭受当局的万般打压,他依旧执着地秉持着自己坚定的自由观念,始终保持着一种完美主义的人生态度。[14]
(二)格罗斯曼自由观的发展历程
1.格罗斯曼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
格罗斯曼自由就建立起了对于19 世纪20 年代前西欧传统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他从小就开始大量阅读原版法语书籍,在其诗人朋友谢苗·伊兹列维奇·利普金(Се мён Израилевич Липкин)的回忆录《生活与命运:瓦西里·格罗斯曼》中,谢苗写道:“他对犹太人的历史知之甚少,他特别喜欢阅读与背诵阿尔封斯·都德的作品集《磨坊书简》。在他的作品以及艺术品位上,无论是绘画、文学还是音乐方面,他都更致力于传统的俄罗斯与西欧经典。受到他作为孟什维克的父亲的启发,他在青年时期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观点。”[15]
2.极端社会政治环境与作家个人自由意志的对抗冲突
结束了瑞士旅居生活的格罗斯曼目睹了由于内战导致的混乱俄国社会现状:若无其事的抢劫、强奸以及谋杀造成的尖叫声夜夜盘旋在别尔基切夫城市的上空,残酷的社会现实坚定了格罗斯曼放弃科学而投身文学的信心。1930 年,格罗斯曼赴乌克兰顿涅茨克盆地煤矿进行考察并创作了小说《格卢考夫的故事》,出版商以小说有意识形态缺陷而拒绝了他。他在给作家高尔基的信件中发问道:“我写的是实话,或者说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现实怎可能是反革命的呢?”高尔基在回信中答道:“世界实际只有两个真相:一个是过去的肮脏真相,另一个是斯大林治理下的新真相。”[16]这一时期的格罗斯曼不再寄希望于文学创作,而是靠埋头工作麻木自己来逃避绝望和压力。
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后的格罗斯曼再度觉醒,他深感自己有义务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人们,随即开始着手创作苏联的“战争与和平”。他仔细思考了为何卫国战争中苏联军队会反败为胜以及战争转折点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道出了答案,即“人类对自由的忠诚”。这一时期其作品受到了苏联当局的高度赞扬,但是时局的剧烈变化再一次粉碎了格罗斯曼重新建立起来的文学信心。1951 年,格罗斯曼因犹太人身份被列入逮捕名单并被投入监狱之中,在他人的帮助下他得以逃离莫斯科,在好友的住所避难。
面对贯穿整个人生的一系列打压,格罗斯曼却愈发展现出坚韧的品质,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他借《一切都在流动》的主人公伊凡之口表达着自己“在铁丝网的两边,自由似乎是不朽的”的自由观念。
格罗斯曼在与苏联极端社会政治环境的斗争中落败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没收对于其的打击是巨大的。到1964 年去世前夕,他的自由观发展成熟到了新的高度,虽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反对人的自由的,但格罗斯曼在作品中始终传达着对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二者割裂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精神自由的渴望。无论帝国的大厦建设得多么高耸,人类的历史或者说一切生命的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
3.格罗斯曼笔下人物世界轴心转变的现实映射
亲历残酷的卫国战争对格罗斯曼本人世界轴心转变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格罗斯曼在《人民是不朽的》中模仿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角色完成了从贵族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变那样,他描绘下的苏联人民的精神在战争洗礼下经历了从阶级自觉到民族自觉的转变。[17]包加列夫被残酷的战争粗暴地从安稳的生活中拉出来,他亲眼看到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苏联军民坚决反抗的意志以及战友之间出生入死的情谊。“簌簌地吹动那些黑簇簇树叶的晚风发着镇定而悲壮的声音,就像一个人知道今日不自由毋宁死,别无选择”,彼时苏联人民的世界轴心便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格罗斯曼在小说中说道:“在这些艰苦的时日,人民所愿知道的是真实的情形,尽管这些可能是不愉快的。而包加列夫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了。”
从包加列夫再到施特鲁姆,格罗斯曼在两部作品中投射的自我形象有了剧烈的变化。格罗斯曼的自由观从建立到崩塌的过程完美地体现在了施特鲁姆身上。他透过《生活与命运》想要告诉我们:“人无法相信他会被彻底摧毁,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该书的成稿标志着格罗斯曼自身对于自由的思考已经从国家层面转变到了每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上。在格罗斯曼的作品中,其对于自由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生活苦难所呈现的表面本质,并且越来越呈现出他对自由更加强烈的渴望。
《一切都在流动》作为格罗斯曼人生最后岁月的绝唱,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当局对于人自由抹杀进行了极为露骨的批判,格罗斯曼或许想要通过这部小说表达的,正是一种不惧怕任何残酷岁月的折磨,永远都不放弃对人类精神自由追求的理想主义的自由观。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形成的思想烙印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民族。“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格罗斯曼通过三部小说告诉整个民族:战争的洗礼、物质的丰富都没能让俄罗斯获得真正的自由,能解放自由本身的就只有面对生活的勇敢、面对荒谬的坚守。
四、格罗斯曼自由观的文学意义
格罗斯曼纵使在一生的抗争中落败了,但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作家本人的自由观念在今时今日却依旧能打动全世界的无数读者。
总体来说,格罗斯曼的自由观超越了当时一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能触及的思想边界,他对于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同时也是朴素的。一方面,格罗斯曼在《人民是不朽的》中描写的苏联人民团结一心,用共同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击退法西斯,获得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解放与自由,表现出他继承了契诃夫的朴素俄罗斯优良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他在所有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于人自由的尊重、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专制集权的批判、对于俄罗斯千年苦难历史的不懈探索乃至对于人类个体自由的超越时空束缚的深刻探讨等等都足以使他永载俄罗斯文学的史册。
利普金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格罗斯曼:“在亚美尼亚(格罗斯曼去世前夕)…我记着他穿着黑色外套坐在山上的某个石头上…他的姿势是如此真实而自然,悬崖峭壁四面环绕着。你无法理解他从哪里来,又从哪里离开。他坐下,微微侧过头看去,脸上带着柔和而悲伤的微笑,仿佛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又仿佛将面庞置于一束温暖的阳光之下。他感受并捕捉这种温暖,双手握得那么紧、那么绝望…在这张照片中,他既被困又自由,这应该就是他的生活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
时间就如伊凡眼前的那般无情地流动着,格罗斯曼去世已经五十载有余,但是“人们真的会因为忘记他而不认识他吗”,格罗斯曼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磨灭,他终其一生对于自由与道德的探讨就如暗夜中的灯塔般让真理的声音愈发清晰可见。从这一点来看,格罗斯曼仍然值得现今的读者对他及他的作品进行理性的认识、思考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