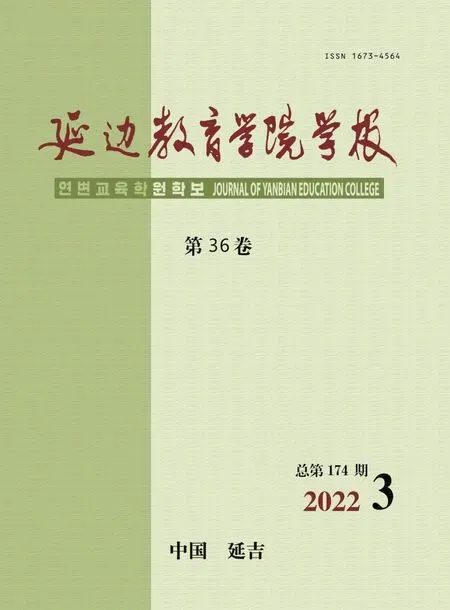众生平等
——论张贵兴《野猪渡河》中的自然主义书写
王玥琪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一、张贵兴自然主义视角的追溯
1.自然主义及其特征
19 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尤其是遗传学的迅猛发展以及现实主义手法的极致研究在法国催生了新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流派众多,且各流派之间对于自然主义的理解也各有出入,但其依旧有着可以把握的共同特征。首先,自然主义流派否定文学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目的,认为作家应保持绝对的中立,即文字中应有“无动于衷”的态度。其次,自然主义流派认同“实验小说”的方法,即将人物放入不同的环境中,试验其在自然法则的影响下形成的活动规律。第三,决定论是自然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之一,即自然主义认同人与生物的平等,认为生物学规律同样可以决定人与生物的身心以及行为。最后,与现实主义中强调的刻画典型时代中的典型人物相反,自然主义强调反映自然,即强调对社会底层、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进行刻画,从而反映真实的自然和社会。[1]
2.张贵兴与他的自然主义雨林书写历程
张贵兴(1956-),祖籍广东龙川,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罗东,在马来生活19 年,于1976 年入学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就读英文系,毕业后留台任教,1982年入籍。张贵兴此后定居台湾,但文字依旧情系与故乡马来,他对家乡的书写奠定了其当代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黄锦树称张贵兴“身体和国籍都已远离而精神却频频回顾”,在台湾创作雨林文字为张贵兴带来了距离的和记忆的挑战,但是没有了“在地性”的限制,同时距离的拉远使得其精神感官更加敏锐,其文字的审美性和自然性反而得到了施展。张贵兴在厘清题材方向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群象》(1998)、《猴杯》(2000)以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正式且隆重的铺陈了其魔幻绚烂的雨林世界观。这三部作品目前被认为是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
其中《群象》重点叙述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共历史,而个中描写则不仅有华人历史的书写,更有“权利游移”的思考。[2]《猴杯》的故事焦点则在于雉以及其上两代在婆罗洲的创业史,不同于其他华文文学中对于华人在马来土地上积极睿智,艰苦创业的书写,该篇更是表达了对华人拓荒史中的侵略性及其他阴暗面的反思。[3]其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实验性的突破,更是在兼顾美学的同时输出了作者对于华人迁入马来西亚所带来的文化碰撞,身份认同以及所有在地人共同面对的历史洪流做出的反思。《野猪渡河》是张贵兴沉寂17 年后的全新长篇著作,该部作品聚焦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将人置于滋生一切善于恶的繁茂雨林,给予人和生物同样的叙事分量,运用自然主义的笔法反映了最魔幻的雨林和最真实的生命。
3.张贵兴的文学立场
《猴杯》中的主角雉的经历几乎是张贵兴个人的真实写照,19 岁的雉负笈台湾,毕业后入籍,但身份的尴尬使得张贵兴并未真正融入,或者真正被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所接受。张贵兴对于身份的归属也常常陷入沉思,在其作品《顽皮家族》的序文中他提到自己曾陷入对故乡是哪里的怀疑,但他最愿归属的故乡,应当还是那个婆罗洲砂拉越雨林。砂拉越物质资源丰富,但贫穷落后,是战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剥削对象。砂拉越在历史上属于文莱,1842 年宣布脱离文莱成为独立的布鲁克王朝。二战时期砂拉越惨遭日军统治,日军投降后随即被英国人剥削,转而又被迫加入马来政府,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各种外来文化并未带领婆罗洲大步走向发展和进步,他们迎接的是殖民者的入侵和资源转移带来的更加贫穷落后。在《都柏林人》(1984)中乔伊斯描写的20 世纪初爱尔兰首都的都柏林人,在资本主义改造过的文化与生活环境面前是瑟缩且向往的。[4]而砂拉越华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的内心保留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强大新奇的资本影响下,处于文化和科技双重落后的他们被渗透着殖民者的价值观,资本内化了他们,而他们也内化了资本。
故土的文化环境处于一种悬空状态,作家的身份认同和作品的文化归属同样是悬空的。本就以华人身份生活在砂拉越的张贵兴毕业后更是定居台湾,这样的经历使他处于一种标准的离散状态里。张贵兴曾说:“将我放在台湾文学中,我不反对,这是可以的:排除掉,我觉得也无所谓;不承认我是台湾文学,我也无所谓。”[5]写作时他也同样没有预设读者群体,这些因素让他避免了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族叙事的弊端,避免了充满民族滤镜的华人史诗的书写,在拥抱中国性的同时解构中国性,在离散的处境中得到了更加中立、理性、反思的叙事视角,从而真正达到了自然主义的雨林史诗书写。
二、《野猪渡河》中的自然主义
1.《野猪渡河》中的实验小说成分
王德威为《野猪渡河》题的序论中提到:德勒兹(Gilles Delezue)、瓜达利(Pieree-Felix Guattari)论动物,曾区分三种层次,伊底帕斯动物(Oedipus animal),以动物为家畜甚至家宠,爱之养之;原型动物(Archetype/state animal),以动物为某种深化,政教的象征,拜之敬之。而第三种则为异类动物(daemon animal),以动物为人神魔之间一种过渡生物,繁衍多变化,难以定位,因此不断搅扰期间的界限。[6]《野猪渡河》中对生物主角“野猪”的书写便基本遵循了这样的三个层次。小说中,猪芭村的猎猪大队在狩猎野猪时,会捕杀成年的强壮野猪,而留下条纹未褪的小野猪进行圈养,此为伊底帕斯动物层次。关亚凤的父亲曾告诉它野猪是与山川大泽融为一体的,人若想感受野猪,必须将自己融入自然,与野猪合二为一。[6]关亚凤的父亲为野猪赋予了象征意义,此为原型动物层次。而小说中最施以笔墨的还是野猪飘忽游移,龇牙咧嘴的与湿热雨林、宿敌人类针锋相对而不可控的泥泞画面。人与野猪的交锋变化多端,人的兽性与兽的自然性不断交织,人与牲畜的界限也难叫人分辨,此为异类动物层次。
而这三种层次的书写则对应了自然主义中的“实验小说”方法,即将对象放入不同的环境中,试验其在自然法则的影响下形成的活动规律和情感规律。[7]《野猪渡河》中作者对于人和生物的书写分量几乎等同,小说中对于人物的书写也不难发现“实验小说”的端倪。全书中最神秘的人物爱蜜莉是泄露“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名单给日本人的细作,究其原因,爱蜜莉竟是日本人小林二郎和南洋姐的孩子,从小被神父收养,天生的政治立场和生长环境战胜了她对猪芭村的感情。这是张贵兴进行的一场“伊底帕斯”实验,将一个自然政治立场与环境相对立的人物放入其中,去预设其活动规律和情感变化,从而进行书写。文中的朱大帝是带领猪芭村众人围剿野猪,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然而他转头就爬上了了13 岁的养女牛油妈的床,又在围剿野猪的夜晚强奸了男主关亚凤的母亲小蛾。朱大帝此生最大的执念就是猎杀野猪王,可兽性胜过人性的他自己或许才是他念念不忘的“猪王”。南洋姐“巨鳄”在猪芭村饱受村民小金的恩惠,对小金的态度也是例外的。小金本以为这是两个落魄灵魂的互相慰藉,即使在战事紧张时也依旧冒死去见她,但“巨鳄”却果断的出卖了小金,使得小金死在鬼子的乱枪扫射之下。或许被压抑的欲望和超越本能的情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人性,但人性本就是复杂多变,难以用几个词汇或标签来判定全部,是否挣脱人性与兽性的屏障仅在一念之间,张贵兴将人性的书写带入“异类动物”的层次,模糊人牲的界限,对人性做出了最大胆,最反转的预设。作者在《野猪渡河》中通过将拥有个人基础人生厚度的人物放入不同环境去预设描写其行为的方式进行了自然主义中的“小说实验”。
2.《野猪渡河》中的决定论
左拉曾说:“人类世界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一样,都服从于同一种决定论。”决定论是自然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之一,强调人与生物的在生理规律上的等同性,他们常常将人物陷入某种病态之中,从而研究人物的生理奥秘。《野猪渡河》中,张贵兴对鸦片给予了不可忽视的写作分量,从老到少,从百姓到战士无不吸食鸦片,也因此村中人物眼中看到的雨林世界也常常是诡迷魔幻,夸张扭曲。文中鳖王秦是个不折不扣的鸦片鬼,在与日军持续几天的游击作战后,血液中缺少鸦片而思维模糊的他将自己的儿子认成鬼子,用混沌的帕朗刀劈碎了儿子的生命。文中另一人物何芸则更是悲惨,原文中曾描述:“她用一张废墟的脸招待过太多客人,拓扑出来的男人乐园建立在破砖碎瓦甚至骷髅冢上,一场春梦转眼烟消云散。”[6]被鬼子抓去当慰安妇的她饱受摧残,怀孕后更是被遗弃街头。身心俱疲的她达到了承受的极限,因此她获得自由后再次接触鬼子时精神完全崩溃,逢人便摆出当慰安妇时的机械动作,“十多个鬼子太少了,她依旧张开双腿,等待下一批鬼子。”
陷入病态,鳖王秦的本能依旧是举起帕朗刀,但是鸦片的作用下却酿成惨剧,何芸的本能是再次承受痛苦,用残破身心熬到自由,却又被自己关进绝望的精神牢笼。病态即是一种撇开道德、人伦以及政治的混沌状态,将人置于病态之中,将一切不合理归为混沌的发生,人最终还是被本能所驱使,生命之重沦为生命之轻,生命之有变为生命之无,一切都变得是非难辨,善恶不分。被一切精彩繁复的因素影响着的人将经历、道德、世故武装在身,然而张贵兴告诉我们,褪去一切,人最终还是被本能决定了命运。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为天地是公平的存在,万事万物的发展皆是顺其自然。张贵兴在其雨林书写中同样贯彻了这一观念。张贵兴的雨林魔幻诡迷,潮湿罪恶,猪芭村因常受野猪侵扰而得名,然而猪芭村原本就是野猪生存的地盘。朱大帝和他的猎猪大队对野猪进行捕杀清剿时无不打着守护村民安全的正义旗号,正如二战时期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口号,看似正义凛然,实则却是带了自欺欺人的“面具”进行剥削压迫。野猪对于猪芭村的侵扰无异于猪芭人对于日军的抗争,都是原住民对于入侵者的不满和对故土纯洁性的守护,二者虽人牲有别,但行为中的动物性本能和人性规律依旧有迹可循。
3.《野猪渡河》中反映的自然
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强调反映自然,现实主义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反映了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自然,即通过对典型时代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刻画来反映自然。自然主义对自然的反映在这一方面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左拉认为:“故事越是平常而普通,越是具有典型性。实践中则表现为对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进行刻画。同时自然主义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加入魔幻、奇诡的成分,这在张贵兴的雨林世界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作者更是以此见长。
小说描绘了一个炽热、华美、潮湿、腐败的矛盾世界,繁茂的雨林中有最鲜活的生命和最荒谬的死亡。《野猪渡河》是一部群像小说,人物之间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丰富而鲜活的生命个体,却也皆是历史车轮下的尘埃,无法挣脱命运。小说中,小人物依次登场,其中有在日军的残忍戏弄下自相残杀的父亲们,而他们原本过着邻里和谐孩儿绕膝的平静生活。也有拿着杀害朋友得来的武器奋勇抵抗日军的钟老怪,亦有家人皆受日军残害致死,决心苦练暗器最终大仇得报的孤儿。更有被世人诟病的达雅克人,在文中他们血腥的猎人头习俗却在日军侵略时大放异彩。还有被兽性支配的有双重身份的朱大帝等。小人物虽然难以撼动历史的砖石,但只有大人物的历史又谈何历史,作者在每个小人物生命的消逝时都给了足量的特写镜头。人们感受战争的恐怖血腥时往往是有着隔阂和钝感的,只有鲜活的生命以或惨烈、或荒谬、或痛苦的方式戛然而止才能给人以最尖锐的痛感,时代或许会因为典型人物的出现而有所推进,但真正的历史是由那些无人在意的悲欢离合构成的。
张贵兴对笔下的生命书写也是热烈且冷漠的,忽地出现,又忽地逝去。小说以开端为结尾,以结尾为轮回,书中描写了主角关亚凤的成长经历,却以他的死亡为故事的开篇。日军投降,小说的内容告一段落,但猪芭村却转而迎来了英军的入驻。太阳底下无新事,猪芭村的抗争究竟是人民对抗法西斯的胜利,还是迎接又一次的权利游戏,无人知晓。人类在历史轮回中无数权谋、无数牺牲,无数的侵略与捍卫,无数的拥有和失去,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野猪渡河。
三、张贵兴自然主义叙事的文学意义
张贵兴特殊的人生经历是他创作的根基,而他悬空的文学归属与身份认同则让他爆发出了一场难以复制的文学风暴。他在《野猪渡河》中对于人、野猪、自然、历史的书写是自然主义在华文文学中的全新发展,虽然继承了经典自然主义中的部分创作方法,但不同于自然主义中依旧以人为创作主体的形式,张贵兴果断脱离了“人本位”的创作桎梏。将自己与山川大泽融为一体,风暴雨水与落叶粪土是他书写文字的窗口,他将自然主义中对人的观察和记录扩大为对自然中更多部分的观察和记录,而人在其中只是一部分可供书写的存在。这样的非“人本位”视角实现了弱化作者个人立场对作品客观叙事的影响,从而规避了华文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类似于“华人拓荒史”“华人抗争史”这类对马来华人的史诗式书写。张贵兴像一名素质极高的法医,那段只有白骨墓碑记载的华人历史在他的冷静的解剖刀下竟能流出汩汩热血来,展示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也预知着每一片土地即将重演的一切。自然见证了一切不堪与反抗,也消解了一切冤屈与罪恶,在“人本位”的创作中,极少能有人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层次,而张贵兴则僻得蹊径,将“人本位”换成“自然本位”,从而获得了全新的叙事角度,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创新和思考。
自然主义,自然才是一切的本源,张贵兴的雨林世界在华文文学的世界中下了一场狂风暴雨,其中夹杂着腥膻恶臭,夹杂着呜咽与死亡,将人类拉下了创作的中心,拉下了主宰万物的神坛,模糊了人与万物的界限,用“无动于衷”的文字将人与万物共同的骷髅末路写给人看,为人们带来了对人与战争、人与历史、人与自然最深切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