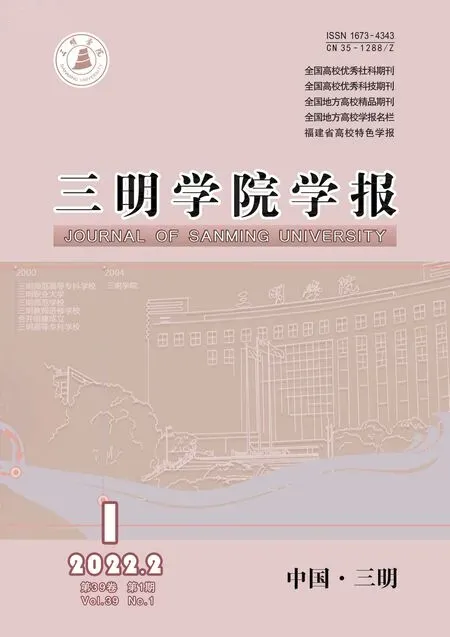基于《全宋文》的宋代福建书院及其出版活动述论
金雷磊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书院是学者和文人讲学的场所,也是藏书和祭祀的场所,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宋代已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等全国范围内的著名书院,它们共同奠定了书院发展的基础。
书院除具有藏书、祭祀与讲学功能之外,还刊刻出版图书。书院所出版的图书,又被称为“书院本”。刻书“既是书院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书院的综合性教育文化机构定位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1]106。据相关文献记载,宋代曾从事图书出版的书院有:丽泽书院刻《切韵指掌图》《新唐书略》、象山书院刻《絜斋家塾书钞》、龙溪书院刻《北溪集》、竹溪书院刻《秋崖先生小稿》、环溪书院刻《仁斋直指方论》《小儿方论》《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医学真经》、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续集》及《别集》,等等。学者邓洪波认为,书院 “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书院与书、读书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2-6。“南宋,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有条件的书院皆涉足刻书,形成堂而皇之的‘书院本’,刻书也就成了书院的基本规制之一”[2]166。学者张煜明认为,“出版书籍要校雠、要经费、要易于流通,三个条件书院皆备,因此书院刻本颇精,为学者所称道”[3]48。可见,书院刊刻出版图书有着自身的特点。
福建书院较有代表性的有建安书院、延平书院、龙溪书院、环溪书院等,这些书院与理学关系紧密。以往书院研究,多从书院祭祀、讲学、藏书等传统功能方面入手,往往忽略其刻书研究。从出版史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宋代福建书院图书出版活动,往往校雠仔细,版式精美,具有福建书院本的特点。《全宋文》作为记录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收录宋人文章全面,文体多样,内容丰富,兼具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里面零星载有福建地方书院及其出版信息。因此,本文主要以《全宋文》为基础,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原始史料,拾遗补阙,考述宋代福建书院及书院图书出版活动,以期进一步推进宋代福建书院及出版的研究。
一、宋代福建的书院
对宋代福建书院发展的认识,学者徐晓望的《宋代福建史新编》认为,“宋代的儒者一直不满于学校——这是因为:州县学校功利性太浓,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围绕着科举制转,将进士及第当作人生最大理想。虽然他们也以儒家著作作为教材,但这些人只是将儒家经书当做敲门砖,达到目的后,大多将之弃之脑后,儒学的本身并未受到真正的尊重。因此,宋代的儒者认为:只有超越科举体系,才能真正地研究儒家学说。于是,北宋的儒者有了讲学之风,他们相聚于一处,探讨儒家学说,这类讲学的场所,有的是寄托于寺院等公共场所。后来,感到不便的儒者自建讲学处,当时称为‘精舍’”[4]504。徐晓望从学人对儒家学说的喜爱和研究层面揭示出福建书院兴起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即这种喜爱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刺激了书院的兴起和发展。宋代福建书院的兴起及其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与普及。
宋代福建书院的数量,据学者刘锡涛的统计,各地数量为:福州50所、建州56所、兴化军22所、泉州12所、南剑州12所、邵武军9所、漳州11所、汀州3所。刘锡涛进而认为:“福建书院分布的特点即北多南少,东多西少。”[5]139-141而学者戴显群与方慧认为:“宋代福建书院,居于江西和浙江之后,列全国第三位。宋代福建的书院高达85所。”[6]105学者卢美松援引《福建省志·教育志》指出:“宋代福建创建的书院共102所。”[7]115学者尤小平在《福建藏书楼》一书中写道:“宋代福建书院得到较大发展,共有五十四所……”[8]7根据以上统计可知,宋代福建书院数量在100所左右,有的书院有名可考,有的则无名可考。在《全宋文》中,有明确记载福建书院创建情况的如下:
(一)紫芝书院
关于紫芝书院的原始文献,目前所见仅有一篇。此篇为宋人楼钥所作 《建宁府紫芝书院记》。书院所处之地建宁府,文风浓厚,士习举业者甚多。楼钥记载:“建宁当闽浙之冲,是为孝宗皇帝龙潜之旧……其山川耸秀,武夷诸山皆非尘境,盖八州之门户也。钟为英杰,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气节,秋赋动踰万数,荐送率八十余人,儒风最盛。学有生徒三百,分十二斋,犹不足以容之。”[9]374他认为,建宁府山川奇秀、堪比仙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滋生了浓郁的学风,孕育了杰出的人才。
根据楼钥的记载,紫芝书院为建宁府郡侯宝谟阁直学士谏议“李公”修建。关于“李公”修建之具体信息,录入如下:
今郡侯宝谟阁直学士谏议李公镇临以来,治行称最,百费具举,功利及物不可以数计周知。而尤笃意于教养,顾瞻府庠,悉加葺治。犹以为未能甚称乐育之意,谓晋范宁之守豫章,大设庠序,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心实慕之。乃捐俸三千余缗,度地于学之东西两隅,广为四斋。鸠工于嘉定三年仲冬朔旦,讫役于明年二月之望。修廊广厦,翚飞跂翼,名斋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以其前挹紫芝之峰,扁曰“紫芝书院”,盖前所未有也[9]374。
“李公”姓李,惜其具体名甚不详。根据记载可知,“李公”主政建宁府以来,向往东晋豫章太守范宁以私人俸禄兴修学校之行为,仿此行为,私人捐出俸禄三千余缗,在建宁府修建该书院。嘉定三年(1210年)冬开工,嘉定四年(1211年)二月完成。因书院前面为紫芝峰,故称为紫芝书院。
书院分为四斋,依据《论语·述而》所称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楼钥对此四斋的命名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道者百圣之所传,非可以须臾离……德者,诚也……仁之为器重……所谓艺者,非如今之技艺,乃礼、乐、射御、书、数,古所谓六艺是也”“是四者出于先圣之言,学之大端莫过于是”[9]374-375。从其命名来看,书院是以传播理学为宗旨。
楼钥在文章中还交代了为书院作记的原因:“或曰郡既有学,而复有书院,不既多乎?是又不然……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以今准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为学当有几所?而谓此为多乎?姑诵所闻,以谢谏议及多士之意。若公余诣学,与郡博士讲明经术,以训迪好学之士,则谏议之任也。钥何敢赘为之辞?”[9]375他讲述了去书院讲学之事,并且认为先有学校,再有书院,对于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来说,并不显得多余。这是楼钥选择到书院讲学,没有推辞的理由,也是楼钥答应“李公”请求,为书院作记文的原因。
(二)延平书院
延平书院为陈宓主政延平(今福建南平)时所建。陈宓(1171—1230年),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莆田人。少年时,他曾跟随朱熹学习,年长后又跟随朱熹的得意门生黄干,嘉定七年(1214年)入监进奏院,历知安溪、南康军、南剑州,宝庆二年(1226年),提点广东刑狱,三上章辞不就,以直秘阁主管崇禧观,著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钞》《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及文集数十卷。
陈宓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记载了修建书院的想法、过程及未来书院的发展设想。比如在《与南康郑教授札(一)》中,他写道:“此间书院亦荷其始谋。”[10]456他随后又在《与南康郑教授札(二)》写道:
去冬杪承台慈赐书,三复感荷知。窃知斋舍一新,士风日盛,况白鹿士友云集,躬率以古道,孰不响应,甚盛……此邦乃龟山传道于罗、李,及生朱文公之地,偶得地城南,创为延平书院,仿白鹿规摹。山川奇秀,中春始役,此月末可迄事。欲遣人至江东西招数朋友此来,未知果辱肯顾否[11]457。
陈宓在信中说道,修建延平书院是因为此地是“延平四贤”,即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诞生地,也是他们的传道之地。显然,此地修建书院有助于道统传播。按照陈宓描述,该地“山川奇秀”,是块风水宝地,“此邦山水竣清,人禀秀气,异于他郡,前贤巨儒,屹若在望,此风俗尤易于淳美者也”[12]378。可见,陈宓创建该书院,也是为了传播理学思想,弘扬理学文化。书院修建完成后,陈宓即可召集士友到此,共同切磋、探讨学问。
延平书院完全仿照白鹿洞书院规制建造,设职事官员25名,山长由教官兼任。陈宓《与闽清令郑君瑞札》写道:“书院久成,生员职事共二十五员,仿白鹿规,皆教官兼山长,所选择不敢容一豪私。”[13]459教官兼任山长,完全是从学术立场出发,避免了山长职务的行政化倾向。同时,教官与山长的选任,不夹杂任何私利。由此可见,延平书院具备较为纯粹的学术交流和学问讨论之特点。
延平书院落成后,陈宓又多次写信给友人,与友人探讨山长、职事聘请及书院的经营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山长聘请问题,陈宓倍加重视,亲自邀请学问俱佳、德才兼备之人担任。其《南剑请蔡堂长念成书》明确记载:
独此郡为四先生传授之乡,某猥以蠢愚,适叨假守,载采舆议,爰辟书堂,幸已竣事。有请于上,以“延平书院”为额,仿白鹿洞规式。而斯堂之长,众谓非得真传曷惬士望,仰惟执事蚤岁闻道于五夫,退处九江之上,孜孜矻矻,以淑后学为己任,学者宗焉。主濂溪之席者十数年,生徒济济。某顷在星渚,尝屈致白鹿,会不果来,至今恨之。兹书院适成,走介致请,执事不鄙,与李弘斋不远千里而来,岂为庸陋哉,四先生阙在是故也。谨诹日具书币再拜申,请屈长阙惠后,使四先生之学不徒诵习于阙而有得阙躬行之实,交修并进。阙之暇,又得承教,惟阙[14]115-116。
蔡念成,原名蔡元思,字念成,号东涧,江西德安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他曾在家乡德安办义学,倡导理学。虞集《瑞昌县蔡氏义学记》载:“自朱文公讲学白鹿洞,环匡庐山之麓,士君子闻风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则有蔡元思……皆卓然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问,必悟彻实践而后已。”[15]649可见,蔡念成跟随朱子学习,师事朱子时间很久,对学问必追问到底且付诸实践。
陈宓在文中深切地表达出对蔡念成来担任堂长一职的渴望之情。从其记载来看,之前在白鹿洞书院时,他曾邀请此人未果,深觉十分遗憾。陈宓认为,延平书院堂长一职,不得理学真传之人不能担任,而蔡念成早年“闻道于五夫”“主濂溪之席者十数年”,在传播理学方面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赢得很多学者的尊敬,获得很多后生追随。所以,无论从学问本身、任职年限,还是从工作经验方面来说,蔡念成都是最佳的人选。
二、宋代福建书院的图书出版活动
书院与图书刊刻关系密切,书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书院本图书刊刻质量甚佳。学者吴永贵曾指出:“书院与书的血缘关系,使得修书、刻书成为书院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书院本’以其精校,精工,易行‘三善’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一大亮点。”[16]310《全宋文》中虽有关于紫芝书院和延平书院的相关记载,但未见其刻书信息。《全宋文》所记宋代福建书院刊刻出版书籍具体可考的,主要是建安书院。
建安书院位于建安县北,是王埜奉理宗之命于嘉泰二年(1202年)建立,书院设斋舍若干间,为学习、讲学之所。郑师尹、蔡模曾任教于此。建安书院出版图书多为朱子相关著作,具体有 《朱子大全集》《朱子年谱》《朱文公正集》《朱文公续集》等。相关史实列举如下。
祝穆所作《朱文公易箦私识》云:
穆观近岁所编 《文公朱先生年谱》,其书易箦时事颇有疑误,恐不容无辨……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数育于家塾。方易箦时,实与童子执烛之列,追念当时所见,恍然如昨日事,谓宜刊正,而《年谱》摹板乃建安书院掌之。僭尝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实斋王公,许以更定而未果,辄私识之,庶几吾党之士尚有考焉[17]162。
祝穆,字和父,祖籍徽州歙县 (今安徽歙县),跟从父亲祝康国迁居至建宁府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祝穆少年时曾随朱熹学习,“性温行淳,学富文赡”[18]73。他常游历于江浙湖广闽之间,所到之处访风俗、体民风,经史子集、笔记小说、金石碑刻、历史地理,无不涉及,凡有可采者,无不抄录,毫无倦色。从祝穆文章中所述“《年谱》摹板乃建安书院掌之”来看,书院不仅刊刻《朱子年谱》一书,还收藏此书书版。该书最早由其门人李方子编纂,洪友成刊刻。刊刻出版后,因其谬误甚众,祝穆遂重新修订雕印。建安书院本《朱子年谱》,既充实修正了书籍内容,丰富了书院藏书,又有助于书院师生阅读,加深时人及后人对朱熹生平经历、交游思想和学术主张等的理解。
景定四年(1263年)三月,余师鲁所作《朱文公别集书后》曰:
因道前事,相顾唶唶叹息,以为距先生没未几何岁,而散失遗落已如此,况后千百年之久且远乎!先生一言一话,门人弟子必录以传,然得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迹,即先生实心之所寓、精义之所存,使毫芒之仅不失者而复失之,谓非通家子弟之罪,不可也。乃视集中所缺者,俾儿曹笔藏之,以俟成编而寿诸梓。朅来丞郡,适在先生里,而所得者益多,厘为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孙市辖见之,慨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谓《大全集》矣,是书当成一家言。且钩考赢余,犹足共锓费,而敢厪吾子乎?”于是精加雠校,楷书送似,而致餐钱薄少以相兹役云……景定癸亥三月朔,孙朝奉大夫、通判建宁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余师鲁谨书[19]55。
余师鲁,福建莆田人。宋景定中为朝奉大夫、通判建宁府。从其“建安精舍有所谓《大全集》矣,是书当成一家言”的记载来看,建安书院出版了《朱熹大全集》。此外,从其跋文来看,当时他是建宁府通判,曾搜集朱熹文章,编成《朱文公别集》十卷。然而,此书的刊刻由于经费所限,颇费周折:景定四年(1263年)先刊二卷,即刻发行,余谦一利用与黄镛同舍郎的关系,嘱托黄镛作序,并随二卷本书籍先行传播;剩下部分,则通过节衣缩食积攒经费,等经费充足后,又花二年时间刻成。该书由余师鲁、余谦一父子共同主持刊刻。
咸淳元年(1265年)六月,黄镛所撰《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序》云:
昔我文公会粹程氏门人所录之语以为《遗书》,且谓其于二先生之语不能无所遗,复取诸家集录参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为《外书》,诚不忍儒先片言只字湮没无传,而天下之理有所欠缺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镂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建通守余君师鲁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为师友。搜访先生遗文,又得十卷,以为《别集》。其标目则一仿照乎前,而每篇之下必书其所从得,且无《外书》不能审所自来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镛于君之长子谦一为同舍郎,亦尝预闻搜辑之意。兹来冒居长席,而余君适将美解,始刊两卷,余以见嘱。于是节缩浮费,以供兹役。盖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后之学者能于是书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玩之,庶有以知其无非精义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书不观,乃贻或者之诮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宁府建安书院山长黄镛谨书[20]168-169。
黄镛,字器之,福建莆田人。宋宝祐间,为太学生;咸淳中,历馆职、监察御史、给事中;德祐初,擢同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从其序文“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镂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宁府建安书院山长黄镛谨书”可知,《朱子正集》《朱子续集》分别由王潜斋、王实斋在建安书院镂板颁行。
王潜斋,即王埜,字子文,号潜斋,浙江金华人,嘉定十二年(1219年)进士。绍定间,官邵武县事、枢密院编修兼检讨,历两浙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副使,知隆兴、镇江府,淳祐末,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年),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吴郡侯,因与宰相不合,提举洞霄宫,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卒。王潜斋能文能武,曾在福建邵武敉平建阳龚贼。端平元年(1234年)八月五日,真德秀在《跋平寇录》中记载了这一切:“吾友王子文讲学论政,素有本原,未尝娴军旅事也。一旦绿林叩境,从容筹画,动中节会,曾未旬浃,俘馘系涂,樵川几危而复安。盖其机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应变不差如此。”[21]232连真德秀都觉得奇怪,认为王潜斋“讲学论政”是其本业,可以理解,但对军事娴熟,却是意想不到的。由此可见,王潜斋不仅编书刻书,还平寇治乱,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王实斋,即王遂,字颖叔、去非,号实斋,江苏金坛人,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历富阳主簿、监察御史、右正言、实录院同修撰、浙西提举,知邵武、遂宁、成都、平江、庆元、泉州、温州、建宁等地。王实斋官邵武时,邵武盗贼甚多,“去非奉命守邵武,时邵武盗方炽”[22]16,治安状况不佳,他也承担维持治安的职责。王实斋也文武兼具,“以公才名,文武兼全”[23]16。包恢对其评价很高,认为“世推名流,公为第一”,且与当世人比较后,评价道:“世之学徒,少实多虚,惟公躬行,德行具孚。世号贤人,多伪少真,惟公意诚,表里惟纯。”[23]15他觉得王实斋为人踏实、待人真诚。黄震也持同样看法:“盖世之欲为善者多计较,世之号治办者类局促。根一念之诚,达之事事物物间,惟先生至诚未有不动,故虽易箦之际,光明俊伟之举,尚足以震动乎流俗。”[24]396黄震认为王实斋具备“至诚”之品性,正是此种品性,使得其出类拔萃。
王埜与王遂都是文武全才,先后主政建宁府,且与建安书院有着密切关系,并主持出版朱熹的《正集》《续集》。集中收录了朱熹的诗文、奏章、书札等,是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宝贵材料。其中,《续集》刊于淳祐五年(1245年),共十卷。王遂除主持刊刻之外,还辑录朱子佚文。其佚文多为朱熹晚年书信,主要来自蔡模、刘文昌等人。淳祐十年(1250年),徐几从刘观光获得朱熹手帖数纸,增补一卷,遂为十一卷。除此之外,据程千帆先生考证,建安书院还刻有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25]138。可见,建安书院所刻书籍,多为朱子及其理学著作。
建安书院在当时名声甚大,曾得到当时皇帝亲笔题名。赵汝腾 《御书建安书院四大字谢表》载:
宸章云烂,肇锡珍题。圣敬日跻,力扶绝学。光躔精舍,喜溢潜藩。窃以建安为英哲之邦,朱熹续周程之学。于皇翰墨,昭揭源流。恭惟皇帝陛下居宽行仁,据德游艺。是道吾所谓道,纯一尚儒;兹文所以为文,雍容肆笔。固聿荣于先觉,实加惠于后来。臣涓吉奉迎,近光舞抃。嘉与多士歌《棫朴》“追琢”之诗,俾绍前修究《淇澳》“切嗟”之业[26]297-298。
从 “窃以建安为英哲之邦,朱熹续周程之学”所述,可以看出建安书院的建立是为了传播和光大理学思想,并且“以祀朱文公而以真文忠公配”[27]2363。
除了上述建安书院所刻书籍,福建书院从事出版活动的还有:淳祐八年(1248年)龙溪书院(位于今福建漳州)刊刻《北溪集》《外集》,景定五年(1264年)环溪书院(位于今福建福安)刊刻 《仁斋直指方论》《小儿方论》《伤寒书活人总括》《医学真经》[25]138。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讨论可知,以建安书院为代表的宋代福建书院,刻书技术娴熟、数量较多、质量较好,充分显示出宋代福建书院出版业的实力。宋代福建书院出版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书院刻书经费富足,经费既有官方提供,又有民间资助,还有学田出租获取的收益。二是造纸、制墨、印刷所需的材料供应充足。三是集中了以朱熹为首的大量理学家,他们围绕书院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讨、编辑出版等活动,他们所撰写的书籍和所出版的书籍,大多内容谨严、校勘仔细,从而形成“连锁反应”和“品牌效应”,致使当时及后世许多追随者效仿学习。
书院的刻书与官刻、私刻、坊刻、寺刻、观刻不同,它是介于官方与民间的另外一种出版系统,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特点。正因为如此,书院出版活动既有刻书所需的充足经费,又能灵活出版自由活泼的学术书籍。“从书院内部规制来讲,刻书服务于学术研究和讲学传道,既展示研究成果,提高教学水平,又扩大社会影响,还可以配合祭祀,强化学术、学派的认同感,有着多重文化功能”[2]167。宋代福建书院刊刻的书籍,为书院教学、讲学所需书籍提供了重要来源;学习所用书籍不用另外花钱购买,而是通过自己的刊刻获得,保证了教学所需用书的供应。同时,书院刊刻书籍也用来出售,通过售书获取利润,增加了书院自身的经济收入,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书院日常的经费开支。另外,宋代福建书院刊刻书籍,也为图书的收藏、保存以及流通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