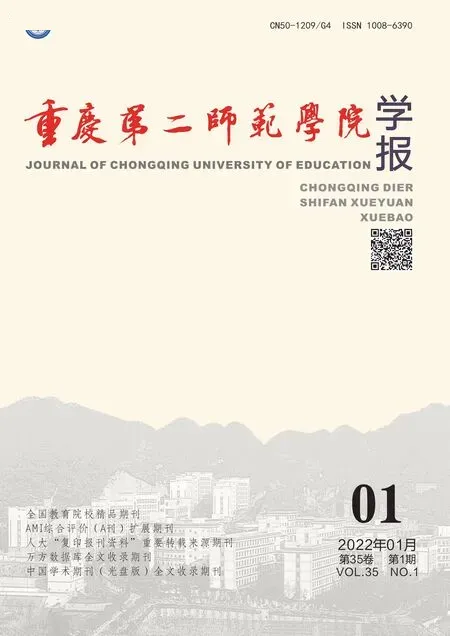雅俗并行:《红楼梦》中的博戏述论
崔健健, 施惠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博戏也作“簙戏”,是古代诸多局戏的滥觞,亦为其统称。《说文解字·竹部》有云:“簙,六箸十二棋也,从竹博声,古者乌曹作簙。”[1]乌曹相传为夏桀时期的大臣,其所作之“簙”,又称“六博”“陆博”等,是中国棋牌类局戏的雏形。洪遵《谱双·序》云:“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2]随着局戏种类和流传度与日俱增,“博戏”“博塞”“博弈”等成为后世诸多局戏的统称,并日渐形成丰富的褒贬不一的博戏文化。《红楼梦》的许多章节,集中描写了人们嬉耍博戏的生活场景。其中,提及博戏十数种,包括骨牌、双陆、猜枚、射覆等,参与人群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贾母、贾赦、贾政等王公贵族,下至来旺、何三、刘姥姥等社会底层大众,三教九流、男女老少皆能“乐”在其中,是解读康雍乾时期博戏发展状况的重要线索,也是评介博戏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视角。
一、《红楼梦》中出现的博戏
清代博戏多传自前代,或原封不动地继承,或在旧戏上再添新意。仅从《红楼梦》来看,清代博戏种类杂多,名目繁多,主要有以骨牌、叶子戏、双陆、围棋等为代表的棋牌类博戏和以藏阄、射覆、猜枚、拇战、抢新快等为代表的持掩类博戏。有些博戏讲究思维和策略,如骨牌、围棋、双陆等,人们往往屏声敛息,寻找胜利之机;有些博戏则追求身心的刺激和气氛的活跃,如猜枚、拇战、抢新快等,大家常常呼朋唤友,以求加油助威。
(一)棋牌类
《红楼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博戏是骨牌,又称“牙牌”“宣和牌”,因“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3]之起源说而得名,是康雍乾时期风行全国的博戏。第七回即有贾宝玉、秦钟观看王熙凤、秦可卿等“抹骨牌”的场景,算账时“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4]113。后续关于宁、荣两府上下人等“抹牌”的描写不胜枚举,明文提及的参与者包括贾母、王夫人、薛姨妈、贾珍、探春、贾宝玉、薛宝琴、鸳鸯、荣国府的几个老管家嬷嬷、贾宝玉房中的众丫鬟、各房的老婆子等;而论对骨牌最钟情者,又属时常“组局”的贾母和独自“抹骨牌”、自娱自乐的麝月。另外,据第七十五回贾珍、薛蟠等一伙人“抹骨牌打天九”来看,当时骨牌的扇数、点数和牌面组合,与北宋宣和年间并无区别,即以三十二扇牌为标配,计二百二十七点,分天牌、地牌、人牌、和牌和杂牌。其中,“天牌,重六也,地牌,重么也,人牌,重四也,和牌,么三也。配以三六与四五各九点为天九,三五与二六各八点为地八,三四与二五各七点为人七,么四与二三各五点为和五,么二与二四为至尊”[5]4901;对局时,每人分摊八扇牌,自由组合,按“以大击小”的原则决出胜负。
牌戏除“抹骨牌”外,尚有“斗叶子”,即民间盛行的叶子戏。书中第七十五回说,贾珍居丧期间,以“习射”为由,邀请世家弟兄来较射,及后“渐次至钱”,“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4]1046。又第八十回写道:“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欢喜,便纠聚人来斗纸牌、掷骰子作乐。”[4]1133叶子戏起源于晚唐,相传由贺州刺史李邰始创,咸通以后,“天下尚之”[6]。随后,李后主周妃编“金叶子格”,刘蒙叟、杨亿又编“彩选格”等。而至迟于明万历间,其牌式已经定型:“凡四十页为一具,一页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曰十万贯,曰万贯,曰索子,曰文钱万贯。索子、文钱万贯皆始于一,尊于九,各九页。十万贯自二十万贯始,至九十万贯、百万贯、千万贯,尊于万。万贯共十一页,绘人形,与十万贯同。文钱一门,最尊者空汤,次枝花,次一二以至于九,亦十一页。”[5]4905其中,典型代表是明末盛行的“水浒叶子戏”,即马吊牌[7]。清以降,马吊、混江、游湖、挤矮、坎玉、坎姤等叶子戏一时并起,正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所云:“马吊去十子一门,谓之斗混江。后倍为六十,谓之挤矮。又倍之为一百二十张,五人斗,人得二十张,为成坎玉。又有坎姤、六么、心算诸例。”[8]
双陆又称“长行”“握槊”“波罗塞戏”,是一种配合骰子行棋的博戏。书中见于第八十八回,说鸳鸯“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4]1231。结合《谱双》的说法,双陆的棋盘呈长方形,上面刻有对等的棋道,即为“梁”,分列左右两侧;每侧各有一“门”、十二“梁”,“门”又把每侧的棋道分隔成对等的六“梁”。同时配置两骰子,六面,数字自么至六;开局前,二人轮流投掷,以“采”决定行棋的顺序和步数。左侧之人执十五墨棋,称“墨马”,右侧之人执十五白棋,称“白马”。执墨马方于右前六梁、左后一梁置五子,于右后五梁置三子,于左前一梁置二子;执白马方与其相对,于右后六梁、左前一梁置五子,于右前五梁置三子,于左后一梁置二子。开局后,“白马自右归左,墨马自左归右。凡马尽过门后,方许对彩拈出。如白马过门,掷六二,即出左后一梁、左后五梁。马遇它彩,然拈马先尽,赢一筹。或拈尽而敌马未拈,赢双筹”[2]。无论是赢一筹,还是赢双筹,当一方的棋子全部移离棋盘后,便可宣告最后的胜利。另据《红楼梦》所言,清代双陆的棋子又称“锤”,棒槌形,亦有黑白之分。
围棋素有“木野狐”之名,“迷惑人不亚酒色”[9],贾府中善弈者亦不在少数。荣国府最高男性掌权者贾政,尤好“下大棋”,即下围棋。第七十一回说,贾政回京后,“一应大小事务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4]977。又第九十二回,贾政与詹光“下大棋”,“单为着一只角儿死活未分,在那里打劫”,随后冯紫英也参与了“观局”[4]1278。其门下有清客相公王尔调,“最善大棋”,想来也是由此得到贾政的赏识。迎春、探春、惜春、宝钗、宝琴、黛玉、妙玉、岫烟、香菱等一众姐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闲来无事便“下大棋”“观局”,自是围弈的高手,毋庸赘述。另外,当时盛行一种“赶围棋”的博戏,类似于古代的打马戏,以两骰子所掷“采”的组合决定行棋的步数,先到达棋道终点者为胜,不同处在于以围棋子取代了打马戏中绘有马型的棋子。如《红楼梦》第二十回,薛宝钗、贾环、莺儿等“赶围棋作耍”,这盘该贾环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若掷个六点,下该莺儿掷三点就赢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转……那骰子偏生转出幺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后就拿钱,说是个六点”[4]273。
(二)持掩类
持掩又称“掩戏”,两汉时已广泛流传于世。西汉盛行藏钩、意钱、射覆等掩戏,至东汉已有人“以游博持掩为事”[10]。后世在汉代掩戏的基础上,衍生出藏阄、猜枚、拇战、押宝诸戏。观《红楼梦》,藏阄最具古藏钩“分二曹以校胜负”之遗意,一人负责藏阄,其他人则拈阄,民间俗称“抓阄”“射阄”等。第六十二回写道:“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全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继而道:“大家想了一会,共得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地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间。”[4]850第七十回也说,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后,众人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进行拈阄,“宝钗便拈得了《临江仙》,宝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4]970。显然,藏阄不易作弊的公正性,以及完全依靠个人运气的平等性,是其盛行的主要原因,诚如第三十七回迎春所言:“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4]490
射覆是最古老的猜物类掩戏,《红楼梦》称其为“酒令的祖宗”,实践性极强,“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11]。覆器通常使用瓯、盂、盒、盆、钵等器皿,覆盖有手巾、扇子、笔、砚台、花、草、鸟、虫等物件。射者则通过观察、推敲、占筮等途径,猜射所藏之物,故尤其受到古代研易高手的推崇,如东方朔、管辂、步熊、麻九畴等易学大师,都是著名的射覆高手。由于明清“谶纬之书,皆有厉禁”[12],古射覆戏很快也失传了。第六十二回贾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等一众姐妹所行射覆,应是清人据古射覆之遗意而仿纂的,失去了观察、推敲、占筮的实践性趣味,更多是以附庸风雅为主——探春是令官,命丫鬟取了令骰令盆,分配说“从琴妹掷起,挨下掷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与香菱对了三点,宝琴说个“老”字,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史湘云教香菱说个“药”字,射的是“芍药栏”的“药”字(芍药栏包含红香圃在内之故);又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覆了一个“人”字,又添覆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射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4]850-851。
猜枚、划拳往往并行,是常用于酒桌助兴的博戏,男女老少皆宜。其中,猜枚又称“猜拳”,源于藏阄、射覆等传统掩戏,明代一些学者还专门就此做了考证,如陆容《菽园杂记》认为明人“以猜拳为藏阄,阄音鸠,古无此字”[1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则言“猜枚乃藏阄、射覆之遗制”[14]。其法简便易行,一方将瓜子或棋子握在手中,由另一方猜断瓜子的单双、数目或者棋子的黑白。第十九回说宁国府搭戏台、放花灯,邀请两府的亲朋好友看戏,贾珍、贾琏、薛蟠等在台下“只顾猜枚行令,百般作乐”[4]254。第七十五回也写道:“贾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饮了一回。”[4]1050划拳也称“拇战”等,其特点如史湘云所云“简断爽利”,且技巧性极强,给双方都留有斗智斗勇的空间,同时因划拳时需大声喊叫,容易让人兴奋,更增加其竞争性。《红楼梦》最能生动呈现当时社会人们划拳饮酒的场景描写,当属第六十二回:“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尤氏赢了鸳鸯。”[4]851
押宝是古意钱戏与骰子紧密结合后演化出的博戏,其典型玩法有摇摊、掷老羊、抢新快等,尤以摇摊最为盛行。《清稗类钞》云:“摇摊,以骰置器中摇之,盖即唐时之意钱。以四数之,谓之摊钱,又曰摊蒲,亦可随手取数十钱,纳于器而计之。每四枚为盈数,统计余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数,分为四门,以压得者为胜。”[5]4906掷老羊、抢新快诸戏,玩法与摇摊类似,娱乐性却远不及摇摊。《红楼梦》中,因抢新快较之掷老羊简便易行、全凭手气且最易“爽利”的特点,成为“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呆大爷”薛蟠和“手中滥漫使钱”的“傻大舅”邢德全最热衷的博戏。第七十五回说:宁国府居丧期间,薛蟠、邢德全二人应贾蓉所邀凑在一处,“都爱‘抢新快’爽利,便又会了两家,在外间炕上‘抢新快’”;算账时薛蟠“输了一张”,“幸而掷第二张完了,算来除翻过来倒反赢了,心中只是兴头起来”[4]1047。
二、雅俗并行,褒贬不一
古代,博戏多被视为礼乐政教以外的末流小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常常显得无足轻重,却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行为,“必有可观者焉”。对于博戏最宽容的评价,当属春秋时期的孔子,他训诫门下弟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5]后世许多博戏爱好者,也常以此为重要论据,意欲为博戏争个“贤”名。如王粲《弹棋赋序》云:“因行骋志,通权达理,六博是也。”[16]3346李尤《博铭》云:“夫无用心,博弈犹贤;方平处下,自不邪偏。”[16]3346《薛孝通谱》更为夸张,以博戏“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几微。履谦谢,则知冲谢以致福;观杀罚,则知当路而速祸;行其道,则掎鹿有归;保其家,乃瞻乌爰集。隐显藏用,莫不合道,龙潜鹊起,率皆趣良,足以谐畅至娱,始协妙赏者也。”[16]3346这些虽然都有美化博戏的嫌疑,却也间接证明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博戏是古代先民为了打发闲暇时光,凭借自身智慧、实践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实操性局戏,具有强大的娱乐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如《红楼梦》中出现的骨牌、叶子、双陆、围棋诸戏,历史久远、经久不衰,多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且规则上各种争奇斗巧、别出心裁——骨牌之算牌精密、叶子戏之斗法丰富、双陆之棋路百变、围棋之布局玄妙等,总能勾人心神。姑以“算牌”著称的骨牌为例。第四十七回说,贾母叫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三人组了牌局,又唤了鸳鸯在下手里坐着“瞧牌”,“五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凤姐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躇了半晌……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凤姐儿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贾母笑得已掷下牌来”[4]628-629。虽是通过描写王熙凤、鸳鸯等合伙在牌桌上“演戏”,来反映在场的众生相,却也可以窥探“算牌”在骨牌中的重要性。其他博戏如射覆、猜枚、押宝等,亦是此消彼长、花样繁众,时时推陈出新,毋庸赘述。此外,博戏还具有易学易会、倚助机运的特点,双方即使存在技巧上的差异,也往往可借好的机运进行弥补,故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妇孺稚童,皆能快速上手,参与其中。正如李渔《闲情偶寄》所言:“双陆投壸诸技,皆在可缓。骨牌赌胜,亦可消闲,且易知易学,似不可已。”[17]
另一方面,博戏作为大众文娱活动,本无高低、雅俗之分,而其中一部分博戏,如围棋、斗草、打马等,因流行过程中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和热烈追捧而日渐雅化,成为公认的“雅戏”。红楼世界中,围棋依旧位列“琴棋书画”四大雅趣之列,是修身养性、活络思维的必备技艺,亦是评价女子才艺的重要标准。如金陵十二钗,个个都是围弈的高手,而以妙玉、惜春为最。第八十七回说,惜春与妙玉“下大棋”,妙玉用一招“倒脱靴势”,“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转一吃,把惜春的一个角儿都打起来了”;继而说,惜春“翻开那棋谱来,把孔融三十六局杀角势王积薪等所著看了几篇。内中‘荷叶包蟹势’‘黄莺搏兔势’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杀角势’一时也难会难记,独看到‘八龙走马’,觉得甚有意思”[4]1224-1229。又第一百十一回写道,妙玉、惜春对弈,“惜春连输两盘,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惜春方赢了半子”[4]1493-1494。而以围棋子为媒介的“赶围棋”,最具打马戏的遗意,属于“博弈之上流”,书中提及的参与者也多为闺中小姐、丫鬟,以及时常游迹于女子闺帏的公子哥贾宝玉。除“赶围棋”外,“闺中雅戏”尚有斗草。与草茎相勾、各持己端拽拉的“武斗”不同,贾府的公子小姐、各房丫鬟酷好以对仗形式互报花草名的“文斗”。如第六十二回,香菱和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4]859-86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博戏如猜枚、划拳、击鼓传花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被广泛用于酒令,成为宴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红楼梦》来看,由于宴饮时间与场合、参与者身份、节日氛围等不尽相同,博戏作为酒令,难度系数亦有高低之分。其中,组织形式和行令内容最为简单的当属击鼓传花,其注重渲染活跃氛围,不需要考较参与者的文化水平和实操技巧,属于全凭运气的酒令。如第五十四回,王熙凤行了一个击鼓传梅的令,“若到谁手里住了”,吃一杯酒或者说个笑话[4]742。猜枚、划拳简单易行,趣味性极强,流传范围最广,但颇强调技巧性,且对局双方“张牙舞爪”、划拳呐喊,往往更受青年男女青睐。骰子令、骨牌令已经属于“文令”,骰子的彩色、牌面的组合等只是行令的媒介,必须与诗赋、词曲、对联、谜语等配合宣令,接令难度远远超过了猜枚、划拳等“武令”。其中,骰子令又称“朱窝令”,见于第一〇八回,用四枚骰子摇掷,并根据令谱来判断四颗骰子组合出的采名,从而进行赏罚[18]。骨牌令名目繁盛,难易可调。如第四十回,宣令官鸳鸯说一副骨牌名,接令者须将三张牌拆开,分别接三句能够押韵的诗词歌赋或成语俗话,最后合成这一副牌的名字,即使如刘姥姥,也能以俗语凑数,轻松应对,难度较低[4]544。而第六十二回,史湘云所宣之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总共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4]851,甚至连“天性聪敏”的贾宝玉,一时也想不出来,还要靠着林黛玉解围,可见其难。
可以说,博戏作为古代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些博戏爱好者无论如何美化,甚至夸大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未能超越“玩物”“怡情”“修身”“养性”的范畴。反之,自博戏诞生以来,更多人以其为奇淫巧技,贻害无穷,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孔子答鲁哀公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也。”[19]匡倩答齐宣王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20]二人显然都是从儒家学派提倡的尊卑、贵贱、上下、亲疏的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君子不博”,以避免损害国家的统治秩序。又《孟子·离娄篇》云:“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21]可见,博戏从一开始便站在儒家“君子不博”思想的对立面,属于与传统生活习惯、崇尚意识背道而驰的旁门左道。后随着其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暴露自身的弊端,受到有识之士更为激烈的抨击。如司马迁以博戏为“恶业”,司马相如认为博戏“失礼迷风”,一些对博戏深恶痛绝者,更贬称其为“牧猪奴戏”,甚至有人提出博戏不祥,足以毁邦灭国,典型的如“明亡于马吊”之说。
结合《红楼梦》来看,博戏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博戏强大的娱乐性和胜负欲,极易勾动人的心神。从《红楼梦》中可发现,康雍乾时期盛行的博戏,除棋牌、持掩外,另有斗戏,而以斗鸡最为盛行。第四回“呆大爷”薛蟠出场时,作者即介绍道:“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今年方十有五岁,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唯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4]63第九回对“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的贾蔷也介绍说:“这贾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明,虽然应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玩柳。”[4]136又第七十五回写道:“贾珍不肯出名,便命贾蓉作局家。这些来的皆系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绔。”[4]1046可见“斗鸡”是当时纨绔子弟日常的娱乐活动,在作者的心目中,其与吃喝玩乐、寻花问柳一般,是典型的不务正业的表现。
其二,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裕,不可避免地对博戏产生深刻影响:对局中“赌取”一定的物质奖励来增加娱乐性,成为博戏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荣国府为例,府里几乎所有的牌局、棋局都是赌“东道”,或者赌取一定财物的,但更注重娱乐的成分,赌取的“东道”、财物在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消费中占据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姑举数例。第二十回说,贾宝玉听闻麝月因没钱而不与晴雯、绮霰、秋纹、碧痕等“抹骨牌”时,说道:“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输的?”随后又写道,薛宝钗、香菱、莺儿、贾环四人“赶围棋”玩耍,“一磊十个钱”[4]271-273。可知荣国府的丫鬟们平日里玩牌、斗棋,都是耍钱的,遑论各位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又第四十七回说,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鸳鸯五人斗牌,王熙凤听闻薛姨妈戏说自己小气,便站起来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4]630显然,此类博戏虽尚属家族内部亲近的成员之间“赌采”的范畴,但不可否认其与赌博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其三,由博戏直接演变而来的赌博,“败坏人性,导引为非”,实为“荡败之媒、强盗之胚胎”,往往是影响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的罪魁祸首。《红楼梦》中沉迷赌博者,如薛蟠、邢德全之流,丧志废业,只知“滥漫使钱”,“家下人借此各有些进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势”,严重败坏了家教门风;尤二姐的前夫张华、来旺的小儿子之流,“成日在外嫖赌,不理生业,家私花尽”,只能落得个“赌钱厂存身”的下场;迎春的乳母、何三之流,输至无物可输时,遂心生恶念,铤而走险,走上偷盗抢劫、谋财害命的犯罪道路。赌博的弊端显而易见,似贾府这种世家大族自有一套颇具成效的禁赌措施。如第七十三回,深知赌博“利害”的贾母雷霆禁赌,前后“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通共二十多人”,又命人将骰子、骨牌等一应赌具尽皆烧毁,“所有的钱入官分散与众人,将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撵出,总不许再入,从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钱,拨入圊厕行内”[4]1010。另外,康雍乾以来国家禁赌举措不断完善,形成了古代最完整、全面和严厉的禁赌法规[22],这在《红楼梦》中也有直观的体现。第一〇五回说,御史弹劾贾珍时,有一款罪状即为“引诱世家子弟赌博”[4]1428,随后贾赦被革去世职、发往“台站”效力,其罪状亦有“纵儿聚赌”[4]1439一条。
三、结语
《红楼梦》对于“无益世教”,且“圣人不书,学者不览”的博戏的生动描写,是后人解读当时社会博戏发展状况的重要线索,亦是评介博戏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又一独特视角。本文通过《红楼梦》关于博戏的所书、所绘与所评,结合时人的笔记文集、诗歌曲赋、小说杂语等,对康雍乾时期盛行的博戏的种类、源流、组织形式、对局之法、参与人群、流行程度等进行了具体的考证与讨论,对博戏的两面性,即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有益身心健康的积极性和破坏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的危害性,进行了初步分析与评价。后续研究中,通过红楼世界绚烂的城市生活长卷,最大限度地还原康雍乾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应是更具学术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