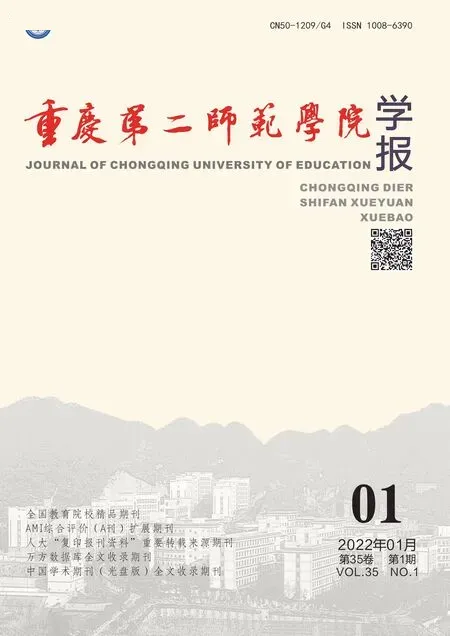论20世纪美国荒野文学的诗学转向
胡 英, 刘丽艳
(大理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与日俱增,地球上的实际荒野不断消失。在这个人类活动甚至已经影响地球地质构造的“人类世”①,关注纯粹自然的美国荒野文学也做出相应反应。所谓内向诗学与外向诗学是体现在20世纪自然文学,尤其是荒野文学中的某种诗学特征。内向诗学强调作者的内视感,作品往往借助自然或者荒野来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作品的焦点在于人类心灵事物的本身;而外向诗学则强调作者作为社会人的角色,更多地往外看,甚至直接影响和参与“公众声音”(public voice)的形成。内省一直以来都是文人的基本特征,对于荒野文学来说,就如拜尔德[1](Gregory L.Byrd)指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作家非常珍视那些与荒野相关的神话和原型,尤其关注自我与社会的疏远、个人异化等。荒野的具体意义在于,当人处于荒野之中便意味着人与社会脱离,因此现代主义写作中的荒野描写往往是将作者异化的内心世界进行外化和具体化。可以说,对于现代主义作家,荒野是以一种心态的方式存在,或者说荒野是作为一个具体现象在自我内心的反映。这一时期的荒野诗歌几乎都遵循向内看的原则,即透过荒野看内心。
不过20世纪中期以后,荒野诗歌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一些中间代诗人如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等的后期作品中开始更多地关注“公众声音”,而不再局限于对自我内心的探究。非常自然地,在20世纪后半期的诗歌尤其是当代的诗歌中,诗人越发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注,因为他们试图影响“真实世界中的真实读者”。当代诗人海恩斯(John Haines)、斯奈德(Gary Snyder)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往往又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他们的散文往往成为了解其诗学的重要来源,因此这种散文、诗歌互相支撑的模式是否也是一种诗学的发展,或是当代诗歌需要散文注释来吸引读者?不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20世纪荒野诗歌的确经历了一个由内部审视转向外部关注的过程,可以概括为由内向诗学到外向诗学的转向。
一、20世纪初荒野文学与内向诗学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与作家在作品中大量运用荒野描写与意象,将之视为其人物得到顿悟与灵感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活,退居荒野成为一种必要,因为荒野之处没有社会法则,或者其社会法则相反,而这种状况为人们获得启示与自我理解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面对文明的失败,将荒野视为避难所,并试图在荒野中找到文明失败的“解药”,这或多或少是对19世纪梭罗等浪漫主义传统的回应。对于这些现代主义作家来说,仅仅进行抗议并不能得到满足,而荒野则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现代主义主要作家如杰弗斯、肖邦(Kate Chopin)、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杰克·伦敦(Jack London)、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艾略特(T.S.Eliot)、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等都是荒野写作的杰出代表。
这一时期的荒野作家对于荒野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一种视荒野为逃离现代文明失败的避难所,弗罗斯特、艾略特、海明威等的作品都表现出类似的理解;一种则认为荒野具有与文明、社会相反的本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肖邦、克雷恩(Stephen Crane)、杰克·伦敦等;第三种则完全拥抱荒野,号召回归原始,杰弗斯就是这种极端观点的积极支持者。然而,这些作家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强调荒野与人类心灵之间的关系,或是通过荒野来审视人的内心,或是将荒野视为人类心灵的表现。例如,杰克·伦敦在他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TheCalloftheWild)中记叙了从小生活在温室环境中的巴克被偷卖到原始荒野当雪橇狗,残酷的现实触动了它向大自然回归的本能和意识,加之对主人的彻底失望,它最终走向荒野、回归自然。故事聚焦于荒野自然环境与巴克内心的转变,认为是残酷的自然环境既锻造了巴克也触发了它内心的原始本能,最终使之回归荒野、与其融为一体。而现代主义诗歌领袖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TheWasteLand),则用现代社会中一片废墟的状况来折射现代人心理荒芜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当时的荒野作家用荒野自然反映人类心灵的做法非常类似。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边疆的退却,荒野实际上不复存在,理应不再是人们借以讨论与解释现代美国人心理的主题,然而事实上,很多现代主义作家如弗罗斯特、艾略特、海明威等在作品中仍充分运用荒野,并将之视为与文明城市中沉闷的社会氛围相反的、能够令人获得顿悟与自知之地。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内心的需求越发渴望,而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都有指向自我、探求内心的倾向。因为定义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我指向”(self-referentialism),诗学评论家帕罗夫(Marjorie Perloff)也认为现代主义者的“自我指向”就是“强调分类的自我,强调面具自我与内心自我间的对抗”[1]。而荒野自然贴近浪漫主义自然观,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更加理性的审视。荒野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避难所,能够安慰人心,而且通过荒野,人类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候的荒野已成为人类心灵的对应物,既反映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也体现内心深处的渴望与需求。
另外一些作家如肖邦、克雷恩、杰克·伦敦等则认为荒野是与文明社会相反的。在他们看来,荒野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人类在此无法控制和掌握周遭的环境及自身的生活,这与意图控制和掌握自然的人类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是克雷恩的《海上扁舟》(TheOpenBoat)还是杰克·伦敦的《生火》(ToBuildaFire),其中的主角都经历了在荒野之中饱受折磨的旅程。在这些荒野的环境中,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控制,人类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令自己舒适,自己身处危险,但同时也摆脱了其他人对自己的控制,甚至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可能无法保障。然而,正是这种失控的状态使得荒野令人着迷,那些在社会上饱受压迫和控制的人们,想逃到荒野获得身体与精神上的自由,而那些在文明社会已经取得足够控制权的阶层,又希望通过回归荒野来感受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在文学方面,回归荒野一向都是那些饱受社会压迫的主角的出路。比如《哈克贝里·费恩》里的哈克和吉姆,一个是为了逃避酒醉的父亲,一个是为了逃离被奴役的状态。当漂到密西西比河时,他们被赋予了新的身份,两人都获得自由,因为这条代表荒野自然的河流是不受控制的,在这里文明社会规则也失去了效用。
20世纪前半叶,美国荒野文学还有一种重要的倾向,那就是原始主义。杰弗斯提出的“非人类主义”(inhumanism)就是对原始主义思想的有力推崇。原始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人类越与自然接近,也就越与上帝接近,因而也就会生活得更加快乐。杰弗斯认为人类及其文明和社会都已腐败、倒塌,只有动物与荒野自然是无瑕的。在诗歌《受伤的鹰》(HurtHawks)中,杰弗斯[2]写道,“如若能免除惩罚”,他“宁愿杀死一个人也不杀一只鹰”。对于动物,杰弗斯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他将人类与动物完全视为平等的,并认为本能高于学问:文明人“不认识他,或是已将他忘记/放纵与野性,但鹰却记得他/美丽而狂野的鹰,和将死的人,却记得他”[2](《野性之主》,TheWildGod)。这里作者肯定那些最具野性的动物与上帝最为接近,实际上是在阐释基本的原始主义信条,只不过他将获得上帝知识的特权从“野人”扩展到“动物”而已。
不管怎样,对于20世纪初直到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来说,荒野都以一种心态的方式存在,或者说荒野是作为一个具体现象在自我内心的反映,这个时期的荒野文学几乎都通过荒野查看人的内心世界,都采取一种内视的角度来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将荒野视为一种心态的内视角度比起19世纪的自然观也有着重要的变化。20世纪初对于荒野与自然的态度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转向一种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观点[3]70。这一转变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关于荒野和自然,文人们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加黑暗的观点。杰弗斯就是这一趋向的领军人物和重要代表。比起爱默生和梭罗那种沉醉于荒野之美、透过荒野与上帝获得完美沟通的做法和想法,这时候的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危机和黑暗。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时期的荒野文学中,人们不仅看到了荒野自然之壮美,同时也注意到荒野自然的黑暗与可怕。而荒野自然中的这些黑暗面正好对应了当时文明社会的黑暗,因此荒野成为现代主义作家们常常描写的对象和使用的意象。
二、20世纪中叶以来的荒野文学与外向诗学
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才得到自己的名称,但实际上这种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萌发。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自然教育令人们熟悉了生态学,甚至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参与自然的程度,比如致力于培养美国人荒野意识的美国童子军《手册》就非常有利于环境主义思想的传播,到20世纪40年代,“《手册》在美国的销量据称仅次于《圣经》”[4]137。1962年,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杀虫剂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环境问题公众化的里程碑,公众意识急剧加强。《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前,只有科学家用“环境”一词,而8年之后,由于各方力量的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条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称1970年是“环境年”,并号召用更新、更严厉的法规来保护环境[3]。到了1970年,环境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思潮,在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那些积极的活动家们甚至成立了“绿色”政党,环境保护的思想已经从某些有识之士传播至全体民众之中,环境保护运动也因此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
也许是随着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的自然文学尤其是荒野文学,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实际活动中来。这个时期的荒野文学家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使命,为荒野的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恢复而努力,因此他们的作品也不再局限于关注人的内心,而是呈现出关注人类外在行为、关注社会动向的倾向,他们试图用作品来直接参与社会的构建,通过作品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来完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目标。这个时期的主要荒野作家几乎都有亲历荒野、深入体验的经历,他们往往将自身的荒野经历与写作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文字为荒野辩护,甚至亲自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项活动中,成为维护当代生态与环境的使者和代言人,如海恩斯、斯奈德、布莱(Robert Bly)、艾比(Edward Abbey)、默温(W. S. Merwin)、贝里(Wendell Berry)、迪拉德(Annie Dillard)等。海恩斯通过他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中25年的生活经历写就了许多诗集,并出版了《星·雪·火》这部享誉全球的自然散文集;艾比则通过他在拱门国家公园的经历,写就世界驰名的散文《沙漠孤行》,并在其去世前几天完成生前最后一部书《荒野中的呼唤》,可以说艾比的一生都在为荒野辩护;斯奈德更是直接表示,自己的政治身份是“荒野代言人”[5]。
作为这一时期重要荒野诗人代表的海恩斯,他不仅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环境运动的支持与响应,同时他还从文学的角度指出当代诗歌应该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参与社会的发展。海恩斯认为当代诗歌衰落的原因是部分作家专注于内省,需要更多地往外看[6]。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白派诗人如日中天,他们坦然暴露内心深处隐藏的一切,即使是自私肮脏、丑恶卑鄙的东西也暴露无遗,把内心最不可启齿的那一面公然诉说。自白派是对新批评竭力反叛的结果,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他们关注的是“坦白地倾诉个性的丧失”,重点在于个人和自我。然而,面对环境问题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海恩斯认为自白派这种做法虽然在艺术上能够勇敢地挑战传统,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对社会、对人类没有担当的文学终归会销声匿迹、失去价值。事实证明,自白派的确如昙花一现,虽然在60年代红极一时,但随之在70年代便偃旗息鼓。海恩斯指出,当那些往外看的作家如史蒂文斯、弗罗斯特、威廉姆斯等的作品衰落之后,普拉斯、塞克斯顿、贝里曼等集中于自我内省的诗歌仅满足于一些机智的俏皮话和草率的意象,这是当代诗歌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诗人应当看向土地,看向历史和前人中的大师们”[6],如若将这些影响带入诗歌,会令诗歌更有意义,更加接近真理。海恩斯鼓励作家们接近“那坚硬的、无法简化的自然事物的世界”[7](LivingofftheCountry)。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布莱与贝里算是海恩斯的志同道合者。从布莱的深层意象诗歌中,海恩斯找到了如何将“深层愿望”(deep wish)与风景相结合的方法;而贝里对于环境的关注与海恩斯不谋而合,此外他们关于文学根植地方的思想也令他们更加地互相欣赏与推崇。海恩斯的首部诗集《冬日消息》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布莱早期作品的简约风格。例如,《被遗忘者的诗》(PoemoftheForgotten)写道:“我,一个年轻的新手/孤单地来到这里/远离世界/我用青苔与木料搭起一个房子/把它称为家/温暖的夜晚坐下唱歌/对着自己唱/明明知道无人聆听/仍然歌唱/阴影下,我用树叶铺床/在秋日的第一场雪中/醒来/寂静充满。”[8]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无法想象诗中的寂静,那是一种与世隔绝、没有机器背景声、也没有人类声音的全然寂静。诗歌非常朴素而简单,但是却把这种真实的寂静带到读者眼前与心中。这也许就是海恩斯诗歌的魔力,他能借着那朴素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种情景甚至进入一种无意识的沉醉状态,就像著名诗评家乔伊亚(Dana Gioia)所说:“在当今社会很多艺术充满假装与乏味,而海恩斯的诗歌非常难得,因为他的诗歌要求关注的不是智力而是精神。”[9]
从贝里对海恩斯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捕捉到了海恩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看似朴素而简单的诗句其实传达的要比其讲述的多得多。就如贝里所描述的,海恩斯的诗歌就如雪花从屋檐下飘落,看似无声,但是不断积累壮大,诗歌的创作过程仿佛河流结冰或是青苔覆盖石面一般缓慢而无声[10]。的确,在海恩斯的诗歌中,时间变得非常缓慢,甚至与空间开始混淆,诗歌如咒语般将读者引入一个远离文明、寂静的远古时代。像这样的诗歌有很多,尤其是在诗集《冬日消息》中,《旅行者》(TheTravel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诗中第二节写了一盏灯:“满是阴影的灯盏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燃烧/那光似乎来自远方/透过帐篷黄色的蒙皮”(第5~8行)[8]。这盏灯似乎连接了过去与当下,将读者自然地拉到文明社会之前的荒野生活,诗歌接下来写道:“千万年已经过去/人们宿营在河流的岸边/阳光下把鱼风干。……我们已经离开很久/冰冻的道路上/一个人从亚细亚来/嘎吱嘎吱孤单行进/脚印在黑暗中已经消失”(9~23行)[8]。
海恩斯后期的作品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回归美国主流社会的倾向,就如伯根(Don Bogen)所说:“虽然(海恩斯)早期诗歌传达着华兹华斯式的视野,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精神复苏的来源,然而后期的作品则更多地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当他专注于这个不断蚕食的机械化的世界。”[11]虽然海恩斯身居荒野,但他仍然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社会发展的文人。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使海恩斯跳出了早期浪漫主义倾向的限制,开始认真关注当下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在他1993年出版的诗集《带着梦中人面具的猫头鹰》(TheOwlintheMaskoftheDreamer)中,诗歌《在没有树叶的森林里》(IntheForestwithoutLeaves)以森林为意象描写当今的工业城市:“在这没有树叶的森林里/由电线和扭曲钢筋构成……/季节就是生锈/和更新/或许完全没有季节可言/……除了金属,什么都不兴旺/它们以自我为食——/电缆为根/节钢的簇丛/铆钉的死结/在雨中膨胀。”[8]诗中的景象犹如世界末日,这里的机器几乎突破了里奥·马克斯所谓的“花园里的机器”范围,俨然霸占甚至取代了花园。
除了海恩斯,当代文学中另一名重要的荒野战将非斯奈德莫属。海恩斯从文学的角度指出了当代诗歌应当往外看,更多地关注公众声音,而斯奈德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仅在文学上践行这一使命,而且还以环境活动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当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来。他指出,“文明时代诗人均背负这样的使命:他们不为社会、但为自然歌唱。由阶级所组成的文明社会好比大型的自我,超越自我便等于超越社会。‘在那彼处’向内即潜意识,向外潜意识的对象就是荒野:这两个词其实等于‘一’。”[12]首先,斯奈德在诗歌中为荒野自然呐喊,把美国土地书写为自我重生的神话之地:“粗犷依旧的星空下——/在峭壁的阴影下/我找回了自己/回到了真正的工作,回到/‘正要做的事情’。”[13]所谓“龟岛”,其实就是指北美大陆,这是印第安人对北美的称呼,他之所以将诗集取名为《龟岛》,就是想表明他不愿从政治角度划分区域,而是从自然存在的角度来进行区分。其次,斯奈德通过散文宣扬他的生态政治观点,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令其获得普利策奖的是他的诗歌集《龟岛》,除此之外,斯奈德还出版了16卷诗文集,其中诸如《荒野实践》(PracticeintheWild)、《天地一隅》(APlaceinSpace)等散文集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对于阐释与传播他的生态主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总的来说,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自然文学,尤其是荒野文学,在诗学方面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转向:那就是由内省转向外视,由关注个人转向关注公众。也许是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演变为全球性的公众问题,因此相关的环境文学更多地看向历史、看向社会,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问题的钥匙。20世纪后半叶荒野文学转向外视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其一就是将诗歌与地方结合,强调诗人的位置感,认为人们只有根植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将之视为家园,才能更好地了解自然、了解自我。斯奈德的位置感在美国西海岸,那里是他的“龟岛”;海恩斯的位置感则在阿拉斯加外围的理查逊,在那里他的心灵与身体都得到安居的家园感。其二就是强调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使命感,认为艺术家应当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并为人类与之和谐相处找到出路。贝里从基督教义出发,结合自己作为农夫的体验,成为生态环境保护者;默温则通过他在夏威夷群岛获得的环境恶化的第一手资料,投身到环境保护运动之中。其三就是这个时期的荒野作家大都具有在荒野自然中的亲身经历,他们的作品往往与之结合,因此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海恩斯与斯奈德的荒野经历自然不必多说,就连女性作家迪拉得、威廉斯等的主要作品都是以其亲历荒野的经历为基础的。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令他们作品的亲切之感扑面而来,其理念也自然深入人心,从而发挥了用文字影响人们保护环境的作用。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荒野作家为了表达对公众声音的关注,往往采取多种文体形式进行创作,也许由于当今这个时代散文的接受程度较高的缘故,很多荒野诗人都同时出版散文和游记,用以阐释和说明其诗歌的立场和意义,海恩斯与斯奈德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
注释:
①“人类世”(anthropocene era),又译作“人类纪”,是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阶段,这一概念由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人类世并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大致从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