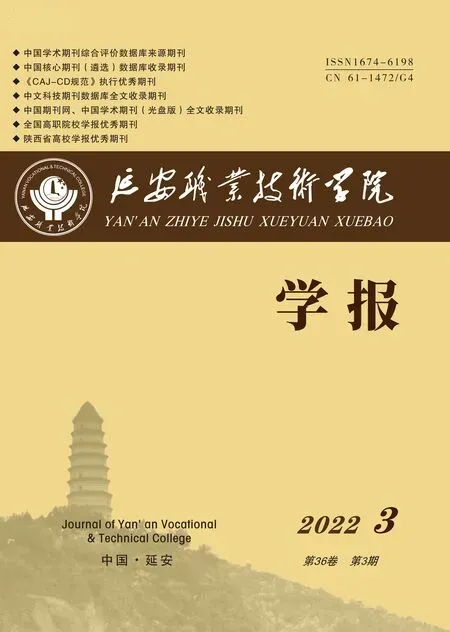浅析陈彦《主角》中的詈语
汪东锋,刘雨涵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詈语,即粗野的骂人话。《说文》中指出:“詈,骂也。从网从言,网罪人会意。”朱俊生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解释道“按,言之触罪网者也。”不难看出,詈语是通过语言来使对方反感、愤怒、进而达到“罪人”的目的。虽然詈语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极高,是人们惯常使用的“工具”,但却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因其内容及形式的特殊性,往往会在正常的语言教学、学术研究中被刻意忽视。而事实上,作为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詈词詈语,最能真实直观地呈现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有很多作家,以使用白话性的詈语为刻画人物和描绘社会万象的“利器”,使得文学作品更加“接地气”,更具人情味儿。陕西籍作家陈彦所写的《主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詈语是音义结合体,以词,或词组,或句子的形式呈现。对于詈语研究,目前涉及到的领域包括詈语的本体性研究、语用价值研究、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等等。本文从詈语语义分类、詈语中蕴含的民俗文化、詈语的功能三个角度分析陈彦的《主角》中詈语的运用。
一、《主角》中的詈语语义类型
詈语又叫骂詈语,由骂意和骂语两个部分构成,骂意体现的是骂詈者的情绪和情感,骂语是用于骂詈的语言材料。根据詈语的语义不同,《主角》中的詈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与牲畜、无生命有关的詈语
这一类的詈语是将人和非人界限错置,将人比作牲畜,降低了他人的人格,将被骂者的某种低劣的品性或品格与动物自身存在的劣根性相联系起来,意在指出他人与牲畜“别无二样”,以达到发泄愤怒或不满的目的。如在《主角》中,有这样的说法:
2.高五福说:“狗贼心还大得很,县里都看不上了。”[2]477
另外,在作品中,还有一类是以“货”为词缀构成的詈语,例如:
3.……他叼着牙刷对胡彩香说:“看你个二蛋货!”[2]55
4.另一个也不蹲了……“看把你个碎货能的些。”[2]13
5.“咋不让人家法院一枪打死算了呢,这个得倒头瘟病的货呦。”[2]105
将人比作“货”,也还是将其划作非人之类,不属于人属的“东西”。实际上是对对方智力、人格的贬低。但“货”类的詈词在陕西方言中并不都是用于发泄不良情绪之用,有很多也用来表示对人不争气的惋惜、或表达长辈对晚辈的疼惜之义,比如例⑤,胡秀英面对弟弟因图一时口实之快被有心人陷害而深陷入狱的遭遇,不由痛骂出“倒头瘟病的货”,这其中更多的是对其弟胡三元遭遇的痛惜,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咒死义。由此可见,方言中诸多的詈语现如今詈骂的浓厚色彩已经开始慢慢淡化乃至褪色。
(二)与性有关的詈语
从古至今,“性”一直是一个隐晦而神秘的话题,“隐晦”在于它有诸多不可置之于口、公之于众的内容和色彩,而因其时常被人故意隐去不提,故而像一层面纱一样具有了隔膜一般的神秘感,成为了约定俗成的禁忌。而和“性”有关的词汇出现在詈语中则表现出人们违反禁忌,给他人施加来自社会的心理压力,对其造成不快和伤害。和“性”有关的詈语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性器官和性行为方面,比如:
6.刚一走进幕帘,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贼他妈,台上热得两个蛋都快焐熟了。”[2]15
7.“没本事,混在这行球不顶。”[2]25
(三)与污物有关的詈语
在宋元时期之前,文学作品中与污物有关的詈语还极少,不足加以分类阐明,从宋代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勾栏瓦肆成为繁华之所,俗文学开始拔地而起,此类作品大多反映了平头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了更好地迎合流连此地的熟客,自然不免将粗俗之语越来越多的带入到作品当中,也就从此开始,詈语开始充满了市井气,变得愈发低俗化。诸如“屄、屁、屎”类的词语,在明清之际,更是在众多世俗小说中出现,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这些詈词经历了百年的变迁,其骂意依然保留至今,并且在方言小说中大放光彩。在《主角》中,如:
8.廖师就骂开了:“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2]113
9.“五、让他把屄嘴夹紧些。”[2]220
10.姥姥就骂他:“买你娘的屄②,又买摩托呢。……”[2]]781
二、《主角》中詈语蕴涵的文化
《主角》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便是文中大量的陕西方言的运用。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以语言为媒介展现出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地域色彩。通过对方言的分析,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地域文化对其形成的影响,更可以从语言的角度揭示文化流变的原因和趋向。由此可见,方言与地域文化是互为表里的。在本书中,作家通过陕西方言向人们呈现出陕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利用陕西方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且饱满的人物形象。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活着”的每一个小人物,从出生之日起便与浸润了几代人的文化共生共存,而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和“侵蚀”。“詈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詈语是最能直接且露骨地呈现一个地方地域文化“俗”的一面,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书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
(一)詈语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伦理文化
男尊女卑的观念古之已有,从夏朝开始,随着男权社会的完全确立,“家天下”的禅位模式彻底颠覆了母系时代。母系社会的日益衰亡,显而易见的便是女性地位的降低,再加之有小农经济这一经济基础的加持,女性由于自身条件的不足自然而然便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弱势群体”。自周朝宗法社会成为体系之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便成为了主流社会的伦理规范。经济地位的缺失以及封建思想的禁锢,使得女性自身也逐渐承认并主动成为这一思想观念延续的“帮凶”。
在陕西方言的詈语中,涉及女性歧视的词汇有很多,大多和女性长辈有关,如,“贼你妈、贼他妈、操你姥姥”“日你妈”等,也有一些意指女性地位卑贱,瞧不起对方的詈语,如“碎蹄子”“碎婊子”“碎货”。而且从各类詈语类型来看,相对于男性相关的詈语数量来说,贬损女性更是占据上风。从语言表征上来看,陕西地区男权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为低下。
(二)詈语折射出陕西的禁忌文化
禁忌语中所蕴含的,是人们出于趋吉避凶的心理而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性的禁忌文化。这种禁忌性文化体现出人们遵从社会心理和道德的制约,自觉地保持和维护这种带给社会团体以稳定和平衡的规范。若冲破规范,则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集体性施压,来自心理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过去在陕西,普通百姓的生活也非常困苦,由此导致突破禁忌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常常使用“性”詈语倾泻了对生活中各种不满或压抑的愤怒情绪。《主角》中就有很多“性”詈语,比如“日他妈、屄嘴、皮膪膪货”,多是与男性生殖器官或与性关系有联系的词语。“性”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禁忌性的话题,而它在詈语中应用,表明人们以语言为出口进行不良情绪的倾倒和发泄,实现心理的平衡和欲望的满足。
(三)詈语旁涉陕西农业生产文化
陕西地区的渭河两岸有“八百里秦川”的美称,这是由于经过数千年岁月的累积而形成的肥沃之地。由于土地肥沃、雨水量充足、气候宜人温和,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了陕西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业”。生活在陕西地区的人们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有关农业生产生活的动物词语自然也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日常话题,甚至变成了陕西方言詈语,其中以牲畜家禽类詈语数量为多。《主角》中出现的这方面的詈语不多,仅有“牛“”驴日“”狗日“”鸡贼”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三、《主角》中詈语的功能
(一)具有交际功能
詈语在交际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攻击”,通过辱骂、训斥等形式将愤怒的情绪倾泻出来。而在小说中,很多詈骂情境都是将攻击与发泄结合在一起。比如:
舅把牙一咬:“嚼他娘的牙帮骨。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开他妈的个瘪葫芦子!”[2]9
“放心,那些给哈怂领导献媚的,我都有办法收拾。”舅把话题一转,说,“你可得把这娃的事当事。”[2]10
在以上示例可以看出,詈骂的攻击作用并不是很强烈,更多的是和不满情绪的发泄结合在一起。
除了攻击和发泄情绪之外,詈语还有讽刺的功能。“骂詈语的讽刺功能就是用骂詈语来嘲笑讽刺对方,这样的骂詈含蓄、委婉、隐晦,被骂詈的对象要能领会其意旨才能使其产生嘲讽功能,达到讽刺的目的。这样的骂詈语通常是骂詈者把握了对方心理,骂詈双方相互熟悉才能出现。”如,小说中,胡彩香给忆秦娥换新买的衣服,因不满胡三元给忆秦娥的穿着打扮,而说道:“看你那大‘摇婆子’鞋。也真是的,你舅个死啬皮,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买一双。”[2]20这段话看似是胡彩香在嘲讽胡三元眼光落后,土气,实则其中含有一种“打情骂俏”的情感,借詈骂的形式表达了对“她舅”这个人过于死抠的无奈。另外,在小说中,出现更多的是作者对角色的“嘲讽”,从第三方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角色,而非产生于人物对话的碰撞,比如,在描写忆秦娥参加县剧团的招生考试中,作者写道“也不知咋的,她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瓜不唧唧地戳上了舞台。”[2]21“瓜”本是形容人呆傻,但在这句描述中,除了体现她的呆气,更多的是对第一次面对这样大场面的一种自然的人物反应。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的詈语,它的交际功能是混合的、多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将贴近生活的真实的人物和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具有塑造人物的功能
詈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其对彰显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小说《主角》当中,詈语的运用无疑是对塑造、刻画普通老百姓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人类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强烈的情感对冲的,而在这样的体验下,就会迸发出詈骂语言,这些语言才是人们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正是这样的共情式的情感特征才能让作品显得更加真实,这是正式的交际用语所无法比肩的。也正是有了詈骂的加入,角色的立体感和真实感才会更上一个台阶。小说中,胡三元就是一个“出口成脏”的人,他常常嘴边离不开的就是“哈怂”“少皮干”这样的骂语,通过这些具体到语境中的詈语,可以使读者深入地认识到胡三元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立体性。胡三元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骂语那样的低俗不堪,而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如果脱离了詈语的描述,那人物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者,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与胡三元形象完全对立的角色——郝大锤。此人虽然和胡三元同样喜欢“出口成脏”,但是骂语和骂意却狠毒许多。比如:
临走临走了,他还给易青娥撂了几句话,“火烧得美美的么,咋想起要唱戏了呢?真是跟你那个烂杆舅一样,一辈子瞎折腾哩。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2]175
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面走,还一边骂:“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披来筛去的,我就头晕。你还嫌我呢,排不成了滚你娘的蛋。”[2]139
显而易见,通过骂詈,郝大锤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技不如人而带来的内心挫败感,骂詈中所包含的恶毒诅咒也把“攻击”这一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借此将这一人物的歹毒狠辣、阴险自负的性格特征塑造得饱满而充沛。
总之,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方言中的詈语,则是地域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角度,折射出普通民众的伦理观念、社会生活。[5]陕西作家陈彦以其细腻独到的观察,深刻认识到詈语的俗文化镜像功能,把陕西詈语运用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借此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原生态的陕西地域文化,可谓是一箭双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汉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淀了发达的语汇和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无数文人墨客,运用汉语铺锦列绣的辞藻,塑造了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传承了泱泱大国的礼俗文明,化育成为今天人们待人接物的美好风尚。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语言文明仍然是传承和构建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工具。毋庸讳言,陈彦《主角》中运用詈语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陕西人千年承袭的民间习俗,这是作品的一个亮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品中这些詈语的书写与使用,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青少年读者的语言接受与习得,某种程度上会对社会的语言文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此,我们呼吁,文学作品如无十分必要,尽量减少或者节制詈语的使用,尽可能以委婉含蓄的文明语言取代詈语,使文学作品更好地服务文明社会的建设。
注释:
“尻”当为古汉语书面语用字,意为“屁股”,读为“kāo”。今现代汉语“尻”也多用于书面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尻”“今俗云沟子是也”。也就是说,“沟子”一词在清代就已经出现了。现在西北方言中指称人屁股时多用“沟子”一词,不单说“沟”,也不会说“尻”或“尻子”。据考察,陕西各地都没有把屁股称为“尻”“尻子”的说法。今陕西各地方言多用“溜沟子”“溜沟子货”“舔沟子”来侮辱人。因此,书中以“尻”“尻子”代替“沟子”疑为作者误写。
——喜迎十九大 追赶超越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