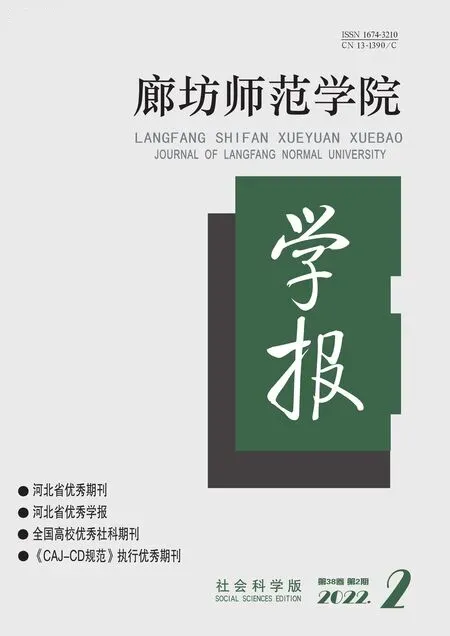廊坊市安次区西安庄登云会的历史传承与困境探析
王 伟,贺文博,房澳秋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她孕育和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充分体现出先人们的集体智慧和创造力。2009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廊坊市安次区西安庄登云会,就是这些遍布于中华大地上既平凡又璀璨的文化明星之一。它曾在京津一带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然而,由于近二三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迅猛变革,其传承与生存遇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探究造成其传承与生存困境的原因①对于民间高跷艺术的研究,主要有蒲娇、唐娜所著的《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汤顺霞所著的《凌空飞舞的秧歌(苦水高高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2021年4月,笔者与团队成员前往西安庄采访高跷登云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绍波师傅,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该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不仅有益于其摆脱困境、传承发展,而且对处于相似困境的其他“非遗”项目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高跷艺术与西安庄登云会概况
高跷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因表演者皆脚踩、腿绑于各式木跷之上,故名高跷。明清时期,高跷会的诞生与发展使高跷文化成为了全社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西安庄高跷登云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一)从高跷到高跷会
对高跷艺术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的著作《列子·说符篇》之中,“宋有兰子者,……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驱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②《列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6页。。可见,在春秋时期高跷技艺就已十分高超,并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下肢踩跷、上肢杂技、单人表演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以高跷为代表的杂技艺术通常是供统治阶级享乐的,其表演者主要为统治者专门豢养的专业艺伎。相应地,高跷表演主要传承了像兰子这类单人高难度绝技表演,门槛高,普及性低。但随着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高跷为代表的杂技艺术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明清两代民间走会的兴起使高跷迎来了变革的契机,高跷不再限于艺伎的个人绝技,逐渐成为民间群体庆祝节庆的集体性娱乐表演。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走会形式之一为迎神赛会。迎神赛会原为中国传统的祭祀、祈福仪式,但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其节庆娱乐属性开始日益增强。而高跷艺术因其直观并适合大规模表演,逐渐成为迎神赛会活动中和秧歌并列的两大民间艺术之一。由于经常同场献艺、相互切磋,高跷学习、吸收了大量秧歌的表演形式,形成了“凌空飞舞的秧歌”。如在明代反映嘉靖年间南京城市风俗的《南都繁会图》中,“势如长龙的走会队伍穿街过巷蜿蜒流动在长街上,隔一段距离有一队高跷艺人前道开路,两队高跷之间便是什锦杂技边走边演……高跷表演,有明月和尚渡柳蟾,渔樵耕读等形象”①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这说明在明代中后期,城市中的秧歌与高跷相融合的民间艺术形式已经逐渐成型。而在二者交融的基础上,至清代中后期,专门的高跷会便应运而生了。
在清代,专门的高跷会在直隶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中逐渐形成了“皇会”这种表演组织。“皇会”最初以衣食无忧的八旗子弟为主。由于每日无所事事,他们通常会寻找各种娱乐方式消遣时间,逐渐成为“票友”。每逢佳节,由八旗子弟“票友”组成的表演队伍在宫门外或热闹街市游动行进,称为“过会”,游到中心地段便拉开场子进行表演。清皇室为了粉饰太平,表示与民同乐,皇帝、太后等有时也会出来观看,因此这种特殊的“票友会”便逐渐被称为“皇会”。②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皇会”的出现,使民间办会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大众杂技艺术产生了一个稳定、脱离生产的专业队伍。在此基础上,一些“皇会”专攻高跷表演,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北京、天津在此期间诞生的一系列“皇会”性质的著名高跷老会。这些老会在“凌空飞舞的秧歌”之上,进一步将直隶地区已经成熟的戏曲文化融合到高跷中,使高跷艺术更加受到大众的喜爱。另一方面,随着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节庆娱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群体高跷表演的直观性与低入门门槛受到普遍欢迎。在乡村地区的旺盛需求下,大量来自城市的流浪艺人走向乡村,将以高跷为代表的杂技艺术带到了乡间,使高跷艺术得以在乡村地区普及开来,成为了沟通城市与乡村文化的重要纽带。清代中期直隶诗人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就对直隶地区乡村的高跷文化做出了如下描写:“村公村母扮村村,屐齿双移四柱均。高脚相看身有半,要知原不是长人。”③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可见,至清代中期,直隶地区的高跷文化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技艺也已经比较成熟。在这一基础上,一种成熟的高跷会艺术形式便在京津乡间社会应运而生。表演者双足缚于三四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进行跳、跃、蹲、踢、仰、俯、探海、分腿、劈叉等高难度动作,边行走边表演,高高在上,有如腾云驾雾,仿佛各路神仙升天凌舞,所以也叫“登云会”。
(二)西安庄登云会
西安庄村位于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东部的津冀交界处,毗邻京台高速公路。从区位交通上看,西安庄位处京津交通往来便捷之地,人口流动频繁;从高跷会的溯源来看,西安庄登云会的起源与京津两市民间文化更有着密切的关系。
1.西安庄登云会的起源
西安庄高跷登云会相传始创于清朝末年,距今已有百余年的传承史。根据登云会“非遗”传人张绍波老人介绍,西安庄的高跷技艺是一位名为笑刘的民间艺人所传。笑刘原为梨园弟子,京剧武生出身,后不知何故结束梨园生涯返回家乡码头镇一带。为了生计,笑刘将自己精湛的京剧功夫融入了当地已有的高跷技艺之中,在精进高跷表演内容后于此收徒授业。在笑刘的教授下,西安庄高跷登云会的技艺突飞猛进,最终名扬京南大地。由于民间疏于文本记载,关于笑刘的详细信息已经无法考证,只能在口口相传中寻觅蛛丝马迹。在访谈过程中课题组注意到,根据传承人回忆,笑刘收徒授业并非仅限于西安庄一地,而是在四邻村落同时进行,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但西安庄是其中的长徒,因此被公认在技艺上继承了笑刘的衣钵。结合笑刘的活动轨迹与当时全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推测,笑刘在离开梨园后和无数流浪艺人一样以表演和授业为生,客观上完成了将城市高跷文化传递至乡村、用京剧的表演形式改造旧式高跷表演的历史重任。
2.登云会的早期发展及原因
根据传承人回忆,笑刘在此收徒授业后,高跷登云会便发展开来,并以其精湛的技艺名扬京南。据传承人回忆,登云会曾到邻近的武清县杨村镇去拜庙①关于此次拜庙的目的地,本文采用了传承人口述的“杨村说”,另有部分新闻媒体报道的“信安说”。。由于庙规森严,狮子把门,打不够一百单八棒(十二套)不得踏入庙内,当时有十八道会都被挡在了庙门之外。西安庄登云会大头形(十六角色中的首角兼领队人,原型为行者武松形象)沙德贵抖棒上前,在庙门前按演练之法打了一百单八棒,一举震开山门,在场豪杰无不为其拍手叫好,随即引领各会进入庙中。西安庄登云会从此威震京南大地,一时间前来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各地青少年无不以拜于西安庄登云会麾下为荣。总体来说,西安庄登云会能够迅速发展,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环境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西安庄登云会的诞生与发展直接受益于京津两城。正如前文所述,早在清代中期京津两城在高跷表演艺术上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西安庄位于京津之间,尤其毗邻今天津武清地区,因此在西安庄登云会的发展史中与武清乃至天津城的高跷组织关系密切。从高跷会的师承与开创者笑刘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直接推测西安庄的高跷技艺源于京津二城。从高跷的角色与表演来看,西安庄登云会的表演绝大部分师承了京津两地较为成熟的高跷表演形式,即以《水浒传》的人物为高跷会的主要角色,二人一对儿,分别表演不同的故事内容。但也要注意的是,西安庄登云会之所以能够在当地高跷会中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其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更在于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革新精神。如与天津城著名的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相比较,同乐高跷老会共七对十四角,这些角色均出自《水浒传》中的人物,根据原作人物性格,在表演中赋予相应的肢体动作及唱词。②蒲娇、唐娜:《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而西安庄登云会则通常采用八对十六角,角色虽然仍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底版,但不是以人物名称来划分,而是以抽象的职业为依据③分别为:第一组大头形与二头形,第二组樵夫与李大老奶奶,第三组公子哥与青竿,第四组渔翁与白竿,第五组傻公子与刘二姐,第六组衙役与寡妇,第七组县太爷与老作子,第八组为傻子与傻大妈。。以樵夫为例,在《水浒》戏中,樵夫可以为石秀,而在其他故事中樵夫就不再是石秀,而是一切樵夫的统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西安庄登云会是纯高跷会,且没有演唱这一内容,因此,便通过增加角色,以丰富故事创作和表演的空间。
其次,西安庄拥有一套适宜高跷表演的环境“硬件”。西安庄地处华北平原地区,传统的经济模式以农业种植为主。由于温带季风气候的季节性特点,导致华北地区的乡村每年都有漫长的“冬闲”时光,这段时光恰恰适合高跷会的集体练习与表演。永定河水系冲积出的黄土地,土质相对松软,也适合隆冬季节高跷的练习与表演。村庄中的公用晒谷场在冬闲时节也就成为了村民们练习与表演的天然优质场地。与城市中的高跷会相比,乡村地区便于村民在“冬闲”中随时大规模练会出会。而相比之下,在城市中练会出会的准备工作就要复杂许多,除了要保证会内排练质量,还要在出会前协调各方关系,包括本地交通队、辖区派出所及街道办事处①蒲娇、唐娜:《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还要协调会员单位请假等。这从出会的时间差异上可见一斑。天津的高跷会在出会时间上,“一般在传统节日出会,但在春节出会的次数较少,因为正值寒冬,如果穿得太厚活动会受影响,穿的少则太冷,而且冬天气温较低,地面易结冰,踩上腿子容易打滑。因此出会时间多安排在正月十五、五月节、八月十五等节日”②蒲娇、唐娜:《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但乡村高跷会则有很大不同,根据传承人介绍,登云会通常腊月练会,出会时间通常为大年初二至正月底,其余时间很少出会。
再次,经济原因。乡村高跷会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不仅是一项文体活动,还是一种经济活动,这也是它和城市高跷会的一项明显差异。以天津“皇会”为例,正如前文所述,“皇会”产生于不愁生计的八旗子弟的娱乐活动,因此城市“皇会”的目的是娱乐和表演,即所谓的“玩会”,会与会之间还存在攀比之风,其结果就是会众往往需要自筹经费维持“皇会”的运转。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后,城市高跷会仍然保留着这种非盈利特征,所以经济上只能通过向会员收取会费来维持高跷会的基本运转。但与出会的庞大开销相比,会员们所交纳的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并不足以支持出会的挑费③蒲娇、唐娜:《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更不用说其他各种各样的水、电、煤气、茶叶、礼品以及对部分会员误工费的补偿。而乡村高跷会则有所不同。由于传统乡村地区收入形式单一,至冬闲季节,并无其他收入。参加高跷会,四处表演(甚至是部分商业性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物质贫乏年代的村民来说,可以增加一定的物质收入(如香烟、点心等),因此受到了参会村民的青睐。
3.西安庄登云会的表演
在田地之上辛勤劳作一年后,每到农历腊月,西安庄村民们便迎来了两个月左右的闲暇时间。此时村民们便要为辞旧迎新的庆典做好准备。在会长等人的张罗之下,高跷会的演员们在腊月便开始集中“练会”。由于“腿子”过于沉重,踩踏表演十分辛苦,因此演员皆为男性。在练会中,有几经风霜的老会员,也有初出茅庐的新学徒。对于新入会的学徒来说,其角色由师傅以其资质来定。在角色确定后,便是“走场”,即在大型空地上练习基本功,推敲角色的细节动作以及练习“场花”(配合)。而那些被选为扮演女性角色的演员们,还要加练倒地翻身的动作。在经过近一个月的操练后,从正月初二就开始进入到正式表演的时段。出会表演的场次与时间并不固定,只要收到周围村落的邀约后即可组织前往。由于西安庄登云会在京南大地上久负盛名,因此各种邀约数量众多又集中在数日之内,且拒绝不得。根据传承人回忆,在早年曾出现过最多一日连走7村的情况。出会的最大规模近40人,平常除了16人的正式表演队伍外,通常还会有4到5人的替补演员。虽是替补演员,但其选才亦十分严格。如果说场上演员是以专精一角闻名,那么替补演员则是以博于众角而著称,只有如此,才能在任何正式演员发生意外时立即进行替补。登云会通常还配备一支最多18人的乐队为高跷表演伴奏。由于乐队主要起着把控节奏的作用,因此不需要复杂的曲目与乐器,只是以鼓、锣、钹这三种声音明亮又节奏鲜明的打击乐器进行演奏。表演时,在锣鼓的鼓点中,大头形、二头形各自带领男女角色双双入场展示,待鼓点改变后再成对儿表演相应的专属故事。由于没有管弦伴奏,西安庄登云会也没有相应的戏曲演唱内容,仅在第8组(傻子、傻大妈)之间有少量对话内容。虽然缺乏演唱部分,但西安庄登云会在高跷分类上仍属于文会,即花活多、配合多。在绝活上,有“老牛拖象”“刘海戏金蟾”“摆香山”等。这些绝活通常为数层演员进行叠罗后,在统一的锣鼓节奏下进行移动。相传,最叹为观止的绝活“摆香山”能够叠罗9层移动30米,现已失传;而“老牛拖象”等叠罗3层移动10米的绝活仍然是西安庄登云会的重要保留项目。
二、登云会面临的困境
和众多“非遗”文化相似,西安庄登云会在“文革”期间曾一度暂停,改革开放后,又得以复兴。1988年,西安庄登云会曾经到天津武清县参加花会调演比赛,并荣获表演第一名。但进入21世纪后,西安庄登云会却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据传承人讲述,登云会每年稳定出会坚持到2007年,此后便只能断断续续地活动。最后一次出会为2018年,此后因各种原因至今未再出会。在和传承人进行交流后,我们将其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乡村宏观社会的变迁
21世纪乡村宏观经济社会的变迁,对登云会的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
首先,登云会对农村青年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西安庄地处京津廊腹地,对于广大乡村青年来说,进城务工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务农并成为获得收入最主要的方式。“冬闲”已从漫长的冬季缩短至春节小长假,且休息与走亲访友成为了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精力上都无法满足高跷会的正常训练与表演,而高跷会带来的微薄收益,也难以引起在外打工青年的兴趣。
其次,新型娱乐方式的兴起替代了登云会的传统娱乐功能。在娱乐匮乏的传统乡村社会,春节走会几乎是每年最为盛大的娱乐与庆祝方式。但在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普及与流行的当代,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手机游戏、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都成为青年人沉迷的娱乐新时尚,足不出户进一步边缘化了需要到户外和现场观看的高跷艺术。
再次,传统登云会潜在的经济功用愈发的边缘化。在传统登云会中,启动与运营资金主要依靠村民募捐或会员自筹。在部分商业性质的演出中,演员再以自己的表演获得少量物质收入。但随着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这种微薄的物质收入与艰辛的体力付出相比,愈发地被视为“不值得”。与此同时,出会的成本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传承人表示,前些年西安庄登云会最后几次出会,负责随行拉道具、乐器的小货车的租金每天大概要60元,加之通常近40人左右的交通、饮食费用,登云会演出的微薄收入根本入不敷出。
最后,登云会的乡村坚守人员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认识不足。在对传承人的采访中,笔者曾对登云会的网上展示情况提出咨询。传承人表示,在土豆网上可以搜索到早年河北电视台拍摄的西安庄登云会的数分钟视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资源。而笔者在搜索后,并未觅得该视频,相反其临近区域,如天津周边区域的高跷会视频却琳琅满目。可见,在借力网络视频传播上,西安庄登云会与其他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二)造血能力的缺失
“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而传承的过程需要很多艰辛的付出。如高跷技艺,踩上高跷,凌空飞舞,已是不易;若想进一步精益求精,更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日积月累。在21世纪前,高跷曾是当地众多中小学生寒假期间的课外活动。但是近20年来,由于中小学过度追求升学率,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学生已经无暇也没有机会接触高跷技艺。即便是在假期中,由于家长对孩子的宠爱,认为高跷危险,或是影响学习,更或是单纯认为辛苦,往往就不支持孩子们加以练习,这更导致高跷技艺后继乏人,造血功能日益不足。
(三)政策扶助的力度不足
除了社会方面的变迁,从总体上看,相关部门在传统“非遗”项目保护上的扶助力度也有待加强。近些年来,虽然文化部门日益重视并保护相关的“非遗”项目,如2009年西安庄高跷会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传承人和集体授予相应证明以及5000元扶助资金。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新的社会变革下传统高跷会造血能力不足的根本性问题,一次性拨付的少量经费对于长时间维持登云会的运转无异于杯水车薪。
三、保护登云会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22-01-1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庄登云会的高跷表演发挥着丰富农民生活、活跃乡村年节气氛的作用。它通过仪式聚集乡邻,联络村庄之间的感情,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凝聚村民奋力建设家乡的热情,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救助模式,不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输血”,更要完善其“造血”机能,从而促进西安庄登云会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与振兴。
(一)合理挖掘登云会的经济价值,提高其“造血”机能
当今登云会传承发展中的最大困境实际上就是其造血能力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输血”是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手段,但根本还是要增强其造血能力。对此,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将高跷与全民健身相结合,让高跷“火”起来。今日,全民健身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国家重视,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②《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国发〔2021〕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01-18,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高跷作为一种传统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手部、脚部力量,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能力,提高灵敏、柔韧、力量等身体素质,有一定的健身价值。因此,可以对高跷的健身价值进行开发,使它和全民健身进行有机结合。
2.将高跷与民俗旅游相结合,让高跷“赚”起来。登云会作为西安庄的一种特色民俗活动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当地特有的民俗风韵和文化特色。西安庄地理位置优渥,位于京津廊腹地,交通便捷,适合发展民俗旅游业。因此可以将高跷表演和当地民俗旅游结合起来,如建设高跷文化广场,登云会博物馆等,吸引本地及周边民俗爱好者和普通游客参观旅游,使其产生经济效益。
3.将高跷与地方基础教育相结合,让高跷“年轻”起来。正如上文所述,登云会传承的一大困境在于年轻人无法接触到高跷,导致高跷表演者青黄不接。因此,西安庄乃至邻近的码头镇当地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可以在体育课中开设与高跷相关的特色课程,聘请传承人到学校进行高跷的普及教育,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增进青少年对高跷的了解和兴趣,进而为高跷的发展和传承培养后继者。
4.将高跷与网络相结合,让高跷“潮”起来。当今网络视频传播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短视频的高速发展,使大量处江湖之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摆脱“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扰。可以通过录制视频进行网络传播的方式,让高跷会上网,让高跷文化上网,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安庄登云会,了解这里高超的高跷艺术。
(二)发挥地方院校的社会职能,破除“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窘境
对于地方高等院校来说,除了接受政府委托做好相关“非遗”项目调查与记录工作外,对以西安庄登云会为代表的“非遗”项目的振兴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对在校学生的“非遗”推广工作。以笔者所在的廊坊师范学院为例,对“非遗”采取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请进来”指“非遗”传人进入校园和课堂。本校近几年来一直持续邀请廊坊市地方“非遗”传人进课堂向学生展示“非遗”精髓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胜芳镇南音乐会传承人胡宝莹来我校授课》,廊坊师范学院官方网站,2022-02-03,http://www.lfnu.edu.cn/col/1445216588182/2017/12/25/1514187139218.html.,邀请师生共同体验“非遗”活动,并基于此开展“第二课堂”②《深挖地方教育资源 打造高效第二课堂》,廊坊师范学院官方网站,2022-02-05,http://www.lfnu.edu.cn/col/1387254539437/2021/10/04/1633358388197.html.等。“非遗”传人进课堂已经成为本校一大特色活动。“走出去”则是鼓励学生假期参加各种“非遗”实践调研,也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③《砥砺青春 走进非遗》,廊坊师范学院官方网站,2022-02-01,http://www.lfnu.edu.cn/col/1387254539437/2019/07/20/1563631221676.html.
其次,相关专业可开设相应的课程,在高校中培养“非遗”后继人才。如体育专业可以开设高跷方向特色课程,为高跷会的传承提供一个专业与学术共存的人才队伍。同时,鼓励并支持学生以“非遗”创新创业④《学校举行非遗文化产业学院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廊坊师范学院官方网站,2022-02-10,http://www.lfnu.edu.cn/col/1387254539437/2022/01/11/1641956435128.html.,利用现代化的理念与手段来赋予乡村地区“非遗”项目以新的生命。
结 语
西安庄登云会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百年来京南乡村地区重要的辞旧迎新的庆典活动的一部分,它还承载着西安庄,乃至京南大地上人民顽强不屈、通过辛劳而步步登高的美好愿望。在采访中,传承人向我们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他们都要坚持传承这项“祖宗留下来的香火”。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仅是传承人的个人义务,更应当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使命,要努力让我们的子孙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得到祖先优秀技艺的活态传承,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