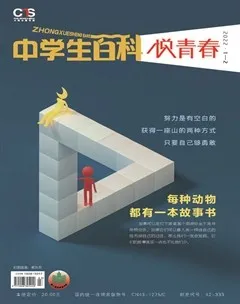子殊
鲜支
我在一次公务活动中见到周启。周启的隔离衣上别着“院感科”的工作牌,他从病房楼长长走廊的那一头走来。
那天的阳光特别冷清。周围声音嘈杂,可周启同阳光一样冷清,穿着白色隔离衣,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真像啊!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像被钉住一样挪不动步。
周启不是临床大夫,他在院感科工作,属于医院二线科室,这次陪同院领导迎接上级检查,远远地跟在后面。我作為检查队伍的一员,虽年轻,但也被环绕簇拥。我在人群中止不住地去瞟周启,目光一次又一次掠过他颀长的身影。
有什么在脑海中渐次苏醒,少年从沉睡的记忆中剥离。
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早上的雾散了,其实,不止早上,不止雾。
我想起张子殊最后对我说:“谢谢你啊!”想起他那双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亮晶晶的,眼眶湿润,却没有流泪。
我在心底微不可闻地呻吟了一声,就像几年前走在墓园里,落叶被踩碎的呻吟。

检查间歇,众人回办公室休息。大家忙着应酬,我趁机离开人群。
周启独自站在门边,见我过来,很礼貌地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抬头:“你有水吗?”
我位置上的杯子明明是满的,浅色的茶水,浮着点茶末,热气蒸腾。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许什么都不需要,或许是需要与他说一说话。
“好的,我给您倒,稍等。”
真是温柔的声音啊,我在心底里默默叹息。
“想要凉的呢。”
“隔壁有纯净水,我去拿。”
我望着他走出去的背影,很挺拔,一看就是年轻人健康而有活力的样子。我想起他刚刚开会时把眼镜摘下来低头擦一擦又戴回去的样子,有点儒雅,有点好看。不,是非常好看。
真好看呀,像极了我想象中张子殊长大后的样子。
坐车回去的时候,有同事大姐心细如发,发现了我的异样,热心地戳一戳我,说:“怎么?医院有小伙子不错吧。我帮你打听打听介绍一下?”
我愣了一下,敷衍地笑笑:“哪有,我还想再自由几年呢。”
那个周启,一个初见的陌生人。留意他吗?是的。喜欢他吗?却未必。
那么想要接近的,分不清是真实的人,还是一个旧日的影子。
我觉得,随着自己不断长大,对生活的感觉在不断流失,能明显感觉到,却又形容不出来。以前走在街上,趁着夏日的晚风,看着落日好像流动的咸蛋黄,云似多彩的棉花糖。而今,好不容易闻到空气中季节的味道,再抬头望天,会发现那种对万事万物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已经从身上流失,眼中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是行色匆匆的自己。
疲惫的夕阳和自己一样困倦,阳光只会让人躁动不安。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也在慢慢流逝——当觉得某人不错的时候,会大大方方上前打招呼,问好,聊天;偶尔会质疑,觉得喜欢的伊始好像不是这样,可具体应该是什么样,也记不起来;相处不再笨拙,不再羞涩,坦坦荡荡,落落大方,可谈风月,可说爱恨。
这也许是好事。
只是,十九岁时那种在一模一样的校服人海中,一眼就认出暗恋之人的超能力,消失了。茫茫人海,熙熙攘攘,若你不是格外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咫尺之内,我便认不出你。
以前觉得郎艳独绝,现在觉得不过尔尔。可幸还是可悲,真的说不清。
原来众生皆似。
偶尔遇到一个不似的……却还是因为像极了十九岁时的暗恋之人。
遇见张子殊的时候,我十九岁。
那时候,我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帮忙。咨询室由我所在的大学开设,与大学旁的附属中学共用,本校心理学专业大二以上年级的本科生可以去见习,兼做义工。我挺喜欢听其中一位心理咨询老师讲课,有空就常去。
张子殊走进诊室的那一刻,我在心里惊叹:这个男孩子真好看啊!
男孩有一种瘦骨清像的美——直背薄肩,身形颀长,宽大的校服挂在身上,空空荡荡;下颌线条鲜明流畅,有一双瞳仁颜色很深的眼,眼神温和,如漾波光。
老师见有人来,招呼他:“同学,来,坐。”
我盯着他的校服,心想:哦,高中生。
张子殊大约是感觉到灼灼目光,回盯我一眼。我明了,这是不欢迎我在场,我该回避了。
我慢慢地踱步出去,在门口装作不经意地回了下头。
张子殊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整个人呈一种放松的姿态,没有之前来咨询心理问题的同学那种情理之中的紧张和拘束。他坐下来的样子愈发好看,碎发遮眸,侧影立体,校服塌在身上显出躯体轮廓,宽肩窄腰,双腿修长。
我禁不住又看了一眼,心想:“他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其实有一点窥私的欲望,想听一听墙根,想知道这样的少年有什么想不开的需要来找医生咨询。抑郁?厌学?压力大?还是原生家庭的矛盾所导致的苦痛?
真令人好奇。
但我终究也没那么做,这点起码的专业素养还是有的。

过了很久,张子殊才从诊室出来。他一开门就能看见我。
我没有走远,站在楼外自成一隅的院子里,全神贯注地仰头望天,就好像那天上有什么稀奇之物费人琢磨一般。
然而什么也没有,无非是天、云和高耸的建筑物。天阴得厉害,云一层层压下来,风开始漫卷。建筑墙面仿佛褪色一般暗淡下来,空气中涌起了尘土的气味——一股大雨即将来临时的潮气的味道。
我循着张子殊的脚步声回头,慢慢转过身。
少年像竹林小径处悠然照面而来的白鹿,晃一眼便乱人心怀,须得小心翼翼地观望,生怕唐突惊动。脑中忽然闪过一句话,我“噗嗤”一声就笑了。
张子殊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你笑什么?”
我未及回应,忽然有水滴从天上掉下来,风好像更凉了些,几滴雨水落下后,雨丝忽然密集起来。一场大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张子殊往外快走几步,经过我身侧。我突然叫住他:“喂,你要伞吗?”
很多年后,当我再度回忆那天的场景,觉得一切都很模糊。
风雨晦暝,水雾腾腾,树影幢幢,只有雨幕中很近地站着的那个人是清晰的,或者说,那个影子是清晰的。
我记得自己又凑近了一点,才突破雨幕看到他的脸。雨水压在了他的睫毛上,他飞快地眨一下眼,那雨水就顺着他的脸颊从下巴淌下去,给人一种流了泪一般的错觉。
“你要伞吗?”我又问了一遍。
张子殊拒绝了我借伞的善意,但从那天之后,开始频繁往咨询室跑,与我慢慢熟悉起来。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有什么心理问题,问老师,老师也不说。
我有时觉得他没问题,有时又觉得他问题很大。
张子殊有时候相当成熟,一点不像十八岁的高中生,能很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情绪,也很会安慰人,对生活的体察上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温柔。
我是个很容易沮丧的人,生活中些微挫折便能令我垂头丧气,食不甘味,感叹“人间不值得”。张子殊就很会开导我,善于从小事里诱导出美好的轮廓。他讲他小时候,跟着外婆住在乡下,他喜欢坐船,外婆就跟邻居几家人拼一条船。大人们轮换着摇橹,小孩子坐在船头,河岸有突出的树枝垂到水面,河道里还会漂着水葫芦……他说,这是一些很简单的记忆,偶尔回忆起来,再难过的时候也会觉得人间值得。
顺着他的讲述,我想象清晨那沾染花香的缥缈雾气,纵然是没有见过的景色,也如身临其境般嗅到了水汽与芬芳。
但有时候,他又相当的不成熟,对自己的人生前途全无考量和规划——明明已经高三了,多么重要的时段,卻偏偏不务正业,执着地泡在心理咨询室,似乎对高考这件事毫不在乎。
我思来想去,觉得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过于优秀,获得了保送资格,要么就是深度厌学。
子殊拒不承认自己会被保送,称自己是个实打实的“学渣”。
我见他对于“学渣”的自我定位十分真诚,便坚定了他厌学的诊断,不免开始替他着急,三天两头见缝插针就劝他一劝:“你这个年纪,就是学习的年纪,什么年纪干什么事。你不去教室里读书复习,整天往这里跑干吗?我看你也不像有什么心理问题的,回去好好学习不行吗?有什么问题等高考之后再解决不行吗?当务之急,孰轻孰重,你要分清楚啊……只要不影响你高考的都可以暂缓处理。”
劝得多了,他倒也不烦,只是笑眯眯地跟我磨:“心理健康也挺重要的啊,我考不上学,顶多是个对社会无用的人,可要是心理出了问题,那可能是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我看他嬉皮笑脸,拿学业前途全不当回事,有点生气:“你有病吧!我看你不是心理有病,是脑子有病。”
他还是笑眯眯的:“是啊,我就是脑子有病。”
我宛如一拳打到了棉花上,完全没了脾气。
脾气虽然发不出,劝,我依旧是要劝的,听,他也照旧是不听的。
如此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我好像从没有这么上心地规劝过一个人,那心境好似薛宝钗劝不动贾宝玉。我看着这个人身上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好,便希望他能前程似锦。
我不是没有过一些自私的绮念,毕竟希望美好的东西能够美好地终结,是一种人之常情。而我也明白,有运气相遇的人未必永远好运相伴,我看子殊如人间惊鸿,我心底的浪漫可以至死不渝,却不必盼人如期归来。
我只是力所能及地想为他做些什么。哪怕他只纯粹地当我是学姐,还是个很爱碎碎念很爱管教人的学姐。
后来,或许是执念作祟,我做过一个古怪的梦。梦里有泾渭分明的两片天,子殊站在接缝处,面前是和风细雨的小院子,身后是茫茫的戈壁,空寂天地,苍蓝天幕上一轮磨砂般的月亮。
我站在梧桐细雨中,招手唤他到小院中来,他却转过身,往那片空茫的天地里去了。
我翻遍《周公解梦》,也解不出这梦境。
后来我想,这个梦或许是在告诉我,这路遥马急的人间,有些人只能陪我走过浅浅的一段。
张子殊没有参加高考。
我淡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因高考之前的一件事令我早有心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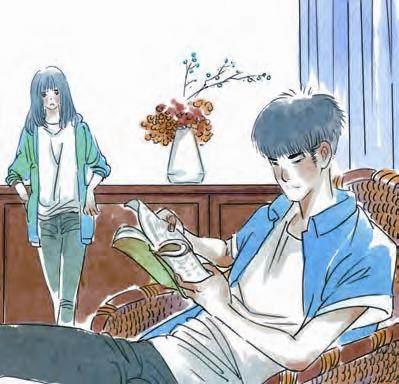
距离高考只有27天的时候,高三有学生选择了逃离。据说是因为最后一次模考成绩差,上课玩手机还被抓,班主任叫了家长来。家长在走廊“当众教子”,孩子头也不回地跑了,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这个孩子其实早有准备,在他失踪后,父母找到了他留下的一封信。他说,“现实太坚硬,我要浪迹天涯”。
我跟张子殊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叹息良久。彼时,他正捧本修真小说,霸占着咨询室的藤椅,一副退休老干部聊以度日的架势。
见我长吁短叹,感慨良多,他引哲人慧言来劝我:“何必为生命的片段哭泣,我们整个人生都催人泪下。”
我叹气:“现在你们这些高中生心理也太脆弱了,这种动不动就逃避现实的孩子才应该来做心理咨询。”
我以为他会以高中生的视角来反驳我,控诉一下教育体制、高压应试或者家长问题,熟料他嗤之以鼻:“对啊,太脆弱了。慈悲不渡自绝人。”
我诧异。
“另外,你叫谁孩子呢?他跟我一样大。”他似乎对这件事更介意。
我笑道:“那你也是孩子。”
一个白眼扔过来,他说:“姐姐你才比我大一岁,倚老卖老什么劲?”
我纠正他:“一岁半。”
他又白我一眼,看起来不太想继续理我的样子。
我赶忙问:“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是学习压力太大吗?”
张子殊终于正眼看我,合上书,道:“赌气,兼愚蠢。殊不知多少人想好好上学读书,都还没有机会呢。”
子殊说,这赌气出走的少年,是盲目轻率,以己胁人。他不是不知道父母爱他,而是太知道,所以他拿这种爱作为报复的武器。他不知道,选择从最熟悉的生活中消失,是没有意义的。父母再怎么懊恼,世人再怎么议论,对他来说还有意义吗?坚持,或者说勇敢面对,才有意义。他只是一时冲动罢了。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有些人为了赌气就能随意抛弃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求而不得的。如果连高考的压力都扛不下去……高考而已,有什么呢?倒宁愿……

“你宁愿什么?”
我盯住他。这太令我吃惊了,他之前明明一直都是一副不想参加高考的样子,到现在手里还不务正业地捧着小说看呢!
“没什么。压力大,就不考了呗,就像我。”他话锋一转,嬉皮笑脸,回归本色。
我一字一顿:“你,真的,不打算考了?你父母,也放任你这样?”
“他们不管的。再说吧。”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高考结束之后,子殊消失了一段时间,回来时整个人黑了瘦了,给我带了和田枣和葡萄干。
炎炎夏日,我想不通他是搭错了哪根筋,非要在这么热的日子里出游,还要去新疆,还是穷游。
他给我讲这趟新疆之旅:为了省钱,住最便宜的旅馆,条件非常差。墙在中午是烫的,夜晚是冰凉的。运气不好的時候会断电,水压也不稳定。白天走在路上,太阳像熔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晒得人头晕目眩,看天地都在慢慢地旋转。黄昏来了,风大的时候,沙子会静悄悄像粉一样撒进窗户。夜来了,断电的时候就点上蜡烛,看它的眼泪流淌成什么形象。不过呢,新疆的天空非常高远,云也白得无瑕,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适合做些尘世之外的梦,还是值得一游的。
我毫不怀疑,子殊此人,是个表面懒散而内心执拗的人,他这一趟是在做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
我本想问他,要复读吗?可看着他,却问不出来。
他骨骼的棱角更分明了些,眼睛显得更亮。眼底眉梢,有一点类似生机的东西,像野草,从精致里拓生出一种荒蛮——于是精致便有了别样的韵味,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从野草和腐烂的荒蛮里诞生出来的。
这样执拗而浪漫,大约自有计较。
我是在一个秋末的早晨,失去了张子殊的消息的。
前一天,子殊最后一次来咨询室,跟以往没什么不同。他下午三点左右来,看了会小说,陪我插科打诨,五点半咨询室关门下班,我们一同离开。
从咨询室出来,日已西斜。往常,我们会一同走一段,出门左转,穿过校园,我回学校宿舍,他回家,前半段路是重合的。
可那天,他出门就往反方向走去。
我问:“你要去哪里呀?”
他并不停步,也不回答,只笑着挥手:“我们不顺路了哦。”
很平常的挥手,就像之前的每一次“再见”。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次,他是打算再也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起了大雾,雾气把世间万物吞噬,留给我一个浓白如混沌初开的天地,能见度不足五米。我等雾散后才去咨询室待了一会儿,子殊没有来,我想他可能有事吧,估计明天能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都没有来。
他再也没来过。
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意识到事情不对。这个人,从咨询室的日常里,从我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那天就是告别了。其实真正的告别并没有长亭古道,没有斜阳芳草,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模一样的黄昏,有的人留在了昨天。
我想起那天子殊离开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那是一条没有内容的短信,只有一个句号,孤零零地悬在对话框里。
我觉得可能是不小心摁错的,便没有理会。
我呀,真是后知后觉,居然许久之后才发现,那其实是有意义的——一个句号,一个终点,一个告别。
我慌张地跑去问心理咨询老师:“子殊,那个张子殊,他究竟是什么心理问题?”
老师自然比我知道的要多,也明白得要早。她大约从子殊消失的那一天起就了然于胸了。
她终于肯告诉我。
“子殊不希望别人觉得他是个病人,所以我答应他不告诉任何人。作为一名绝症患者,他一直想知道,当一个人年纪轻轻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在人生起步时就看到了终结,该怎样与自己、与死亡和解。”
张子殊是脑胶质瘤患者。脑胶质瘤,一种极凶险的恶性肿瘤。
我立马上网去查了这个病,只看了几行字便满心绝望。
“最常见的颅脑恶性肿瘤,好发于青少年,恶性程度极高,死亡率高,发病至死亡病程短,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
我走出咨询室所在的小院,抱膝在院子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梧桐叶子落得只剩光秃枝丫,指向漫天云霞。对面是往老菜市场去的路。香火店的屋檐下缭绕着烟,扑进早冬的冷气里,白茫茫的,又被捎着热的暖光融去了。
放学的孩子脚步杂乱,把被树影割开的夕阳踩得更碎。三两个凑到铺子前头买吃食儿,或彼此追逐着跑上石阶,任暮光把小小的人影拉长。
我的耳中万籁俱寂,眼前光影如走马,都是很平常的景象,我却仿佛今日才第一次看到。
我找到张子殊的时候,他在市中心医院的病房里,穿着病号服,剃光了头发,让人有点认不出。
老师说过,他不想让人来看他的,老师想来探望他都被明确拒绝了。
可我还是来了,突兀地、没有礼貌地、未经允许地来了。
子殊见到我,很诧异。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是笑笑,将手里的果篮放下,泪水就这么一点也不听话地、汹涌地流了出来。
子殊嫌弃道:“你知不知道,你哭起来的样子真难看。”
我用手背擦一把泪,佯装自己并没有不知所措。他指了指床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来。
阳光那么好,那么暖,铺满了椅背,坐垫上都是融融暖意。我一点一点陷下去,第一次觉得,温暖也可以令人窒息。

子殊的膠质瘤位置不好,靠近脑干,无法手术。自确诊至今,已经有8个月时间。这种肿瘤扩散迅速,没有可靠的治疗办法,预后很差。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就与死神相望,日子要按月按天来计算了。
放疗和化疗是目前已知的对延缓病情有确切疗效的治疗方法,但因每个人体质不同,对放疗手段和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所以治疗效果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看运气。
疗效是需要看运气,但治疗对于剩余生存质量的摧残性打击却是普适性的。用过放疗和化疗药物的病人,普遍痛苦、虚弱、并发症多,总之,不再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了。所以,张子殊拒绝治疗。
他说他其实害怕医院这个地方,怕一旦住进来,就走不了了。他在网上查了很多病友的经历自述,发现有好多人,都是住院的时候以为只是短期住一下,没想到直至生命终结,再也没能走出医院半步。
他不要这样。所以在与家人爆发过无数次争吵抗争之后,他走进了老师那间心理咨询室。
他更愿意用这些时间,尽可能停留在正常的生活里,去交谈、去旅行、去无所事事地虚度些时光。
而现在,是不得不……
他已经出现了癫痫症状,大约是瘤体太大,压迫到某些重要的神经。他会在半夜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翻滚到地上拼命抽搐,吓坏了家里所有人。
一次,两次,三次……于是他知道,终于,拖不下去了呀……他是该住进来了。
而今,医院窗下明媚的阳光里,他笑望着我:“真感谢遇到了你们。这半年时间我过得很好。咨询室外的植物葳蕤漂亮,气味好闻。那张藤椅很舒服,适合晒太阳。老师开导我的话都很有用,你看我这么久才发病,像一个奇迹。”

没有了头发的他,憔悴的苍白的他,笑起来竟还是那样好看。明眸皓齿,温柔缱绻。
子殊说:“剩下的日子,我会好好地配合治疗。”
我不知道自己又哭了。我觉得这个阳光里的少年大约不属于这人世间,所以做好准备要回他的天国去了——这么美的少年,是俗世难留的惊鸿。
他拿着纸巾拂上我的脸,有点无奈:“你还学心理学呢,你这菜鸟也太菜了,典型的人菜瘾大。一看就是个不称职的心理咨询师。”
我握住他拿纸巾的那只手,细瘦,修长,骨节分明。大约是太瘦了,握着都觉得硌人。
他没有抽手,静静地任由我握了一会儿。他似乎湿了眼眶,却没有流泪:“不过菜有菜的好,我蛮喜欢。”
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恍惚了,只能回忆起散乱的对话碎片。
我问他:“疼吗?”
子殊说:“头痛啊,很痛。”
我明白,那是一种非常残忍且剧烈的疼痛。我张了张嘴,想要告诉他:痛就让大夫给开镇痛药。都到这时候了,还管成不成瘾吗?即便成瘾,又还能用多久呢?
我畏惧这样的直白,于是话到嘴边,变成了:“坚持一下,会好起来的,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看到他强撑的熠熠的神色暗了下去,我心头猛然一悸,几乎要咬了自己的舌头。可话已出口,咽不回去。
我知道,他已不想再听鼓励的话。
他当然不是第一次听到鼓励,可能他从第一天得病的时候开始一直听到今天,所以他实在不想再听了。
鼓励的话其实是非常带有社交色彩的,一旦说出了鼓励的话,很多真心话你就说不出来了。
子殊也知道,我来见他,抑或他见我,很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的,可我说出口的却是:“没事,等你出院了,我们再去干吗干吗……”这话一出口,原本的心里话就说不出来了,因为这些话给他、给我、给我们一个“还会再见”的虚假的期许。
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却谁也不会再去戳破它。
这些话堵住了他的嘴,很多话他就不会说了,而这些话也堵住了我的嘴,因为他不说那些话,有些话我也不能说。
我后悔了,话音未落便后悔了。还是太晚了。
可我除了这个,除了这个,还能说什么呢?那些在心底盘桓很久的东西,似乎也不宜说。
所以话未尽,意已非,唯有沉默。
我给子殊削了个苹果,他摇头:“苹果看起来真不错,但我其实吃不下。”
我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的杯盖上:“那等你一会儿有点胃口再吃。”
子殊向我展示他最近在读的书,娓娓道来,说这本书不算有趣,但有句话他很喜欢,大意是这样的——当陪你的那个人要下车时,即使你再不舍得,也要心存感激,挥手告别。每个人的故事,开头都是极其温柔,但往往故事的结尾都配不上这个开头。只好把每一个意难平的结果,都当作我们最好的结局。
我不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是的,我不想知道。
就这样吧。
子殊将那个削好的苹果切成两半,自己拿起一半咬一口,另一半递给我:“谢谢你啊。”
单位的同事大姐居然真的去打听了周启,结果令她觉得惋惜。
周启有个从大学开始就交往的女友。
“你看人家优秀的小伙子都有主了,你也得抓点紧啊……没事,丫头,我再打听打听,有好的就帮你介绍介绍。”同事的热心有增无减,情绪似乎更加高涨。
“那谢谢您费心了。”我客气道。
周启有女友?这我倒是没料到。
那天离开医院的时候,我走在队伍末尾,跟周启前后隔了半步。周启紧走几步,与我并肩,问:“之前光忙里忙外,都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周启,你呢?”
“林繁。”
“哪个繁?”
“繁花的繁。”
“好名字,好听好记。”
医院走廊很长,阳光比来时更好。当年子殊看我这名字,皱着眉,嘴损得很:“白瞎了你两个字的名字,用这么复杂的字,试卷上写名字都比别人耗时长。”
原来温柔与温柔,还是不一样。
“方便加个微信吗?有空请你吃饭吧。”周启转头看着我,那双眼瞳仁颜色很深,神色温和,如漾波光。
如若子殊能如常长大,这样的脸,这样的神情,该引得多少女孩芳心暗许啊。
医院门口的台阶不长,几步就下到底了。我掏手机的动作犹豫了一秒,只一秒。我说:“不了吧,谢谢。”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人也不会有机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拿记忆与现实交相映照本就是幼稚的痴人说梦,既是对回忆的消磨,也是对现世的不公。
时隔多年,我又去了子殊安眠的墓园。
独自走在安静的墓园,我心里已能夠保持宁静。这里比想象中静谧得多,墓碑干净,洒扫齐整,显然都是有亲人在用心维护。
小时候我很怕鬼,长大后就不怕了。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教育令我相信了这世上本没有鬼,而是我明白了,坟地里你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想见却再也见不到的人。
子殊的墓也被维护得很好,墓碑无垢,碑前插花的瓶里换了水,似乎有谁不久前来过。他的父母对他一直很上心。
我想跟他说说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有时会觉得,在我十九岁到二十六岁这段日子里,时间好像被偷走了一部分。上个季节还没来得及过去,就被推搡着走到了现在,一切好像刚刚睡醒,刺眼的光照进来,我就变成了现在的我。
我该如何,向停留在十八岁的你,讲述一个二十六岁的我呢?
直至离开墓园,我片语未言,只留下一束花。
是夜,记忆千里迢迢赶来——
晚修停电的夜晚,星星比平时更亮;
午后闷热的时候,打开窗等风来;
院子里的梧桐细雨,淅沥打湿了一夏;
少年从走廊的尽头,漫不经心地走来。
人说,年少时不要遇见太惊艳的人,不然往后余生全是遗憾。我懵懵懂懂走进了这往后余生的年年岁岁,遗憾或不遗憾,其实说不清楚。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编辑/梁宇清
1599501705277
——以广西高校为例
——以长沙职业技术学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