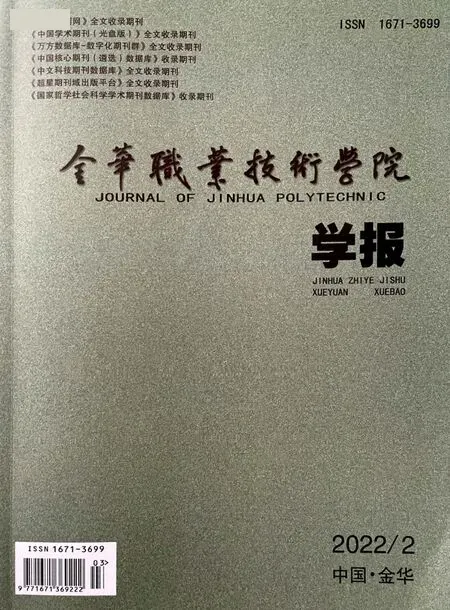浪漫新编与复仇路径:重读《复仇(其二)》
孙士棋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故事原型中作为爱与牺牲者的耶稣,却在鲁迅笔下转变成了复仇者。复仇作为一种行为,应该具有主动性并要求实质性地完成这一动作,但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似乎并不存在这一动作。尽管《复仇》中也缺少实质性的复仇动作,但“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两个人终于“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使看客们“干枯到失了生趣”,从而以间接的“杀戮”实现了他们的复仇。而在《复仇(其二)》这一标题下,却只有对于人们钉杀耶稣的过程和耶稣所感到的痛苦的描摹。
耶稣因何复仇,向谁复仇,如何复仇,复仇的意义如何,构成了这一文本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而在这一基本结构背后,贯穿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传统与文学资源。作为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拜伦,也曾改写过圣经文本并盛赞过前人的改写。他自二十世纪初被绍介进中国以来,便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07年发表《摩罗诗力说》到1925年的《杂忆》,鲁迅始终对拜伦保有强烈的兴趣与关注。他对拜伦式摩罗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考察复仇内在生成路径的基本语境,而《复仇(其二)》与《圣经》所共有故事内容的异同,则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浪漫传统:摩罗精神与拜伦文学资源
尽管鲁迅从未明确提及作品中的“他”是耶稣,但不难看出这一故事取材自《圣经》。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在内的“四福音”中,耶稣受难都是一个核心情节。有学者通过文字对比后指出:“鲁迅用《马可福音》作底稿,进一步编修了《复仇(其二)》。”[1]两部作品除了存在文字上的异同,鲁迅的选择在思想内容上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四福音书”因为所预设的目标受众不同,所以在主题上有不同的侧重点,而《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耶稣乃神之子。杨剑龙先生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显然是将受难的耶稣当作‘人之子’描绘的,他关注的是耶稣身上的人性,而非神性。”[2]29因而,鲁迅一方面对人物原型“进行了再创造,突出了耶稣受难时的心理感受和复仇心态,塑造了一个为民众而献身却不为民众理解的孤独的英雄形象”[2]26,另一方面“反对基督教的原罪、宽恕、神迹等教义,却十分推崇基督充满着爱与牺牲的救世精神,这构成了鲁迅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的因素之一”[2]30。可见,鲁迅笔下的耶稣与其故事原型共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境界。同时,鲁迅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这更具有一种人格的自我投射,但这样也使“复仇”两个字的含义无法落实,从而造成形式与内容上的悖反。“复仇”作为本篇的题目对作品具有一定的总括性的意义,是对作品所要传达的核心意义的精炼表达。而“爱与牺牲”虽是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思之一,但是从对《圣经》原型的类比中得出的,如果鲁迅所要表达的只是“爱与牺牲”,那么显然与作为题目的“复仇”是相抵触的,因而鲁迅注入作品中的含义必然会更多一些。尽管鲁迅使用了《圣经》的故事原型,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外框架,在精神内涵上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甚至重铸。而以拜伦为首的浪漫主义诗人或曰摩罗诗人,恰巧也曾进行过类似的文本试验。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盛赞过摩罗诗人,希望将摩罗精神引入国内,他这样写道:“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3]68鲁迅认为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人具有一种在“秋肃萧瑟”中敢为新发声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这是一种“争天拒俗”的伟大之力与雄伟姿态。因而,这种打破传统、振聋发聩的宏声令假面下偷生的渺小庸众感到恐怖,急于避而远之,甚至对英雄群起而攻之。在拜伦身上,鲁迅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契合感,更感受到了一种感同身受的不为群众所理解的孤独感。但鲁迅也对拜伦的形象进行了一种创造性改写:“在对拜伦基本生平史实的译述中,鲁迅是要祛除拜伦的贵族身份并突出其海贼的家族背景,带来一股平民化的草莽气,以此来应和‘摩罗诗人的’的呼声。”[4]与此相类似,他也盛赞拜伦对《圣经》故事原型进行再创造的试验精神:“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3]79
正如鲁迅盛赞拜伦敢于对《圣经》人物原型进行再创造的精神,拜伦也认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是《失乐园》里真正的英雄,由此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恶魔传统”。实际上,就弥尔顿的创作实际情况而言,他笔下的撒旦并非是一个所谓的“史诗英雄”。他的意图在于通过一个虚伪的、本质是恶的、言过其实的撒旦来衬托并体现上帝至善至公的光辉形象。正如莱肯指出:“在16、17世纪的英美国家,圣经主要是基督徒作家和读者人生中的宗教权威性著作。至于作家们采纳的文学用法,乃是从对待圣经的这种宗教态度中流溢出来的。时至18、19世纪,对圣经的宗教理解逐渐消减,相应地,圣经通常被文学家仅仅视为一部文学著作——自然是宗教文学著作,而非一部圣书。”[5]对于弥尔顿来说,他的《失乐园》不仅直接取材于《圣经》,并且后者也是他作品意义的来源,因而它的美学形式是与其神学意义相统一的。但对于拜伦来说,《圣经》已经失去了它的宗教意义,只要它能够有效传达自己的理念,便与其他各种故事原型并无重大区别。换言之,他笔下的圣经故事尽管还保留着《圣经》中主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但其美学形式及精神内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用自己的精神气质将这些故事原型同化,因而都颇富“拜伦气质”。
对于鲁迅来说更是如此。他不仅从拜伦以高扬的摩罗精神注入圣经故事和各种前人作品及其形象的试验中受到启示,也将自我的精神气质投射到拜伦身上,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鲁迅拜伦”现象,并从中学习并掌握了一定的“故事新编”的方法和技巧。从鲁迅对于《摩罗诗力说》的珍视及他一生中对拜伦的推崇备至,可以看出《摩罗诗力说》及摩罗精神同《复仇(其二)》具有一定的潜在联系,且很可能成为鲁迅的一个写作资源。
这种依托于“五行”学说,同时援引阴阳理论的占术在星占文献中也有体现。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以五行学理论为基本框架,但在“金星占”论及战争胜负的判定时,占文将一个月分为阳、中、阴三旬,又依据列国之南北相对位置赋予其阴、阳属性,如此则时、空属性相合者为利,相犯者为伤。显然,“阴阳”在这一占法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可以说,从春秋末期至汉初,“阴阳”对于“五行”说的影响似有愈加见重之势,至少在传世的战国秦汉五行学文献中,“五行”多扮演支撑文本结构的功能,而“阴阳”往往才是判定吉凶的关键。究其原因,则与战国中后期“五行”说与时月令文献的广泛融合有关。
二、“故事新编”: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转化
“作为文学的圣经”的文字和叙事在整体上具有语言简单、细节精炼的特点,能产生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美学效果。“四福音书结构相同,其目的是为了让耶稣受难(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系列细节动作)成为故事发展的最终高潮”[6],这意味着有关耶稣从出生、死亡直到复活的叙述并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简单叠加,不论它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层,是为指向耶稣受难这一核心情节服务的,而其中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则在于它的神学意义,即上帝通过这件事来昭示自己。
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他以具有摩罗精神的主体投射对耶稣受难的故事原型进行改写,从而改变了它的美学形式和精神内涵。首先,鲁迅将耶稣的受难从一系列事件中截取,并把耶稣从众多人物中突显出来。一方面,他删去《新约》中富于神性的耶稣的降生和复活及其所行的神迹,突出耶稣作为“人之子”的身份。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转变为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猜疑、憎恨,乃至毁灭;将一种荣耀的神性之美转化并渲染为一种人的悲剧之美。另一方面,在耶稣受难这一具体事件中,他又删去了彼拉多及其为耶稣所作的辩护,意在说明耶稣确实无罪,以及耶稣以无辜之身献身的神性、爱的胸怀;删去之后,更能体现出作为整体的人群与作为个体的耶稣之间的对立,突出耶稣的孤立无援以及人群的人性之恶与嗜杀本性。正如鲁迅所言:“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细看。倘若不懂,可以想想福音是什么体。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8]
其次,鲁迅笔下的耶稣受难被强烈的感情色彩所充盈,具有很强的感官刺激,产生了特殊的视觉、听觉、触觉与感觉效果。与《马可福音》中长句和短句的夹杂使用相比,鲁迅将原型故事中对外在动作的叙述性描写改写为几个连续的短句;不仅添加了耶稣的内心感受,并将这一心理描写处理成长句子,从而激化了外在动作与内在心理的冲突。
关于兵丁戏弄耶稣的部分,《马可福音》里的处理较为细致,长短句夹杂,是一种叙述性语言: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吐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7]61
鲁迅则删去了部分细节,将句子缩短并变成一种“蒙太奇”式、动作与动作直接组接的短句: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9]178
同时,这也与对耶稣的心理描写所使用的长句形成了对比。越是节奏短快、鲜明、跳跃,具有某种旋律感的外部动作,越是能衬托并突显耶稣内心的痛苦与孤独,以及他此时心理活动的深沉。这样一种悖反式的感觉描写,也更加突出了耶稣与人群的对立: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9]179
相比在人群中的孤立与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疼痛当然柔和得多。这样一种行刑时“丁丁地响”的音响效果,与灵魂在痛苦中的独白相互交织并强化,产生了一种诡异且富有魅力的艺术氛围。正如詹姆士·里德在《基督的人生观》中谈及基督的受难时指出:“在这不寻常的死寂般的宁静中,一连串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诅咒、冷笑、嘲笑、狂笑。对基督富于情感和敏感的心灵来说,一句冷酷的话对他就是一次无情的打击,更何况这么多的冷嘲热讽。正是他自己的人民把他送上十字架的,又给他增添了这样的痛苦,而他们正是他竭尽全力去帮助和拯救的。他为他们奉献出了自己。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基督已经进入了我们人类所有痛苦经验的最深处。”[2]27如果说这还是通过“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式的个人想象来补白《新约》叙述性语言所给出的“空白点”,那么鲁迅则用自己的笔,绘制出了一幅令人身临其境,满含血肉感的耶稣受难图;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又与《复仇》中那场无形无声的“杀戮”不同,仿佛一场神秘而迷人的布道。
如果说酒神精神意味着在痛苦而不囿于痛苦的兴奋与迷狂中,获得一种生命的狂喜与飞扬,那么鲁迅笔下的耶稣,正是在这样的大痛苦中,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与精神的升华,从而获得一种作为“人之子”的崇高主体性;与此同时,这样并未将耶稣与庸众悬隔成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在让耶稣“悬在虚空中”,感到深深“仇恨”的同时,也“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正如丁帆先生所指出的:“作者试图用一种难以言喻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毁灭的情绪来阐释一种对人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生命哲学批判。鲁迅的悲剧观一直是建立在对人与生命的肯定基础上的,他往往是通过否定的形式,在对人的劣根性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来肯定人和生命之本体的。”[10]鲁迅从对自我“痛得舒服”与对庸众的毁灭性冲动的“仇恨”的否定之否定中,获得了一种对生命的肯定。肉体的痛苦提醒着人性的存在。鲁迅越是强调个人的痛苦与毁灭,以及庸众对个人所带来的痛苦与毁灭,越是能突显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并热切地希望这种能量能够转化成每个个人与集体的力量,从而获得个人与民族生命的更新。
最后,鲁迅将耶稣的行为从上帝的叙事法则中剥离出来。在《圣经》中,耶稣的献身既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上帝的意志。比如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7]60鲁迅则将耶稣处理为一种完全是出于个人意愿的,如同在萨特式“极限境遇”中做出自由选择、孤勇的英雄主义者,“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9]178,“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9]179。这里鲁迅使用了“自以为”,从“自以为神之子”到“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暗示了一种狂人式的月下觉醒与其后的幻灭。在耶稣受难的故事原型中,他的确是神之子,人类所犯下的罪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他没有人有资格实施救赎,因而他主动去背负十字架。另一方面,对于法利赛人在内的人来说,耶稣是被送去钉十字架的,“因为他们说:‘他说僭越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在这一反对的背后是旧约的一个核心信念:只有上帝能够赦免罪。除非耶稣是上帝,否则他就没有权利说这话。他要么是在骗人,要么是犯了亵渎的罪。”[11]因此他们要把耶稣送去钉十字架,在他们眼里,后者是被送去的,是一种被动性的行为。
在鲁迅的笔下,从“因为”到“所以”,通过微妙的字句上的强调,删除了神性而只保留人性。在前半句中,作为动因的“自以为”突显的是耶稣选择献身的决定之不受外界影响的主动性;后半句则凸显了这一主动选择的后果。换句话说,耶稣之献身,既不是因为上帝的引导才去救赎人类,也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有罪,于是要被送去钉十字架;而是无论如何,他都具有一种拜伦式的如同主动献身希腊民族的摩罗精神。这样,鲁迅就完成了对圣经故事的摩罗化改写,将一种摩罗精神贯注到耶稣这一人物原型的胸中。
但是,鲁迅又感到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于是,当鲁迅本不怎么相信,但受时代氛围和他人的鼓励才终于燃起“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而几乎就要相信一种神性时,这种炙热、高涨的甚至是浪漫的主体精神,突然遭遇冷漠、平庸、丑恶并且一成不变的现实时,难免生出“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的如梦方醒的幻灭感。他不仅回复到原有的“确信”中去,并且产生一种想要“复仇”的冲动。鲁迅说:“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2]“复仇”之于鲁迅的《野草》,以及他的许多作品都有着重要的主题级意义。可是鲁迅虽然赞赏拜伦本人所具有的摩罗精神,但他并不赞同拜伦笔下那些虽然勇敢却也孤独忧郁以至于沮丧而离群索居的“拜伦式英雄”,也更不会“对谁都开枪”。他的“复仇”显然具有一种更复杂的生成路径。
三、“憎的丰碑”:复仇策略与主体性反思
首先,鲁迅的复仇当然是对庸众的复仇。但如果仅根据“个人的自大”与“合群的自大”的矛盾关系来解释文本,庸众与先知就成为了两个机械且孤立的方面。更何况在表面上,文本呈现出的只是庸众对先觉者的迫害而非后者的复仇。复仇的完成必须放在与前文本的异同之处中考察,是通过对受难故事内在逻辑改写达成的。耶稣的复仇并非对于庸众肉体或精神上的实质性报复,而是表现为更为形而上的方式。在《圣经》中,作为神之子的耶稣,以自己绝对的义,流自己的血和水,来洗刷不义人的罪。但是,鲁迅笔下被人们钉死的耶稣,终究是人之子而不是神之子。那么,不仅人们原有的罪孽不会因他的死而获得救赎,并且要因为钉杀了人之子而使原本沾满鲜血的双手更加罪恶:“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9]179正如鲁迅所言:“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13]人们杀死了作为先觉者和改革者的耶稣,以他们现在的无知和残暴,证明了自己是毫无前途的。
其次,鲁迅的复仇是一种对“寂寞为政”的天地与麻木无知状态的复仇。耶稣以自己敏锐的感觉,见证了周围并非绝对的虚空。鲁迅抓住了耶稣信心动摇的一瞬间,并将其作为抒情的中心。疼痛与悲哀,以及悲痛到极点之后冲决而出的呐喊,打破了无声的麻木。这既是对上帝或曰命运的反抗,也是在平庸的生命状态与蒙昧的庸众中区别自己的绝望的反抗。鲁迅笔下的耶稣具有一种自毁式冲动,他以自己之必死证明上帝之必无;上帝在离弃他的同时,也实现了他对上帝的离弃。他明知前面是十字架而偏要去钉,而既钉十字架,又不为庸众所理解,于是加倍感到“遍地都黑暗了”的悲哀;因而他以“遍地都黑暗了”的决绝态度,对天地人事全都施以“一个都不宽恕”的报复。如同为“熔岩一旦喷出”而“无可腐朽”作“见证”的野草,鲁迅以这种个体的疼痛与自毁见证了自我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是对寂寞且麻木的世界与庸众所施的强烈否定。在《圣经》中,使徒们也是见证者,见证爱的大能并以此传播爱的福音;那么,鲁迅的耶稣则是一座“憎的丰碑”,以对当下的仇视,想象另一种未来。换言之,是以这种自毁式的受难,呼唤另一种“有”,又或者正在来临之中更大的“无”。
最后,鲁迅的复仇是一种精神对肉体的复仇。正如有论者从佛教视域出发所指出的,生命的苦痛如同重负,使精神无以升华,正是在对肉体的折磨乃至终结中,才能获得精神真实活着的感觉,“当精神在刹那间结束了肉身的生命延续,苦痛势力便失去了他肆虐的对象,为苦痛所折磨而又无法可想的精神便以最极端也最简捷的方式复了仇,生命本身的意义也就达到了飞扬与极致,于是便有了大欢喜”[14]。但是,这样的复仇也可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即肉体的本能冲动向精神提供了所必需的能量,“精神所无能为力的是:自己创造或消除任何本能的能量。但不仅这个发自精神的压抑,而且那个最终目标,也是某种积极的东西:内在的自由及自足变化和获得强力及行动——简言之,赋予精神以活力。只有这才理所应当地称得上生命向精神的升华——然而却不是那个据说创造出新的精神品种的神秘过程”[15]。在基督教的视域中,精神无法与肉体截然分离,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精神无法超拔肉体而存在,它们要么相互促进或相互阻碍,要么只能共同走向毁灭。在鲁迅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更为紧张的精神同肉体的相互冲突。他以一种近乎不断剥夺肉体的冷酷方式,借以使精神达到几乎可以弃绝肉体的存在。但是,由于鲁迅并不相信存在一种终极性的超越,认为前路的终点只能是“坟”,也即是说一种必然消亡的肉身存在。那么,精神不断剥削肉体,以求速朽的结果,只能是失去了肉体的精神也就无处依附,导致精神同肉体的同归于尽。
然而这三个方面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它们是一个由外部世界向内部自我回收的动态过程。不仅如此,在鲁迅对耶稣受难故事进行浪漫新编的背后,反映出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整个“五四”前后始终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浪漫气质,拜伦和普罗米修斯,则因充分体现了文人学者对这样一种盗天火向人间的启蒙精神、社会责任感与浪漫气质的向往,成为了他们的自我期许与精神写照。鲁迅就像他眼中的拜伦一样,将摩罗精神灌入到圣经故事中,并将自己的主体投射到耶稣身上。鲁迅不仅为整个文坛,也为自己的转向与如何“故事新编”,即为政治立场的转变与创作方法的更新,提供了可行的视点与路径。“……在对基督教以致一般的宗教精神加以肯定时,他已把基督教普罗米修斯化了。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又力图把耶稣基督彻底地历史社会化——耶稣不过是历史英雄而已。”[16]“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耶稣播种上帝之爱;天神因其为人世盗火而惩罚普罗米修斯,上帝却通过耶稣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以便把自己的爱全奉献给大地。”[16]477
鲁迅笔下的耶稣,正因为一种“争天拒俗”的精神,而有了同具有浪漫色彩的普罗米修斯相融合的倾向。但是,也必须看到,鲁迅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既不是耶稣为全人类作牺牲的神性的荣耀之美;也不是普罗米修斯宁愿忍受永罚也要盗火的悲壮之美;鲁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共同点:独自献身且不为群众所理解的孤独的悲哀;在创造性改写完成后,“爱与信仰”或“爱与牺牲”的主题发生了偏转与变异,“憎与怀疑”从这一故事中内部地生成了。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具有原型性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鲁迅从《摩罗诗力说》时期开始,就潜藏着“由来已久的虚空感、爱的无力感以及无法挥去的懊恼感”[17],那么这种仍在“地下运行”的“鬼气”,必然随着社会环境与个人心态的变化而逐渐喷薄而出。鲁迅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衰变提供了可观察的轨迹。
《野草》作为处在鲁迅过渡时期的作品,即从启蒙道路向革命道路转向的转捩点上的重要作品,《复仇(其二)》则揭示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与其说鲁迅是转向了革命道路,不如说是基于启蒙基础上的发展。他从未放弃过他的启蒙立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并且具有一种发扬踔厉、敢为新声的摩罗精神,只不过如他自己所言:“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哪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18]他始终携带着一种“两间余一卒”的孤独感与挥之不去的“鬼气”,在“遍地都黑暗了”的悲悯与仇恨中,不停地向他的另一种“坟”走去。
这种具有感伤气息的浪漫精神看似与启蒙的理性精神相抵触,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将自由意志作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支点,那么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情感等对实现一个自律的创造的个体生命而言,都不具备完整的本体价值,它们只有被纳入自由意志的塑造中时才是有意义的”[19]。在此意义上,当一切外在价值都失效时,鲁迅并没有陷入渺茫与虚无,因为他把个人意志作为原点与归宿,最终完成了由启蒙他者向自我启蒙的转变。因此,鲁迅的复仇既是指向外部世界的否定,也是指向过去和自我的超越,并在这场复仇中迎来意志更为坚定的新我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