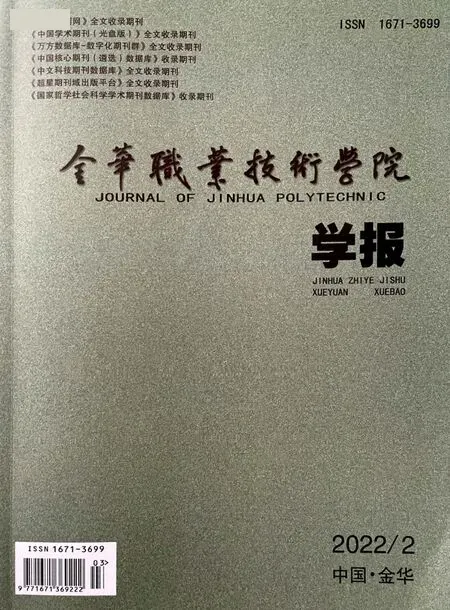家与国:论老舍的国民性批判与建构
——以《四世同堂》为例
俞佳宜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
二十世纪以来,以家族为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对国民性展开思考的也不乏其人,而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亦是其中之一。小说以北平一个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为透视点,把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兼顾十来户邻居,透过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不幸遭遇,揭示战争带给人们的物质创伤和精神创伤,同时挖掘传统文化影响下保守苟安的国民劣根性,从而反思重建民族和国民性等问题。而与其他家族小说不同,老舍先生是在由战争导致的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反思家族文化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在反法西斯侵略、期望世界和平的伟大主题之外,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老舍先生对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本文以家族文化为切入口,重新审视《四世同堂》,首先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贤母良三种伦理表现先生对传统家庭的眷恋,其次分析祁老人、瑞宣、冠晓荷等人物形象以揭示国民性改造的迫切性,由“家”至“国”最终上升为对重建国民性的思考。
一、眷恋:家庭伦理的传统选择
相较鲁迅、巴金、曹禺对封建家庭、家长专制的激进态度,老舍先生则是情不自禁地对四世同堂式的传统家族亲情流露出依恋之情。在老舍先生笔下,“家”不是年青人以出走来反抗封建家长的精神炼狱,也不是逆子以自我沉沦的方式来仇视父亲的荒原,而是一个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伦理的和睦家族。在《四世同堂》中,我们能看到慈眉善目的家长、愚顺可嘉的儿子以及操持家务的贤内助,看到一个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气息的温馨家庭。
(一)父慈子孝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为核心体系,而“仁”则是儒学的基本观念。“仁”作为五常之首,被具体放置于家庭中则衍化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观念,因此慈父孝子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理想的人格形象[1]。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家庭的长者,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已不再是巴金、曹禺笔下的专制家长,而是一个温厚、慈祥的传统理想家长。他对孙子瑞全未经自己允许就离家抗日虽有不满,但更多的是担心瑞全的安全;他对于小顺子和小妞子所表现出的淘气、过错也表现出无限宽容。另外,祁老人的儿子祁天佑也是维护家庭伦理的代表之一,即使生意惨淡到无法继续经营,他仍不忘筹办父亲的八十大寿。祁天佑既是祁老人的儿子,也是大家庭的长者。他虽然在思想上与子辈存在代沟,但与祁老人一样并不是专制的家长。当得知儿子瑞宣因辞掉英文老师的工作而减少部分收入时,他不仅没有责怪瑞宣,而且还认为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着分寸[2]。祁天佑一方面作为儿子,孝敬父亲;另一方面作为父亲,疼爱儿子。可见祁天佑与家人是相处融洽的,正是慈父孝子形象的代表。
总之,作为四世同堂家庭中的长者,祁老人、祁天佑二人与各自子女之间的关系不是“君臣父子”式的等级关系,而是相互关照、理解的亲情关系,这也正体现了老舍先生对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优秀伦理的认同。
(二)兄友弟恭
兄弟姐妹长期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相互帮助、互相信赖的骨肉之情。如孟子所言:“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3]兄弟间就应该相互关爱、友善相处。在现代社会中,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已逐渐被以父母、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但老舍先生仍对兄弟之间那份互敬互爱的情感流露出眷念之情。
《四世同堂》中温文尔雅的祁瑞宣,既孝敬父母又对兄弟宽厚忍让。他与三弟瑞全之间更是有着强烈的默契。瑞宣先是帮助瑞全离家去报效祖国,在弟弟回来之后又与其密切配合,为地下抗战提供情报。对待二弟瑞丰,瑞宣更是表现出一再忍让,他不但没有责怪瑞丰在自己被日本人抓去时对自己的避之不及,反而在家境困难之际主动接纳了因丢官而落魄回家的瑞丰。可见,瑞宣作为长子所表现出的对弟弟们的疼爱和怜惜。瑞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毫无怨言地将家族的一切责任扛在自己肩上。他的身上鲜明地表现出老舍先生对兄友弟恭式的传统家族伦理的眷恋,以及对家族观念、宗法伦理的强烈体认。
(三)妻贤母良
老舍先生在《小人物自述》中写道:“对于那不大会或不大管家事的妇女,不管她是怎样的有思想,怎样的有学问,我总是不大看得起的。”[4]这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老舍先生对传统贤妻良母的喜爱与赞美。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是传统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她平凡普通,每天关心的不过是些柴米油盐般琐碎的家务事。然而正是她默默无闻的付出,一家老小才能在战乱年代得以平安地生活下去。在老舍先生看来,韵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皆因她是一位传统的贤妻良母。“唯其因为她心中装满了家长里短,她才死心塌地为一家大小操劳,把操持家务视成无可卸脱的责任。这样,在国难中,她才帮助他保持住一家的清白。”[5]971在老舍先生看来,这正是在中国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传统女性的优秀美德。
由此,老舍先生通过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贤母良式的传统家庭关系的描绘与展现,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传统家庭、和谐人际关系的深刻认同与眷恋,并借由对和谐家庭关系的追求,进一步上升至对国家和国民性的思考。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所谓“齐家”就是要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家齐”之后才有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可能。可见,老舍先生在反思因战争而映射的国民劣根性之前,率先展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选择和青睐。
二、批判:国民性改造的迫切性
由于长期处于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已沉淀在国民的心中,并通过国民的言行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前文的描述表现出老舍先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依恋,对受满族文化熏陶的老舍先生而言,这些都是耳濡目染的家庭观念。但当民族危机来临之时,老舍先生又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化所带给自己的矛盾,于是采取了温情的批判,借文化来审视国民的病弱。
(一)家族礼教的维护者:祁老人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祁老人作为祁家的最高代表,虽不再是封建专制的家长形象,但依然是固守传统礼教的典型。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到人生态度,他始终表现出因循守旧的一面,是儒家“中庸”“平和”的文化所铸造出的顺民、庸民的代表。
国难来临时,不管外面的战争进行得怎样,他仍想着如何庆祝自己的寿诞,认为只要存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便足以避难。当胖菊子向瑞丰提出离婚时,祁老人表示绝不答应,因为在他看来离婚意味着“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5]697可见,对于外来的侵犯,祁老人只会用“破缸顶上大门”[5]691,而对于家里的变动,他坚决守住四世同堂的堡垒,深信自己有把控的能力。
保守妥协、苟且偷安是以祁老人为代表的传统顺民的典型性格。当国家遭遇危难时,他们是愚昧胆小的,对国事是漠不关心的,一心只想着建构自己小家庭的四世同堂。这里,老舍先生通过呈现以祁老人为代表的家族礼教维护者的愚昧、麻木的生活态度,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家”本位的封闭与落后,以及国民在森严秩序压迫下形成的奴性。
(二)新旧思想的彷徨者:瑞宣
在太平时期,祁瑞宣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过新式教育,原本可以做一个慈父、孝子,维系家庭的稳定。但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机使这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在传统“嫡长子继承制”的规训之下,作为长子的瑞宣无奈卷入了在“家”与“国”之间痛苦抉择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作为家中的长孙,他必须承担起照顾家族的责任;另一方面,当国难来临时,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年轻一代,他苦于家族的束缚不能抛开小家为国效力。因此他彷徨、自责,日军侵占学校时,他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愤然辞职;他到处搜寻抗战前线的消息,因听到抗战的广播而兴奋;他帮助弟弟离开北平去抗战,鼓励周围的人逃走。可见,他是一个有气度、有文化、为国而忧的新式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囿于家庭的桎梏之中。
老舍先生一方面对瑞宣正直宽厚的品格给予充分肯定,表达了对传统伦理的欣赏;另一方面又对孕育瑞宣此性格的宗法文化表示强烈的批判。在民族危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用“爱克斯光”[7]透彻地审视了瑞宣身上所凝聚的传统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揭示出改造传统文化的迫切性。
(三)卖国求官的投机者:冠晓荷
此外,老舍先生还塑造了以冠晓荷为代表的卖国求官的投机者形象。在民族危难之时,他们为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既没有家庭的责任感,更没有为国捐躯的勇气。老舍先生正是通过这一类民族渣滓来批判他们骨子里的封建文化“官本位”思想。
日本人刚到北平时,冠晓荷就看到了“乌纱帽”在向他招手。当他得知邻居钱家二儿子钱仲石准备借着给日本人开车的机会,将车开下山洞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时,冠晓荷趁机向日军告密以求立功。他对于钱家的家破人亡没有丝毫愧疚,反而为能在日本人手下谋得一官半职而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官”与“钱”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逢遇到日本人他总是毕恭毕敬,无比虔诚,就连日本人问他对于自己妻子“大赤包”死在日本人监狱中这件事是否觉得反感时,他仍旧“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道:“你们给我一个官作,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5]901甚至在被日本人活埋的那一刻,他仍坚持称日本人是自己的“朋友”。老舍先生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国家、亲情观念淡漠,以作汉奸为荣,专注个人享受的民族渣滓,来批判封建文化腐殖下的病态社会与病态人物。
老舍先生通过上述三种类型的人物,完成了对传统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无论是保守懦弱的祁老人、犹豫彷徨的瑞宣,还是卖国求官的冠晓荷,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传统文化束缚下国民性格弱化的局面。他们皆囿于个人或小家,没有上阵杀敌、为国捐躯的意识和勇气。于是,老舍先生暂时搁置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留念,迫切地提出改造国民性这一话题。
三、建构:重建国民性的可能和路径
冯友兰先生认为:“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8]《四世同堂》正体现了“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9]。“家”中孕育出的长幼尊卑、责任担当等诸多伦理准则,在民族危亡之际唤醒了民众心中“国”的意识。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在现实社会中重建国民性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一)如何可能——潜藏的国家意识和隐现的理想国民
祁老人的“四世同堂”理想贯穿始终,瑞宣新旧思想的矛盾时时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得以传达,瑞丰、冠晓荷、蓝东阳等投机者的塑造更表明了国民思想的羸弱和缺陷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境地。国民性改造迫在眉睫,通过群体觉醒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10],老舍先生传达出国民性依然有重建的可能。
面对丁约翰下达的示好日本人的命令,白巡长坚决地拒绝:“无论怎么说,咱们是中国人。”[5]1074天佑太太宁愿卖房也不肯向日本人屈服,她说:“咱们死,也死个清白!”[5]1025当为日本人做事的胖菊子提着礼物来到祁家时,祁老人不顾“四世同堂”的理想,在门口拦住胖菊子并大声喊了一句“滚!”可见,向来讲究和气的北平人在面对侵略自己国家的日本人以及卖国求荣的投机者时,虽没有上阵杀敌的勇气但也还没有愚蠢、懦弱到去巴结和讨好的地步,而这恰恰是潜藏的国家意识的体现。
除了揭示潜藏于国民心中的国家意识之外,老舍先生还在两个理想的国民身上发掘了重建国民的可能。钱默吟本是一位只知闭门读书、饮酒栽花的诗人,但经过日军占领北平、儿子牺牲、因冠晓荷出卖遭日本人酷刑等一系列的遭遇后,他从孤僻清高的文人转变成地下抗日的战士。他脱去长衫,戒茶戒酒,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发传单以鼓励每一个中国人站起身来反抗外敌。同样,年轻人瑞全受新文化的熏陶,毅然走出小家,放下书本拿起刀枪,来到黄土地与抗日乡民融为一体。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指甲缝中的黑泥以及鞋子上的灰土,他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骄傲,甚至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也应有几个”[5]990。从一个在“家”受到庇护得以安心读书的青年,到走出家门成长为一个为国效力的硬汉,瑞全身上寄托了老舍先生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二)怎样建构——传统文化的现代烛照
老舍先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既未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也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是在中西文化相互参照的基础上,指明了建构新型国民的路径[11]。正如老舍先生在《文博士》中所写:“这点调和的精神仿佛显出一点民族的弱点:既不能顽强得自尊,抓住一些老的东西不放手,又不肯彻底地取纳新的,把老旧的玩意儿扫光出尽。”[12]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扫光旧的,取纳新的”才能清除传统文化接受中半推半就的妥协心理,才能重建国民性。
钱先生在与瑞宣谈话时说:“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会变成人的累赘。”[5]628于是,他自己从一个只会饮酒栽花的诗人转变成一名投身抗战的战士;而瑞全在面对国家责任时毅然抛弃小家,积极投身抗战,不惜杀掉自己曾爱过的招弟,只因她日本特务的身份。钱先生和瑞全的转变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和内在逻辑,现实依据就是国耻和家仇,而内在逻辑则是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传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13]。由此,老舍先生在固有的文化体系内部找到了一条重建国民性的道路。
同时,老舍先生的五年留英经历使他在作文化对比的基础上,自觉地以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批判与认同的文化主义者的关照视角[10]43,审视传统文化的保守与封闭。《四世同堂》不仅表现了战争的罪恶、日本军的野蛮,更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用开放的眼光、反省的方式,看到了日本民族的优良品质。小顺子和小妞子因得到了油条和烧饼而欢天喜地,而日本邻居家的小男孩在亲人阵亡时规规矩矩地立在门外,不哭不闹。在这里,老舍先生肯定了面对死亡时日本人表现出的冷静和严肃,并将之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哭天喊地的状态相比,他不禁感慨:“中国人会毫不掩饰地哭。而日本人,连小孩都知道怎么把眼泪存在心里。”[5]967日本文化中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恰恰是当时中国人所缺乏的。这传达了老舍先生的文化理想,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文化理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意识[14]。
毋庸置疑,老舍先生在对传统家庭、文化充满眷念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民族国家而言,是“灾难性的”[9],所以必须去除传统文化中麻木、苟且等糟粕,吸取新的文化观念,既看到自己的短处也看到他者的长处,传统文化才能除旧纳新,国民性才能得以重建,中华民族才得以新生。
四、结语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先生真实还原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动乱及北平小羊圈居民在帝国主义入侵下所处的“惶惑、偷生、饥荒”的生活现状,借此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代沿袭现象,突出了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落后保守的一面。
作品中随处可见传统家族文化对国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正是因为家族观念早已深深刻入国人的骨血之中,所以国人在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难时依旧倾向于固守、自足。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传统文化的检讨书”[15]。老舍先生在作品中不仅讽刺并批判传统社会和国民,而且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清污与洗涤。更可贵的是,在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透露出老舍先生对重塑国民的期待,即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正确汲取外来文明的精华,在中外文化融合中重建国民性。正如书中所写:“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才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英勇和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牺牲。”[5]633这才是老舍先生憧憬的理想国民和理想文化,这个理想国民是“诗人”和“猎户”的结合,这个理想文化是和平与勇敢的连结。
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直到如今,我们依然面临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后带来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仍需思考应如何发扬自身优秀的民族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以及建立理想的国民性格。从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虽然旧文化终究要被新文化所代替,但旧文化也并非完全是糟粕。我们只有坚守传统文化中优秀、精华部分,才能在强大的文化融合之流中始终保持清醒,也始终保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