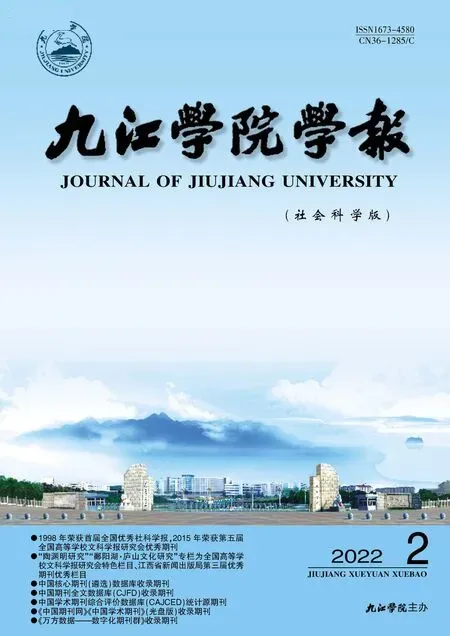从“已发”到“未发”
——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董津含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日照 276800)
《中庸》自问世以来便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其“中和”这一核心概念更是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宋代以前,对于“中和”的诠释多停留在先验之“诚”在人伦的落实这一层面上。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中和”说才迎来了突破性的解读,而程颐、李侗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和”说从程颐“已发之后求中”到李侗“未发之前求中”的内化趋势下,逐渐提升了其抽象性含义,并直接影响了后世学者如朱熹对于“中和”问题的理解。
一、“已发之后求中”:程颐对“中和”的超越性解读
宋朝时期,由于其“与佛学相对应的心性之学与修身论”[1],《中庸》一书受到了宋儒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因而在对于“中和”问题的理解上与先秦时期有着明显的改变。在这其中,最具有转折性含义的便是程颐对“中和”的解读。他不仅将“中”与“和”各自的含义作出了细微的区分,更是将“中和”上升到“已发未发”的心性论视角进行阐释。
在与其弟子的论道中,程颐对“中”与“和”的含义作出了诠释,并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之处。“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2]
程颐对于“中”与“和”的界定是从“心”出发的,即以“心”的“已发”与“未发”的状态作为标准,来对“中和”二字进行一定的评析。在程颐看来,“中”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心之“不动”,也就是在人的喜怒哀乐存于心中,还未开始发用并表现于外在的行动上的状态。而“和”最基本的含义是心“动”,即人的喜怒哀乐在已发的状态下,得以与外在事物感应通达,并依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道状态。在这里,程颐将“中和”的概念与《易经》相联系起来,并用于说明“和”如何能够融于中道的问题,但实际上程颐在此已经将“中和”二者的体用关系予以说明。并且,他在《与吕大临中书》中明确作出“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3]的判断,可见程颐已然将“天下之大本”的“中”视为最根本的本体,而将“天下之达道”的“和”视为“中”的发用处,这为他之后对于“中”与“和”的进一步剖析埋下了伏笔。
从对“中”与“和”的界定与论述来看,程颐已然将“中和”问题转向“已发未发”的心性论视角,这种转变对于之后的宋明理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程颐之后,学者对《中庸》文本的“中和”诠释基本都从“已发未发”的心性论视角进行解读,并与其动静涵养等工夫论息息相关。在完成这一视角的转变之后,程颐又进一步对“中”与“和”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并提出了“在中”与“时中”的概念。
“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既发时,便是和矣。发而中节,固是得中(时中之类)。”[4]在程颐看来,心之喜怒哀乐的未发状态便称之为“在中”,即人的主观性情绪尚未表现出来时,能够“恰如其分,无所偏倚”[5]的中道状态。那么心之喜怒哀乐的已发状态便称之为“时中”,即人的主观性情绪表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保持各得其所、处理得当的符合中道的状态。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程颐实际上将“中和”之“中”称为“在中”,“和”称为“时中”,并将二者都归结于“中”这一根本概念上。相比较而言,“在中”(即“中”)这一概念更多作为蕴含天地万物的根本定理,即具有抽象性;而“时中”(即“和”)这一概念的含义更广泛体现在人之具体实施过程中,即具有实践性。结合上文程颐对于二者体用关系的论述来看,不难看出,程颐借“在中”与“时中”的概念来对“中为和的根本,和为中的发用”这一论述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在明确“中”与“和”的体用关系之后,为求得“中”道,通达这一根本定理,程颐在“已发”与“未发”之间作出了选择,并“已然倾向于‘已发’”[6]这一向外求索的方法。
或问:“有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可也。”子曰:“求则是有思也,思则是已发也。”[7]
程颐明确反对于“喜怒哀乐未发前求中”的方法,主要着力点在于使用“求”这个字眼。“求”字本身便带有向外求索的含义,即已然倾向于“已发”状态,基于这一判断就不能再说从“未发之前求中”,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可见程颐也注意到了这一矛盾点,故提出于“已发之后求中”的方法。除此之外,程颐还提出了“存养”的方法,用于时刻从“已发”处下工夫。就像孟子言“养浩然之气”一般,通过时时涵养,则自然而然便得以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融状态。
总而言之,程颐对“中和”的超越性解读将《中庸》文本的内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以此而奠基了后学对于《中庸》“中和”说论述的基调与视角。在他之后,有众多理学家都开始重视《中庸》一书,并纷纷对其中的“中和”问题进行创新性解读,大大丰富了其中的学术价值。
二、“未发之前体中”:李侗对“中和”诠释的进一步内化
随着宋代理学的发展,学者对于“中和”概念的诠释已经不满足从“已发”的外在视角进行求索,转而向更为隐蔽的“未发”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李侗便是其中的一员。对于“中和”这一《中庸》要旨,李侗认为应当首先“体之于身”然后“扩充而往”,才能达到“无所不通”的境界,这里便可以看出李侗对于“中和”的把握完全是由内而外、自然生发的,更加注重于身心的体验。
实际上,从“未发”这一角度来对“中和”问题进行探讨并非是李侗的独创。早在北宋时期,作为程颐得道弟子的杨时因认为“中和”之道“精微隐蔽,非言语所能完全表达”[8],故将程颐的“求”中之道改为“体”中之道,以一字之差将“中和”的含义推向于更为内化的体验,并提出了“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9]的论断。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杨时的二传弟子,李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杨时这一表述。对此,朱熹在与弟子陈淳的交流中曾对此二者的观点作了一番评论:
淳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著意看,便也是已发。”[10]
朱熹认为,杨时与李侗对于“中和”的解读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杨时强调“体验气象”,在带有一定的考量成分时,实际上便已经处于“心动”之时,即“已发”的状态。而李侗强调“观其气象”,在加入一定的思虑时,便也是处于“已发”的状态,故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朱熹的这番评价,肯定了李侗对“中和”问题解读的视角是直接来源于杨时一脉的。
李侗对“中和”诠释的视角转变,除了继承杨时等学者的思想以外,更多的还是源于他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理论的深入思考。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曾有这样的论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11](《太极图说》)
在这一段中,周敦颐实际上依据《周易》这一儒家经典,结合“动与静”“阴与阳”两组范畴,对宇宙的发生过程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极”字原意为栋梁,后又引申出至高至远的标准与秩序这一含义,而“太极”便指的是最高、最根本标准与秩序。“太极”作为天道的根本,动则生阳,静则生阴,然而“动与静”“阴与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化生,这便构成了由阴阳、动静等持续流转为条件的宇宙发生论。但在“太极”之前,还有“无极”这种不具备任何形象、寂然不动的最原始动因。正是由于“无极”这种看似虚静的状态却蕴含着万千世界的生机,所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黄帝阴符经》)便是这种玄妙之处。然而即使这样,我们并不能将其论断为由“无极”而产生了“太极”,甚至于产生“阴阳”“动静”等等。实际上无论是“太极”“阴阳”“动静”等都是“‘无极’的分有和延续”[12],包括在这之后产生的“五行”“四时”乃至人伦秩序都分有了“无极”的根本属性与特质,故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萌芽。
而对于周敦颐的这一论述,李侗和朱熹曾有过一段极为详细的探讨过程。
熹疑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13](《答问上》)
在这里,朱熹将“太极动而生阳”这一论述与《周易》中《复》卦的彖辞联系起来并作了深入的思考。《复》卦上经卦为《坤》卦,下经卦为《震》卦,寓意着阳气上行、阴气顺行,象征着天道以七天为一次反复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其《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更是代表了阴阳二气反复消长,从而产生的天地生生不息的本原意志。由此,朱熹认为二者所描述的现象是没有不同的,都是阐述了宇宙发生的自然之道。但朱熹又借《复》卦对“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进行了一定的区分,认为由天地之间阳气生发所呈现的“天地之心”与阴阳和合所产生的“人物之心”应当看作这一自然过程的两个部分。而对于朱熹的这一观点,李侗给予了极为坚决的否定。
先生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今欲作两节看,切恐差了。”[14](《答问上》)
在这里,李侗将“太极”视为“至理之源”,并作为最根本的本体贯穿始终。故无论是“天地之心”还是“人物之心”都是对“太极”这一本体的分有与延续,都继承了“太极”的全部基本特质,因此并不能“做两节看”而淡化这一根本定理。故李侗提出,《中庸》喜怒哀乐以“已发”与“未发”的两种状态推之于人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了能够追求“大本达道处”,明了天理的玄机之处,就必须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并且李侗更倾向于“从未发处看”。然而,《中庸》的“已发未发”与《太极图说》的“太极动而生阳”以及《周易》的“复见天地之心”细究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李侗认为“不能用言说人的未发已发之概念来把握‘天地之本源’的‘动而生阳’和‘复见天地之心’”[15]。
虽然李侗在“中和”问题的诠释上要求从“未发之前体中”,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已发”状态的全面忽视与否认。为使得喜怒哀乐等主观情绪得以“发而皆中节”,李侗提出了让心时刻保持“虚一而静”状态的方法。
李先生曰:“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16](《答问下》)
李侗认为,“心”在“中和”之道与人本身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它贯穿了人得以通达天理这一过程的始终,并为人得以使喜怒哀乐等主观情绪“发必中节”,从而体验“中和”之道提供了可能和方法。这便从侧面指出了其本体论与心性论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心为“实”,便会被物欲所牵累而动,那么污浊之气便有机可乘,从而不能达到“发必中节”的超然状态。因此,只有拥有虚静之心才能够通达明理。然而,虚静之心并不代表完全的“空心”,并不代表没有一毫思绪,只是要求此心在任何时候不可轻易波动。此外,在保有虚静之心的基础上,更要时时反身修己、爱身明道,守住这一虚静之心。只有这样,喜怒哀乐才可“发而皆中节”而不至于为其他所左右。
至此,李侗对于“中和”探讨的视角已经基本转变,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内化了对“中和”诠释的深度。然而,在完成这一视角转变之后,李侗并没有将它仅仅停留在心性论意义上的抽象层面,而是致力于寻求“未发之中”的洒落气象。
三、“体验气象”:李侗“中和”说的探求目标
在明确以“未发”的视角来审视“中和”问题之后,李侗将其由较为抽象的概念化解读开始转向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实际上,李侗“中和”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为如何”[17],这也是他为什么致力于将程颐“已发之后求中”的理论进一步内化的原因。李侗把“中和”概念放到了“未发”这一更为抽象的层面,实际上更加突出“心”这一更为精妙的作用。如上所述,只有将“心”时刻保持在“虚一而静”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中和”的通达之处,才能从“静”中寻求“自然中节”的洒落气象。这不仅是李侗所追求的,更是后来很多宋儒都致力于寻求的超然境界。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气象呢?李侗提出的第一种方法便是持守敬心,使它“渐渐融释,使之不见于有制之外”[18]。李侗认为,人之洒落气象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长时间地持守涵养,逐渐使得自身与心不为外物之事所累,也就是“融释”的境界。而最需要如此持守涵养的便是“敬心”,这与程颐的“持敬”思想不谋而合。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虽然李侗对“中和”诠释的视角与程颐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侗依然深深受到程颐理论的启发与熏陶。而在“持守敬心”的基础上,李侗又提出了“心与气合”的概念,这实际上便是一种从“知言”上所求的工夫理论。
先生曰:“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差。”[19](《答问上》)
在这里,李侗以孟子“养浩然之气”为例进行说明,而孟子在“养气”一章中对“浩然之气”的界定是非常丰富的。有学者曾经指出,孟子对于自己理论中的“浩然之气”“平旦之气”以及“夜气”都是与“仁气”“义气”以及“礼气”等概念相互呼应的,且这些都属于“德气”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达方式并不代表这些品质本身就属于“气”这一概念,而是指这些品质“与气融为一体时在行为者身体上所呈现的一种实然状态”[20]。具体到李侗的表述上来说,“心与气合”中的“气”便指的是浩然之气,也就是“仁”这一抽象本体与本然之“气”相互融合而生发的虚静状态,而人所涵养的“持敬之心”则要在通晓他人言辞的基础上与“气”交融,从而得以见到洒然自得的纯粹气象。我们不难发现,李侗“心与气合”的“养气”论虽然建立在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无论是其理论内涵还是发用处,都比孟子的理论深了一个层次。孟子的“养气”论最终目标是为了求得仁义道德,而李侗则通过强调心与气的交融过程从而对不偏不倚、至中至和的洒落气象进行体认,可谓用意深远。
除此之外,李侗提到的另一种得以见此气象的方法便是拥有“遇事无滞”的超脱之心,使得身心得以无所障碍。
庚辰五月八日书云:“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心阔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道理一贯。若见事不彻,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21](《答问上》)在这里,李侗明确地提出,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时,人应当存有开阔明亮的洒落之心,并能见得各事的本质所在,才能做到此心不被任何事物所妨碍,从而符合无所偏倚的中和之道,方可最终达到洒然融释的超然境界。细细品味,李侗这一气象工夫与华严宗的“四法界”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华严宗将对世界不同层次的理解程度分为四种法界,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分别代表了世界现象与本质之间不同的圆融关系。而李侗的“遇事无滞”的理论与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法界有相同之处,即万千事物都与其本质相互交融,互为存在的依托,但因为此心已然明了事物的本质,故二者各自存在却无所碍滞。从这里便可以看出,李侗的这一气象工夫从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教的相关理论。
从“已发”到“未发”,无论是程颐的“已发之后求中”思想还是李侗的“未发之前体中”理论,二者对于“中和”的诠释在宋代《中庸》研究的长河中留下了精彩的一笔。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领军人物,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想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而李侗虽并未建立起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中和”思想依然深深地影响了诸如朱熹等后学对《中庸》的诠释,故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