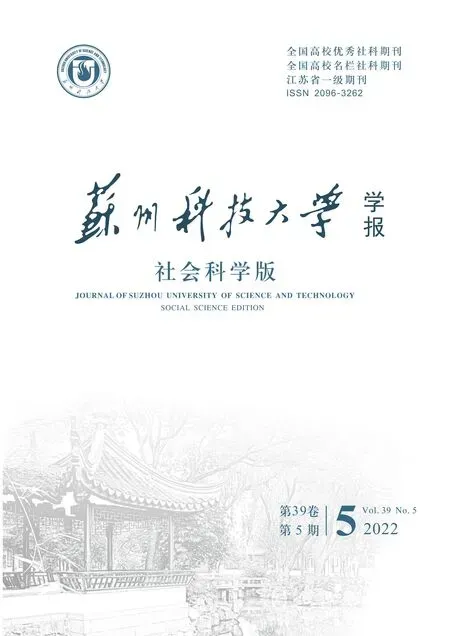章太炎佛学思想中的人性研究*
朱 浩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人性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哲学思想中具有特色的一个重要议题。到了近代,面对社会危机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正确认识人性,如何改造人性,并使之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崛起的不竭动力源泉,则成为当时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对于人性命题探讨的初衷。纵观章太炎探讨人性的诸多文字和论断,其中不仅折射出他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深邃造诣,而且体现出他力图从改造人性入手,以探求近代化本质的尝试。恰如姜义华先生所说:“章太炎从《菌说》到《辨性》的人性学说发展演变过程,不仅表现了章太炎本人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个人的洞察力、创造力,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他从中吸取乳汁与营养的中国社会以及二十世纪帷幕方揭的世界所蕴涵着的内在矛盾。”[1]从《菌说》到《辨性》是章太炎人性思想从初生到走向成熟的完整阶段,也反映了近代先进的中国思想家不断探求救亡图存的心路历程,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反复思索其中的奥义,以还原历史发展的本真。
随着学界有关章太炎思想各类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他的人性理论也得到广泛的关注。有学者在充分研读了章太炎于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的《五无论》后,提出章氏的人性观点本质,就是以“五无”为代表的“自我解脱的出路”[2]。蔡志栋先生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五无”论的提出是“对基于真如哲学的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彻”[3]。张立文先生在《章炳麟的唯识哲学》一文中则从“俱分进化”的视角畅谈章太炎的人性观,论证了“人性善恶的起始是兽性”的论断,体现出“进化必有所处,而后能进”[4]的观点。
约言之,上述研究成果的出发点各自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几位学者都没有深入章氏人性思想产生的理论根源,即从佛理角度论证其人性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也就不能全面和准确地领悟章太炎伦理思想的真实内涵。
一、章太炎由佛学审视人性的动因分析
章氏对佛学的接纳经历了一个过程,正如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所说,“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待经历了“《苏报》案”后,在东京期间才广阅唯识经典,参之以西学论著,佛学修为才有了很高的提升。[5]165章太炎重视宗教的作用:“凡诸宗教,过弛则风节衰,过张则职业废,吾所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兰若。”[6]396从中可知,宗教的价值需要重新予以估量,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宗教在激发民心士气、提升人们道德修养中发挥的作用,以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这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意义非常明显。
近代佛学走出了“末法”时期的衰落,成为无数思想家的理论武器。这绝非偶然,其中佛理主张内省,关注人性问题的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佛理在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影响力着重表现在它的教义之中,正如章太炎所说:“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6]273佛教的影响力遍及上智、下愚,反映出其教义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能够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接受。这其中既有玄思意味浓厚的中观、唯识思想,也有贴近于世俗的净土、禅宗理论。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只是追求信徒的信奉和顺从不同,“佛经不过夹杂几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6]509。一方面,章太炎指出了佛理中的宗教气息;另一方面,他更希望信众能够主动地从本我的视角思索宇宙、人类的本质等问题,以获得纯粹的真知,而不是仅仅囿于佛理的说教。这也是章氏从佛理角度思索人性,乃至借助于佛理思索其他哲学命题的根源。
在谈佛理的数十篇论文中,章太炎认为,在门派众多的佛学诸家中,只有在伦理道德方面有助于明心见性者,才能有助于改造国民的秉性和振奋民心士气。葛兆光先生指出,佛学理论在中国思想界长期保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其“不仅有坚实的依据和细密的理路,而且要从中推导出实现人性圆满境界的程序与方式”[7]。中国的佛学思想倡导“依自”,重视内心的修养,强调凭借自我的克制,主张透过纷繁的表象世界探求意识的本真——“如来藏”。这个过程既是宗教精神的要求,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实践的现实方法论路径。章太炎说:“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6]274由此可见,在章氏的道德哲学体系中,佛学带来的启迪关乎人性的思索。虽然他后来对华严宗不乏批判之语,但仍旧肯定了该宗倡导的“普度众生”和“仁者爱人”的成佛精神可以激发人们的善性;而法相宗劝诱人们只有认清诸“相”,才能领会“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的道理。这更是期待人们能够不被通过眼耳鼻舌所获得的表象之知迷惑,勇于探求真正的人的本性,以实现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
二、章太炎之佛学思想中的人性观念
人性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儒家哲学中心议题之一,还在佛学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就前者而言,儒家思想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辨不时成为思想家谈论的重点;自后者言之,无论是印度佛教之空、有二宗,还是中土佛教中的各派,均留有大量有关人性问题的探讨性文字,以供后人参悟。章太炎的佛学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关人性问题思索的方法、结论,同时他还加入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和想法,这些使得其佛学思想呈现出独特的风采。
善恶两端是探讨人性的核心议题之一,章氏佛学思想中的较多内容都是围绕这个议题展开的。何谓性呢?章太炎说:“性即众生心,人有心而不自见,犹不见其手足百体也,聋盲不泰甚乎!虽然以心求心,无有少法,能取少法,所见者但其影像耳。犹有性者存乎吾心,则未离见相二取,而所得皆幻也。”[5]86性即心。也就是说,原初之心体即人的本性,而人性之说就是在探求人们最初的本心。我们不需要在心体之外苦苦思索人性的内涵,只需返回本心,就能够知道人性的真正含义。一些思想家脱离本心,盲目求索“性体”“心体”,最终只是体认到人性的表象,而未能触及其内涵。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概念尚不具备寻常所言的善恶两端的道德评判标准。“人心虽有非善恶的妄见,惟有客观上的学理,可以说他有是有非;主观上的志愿,到底不能说他有是有非。”[8]16在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是非与善恶的概念,实则是一种“妄见”,也可理解为“萨迦耶见”,其并非源自本来的“性体”,而是在经历各种杂染之后产生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判断。
章太炎在研究佛理后意识到,佛教哲学中的诸性概念与人性之说的本旨相距辽远。佛学主张的人性更像是精神驱使之下的“悟性”。在康德哲学中,“悟性”强调的是先天的“知”对于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理性的真正目标,就它是实践的,即能够影响意志的这方面来说,必定是要产生一个本身是好的意志,而不只是作为别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才是好的意志。”[9]简言之,理性不应当是虚无的存在,而应当体现在对人们意志的影响。这种理性作用之下的“好的意志”,可以引导我们领悟世界的本质,不为种种经验得出的表象所迷惑。反观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发展历程,在最初的《菌说》中,他明确提出:“彼无善无恶者,盖佛之所谓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6]137紧接其后,章太炎指出:“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6]137“性海”指代理性的汇聚处,并非人性。只有当理性经过“六道”辗转,被认识者证得后,方能被称为人性。这句话中的“六道”已经脱离最初的含义,代表理性驱动之下的意志力,它可以在认识活动中不断地透过复杂的现象世界获得对世界本质的认知。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才能真正领会人性的含义。在肯定了人性的理性主义特征的同时,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性并非无善无恶,而是善恶并存。人的性善与性恶取决于意志力的抉择。太虚说,就阿赖耶识而言,“一切种子,都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种子是所藏的,阿赖耶识是能藏的处所,所以名能藏”[10]。阿赖耶识又名为“藏识”,善恶种子藏于其中,可以使人性呈现出善恶两端。与经典的唯识宗观点稍有不同,章太炎强调了意志的作用,分析了意志在人性善恶间的抉择过程。“以藏识为性者,无善无恶者也;以藏识所含种子为性者,兼具善恶者也。为不善必自惭恨,斯曰性善矣。”[5]83这句话不仅肯定了唯识宗对于人性问题的一般性观点,还提出了意志力具有本然的判断能力——“为不善必自惭恨”。由此可见,章太炎立足于佛学思想探讨人性,并未如佛理中将之归结为无善无恶,而是在肯定了人性有趋善与趋恶的同时,强调了善性有不虑而能的特征。
综上,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对于人性问题的思索,克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诸多错误认识。他明确地告诉世人,真正意义上的人性不是来自后天的经验或教化,而是源自理性精神驱动之下的意志力的价值判断。当然,这种意志力虽非绝对向善,但有强烈的善性藏于其中。
三、人性中的伪善与伪恶
伪善与伪恶的区分是中西方哲学思想中经常触及的命题。善性与恶性本是对道德人性评判的词汇,而在善恶之前冠以“伪”字,实则表明了在探讨人性问题的时候,存在诸多理论陷阱,需要详细地分辨。前文已经初步涉及伪善、伪恶的概念,但伪善、伪恶何以在人性中出现,以及对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人性产生的影响,我们却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
伪善、伪恶产生的源头需要澄清。章太炎认为,人性之伪源自性体自身。他说:“大抵藏识流转不驻,意识有时不起,起位亦流转不驻,是故触相生心,有触作意受想思五位。”[11]81人们的意识流在不断地运动着,“触作意受想思五位”实则代表意识本体的运动方式。意识本体通过感觉、直观、抽象等产生对于人性的觉解,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意识体对自身的内省。由于认识力的差异,每个人对善恶的判断自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辨析名相,而不被湮没在名相当中,从而把握住人性真实的一面。章太炎认为:“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即于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无有为有,即彼事自性相似显现,而非彼体也。”[11]75何谓“成心”呢?郭象的观点比较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12]。言下之意,心体是先验之知的来源,且能支配意识活动。由于人们的认识力受到“成心”的左右,因此不能获得对于人性本质问题的正确结论。如此,伪善、伪恶便成为人们对人性问题探讨中的两重障碍。如果认识者不能越过伪善、伪恶布下的迷阵,则人性问题的探索就无法取得突破。
伪善、伪恶的产生同样来自人们自身的“秉性”。宋儒喜谈人性,由于受到佛学的影响,“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概念因之产生。理学家对于人性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特质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从本体角度谈人性;第二个层面是从个体禀赋处言说人性。当谈及人性之伪时,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似乎也套用了这条法则。他说:“杨子以阿罗耶识受熏之种为性。夫我爱我慢者,此意根之所有。动而有所爱有所慢,谓之意识。意识与意根应,爱慢之见,熏其阿罗耶,阿罗耶即受藏其种。”[13]“我爱”“我慢”是佛理所说的“四烦恼”中的两种。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烦恼业障,是因为“阿赖耶识”无善无恶的本性受到“熏习性”的熏陶,使得认识者丧失了对本有之性体认的能力。“熏习性”如何被理解呢?它可以被认为是经验之后获得的有关人性问题的知。由此而得出的关于人性善恶的论断,就可以被称作“伪善”“伪恶”。
根据章太炎“俱分进化”的观点,进化并非尽善尽美。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善恶如影随形,伪善、伪恶在其中更被误认作真正的人性道德的内涵,正如章太炎所说:“今自微生以至人类,进化惟在智识,而道德乃日见其反。张进化愈甚,好胜之心愈甚,而杀亦愈甚。”[8]79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类,“智识”是生物和人类进化的主体。人性道德在进化中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呈现出明显退化。昔日为人性道德不齿的诸如好胜之心、好杀之心,在进化中反而被认为理所应当,且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这正是近代以来西方伦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特点,“善恶的标准应该由理解力来确立。这种理解力依照自己所确立的善恶标准,对行为的对象进行选择,确定哪些对象是可以追求的,哪些对象应该避免”[14]。该论述提出,善恶的价值标准来自单个认识者的认知能力。这就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本质,强调了认识者在善性、恶性诠释中的主体地位。在此情形下,针对善恶本性的探讨,带有很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善恶只不过是两个可以任意粘贴的道德标签罢了。反观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背景下,他并没有否认人性道德观念中的主观性因素,而是从一般的道德价值观入手,否定近代西方伦理学的说教。他明确提出:“人类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8]83人性问题的考察应当放置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命题中,以得出具有根本性和本质性的结论。
综合以上论断可知,伪善、伪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正确地认知上述概念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掌握章太炎人性思想的真正本义,以之为根基,才能进一步探究他基于佛理而提出的人性改造理论。
四、从“佛性”中探求人性改造的路径
“佛性”之说尚无非常准确的定论,今以《摄大乘论》中一句为例,简要剖析。“如是所知依说,阿赖耶识为性。阿陀那识为性,心为性;阿赖耶识为性,根本识为性,穷生死蕴为性等。”[15]从唯识论角度看,“佛性”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不仅包括从认识论角度探究人性的路径,还提出如何看待现实人性问题的方法。在晚清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思想家群体由“佛性”探讨人性的尝试,不仅仅是理论延伸的要求,也是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因为“佛教自始至终,把它的着眼点放在心性问题上”,所以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不断地努力从各种佛理之中“专注心性问题的研究和阐发,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学说”[16]。质言之,章太炎等晚清思想家的佛学理论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墨守旧说,还融合了诸多对于现实、理论的思考成果,重新构造了又一种佛学思想,其中与之关联的心性之说占据着显著位置。
章太炎的思想发展经历了由“尊荀”向“尊孔”的转变,但是荀子思想对章太炎的人性说和社会进化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在章氏的佛学思想里,特别是有关人性方面的论述中体现得很突出。有观点认为:“荀子严格区分人的自然生理之性和人的社会道德之性,认为生理自然之性是天然生成的,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道德之性则是人为(伪)之性,是后天环境教育养成的。”[17]“社会道德之性”是人们在经历了社会生活之后,经过教育、教化而形成,且为社会允许、褒奖的人性道德理念。所以,与“自然生理之性”的道德自觉相比较,“社会道德之性”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强烈的反差。从章太炎佛学思想中的诸多观点看,他的批判矛头主要针对的是“社会道德之性”,并认为这是伪善、伪恶产生的根本原因。“今之习惯,非能使天性迁移,特强制之使不发耳。谁无瞋心,谁不屠杀有情以供餐食。是好杀之习惯由性成,而不杀之习惯为强制也。”[8]73“今之习惯”指代社会存在环境下产生的“社会道德之性”。章太炎主张人类本有的道德属性不会因习惯性的道德而被忽略。正是由于习惯性的道德存在,很多本应该受到伦理道德批判的嗔言、妄杀行为,在习俗观念之中反被认为是人性中的合理存在。上述论证体现出荀学与佛学的结合。前者从人们的具体行为出发,引申出人性的弱点,但是缺乏学理的论证;后者运用唯识思想从主观意识出发,认为既存的客观世界为一种迷妄,强调以“内省主义”扑灭一切现象,以使思想者认知本来之性。[18]
相较于一般宗教辨析人性的理论和方式,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否定了原罪之说,并借以否认人性本质,即恶的说教,这是其佛学思想很有特色的部分。他说:“且世界之有善恶,本由人类而生。若不创造人类,则恶性亦无自起。若云善有不足,而必待人类之善以弥缝其缺,又安得云无所不备乎?是故无所不备之说,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8]29善恶并非上帝因人类的诞生赋予人类,而是人类在产生以后自我形成的关于伦理价值判断的一整套理论安排。作为人类自身精神世界发展的产物,宗教虚构了善恶的救赎论,以赢得信徒对于神祇的尊奉。章太炎虽否定了人性的原罪属性,但肯定了“业障”存在。他认为:“自然者,物有自性,所谓求那;由自性而成作用,所谓羯磨。故合言之曰自然。知物无自性之说,则自然之说破。或有言本然者,与自然同趣而异名。或有言法尔者,则以物无自性,一切为无常法所漂流。”[8]92佛说“自性”,即物与物之间有别的特性,或者说是本性。这是一切善业、恶业等羯磨产生的根源。“羯磨”在宗教观念中是对人性的某一种分辨,如果把它放置于法尔自然的维度审视,重新思考自性引发的各种善业、恶业,则宗教、俗世中人性本质之说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一切皆是自然中的表象存在,而不是实在。
在章太炎的哲学思想中,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色彩浓厚。更确切地说,章太炎引入佛理以阐述庄子学,也折射出他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人性的尝试。有观点指出,章氏在“谈及之所以有善有恶时”,是因为他能够“完全抛开了社会根源(特别是阶级根源),而完全把它们归因于内心(若种子,若我慢,均是如此)”[19]的活动。庄子的“齐物”思想,以近似于虚无主义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一切伦理价值观,这些对于章氏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章氏说:“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原来有了善恶是非的见,断断没有真平等的事实出来。”[8]14-15针对世俗经常谈及的人性善恶判定的问题,他又有不同的认识:“至于善恶是非的名号,不是随顺感觉所得,不是随顺直觉所得,只是心上先有这种障碍,口里就随了障碍分别出来。”[8]15庄子哲学中的“齐物”本义是,认定万事万物的差异在人们的意识中都是同样的存在,无不是由主观意志而产生的名相,人性的善恶也莫不如是。章太炎发展和扩充了庄子的观点,不赞成善恶只是名相。他肯定了俗世只是借用了善恶的名号,而未能悟出两者的本质含义。
此外,章太炎从佛学视角思索“齐物”思想,人性观念的变革着重于意识自身的反思。人们通过不断地对本性的思索,以否定一切通过善恶种子、感知器官获得的各种妄念,如是,才能真正领悟人性。章太炎晚年在论述由“佛性”出发、改造人性的问题时说:“佛法虽称无我,只就藏识生灭说耳。其如来藏自性不变即是佛性,即是真我,是实是遍是常。”[5]5“如来藏”本无生灭,只为妄念遮蔽,其所代表者正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内容。佛理的目的不是向人们述说来世的福音,而是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世界中解脱自身的烦恼,把认识者从纷繁复杂的意识、物质世界中解救出来,并向人们展示人作为人的最本质属性。“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群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8]51“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德色心”等皆非人性中的固有之性,它们产生的根源是人们未能知晓人的本性自身就已经具有一种慈悲、轻去就、众生平等的情怀,故而徘徊在世俗人性所追求的名相中无法自拔。
章太炎尝试从“佛性”中探求人性改造的路径,看似迂缓、晦涩,却能够深刻地展示人性的最本质特征,正如赖永海先生所说:“中国佛教的佛性说,就其主要倾向看,更注重心性。”[20]与印度佛教相比较而言,中土佛教由于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将理论的侧重点倾注到诸多与道德伦理相关的议题中。章太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然则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使震旦齐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尚在,不在老、庄则在释氏,其为益至闳远矣”[6]394。在章太炎看来,儒家的人性道德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其理论富有理性主义精神,却无助于激发人们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只有佛学倡导“自贵其心”,不再要求人们恪守先贤的道德法则,而是倡导发挥意志的力量,从心灵的最深处寻找到人性的真正内容。
五、结 语
佛学是章太炎思想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他肯定了佛学理论在分析人性问题时的优势——能够从人性本质入手,把各类道德观念归于现象,纳入人们的意识活动范畴。他由此主张,认识者要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努力深入善恶观念产生的根源,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人性命题,克服社会进化的两面性。“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8]6“理论极成”表彰的是佛理的精密性和完整性,在分析道德意识运动过程时,其表现得最为明显;“圣智内证”体现了佛理思索“人性与道德”等命题时的根本方法。佛理具有导人向善的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它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人们“发明真如”和“实证真如”,真正使自我领会到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一切道德意识活动的本质属性。这也是晚清时期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学在中国再度复兴的深层次动力。同时,这种复兴更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家不愿意屈就于西方道德哲学的话语范畴和思考路径,他们不断尝试在本土固有的道德哲学思想框架内架构更加具有个性色彩的伦理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