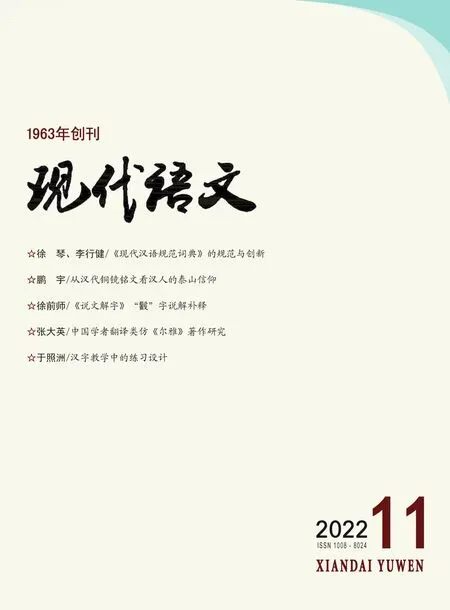语言视角下的俗字
薛 蓓
(常熟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江苏 苏州 215500)
近些年来,随着各类民间文献的不断发现,俗字研究逐渐兴盛。前修时贤在俗字的辑录、疑难俗字考证、俗字理论、字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俗字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关于俗字的定义,学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俗字的判定尚未形成公认的标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时角度,分别考察传统语文学时期有关俗字的记载、现代学者对俗字的观点,以此为基础,站在语言的立场上,探讨俗字的本质,厘清俗字的内涵。
一、传统语文学时期的俗字观念
有学者指出:“由于汉语书面语使用的文字——汉字的特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主要是抓住汉字,分析它的形体,探求它的古代读音和意义,形成了统称‘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1](P2)总的来看,传统语文学时期关于俗字的记载,大多是将某些字直接定性为“俗”,既未阐明其定性的理据,更未对俗字予以明确的界定,它主要是对用字现象的描写。不过,仔细分析这些材料,却可以窥探出这一时期是如何看待这类文字的。
(一)语言文字中的“俗”观念
语言文献中有关“俗”的最早记载,应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从角黄声。其状觵觵,故谓之觵。觥,俗觵从光。”[2](P85)在《说文解字》中,常以“俗某从某/从某”“俗某从某某声”“俗从某”的形式,指出该字的某种写法为“俗”。如:“髆也从肉,象形,俗肩从户。”“躳,俗从弓身。”共15 例。这说明至迟到东汉时期,人们已经产生了与文字有关的“俗”观念。
此后,历代字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正字通》卷三:“宂,俗从几作宂,或作冗,并非。”[3](P667)《广韵·上声》:“柁,正舟木也。俗从㐌,余同。舵,上同。”[4](P175)《字汇》首卷:“凡俗作凢……姦俗作奸。”[5](P39)这些字书,均明确标注了某字或某字的某种写法为“俗”,对单个字形进行定性。不过,它们都未解释将这些字定性为“俗”的依据是什么。
后世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俗”或“俗字”问题,并将其运用到文献校勘中。如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诗经稗疏·诗经考异》云:“‘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月令》郑注:‘觥’作‘觵’,‘万寿’作‘受福’。许慎:‘觵,俗从光。’经典不应用俗字。‘我姑酌彼兕觥’,亦当作‘觵’。”[6](P243)王夫之认为,在经典文献中,是不可能使用“俗”字形的,因此,《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中的“觥”本应作“觵”。
(二)关于“俗字”的相关记述及观念
关于俗字的最早记载,似应出自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如《书证》云:“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为必。末世传写,遂误以虙为宓。而《帝王世纪》因误更立名耳。何以验之?孔子弟子虙子贱为单父宰,即虙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7](P447)作者认为,虙、宓二字因形近而传写讹误;“误以虙为宓”“俗字亦为宓”,则说明当时“宓”作为俗字已经十分流行。在《颜氏家训》中,类似的材料还有一些,可以反映出颜之推及当时学者对俗字的认识。我们将这些材料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特殊字词考证的,此类关于“俗”的记载和分析,均与方言有关。其中,有些是不同方言区域使用不同的方言词汇来表达同一事物的,这些条目中的“俗”主要指的是方言词语不同;有些是方言中虽然有这一词语,却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字形,故另造新字的;有些则是由于方言语音不同而使用不同字形的。第二类是关于典籍讹误考证的,此类关于“俗”的记载和分析,如“俗写”“俗本”“俗儒”“俗学”“俗传”“俗之学士”等,主要是与书写者的文化水平有关。其中,有的是由于书写者学问不精而造成字形讹误的;有的是由于书写者不懂假借等规则而误解典籍的;还有的是因“俗儒”“俗学”主观臆断而随意解释典籍、增加文字的。
从中可以看出,《颜氏家训》中的“俗”或“俗字”具有两个要素:一是受到方言影响,如方言语音、方言词语等;二是文字的书写者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上述现象,颜之推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是“鄙俗”的,“此臆说也”。同时,作者也承认这些现象已成为文字使用的现实:“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7](P516)这段话说明当时俗字的使用已经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致于作者担心使用正字则无法正常交流。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颜之推主张采取“通变”的策略,即根据文字的使用语境来选择字体、字形。在文章著述这种权威性、规范性语境中,要使用正字;而在官曹文书、世间尺牍这些与世俗生活密切联系的语境中,则可以使用俗字。
在《颜氏家训》之后,也有一些古代文献涉及到“俗字”的论述。比如,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云:“矛矟:矟,山卓切。《埤苍》:‘矟,长一丈八尺也。’经文有作‘梢’,所交反,(木)名也。或作‘槊’,北人俗字也……或作‘銏’,江南俗字也。”[8](P6)这里的“俗字”,应是指同一词语因地域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字形。唐代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只如田夫民为農,百念为憂,更生为甦,两隻为雙,神蟲为蠶,明王为聖,不見为覔,美色为豔,囗王为國,文字为學。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9](P23)这里所说的“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则反映出作者对这类字体的鄙夷态度。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俗字》云:“广西俗字甚多。如,音矮,言矮则不长也。,音稳,言大坐则稳也。奀,音倦,言瘦弱也……”[10](P162)这里的“俗字”,是指为记录广西地区方言词而造的字。清代蒲松龄《日用俗字·自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11](P1)蒲松龄认为,“日用俗字”即记录日常生活的字,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为了满足“苦不能书其名”的现实需求,而造出记录特有方言词语的字;二是“点画率皆杜撰”,这是将所谓“正字”字形改造后的字。
(三)关于俗字的分类
第一次对俗字进行系统分类的,应是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12](P9-11)按颜氏所说,文字应按照使用场合区分为俗、通、正三类:在籍帐、文案、券契、药方等日常生活场合,可以使用俗字;在表奏、笺启、尺牍、判状等应用性的公文中,应使用通字;在著述、文章、对策、碑碣这类典雅严肃的场合,则宜使用正字。
按照颜元孙的分类原则,同一个字,应该具有三种不同的形体,才能满足不同使用场合的需要。实际上,在《干禄字书》中,有些字确实是三体皆有,如:皀、皃、貌,上俗中通下正;有些字仅有通、正,无俗,如:狸、貍,上通下正;有些字仅有正、俗,无通,如:聡、聦、聰,上、中通,下正;还有些字仅有正体,如:栖棲,并正。虽然俗、通、正对应三种使用场合,但现实中并没有三套字形。正字既可以在典雅、严肃的场合使用,也可以在“通”或“俗”的场合使用;不过,即使在“通”或“俗”的场合使用,这类文字的性质仍然是正字。如“栖”“棲”,无论在哪种场合使用,都属于正字。当籍帐、文案、券契、药方等场合在记录某词时,由于某种原因,采用了与正字不同的字形,这个字形就被认为是俗字;如果在籍帐、文案、券契、药方等文献中,未使用与正字不同的字形,那么这个字就没有俗字。如“狸”字,并不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中没有这个词,而是上述文献中在记录“狸”时,就是采用了正字的写法。
由此可见,在俗、通、正三体文字中,正字是文字的典范,认可度最高,可以使用在“俗”“通”的语境中;而“俗”“通”则仅能在各自的场合中使用。即使一个字俗、通、正三体俱全,正字也更具权威性。颜元孙认为,俗字是在“非涉雅言”的场合中所使用的文字,也承认此类俗字的存在,但并不鼓励使用俗字,如果能够改用正体,那就更好了。对通字的态度和俗字一样,只是承认,并不鼓励,认为到了真正写文章或者参加正式考试时,还是要使用正体的。
总之,在传统语文学时期,很多研究者均认为,俗字主要是受方言影响或因使用者文化水平不高而产生的,大多是在非严肃、非典雅的场合使用。同时,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俗字使用现象的描述,并未对俗字予以明确的界定。
二、当代学者对俗字的界定
到了现当代时期,随着各类民间文献的不断发现,俗字研究逐渐兴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关于俗字的界定亦成为研究的热点,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俗字内涵的说明;二是侧重于俗字外延的判定;三是从使用情况来描述俗字。
(一)侧重于俗字内涵的说明
这种观点认为,俗字是民间流行的,它是与正字相对立的文字。代表性观点主要有:
马叙伦:此盖由其字不见于《史籀》《仓颉》《凡将》《训纂》及壁中书而世俗用之,故不得不削,别之曰俗字。[13](P27)
蒋礼鸿:俗字者,就是不合六书条例的(这是以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俗字中也有很多是依据六书原则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认为不合法的、不合规范的文字。应该注意的是,是“正字”的规范既立,俗字的界限才能确定。[14]
郭在贻、张涌泉:所谓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正字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字体,俗字则是指在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体。[15](P235)
张涌泉:汉字史上各个历史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16](P6)
蒋冀骋、吴福祥:俗字是相对正字而言的。……俗字指那些不见于《说文》,不能施于高文大典,民间所习用的字。[17](P25)
蔡忠霖:写法有别于官方制定之正字,乃经约定俗成而通行于当时社会,且易随时、地不同而递变之简便字体。[18](P55)
郑贤章:俗字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出现在民间,多数具有简易性特点,相对正体而言的或者新造的本无正体的字体。[19](P101)
这类观点在当今俗字研究中影响最大,接受度最高。它主要是从俗字的内涵出发,强调俗字具有两个要素:一是流行于民间,二是与正字相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字”和“民间”这两个要素,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把握。
首先是关于“正字”的辨析。在上述观点中,都提到了“正字”或“正体”,如“正字的规范”“相对于正字而言”“官方制定之正字”“本无正体”等。马叙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正字,但“《史籀》《仓颉》《凡将》《训纂》及壁中书”,实际上也是颇具代表性的正字文献。蒋礼鸿认为:“‘正字’的规范既立,俗字的界限才能确定。”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与俗字相对立的正字呢?在中国历史上,官僚士大夫阶层对书写规范有一定要求。《汉书·艺文志》云:“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20](P1720-1721)《唐会要》卷七十七云:“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21](P1402)可见,无论是在学校教育方面,还是在官吏考核方面,书写(包括字体)都非常重要。因此,从理论上说,汉字应该有一套正字系统。实际上,历代并没有官方所明文规定的正字,有些字书虽然标明了正、俗,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并不属于官方字书;有些工具书虽然是官方颁布的,但对于文字的俗体、异体和正体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如《广韵》《集韵》和《礼部韵略》,虽然同是宋代官方颁布的,但由于编纂目的和使用范围不同,它们所记录的俗字和异体字亦有所差异。因此,将“正字”作为“俗字”的对立面,虽然从理论上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找到可以对照的历代正字系统。
其次是关于“民间”的辨析。在上述观点中,还都提到了民间,如“世俗用之”“平民中日常使用”“在民间流行”“流行于民间”“民间所习用”“通行于当时社会”“出现在民间”等。在研究俗字时,学界也不约而同地选择民间文献作为主要材料,如契约文书、明清小说、戏曲等。在通常观念中,“民间”总是与“官方”相对应的,就此而言,俗字在民间使用,也就意味着官方不用。不过,在部分官方文献中,却存在相当数量的俗字。杨小平指出:“流行于民间,与正字相对,已经成为判断俗字的主要标准。但是从清代手写文献来看,俗字被官方文书广泛使用,郡县官员的判案批词中出现有不少俗字,甚至官方来往的公文中也有不少俗字。由此可见,俗字并非不能应用于大雅之堂,也不局限于平民百姓使用,也流行于官方。”[22](P29)因此,使用俗字的“民间”,并不是“官方—民间”这组对应概念中的“民间”,而是应该有其他指向的。
(二)侧重于俗字外延的判定
这种观点认为,俗字是异体字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主要有:
黄征:汉语俗字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社会阶层的不规范的异体字。[23](P18)
蔡忠霖:我们也可以说一凡一字因各种因素而衍生出不同于正字的其他写法,都可称之为异体字。而俗字只是异体字构成因素之一,是异体字中一部分,虽然它也属于一种异体字,但并不等同于异体字。更明确的说,俗字是以“便利”为取向,且通行于社会的一种异体字。[18](P57)
张涌泉:凡是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都可以认为是俗字。俗字可以是简化字,也可以是繁化字,可以是后起字,也可以是古体字。[24](P6)
这种观点均从汉字形体出发,认为俗字和异体字有重叠部分,只是对重叠范围的程度看法不一。黄征认为,俗字属于异体字中的一类,是“不规范的异体字”。蔡忠霖认为,异体字包括俗字、通假字、繁简字、古今字、形误字等,俗字只是异体字中以“便利”为取向的一种字。不过,“不规范”和“便利”这两个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比较难以把握。根据相关研究,有些俗字的字形比正字更加复杂,俗字并不都是便利的。张涌泉则认为,俗字和异体字的范围基本是等同的,俗字包括“简化字”“繁化字”“后起字”“古体字”等。这种对俗字外延的界定最为清晰,可操作性最强;在整理俗字时,很多研究者也将其作为划分俗字的主要标准。
(三)从使用情况来描述俗字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文字使用者的角度入手来界定俗字,代表性的观点是:
陈五云:俗文字是正字系统的补充,是正字系统由于时代的不同形成的历时变体,是正字系统由于地域因素造成的方言变体,是正字系统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变体。[25]
曾良:一是“俗字”实际上是与“正字”相对待出现的概念。二是俗字必须被一定的人群默认使用(约定俗成)。这个群体可大可小,大可以是一个国家,小可以是某个地区;既可以是民间流行,也不排斥官员也写俗字。[26](P1-2)
这类观点一方面和第一类观点一样,指出俗字与正字相对;另一方面,则指出俗字有特定的使用场合。如陈五云指出,俗字是正字系统由于时代、方言、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变体,有其特定的使用时间、地域和文化背景。曾良则认为,俗字必须被一定的人群默认使用。关于此类观点中所提到的地域、文化等因素,张涌泉在《汉语俗字研究》中也指出:“俗文字在其流延之初,总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被使用,因而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区域特征”[24](P135-136),并引《颜氏家训·书证》“吴人呼绀为禁”为例,说明因方言语音而产生了字形变换。张涌泉还指出:“除地区性的俗字以外,各地还流行一些行业性或者团体性的俗字”[24](P138)。因此,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俗字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社会文化属性。
从现当代学者对“俗字”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从“不规范的字”,到俗字与异体字的区别及联系,再到俗字的使用,这一术语与“正字”“民间”“规范”“异体”“方言”“文化”“时代”“地域”等众多概念都产生了联系。那么,俗字为什么能够将这些不同层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呢?
三、站在语言的立场看俗字
李荣指出:“文字的基本作用是记录语言,其他作用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27](P1)张永言也认为,文字是词的书写形式[28]。站在语言的立场来看,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俗字”应当是与其记录的语言形式以及该语言的使用者有关。汉语是一种有着复杂层级结构的、动态的语言,在汉语内部存在很多变体。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汉语依次经历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现代汉语等阶段。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地域、社会文化的差异也造成了汉语的诸种变化。就地域差异的影响而言,不同区域的汉语往往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语言变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中的众多方言。就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言,主要是指说话人由于具备相同的社会属性而形成一个个群体,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相关成员会在群体内部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字进行交际,从而形成各种语言变体。
在汉语的众多语言变体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雅言。所谓“雅言”,是指在正式场合中所使用的高度规范的语言形式,它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代都将雅言作为全社会的标准语言。它一般是以某地方言为基础,经过不断规范而形成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基础方言会有所不同,但一直都是语言规范的代表,属于语言变体中的高变体。雅言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大量的经典文献,主要是在典雅严肃的场合使用,是汉语语言规范和典雅的范例,必须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才能掌握。因此,雅言的使用者一般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记录雅言的汉字也相应地成为具有雅正特点的汉字,成为汉字规范的代表。相对而言,汉语的其他变体则被排斥在典雅场合之外,主要应用于各种非正式场合,属于语言变体中的低变体,其使用者也大多没有接受过精英教育。在记录这类低变体时,书写者可能会受到时代、地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使用一些与记录雅言的正字不同的字形,由于这类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形式是非雅言的,使用场合是非严肃、非典雅的,因此,使用雅言的士大夫就将其称为“俗字”。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俗字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语言层面上的俗字;二是文字层面上的俗字。
就语言层面上的俗字而言,在汉语低变体中存在一些雅言所没有的词语,为了记录这类词语,书写者往往会采取新造字形这一方法。当汉语低变体中某词的语音与雅言不同时,书写者通常会使用更能反映实际语音的字形,如《颜氏家训》中所提到的“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7](P491);或者是根据实际语音对正字字形进行改造,如《颜氏家训》中所提到的“呼‘绀’为‘禁’,故以糸傍作‘禁’代‘绀’字”[7](P491)。汉语低变体的使用者,有时还会为了突出所在社会群体的某种文化特质,或表达某些特别的意义,而对字形进行改造。如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陶务方略”条:“景德镇陶业,俗呼货料,操土音,登写器物花式,字多俗省。”[29](P88)这些都是因为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俗字。
就文字层面上的俗字而言,汉语低变体的使用者,大多不知晓汉字的造字理据,书写时只要能满足基本的交际需要就可以,并不具有文字规范的观念。同时,由于汉语低变体主要使用于非正式的场合,书写者在记录这类语言时,主观上有时也会降低对文字规范性的要求。因此,记录汉语低变体的文字,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合规范的情况,如任意改动构字部件,随意类化、符号化,借用同音字,新造字形等。从产生原因上看,这类字虽然属于别字、误字等不规范的用字现象,但有些字形已经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在社会群体中代代相传,于是就成为文字层面上的俗字。
如上所述,由于俗字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论及俗字时,需要注意以下情况:
第一,雅言作为官方的教育工具,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记录雅言的正字,也应是全体社会成员需要学习的对象。俗字只是作为汉语低变体中的特殊情况而使用,因此,大多数民间文献仍以正字居多。李荣指出,有的人有错误的假定,以为小说一定是满篇的俗字、简笔字。就我们考察的小说而言,用字跟平常书籍没有多大差别。其中大多数字符合一般的习惯[27](P15)。杨小平也指出,清代手写文献俗字虽然数量较多,但是俗字在全部文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正字使用仍然较多[22](P47)。
第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雅言和汉语其他语言变体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者会根据交际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语言变体。雅言的使用者在某些交际场合也会用方言,写俗字,如《颜氏家训·书证》所言:“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7](P516)
第三,在语言的历时发展中,雅言和其他变体的界限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雅言可以吸收来自不同语言变体中的成分,雅言中的成分也可以进入其他语言变体。与此相应,正字和俗字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俗字可能会进入雅言文字系统而被正字体系所吸收,历史上的正字也可能会转变为俗字。
第四,汉语低变体的使用者,大多没有明确的某字应该用哪种字形的观念,只是在临文时直接选取了某种字形。这一字形可能是简化字,也可能是繁化字;可能是后起字,也可能是古体字。很难说书写者是因为这个字形具有简体、繁体或者时代的属性而特意选择了它。
第五,某类文献中是否使用俗字,主要是与这类文献所记录的交际语境有关。各种州县档案、官府文书等,从性质上说虽然是属于官方文献,但这类文献直接反映民间百态、基层情况、衙门运作等,它们所使用的语境与汉语低变体关系密切,因此,这类文献中会使用大量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