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功到立德:柏拉图论立法者教育
王江涛
提要:柏拉图把立法者教育视为实现法律统治的次好政制的关键环节。在《法义》中,他首先以克里特法律为例,分析了法治的结构性难题,进而得出结论,着眼于战争的立功不应成为立法的目标,立功立法观克服不了法治的结构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须从立功转向立德。立法者教育须以立德为价值取向,使立法者认识德性的自然秩序,形成对立德立法观的主观认同,愿意以完整德性为依据,建立法律统治的秩序。
因此,如何创制出一个法律行为的主体,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替法律应对各种突发的政治危机,成为破解法治结构性难题的关键。柏拉图在《法义》中深入分析了这一难题并指出,立法者教育是创制法律行为主体的关键,而立德又是立法者教育的中心环节。(4)本文不打算全面评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而是致力于立法者教育这一主题,关于其教育思想的综合论述,参见Christopher Bruell, On the Socratic Education,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建立法律统治秩序,要求对立法者施行德性教育,重塑其立法观,使其洞悉德性的自然等级秩序,如此方能创制出以完整德性为目标的法律,使公民“懂得如何依正义行统治和被统治”(643e)。(5)凡《法义》引文,皆引自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引文按惯例随文附注斯特方边页码,不再另注。
一、克里特法治的结构性难题
在柏拉图看来,由哲人统治的城邦之所以是最好政制,不仅因为知识比法律更强大,还因为哲人统治已先行消除了法治难题的结构性前提。正如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说,“哲人王在生存意义上与其他人不一样,因为神的秩序本身能够在他们的灵魂中实现;法可以进入他们的灵魂,以至于他们能够变成活着的法”。(6)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由于哲人统治难以实现,人们不得不退而追求次好政制——由法律统治的城邦,让统治者成为法律的仆人(715d)。法治的结构性难题这才成为摆在柏拉图《法义》面前的实际困难。
《法义》记述了一位雅典哲人与克里特立法者克勒尼阿斯(Kleinias)、斯巴达立法者墨吉罗斯(Megillus)的漫长对话。(7)关于雅典哲人的身份辨析,参见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的对话者》,《求是学刊》2012年第2期。首先,雅典哲人以克里特法律为例,揭示出立功立法观是以战争为目标,造成了法治的结构性难题。其次,雅典哲人让克勒尼阿斯看到,立功立法观实际上是以勇敢为立法目标,引导克勒尼阿斯实现从立功到立德的立法观转向。最后,既然立德成了立法的真正目标,立法者显然应确保立法的目标是“完整的德性”,而非“跛脚的德性”,仅仅追求勇敢在动机上便不再充分,追求明智、节制、正义、勇敢旋即构成了立德的实质性内容。
《法义》用克里特法律这个例子来阐明法治的结构性难题,有一定普遍性:第一,克里特法律最古老、最神圣,就连荷马也不否认克里特法律的神圣起源。虽然在古典时代,克里特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但古风时代的克里特对希腊文化有诸多贡献,在全体希腊人心目中具有特别高的声望。(8)Gleen R. Morrow, Plato’s Cretan City: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7-19.第二,克里特法律最务实,因为它以战争为依据,战争是希腊城邦世界的常态,城邦通过战争走向强大,个人通过战争成就事业。不难设想,如果连既神圣又务实的克里特法律也存在法治的结构性难题,其他任何城邦必定难逃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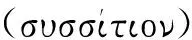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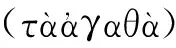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上述两个因素的深层关联,将动摇克里特法治的基本结构。克勒尼阿斯坦言,为了应对严酷的战争,克里特立法者制定了会餐、体育、武器等具体的法律。这些措施不仅约束公民的外在行为,还养成其内在品格。因为,会餐制不仅便于防卫,还创立了许多节俭粮食的办法,提倡节约精神。(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95页。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增强体魄,更能砥砺灵魂。“在那些体育运动和艰苦的训练中,他会吃苦耐劳,看重他本性中的精神力量,并且不断激发它”(《理想国》410b)。(12)译文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但是,克勒尼阿斯并未提到涉及音乐的克里特法律,一昧强调体育锻炼而忽视了音乐教育,容易使人变得野蛮、残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专门指出,一个在体育锻炼上很卖力的人,
像一头野兽凭暴力和粗野达到一切目的,生活在无知和愚昧之中,没有节奏和风度(《理想国》411e)。
由此可见,克里特法律孕育出的是一群灵魂躁动的好胜者。他们向往胜利,崇拜胜利,坚信胜利可以带来他们所欲求的所有善物(其实仅仅是外在诸善),而外在诸善反过来刺激他们的求胜欲,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永无休止的战争”中。无论是这样的个人,还是这样的城邦,他们的宿命在于打败一个又一个的敌人,直至打败自己。
克勒尼阿斯并不否认“每个人内部都进行着一场我们自己针对自己的战争”(626e)。其中自己战胜自己最好,自己打败自己最坏。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造成这种最坏状况的根源竟然是提倡立功的克里特法律。一个一心想立功的人会“像孩子躲避父亲一样躲避法律” (《理想国》548b),毕竟,受欲望统治的人哪会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统治呢?推崇立功的克里特法律孕育出否定自身的因素,这是构成其法治难题的主要原因,也彰显出立法者教育的必要性。
二、改造立法观:从“跛脚的德性”到“完整的德性”
关心立功胜于立德,是克里特立法者克勒尼阿斯与斯巴达立法者墨吉罗斯的共识。既然立功立法观存在缺陷,这意味着在雅典哲人看来,二位实际立法者“所接受的教育不够充分”,胜任不了创立法治秩序的任务,还需要像米诺斯那样,进一步接受教育。(13)Sandrine Berges, Plato on Virtue and the Law,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9, p.132.伯纳德特指出,《法义》“重构了宙斯和米诺斯之间的交谈,在这场交谈中,米诺斯不得不接受教育,以便变成一个立法者,然后他才能自由地立法”。(14)伯纳德特:《发现存在者——柏拉图的〈法义〉》,叶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页。立法者教育的出发点,在于改造二位实际立法者的立法观。《法义》第一卷分析了雅典哲人如何实现立法目的从立功到立德的转变。端正了立法目的,才有可能克服法治的结构性难题。

有德性的法官——如果终究应该有这么一个法官的话,他能接管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不消灭任何人,反而为他们的来日制定法律来调解,以守护他们彼此之间的友爱(627e-62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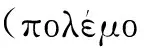
通过引述提尔泰俄斯与忒奥格尼斯两位诗人,雅典哲人推进了内省的立法视野,把目光投向公民个体的灵魂构成。虽然提尔泰俄斯表明,立功在本质上以勇敢为德性基础,但是,紧接着引用的第二位诗人忒奥格尼斯则表明,提尔泰俄斯对德性的理解颇为片面,尽管勇敢是战争中最不可或缺的品质,却并非最高品质。集正义、节制、明智、勇敢于一身的人显然好过只有勇敢本身的人(630b)。
提尔泰俄斯将勇敢与财富相提并论,肯定了身体诸善造就外在诸善的立功逻辑。提倡勇敢非但没有否定立功立法观,反而是在灵魂层面证明了立功立法观的正确性。真正的转向发生在忒奥格尼斯的引诗中。忒奥格尼斯表明,德性有高低之分。他不仅把勇敢排在四种德性的末位,还称提尔泰俄斯式的勇敢近似鲁莽,无异于一种“跛脚的勇敢”。柏拉图借西西里诗人而非雅典哲人之口,对立功立法观提出了最激烈的批评。克勒尼阿斯立马看出,这番说法全然否定了立功立法观,并且冒犯了吕库戈斯和米诺斯,因为他们在设立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法律时,主要是为了战争。于是他向雅典哲人抱怨,忒奥格尼斯的说法把他们的立法者抛入低级立法者的行列(630d)。克勒尼阿斯的抗议表明,改造立法者的立法观极其艰难,因为以勇敢著称的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会像守卫自己的财物那样守护自己的传统法律,更不会放弃这一法律的根据——立功立法观。克勒尼阿斯的抗议是对雅典哲人改造立法观工作的巨大考验,考验他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德性和政治智慧。
雅典哲人明智地指出,贬低米诺斯的不是忒奥格尼斯,恰恰是克勒尼阿斯本人,因为他误解了神圣立法者的意图。克勒尼阿斯两次断言“立法者规定一切皆着眼于战争”,可在这两句话中间,夹杂了一个不起眼的“我以为”(625e5)。换言之,立功是克勒尼阿斯自己对米诺斯立法意图的主观阐释,不能等同于米诺斯的立法意图本身。
与之相反,雅典哲人不仅没有看低克里特的神圣立法者,他同样没有看轻克里特的实际立法者。对于克勒尼阿斯的片面立法观,他不动声色地用“我们”取代“我认为”(630e),引导克勒尼阿斯超越自己的意见——把立功看作立法的目的,实乃误解了神圣立法者的意图。神圣立法者的眼光不会如此短浅,他在立法时并非着眼于德性中最低的部分,而是着眼于完整的德性或德性的样式。雅典哲人不动声色地把完整德性注入克里特法律,并声称由于这个缘故,克里特法律才会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声望极高。
既然克里特法律致力于不止一种善物,就有必要为这些善物排序。根据雅典哲人,克里特法律带来了八种不同的善物,这些善物被划分为属人之善与属神之善。属人之善有健康、俊美、强健和财富——会餐制和体育锻炼所着眼的强健仅列第三;属神之善有明智、节制、正义和勇敢。属人之善和属神之善并非按字面含义解作人的属性抑或神的属性。它们特指身体诸善,以及灵魂诸善,即德性。正如天神高于凡人,属神之善在自然等级上也高于属人之善。所以,属人之善要向属神之善看齐,而所有属神之善要向领头的理智看齐(631b-d)。立德立法观是否具有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是否一如既往地把善与幸福看作法律与德性之关系的根本”。(15)Julia Annas, “Virtue and Law in Plato”, in Christopher Bobonich ed., Plato’s Laws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9.与克勒尼阿斯对本邦法律的阐释相比,雅典哲人为克里特法律增添了灵魂之善的维度,使之更加完善。法律要使人获得幸福,需要同时着眼于外在诸善、身体诸善以及灵魂诸善。外在诸善取决于诸神的眷顾,身体诸善由自然赋予,而灵魂诸善则取决于法律的教化。
经过雅典哲人的阐释,克里特法律的自然基础从崎岖不平的自然地理变成了诸德性的自然秩序。雅典哲人小心翼翼地教导米诺斯的后人,神圣立法者着眼于善的等级秩序,立功不应是立法的目标,立法须以立德为宗旨。一方面,雅典哲人的确否认了克里特法律的立功目的,另一方面,他并未否认它的神圣性。正确理解米诺斯的神圣性,需要扭转视角,正确认识诸德性的自然秩序。
三、立法者的德性教育
雅典哲人向克勒尼阿斯和墨吉罗斯讲述德性的等级秩序时,尚未涉及此德性秩序与教育的关系。雅典哲人在概括立法者的任务时,也全然不提“教育”一词。因此,在阐明灵魂诸善乃德性的自然秩序之后,雅典哲人提议,“有必要再次从头开始”,从教育的角度探讨灵魂诸善的四种德性(632d-e),树立立德立法观。立德是雅典哲人至始至终坚持的立法者教育的落脚点。立德在《法义》中有立民德和立立法者之德二义。民德与立法者之德的差异,既牵涉到立法与立德的关系,也指向依据什么展开德性教育的问题。
教育问题贯穿整部《法义》。雅典哲人在第一、二、七、十二卷都谈论了教育问题。首先,立法的目标主要在于培养公民的德性,第七卷主要处理的就是立民德的问题。第八卷关于军事和农事的规定,甚至可以看作立民德的后续工作。其次,对公民进行德性教育,反过来对立法者本人的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观察到,“论述儿童教育的卷七不仅与卷二相协调,同时也与卷一关于饮酒重要性的论证相协调”。(16)John Russon, “Education in Plato’s Laws”, in Gregory Recco, Eric Sanday ed., Plato’s Laws: Force and Truth in Poli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1.卷一的饮酒部分虽然显得像一段离题话,处理的却是更要紧的立立法者之德的问题。欲立民德,必先立立法者之德,欲教育民众,必先教育立法者。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把立立法者之德的情节安排在立民德之前。
然而,雅典哲人欲立立法者之德之际,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尽管二位立法者对德性的自然秩序有了客观认知,但他们能否对高于勇敢的其余德性产生主观认同,还是一个未知数。立德立法观随时有滑落回立功立法观的危险。坦率地说,除了勇敢,二位立法者对德性所知甚少。除了从勇敢的角度理解立法与立德,雅典哲人似乎别无办法。所以整个讨论不得不回到勇敢,重新出发。雅典哲人与斯巴达立法者围绕各自的习俗——会饮和会餐——展开了教育与立德的对话。
在第二轮关于勇敢的讨论中,墨吉罗斯取代克勒尼阿斯成为雅典哲人的主要对话者。(17)墨吉罗斯是《法义》中发言最少的对话者,但他在第一卷共计发言23次,是他发言最多的一卷。事实上,墨吉罗斯与雅典哲人真正形成对话的部分正是他俩围绕会餐与会饮展开的交锋。雅典哲人与他达成一致,神圣立法者未曾制定一种“跛脚的勇敢”,真正的勇敢不仅仅是与痛苦和忍耐的斗争,还是与快乐和放纵的斗争。这样勇敢就暗中包含节制,在属神之善中升至次席。雅典哲人凭靠这一全新的勇敢概念,批评斯巴达的会餐制败坏了“某种依据自然的古老礼法”,因为它没有与同性恋的快乐作斗争,没有节制这种违反自然的快乐(636a-e)。墨吉罗斯奋起反击,用他全篇最长的一段发言捍卫本邦法律。简而言之,“斯巴达制定的有关快乐的法律,乃是人类最美好的法律”(637a)。因为,斯巴达立法者针对最肆心的快乐——会饮(συμπσιον)——进行了正确的斗争。他在为本邦辩护的同时,把矛头指向雅典。众所周知,会饮是典型的雅典风俗,而会饮鼓励纵酒狂欢,教人失去理智,沉溺于感官享乐之中。雅典哲人辩解道,会饮如果举行得正确,也能带来很大好处。然而,若不能清楚而充分地论述音乐的正确性,绝不可能依据自然管理好会饮;而没有论及整体教育,则绝不可能阐述好音乐。
为了正确理解会饮这一突如其来的离题话,雅典哲人顺理成章地将教育引入对话。他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第一种是职业教育,其核心在于“尽可能把孩子的灵魂从玩游戏的爱欲引领到他必须做的事情上,以使他在职业德性上成为完美的男子汉”(643d)。第二种指德性教育,“那种教育让人渴望并热爱成为一名完美的公民,懂得如何依正义行统治和被统治”(643e5)。只有后者才配称作“教育”,那种旨在获得金钱、强力或其他才智的,应称之为“庸俗的或不自由的”(644a)。教育被等同于培养德性的公民教育、进而被等同于立德。为会饮辩护,给雅典哲人提供了一个施展德性教育的绝佳机会。从主题上看,会饮似乎是最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活动,在讨论立法观的途中讨论会饮难免让人困惑。可如上所述,会饮具有鲜明的雅典性,如果雅典哲人挺身而出为会饮辩护,意味着他会像一位勇士那样守护自己城邦的风俗。富有勇敢德性的雅典哲人自然会为同样提倡勇敢的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所青睐。这样一来,雅典哲人借着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对勇敢的熟悉与欣赏,暗地里引领他们朝向更为整全的德性,便有机会在主观认同方面也实现从立功到立德的转向。
因此,关于会饮的辩护实质上是一种德性教育。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公民、立法者以及立法哲人本人都能从中受益。可以说,教育的立德功能也在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第一,饮酒训练能提升公民的节制。根据雅典哲人的讲法,会饮就像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中的交往,针对这种交往的立德具体指教人节制。雅典哲人用“控制自己”取代克勒尼阿斯“战胜自己”,暗示了这一点(644b5,626e)。控制意味着灵魂内部有多重相互对立的要素。为了帮助克勒尼阿斯和墨吉罗斯理解这一点,他讲述了一个木偶的德性神话。人是神的玩偶,体内有像绳索一样的激情拉扯着人去干相反的事情,德性与邪恶将在拉扯中各自显现。会饮相当于灵魂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强德性的拉力,抵御快乐的反作用力,避免沉醉在这种肆心的快乐中。正如体育锻炼能提高人们对痛苦的免疫力,变得更加勇敢;同理,灵魂的锻炼也会提高人们对快乐的免疫力,使他们久经考验,不会“陷入某种极不光彩的行为中”,懂得“在喝下最后一杯之前离去”,从而变得更加节制(648d-e)。“一旦学会抵制它们,灵魂便赢得了最重要、最好的胜利——战胜自己”。(18)普兰尼克:《神立法还是人立法》,林志猛编:《立法与德性——柏拉图〈法义〉发微》,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126页。它是立民德的“正确教育的护具”(653a)。
第二,谈论饮酒能使年老的立法者变得更加勇敢。除了使人节制,饮酒还有更直观的作用,即教人大胆、有勇气。克勒尼阿斯和墨吉罗斯作为立法者,本身就是守法的公民。但是,守法的节制并不造就杰出的立法者,尤其是对于寻求更好法律的立法者而言。守法固然值得赞赏,可一昧遵纪守法,容易沦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保守,这种保守亦蜕变成一种“跛脚的”节制。众所周知,饮酒能使人变得更坦率,从而摆脱习俗的约束。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立法者不能真的饮酒,因为这会让他们变得不清醒。他们必须在言辞而非在行动中饮酒,以此使他们话多;使他们年轻;使他们大胆、勇敢、愿意创新。(19)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3页。可以设想,立法者若默守陈规,不敢自由发言、不愿自由思考,立法者之德必定立不起来。只有经过饮酒教育,他们才有勇气告别有缺陷的传统神话,接受木偶神话以及神话背后的哲学基础。可见,谈论会饮比起谈论会餐更能增进立法者之德。
第三,除了立民德的节制教育和立立法者之德的勇敢教育,会饮教育其实还意味着立法哲人的自我教育。有研究者发现,《理想国》讨论最好政制以及《法义》区分最好政制与次好政制的语境,有助于我们领会哲人自我教育的意涵。在《理想国》中,最好政制与哲人统治相关,诸神并未出场;在《法义》中,最好政制是为诸神以及诸神的后裔准备的,次好政制乃是对最好政制的摹仿。(20)王恒:《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了向年轻的格劳孔兄弟讲清楚什么是正义,引入了最佳政体,通过最佳政体揭示政治的限度,由此构成反思灵魂正义的重要步骤;在《法义》中,雅典哲人没向二位实际立法者大谈最好政制,他向年老的立法者隐藏了政治的界限,仅仅满足于受法律统治的次好政制。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旨在净化格劳孔们的政治爱欲,并将他们引向哲学;在《法义》中,雅典哲人对政治并不反感,他愿意帮助年老的立法者创立新法。最重要的是,在《理想国》中排第三的节制在《法义》中升至第二,仅次于明智,而在《理想国》中居首位的理智在《法义》中的位置暧昧。(21)理智不属于灵魂诸善,只是节制跟随的目标。关于理智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牵涉到对不同抄本的辨析,参见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37页。如何理解哲学的显隐之别在《理想国》与《法义》中造就表现的差异?
或许可以说,对于理智和节制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哲人在运用理智进行哲学思考时,并不需要节制。苏格拉底曾告诉格劳孔,哲人会像登徒子好色、酒徒好酒那样沉迷于哲学思辨(《理想国》474d-475c)。这种思辨的最高境界是不受限制的思考。但是,对于非哲学的事物,尤其是政治事物,节制不可或缺。节制没有必要去限制哲人探究真理的思辨,却有必要告诫哲人,勿忘其自身的政治处境。从真理世界返回政治世界,如同从光明的洞外返回黑暗的洞穴,哲人需要锻炼自己的视力,当他从真理的光明下降到政治的阴影中时,光影的转换必定使他头晕目眩,进而导致思维的不清醒。返回洞穴造成的不清醒体验与饮酒造成的不清醒体验如出一辙:感官的模糊、思维的迟钝、言语的混乱。如果说返回洞穴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那么,这种基本特征确实由节制所主导——不留恋洞外世界,提醒自己坦然返回洞穴。正如中古哲人阿尔法拉比在疏解会饮的作用时所评论的那样:
立法者只有首先身体力行自己制订的法律,才能要求大家来实行。因为,他如果不实行他去要求别人实行的法律,而且以要求别人的东西来要求自己,那么他的要求和观点,就不会被他所要求的人良好地和恰当地接受。(22)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这段话评论的不仅是立法者,更包括立法哲人在内。立法者和立法哲人的这种节制乃实现良性法治结构的有效保证,它保证没人因肆心而凌驾于法律之上。雅典哲人心里很清楚,关心人类的诸神存在,对于健全的法治秩序有多重要。这一点尽管没有出现在扭转立法者立法观的环节中,但雅典哲人依然在第十卷以极大的耐心证明了诸神的存在。根据林志猛的看法,雅典哲人的论证充分体现出这种最高类型的节制德性。(23)林志猛:《立法哲人的虔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9页。对《法义》这部长篇巨作的深入研究和精到译注中,他有个一以贯之的线索:始终尝试在自然与礼法的张力中去把握德性教育这一《法义》的隐秘主题。他细致入微地解读了立功的立法观、善的等级秩序以及各个层级的德性,让我们更为透彻地看清立法与德性、教育、宗教的紧密关联,从而回答这一尖锐的问题:哲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何以可能成为法律的基础?
为此,林志猛在书中与施特劳斯展开深层次对话。他不是想借施特劳斯证明,立法须以善的等级秩序或自然正当为哲学基础。恰恰相反,法律统治要求理性的洞见与非理性的同意相协调,自然正当需要与神圣的事物达成根本的妥协,以便让纯粹的善转变为合法的善。真理必须转化为民众熟知并接受的意见,才变得合法。所谓“协调”或“妥协”,是节制德性的产物。由此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澄清自然正当能否成为立法的哲学基础,而在于让节制分别在公民、立法者以及立法哲人的灵魂中生成。依据自然的立法安排需要在神法中去寻找,毕竟,“神法需要人的转化和解释,以成为统治人的现实法律”。(24)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四、余论:破解法治的结构性难题
对话尾声,沉默良久的墨吉罗斯激动地请求克勒尼阿斯把雅典哲人留下(969c)。(25)墨吉罗斯上一次发言还是在第十卷891b。二位实际立法者显然感受到了立法者教育的必要性和力量。柏拉图关于立法者教育的探讨,为彻底解决法治的结构性难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思路。为了避免法律沦为统治者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必须赋予法律更权威的地位。然而,法律作为人类立法活动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立法者的意志。因此,破解法治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从根本上端正立法者的立法观。
改造立法观,需要让立法者认识到,立功不能成为立法的真正目标,因为立功着眼的外在诸善会使人变得肆心,不愿服从法律的统治。法律要想获得统治资格,应“意图发现存在的秩序”。(26)柏拉图:《米诺斯》,林志猛译,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19页。准确地说,意图发现德性的自然秩序,构成对德性的自然秩序的客观认知。不过,德性的自然秩序不能直接成为法律本身。德性要想成为立法的直接对象,需要与法律的神圣传统相结合。这样才能引导立法者对德性的客观认知内化为主观认同,认识到灵魂之善才是实现个人和城邦幸福的关键。
尽管立法者教育对实现法律的统治秩序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雅典哲人并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立法者教育就能破解法治的结构性难题。毕竟“几乎每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一开始不会接受任何法律”(752c)。亚里士多德也指出:
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2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2014年,第3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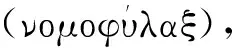
可以期待,经过雅典哲人的教育,克勒尼阿斯将从立功转向立德,成为真正的护法者。真正的护法者可遇不可求,若缺乏真正的护卫者,法律只好追求更低的德性。如果碰上真正的护法者,立法者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在这个意义上,《法义》是柏拉图的立言,它将成为立法者教育的永世瑰宝,教育那些向往公民幸福的人们,法治的意义在于让“理智捆住法律,并可以宣告它们跟随的是节制和正义,而非财富或爱荣誉”(632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