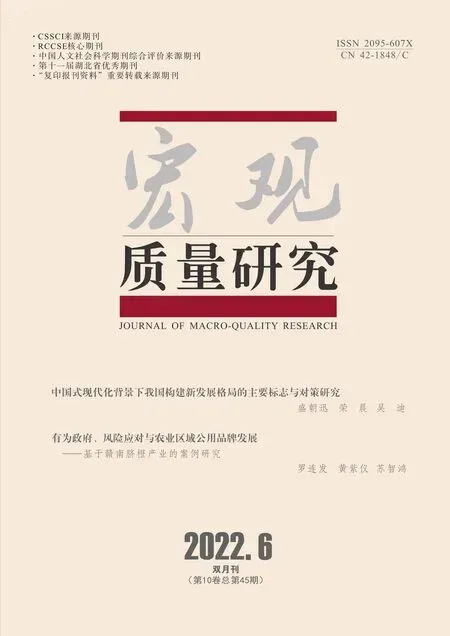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理论演绎*
丁 霞 徐经纬 吴啸峰
如果说,21世纪是一个比以往更期盼以质取胜的“质量的世纪”,那么,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更是名列高质量发展世纪前茅的佼佼者。中国化时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构筑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从而有助于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篇大文章。
一、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
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思想并且以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产物,尤其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产物;其主题是着眼于“从属”型发展和“创造”型发展并举、生产力-生产关系-“总合力”辩证法的整体发展观,并且从七大维度阐述中国化时代化高质量经济发展理论,旨在弄清楚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满足经济社会诸领域以及所有地区的全方位、全过程、长时段的高质量发展总要求,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流派的识别标志。后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总合力”整体发展观,而“质量”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对象。
(1)基础性研究对象之一即“质量”,因其不同视角赋予其差别各异的特殊规定性。如事物存在和发展(物理学意义上)的质量,哲学意义上的质量,经济学意义上的质量,国家治理层面上的质量发展安全战略,以及质量文化和道德诚信原则,等等。
物理学视阈下的质量观涉及到与事物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的质量与数量或者时间与空间产生之谜。中国朴素的质量观推崇“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则将质量变成重量。粒子物理学、“上帝粒子”也是一种解读。暗物质和黑洞理论掀起了“霍金热潮”,而量子力学与“量子纠缠”现象,更为引人注目。
哲学视阈下的质量观涉及到关于有与无、存在与意识的辩证法,以及质量转化规律,即关于事物由增加数量为主阶段向以提高质量为主发展阶段的转化规律。恩格斯是强调物质的实体性和精神的非实体性,即物质是各种实物的总和的抽象;而列宁则把唯物主义真谛视为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即物质是一种不依赖人的感觉的存在物,这是列宁对恩格斯物质概念的继承和发展。
国家战略视阈下的质量观就是质量立国、质量兴国、质量强国以及质量兴国之道、强国之策。这是因为质量问题如服务质量、生活质量及其幸福指数、环境质量、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关系到国家形象,关系到发展可持续性,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60年代,日本政府主导实施“质量救国”战略,日本的经济振兴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质量革命。
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上升为“战略目标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宗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文化视阈下的质量观强调 “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文化的创造性与多样性“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这种最高目标的文化理念及其企业质量文化十分重视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重视道德建设,重视社会责任,并且在微观上体现出企业的整体素质(包括企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宏观上则体现出整个民族的素质(彰显软实力、软权力、软国力和精神生产力)。以至于每年评选全球最道德企业,乐此不疲。2012年全球最道德企业评选,企业道德规范占25%的权重,声誉、领导力和创新能力占20%、企业管理占10%、企业公民表现与社会责任占25%、企业文化占20%的权重。
综上所述,基于不同视角(物理学、哲学、经济学、发展战略、文化)的“质量”,彰显其差别各异的特殊规定性。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质量”的自然属性就是量度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的物理量抑或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而基于社会属性的“质量”,就是衡量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是指对经济事物社会价值即其优劣性的判断,从而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性。
(2)基础性研究对象之二即“发展”,既具有基础性也具有广泛性,随着经济发展各要素(资本、士地、劳动力、管理、信息诸要素)扩展,并且越来越把研究扩展到非经济学领域,政策制定也涉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发展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期而降,蔚为大观。
而衡量多层次、多维度、动态或静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也随之多元化。狭义指标如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广义指标如HDI(人类发展指数)、GPI(真实发展指标)、MDP(国内发展指数)、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GNH(国民幸福总值)、绿色GDP,并且涉及到投入结构的变化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文化发展即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发展即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等等。此外还包括发展方式(粗放的低质量还是集约的高质量发展方式),政府、企业和社会等不同质量主体的博弈,质量管理层次(如50年代的统计质量控制阶段、60年代开始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以及数量质量综合度量的测度工具如GDP质量指数及其五大质量子系统(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等等。
综上所述,发展与质量都是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对象。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中国化时代化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本土化特征,其最终目标是科学地阐释“what”(高质量发展经济学是什么)、“how”(怎样发展)、“for”(为谁发展)、“by”(依靠谁发展)、“of”(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重大问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学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学说,也就是凸显“从属”型发展和“创造”型发展并举、生产力-生产关系-“总合力”发展规律的整体发展观。
(一)马克思的发展学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对于发展的“总体”性辩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性做了表述,开拓性地推出了关于“从属”和“创造”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其中“发展”一词使用了七次,“总体”出现了四次。
他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1979)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回答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总体”或“整体”“体系”“有机体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内在机制,批判以三个“不是”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揭示了“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的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具体总体”“思想总体”“生产总体”“精神具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原生态生产关系”与“派生的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强调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两条路径,亦即“从属”性发展(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与“创造”性发展(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翌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评判·第一分册》中,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术语、概念与规律得以固化。
(二)恩格斯的发展学说
一是批评了关于经济因素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起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错误,提出了关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发展机制即“总的合力”的历史发展观,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总合力”发展规律的整体发展观,强调“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并且“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此外,强调关于非经济因素、非物质因素因其反作用从而呈现相对独立性,诸如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也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可以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是批评把术语“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之中,强调关于“在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阐明”术语、概念、范畴“变形”或“革命”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鼓励大学生和青年作者“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毋庸置疑,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总体性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法,为解决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之谜"(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为告别"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做出了世界级的贡献(萨克斯,2007年)。
三、借鉴与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合理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可供参考、借鉴的合理元素与思想资料。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支,兴起于二战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崛起阶段(20世纪40—60年代)。1945-1960年这一段时间,也是非殖民化运动高峰时期,这是发展经济学萌发的温床。“在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这一领域里的各种基本思想和模式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引起争论,使这一分科充满了活力。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家的发展远远超过它的研究对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穷地区的经济发展” (赫尔希曼,1982) 。一般认为,结构主义思路在这一阶段占主流地位,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著,如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1943年7-9月)、斯塔利的著作《世界经济发展》(1944)、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4)。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经济体由“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组成)是结构主义思路阶段的代表作——吸收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以及伯克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思想材料——以后又被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等予以补充和发展。尤其“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而阿尔伯特·赫希曼,即《经济发展战略》(1958)、《迈向进步之旅》(1963)、《发展项目之观察》(1967)的作者,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推出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隧道效应、极化涓滴效应等观念。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低潮阶段(20世纪70—80年代),也是新古典主义复兴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有所停滞从而处于"收益递减阶段"并且已濒于"灭亡的困境"(拉尼斯、费景翰,1987)。大多数学者对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是肯定的,只是哀其不幸,怨其不争。但新古典主义者拉尔则彻底否认发展经济学的存在价值,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1983、1985)一书中指出: “在这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的年代里,要在自由放任主义和经济统制教条之间走中间道路是徒劳的。不过,根据过去的并且是不间断的对发展经济学的抨击,就作者而言,是不能和赫尔希曼一起去悲叹它的衰亡。因而,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拉尔,1992)。”
第三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进入再度“复兴”阶段(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正处于两大社会经济制度进入长期并存共处、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以及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纷至沓来。再度“复兴”的标志,一是《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七项原则,二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佩鲁名著《新发展观》(1987)问世。三是发展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愈演愈烈,流派丛生,从而彰显大百科全书模式的古典经济学发展思路或派别的回归和“复兴”。
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国际社会各国际组织大量使用发展经济学的话语,这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产物。例如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本、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一系列的新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基于新公共服务型政府和预算国家理论的全球性“政府治理革命”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诸如“绿色GDP”核算方法(詹姆斯·托宾、威廉·诺德豪斯),涵盖“HPI”(人类贫困指数)、“GDI”(性别发展指数)、“GEM”(性别赋权尺度)在内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世界银行还特别推崇“社会资本”这一话语:“另一个能够对高质量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强化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制度,即所谓的‘社会资本’”(世界银行,2001)。这是因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只重视国家与市场两个组织,而社会资本理论除此之外则更为注重社区组织。“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合作和协调可以被看做是调节人们的交往和产生外部性的‘民间社会资本’”“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之后,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又把‘社会资本’加到增长的源泉中”(G.M.Meier、J.E.Stiglitz,2001),以至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市场至关重要”、“制度至关重要”(高鸿业,2004)(伊特韦尔,1996),演化到“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社会资本是一种人际网络的加总”)(帕萨·达斯古普塔,2005),大大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以及理论框架。
发展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引人注目,呈现了跨经济分析与非经济分析、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紧密结合,以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理论相互影响、发展经济学各学派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发展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堂而皇之地跨入正统经济学固有领域,并且不断“入侵”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阵地。尤为甚者,一批发展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把伦理因素重新纳入了发展经济学,“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剧变”,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最终应该归结为人们“是什么”和“做什么”,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五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以及保护性保障,并从自由中产生发展的能力。他用大量的证据证明,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
流派丛生更是发展经济学兴旺的重大标志。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初结构主义思路及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创立到7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复兴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转变,尤其到90年代初新制度主义思路与发展中计划经济国家体制改革浪潮的兴起,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思路目不暇接、流派更是五花八门。钱纳里以及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等把发展经济学分成新古典学派、新马克思学派和结构学派三大类。托达罗则以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新古典学派结构变化模型、国际依附模型予以分类。增长经济学流派经历了下述三大发展阶段,即从斯密型古典增长理论阶段,转向新古典增长理论阶段,接着又继之以新增长理论阶段;五大增长型取向(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内生技术变化型、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型,以及线性技术内生型与开放经济内生型)昭然若揭。此外,还有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激进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派。而“微观发展经济学”派别也不容小觑。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及其理论派别也是方兴未艾,如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依附论、巴里落克模式、新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体制变革论、重新定向论。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主义”的争论延续百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主义”成为统治全球的西方发展或增长经济学的霸权话语,发展成为不要理由的绝对正当性理念。实际上,殖民地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发展”境界。《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现象:“Jobless”(经济增长而没有创造就业机会)、“Ruthless”(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无情的增长”)、“Voiceless”(无声的增长即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Rootless”(没有文化根基的“无根的增长”)、“Futureless”(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无望的增长”)。此外还有Independenceless(依附型的“低头的增长”)和Controllou(失控型增长)即韦斯凯尔(T.Weisker)所评论的 “愚蠢的、不受约束的、漫无目标的、无政府状态的增长”。有鉴于此,21世纪初期,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提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PPG),还有“理性增长”(T.S.Szold、A.Carbonell),“发展型国家”(Meredith-Woo-Cumings),以及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报告中指出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等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还一度推出越南这个案例,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盛赞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
综上所述,西方发展经济学以及增长经济学与转型经济理论,无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可借鉴的实用性,而后者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学说,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
四、时代化中国化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学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世界银行最新报告公布的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这一数字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从而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十年令人瞩目的是:一是随着中国加速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快了建设以"质量强国"为重要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步伐;二是中国已消灭绝对贫困,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实现了新飞跃。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11890美元,较2012年增长1倍。世行在公布的人均GNI排名中,中国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68位,提升了44位。
(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从“九个必须”到“十个坚持”,以及发展理论与政策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学说赖以产生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经济发展学说从历史深处走来,其中包括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江泽民,中共十六大2002年),“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胡锦涛,2008年)、“有质量的增长”(温家宝,2012年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习近平,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2017年,十九大报告)、“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习近平,2019年)、“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习近平,2021年)。党的二十大进而把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高度,列入“五个必由之路”“五项重大原则”“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在实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洞察与把握中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与小国发展迥然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以及完备的产业分工体系优势和生产集群规模优势),以上规模、大体量为特征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与后发优势,具有潜质的国内消费市场体量优势(四亿中等收入人群),基于党领导一切经济工作从而凸显的体制性优势(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另一方面,应该清醒地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就需要着重关注“四情”即世情、国情、党情、舆情,实事求是,由此而决定一国一城一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与具体政策。如,中国西部地区是全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该怎么办?《中国西部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刘以雷,2021)弄清楚了影响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六个短板,提出了构建六大体系、抓住四个关键措施点或方略。贵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勾勒出的贵州高质量发展路径,就是把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作为重要抓手,把大力推动“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旅游产业化)作为主攻方向,把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
(3)全面学习与把握习近平中国化时代化高质量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是我国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40年的经验总结,集中体现我党对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他看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而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重视量的发展,更要重视解决质的回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五个“看”(供给、需求、投入产出比、分配、宏观经济循环)和五个“牢牢把握”。后者强调把握与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的要求;工作主线是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路径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着力点;制度保障是有效、有活力、有度的经济体制,以及促进建设“质量强国”,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述评,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1129/c40531-32293980.html。。
习近平中国化时代化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精髓,就是正确理解关于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辩证法,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共享之所以居压轴地位,是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绿色发展日益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过去十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全球现有的“国际湿地城市”有43个,中国就有13个,是“国际湿地城市”最多的国家。
(4)“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的发展战略(2)中国新闻网: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围绕“四新”抓“四化”, http://www.gz.chinanews.com.cn/jjgz/rdxw/2021-04-29/doc-ihaktsyz0524819.shtml。,应该与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对接,关注生产力空间布局,总体性资源配置。如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东数西算工程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资源总体性配置的杰作。“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区域、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注重区域性一体化协调联动发展。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着力构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高地”,诸如创新平台和开放发展平台建设,国家示范区,区域性经济增长极,智慧园区,自由贸易区,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乃至于世界级产业集群(丁霞,2021)。
关注以国内大流通为主体的全球性四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链条(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区块链),关注生产力空间布局, 促进以国内大循环(内需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构建以“一路一带大市场”为标志的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促进生产与消费(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资源总量管理和科学配置,加快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力图打通经济循环即交换或流通的堵点和短板,建设高水准消费驱动型经济。这是凸显整体性、系统性、均衡性、融合性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题中必有之义(3)中国网.新闻中心:习近平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全文),http://news.china.com.cn/2022-01/17/content_77995095.htm。。
(5)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撑、必由之路、突破口,就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尤其要紧紧利用与把握新的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健全针对“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核心技术突破口,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攻关强大合力(4)央广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https://china.cnr.cn/news/sz/20220907/t20220907_526002069.shtml。,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1%已经提高到了2.44%,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了第12位。
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息息相关的生产要素先后有资本、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知识、信息等。尤其数据、算力及其基础设施(构筑十大新基建即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东数西算”中心)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芯片制作技术等,是新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中,创新极为活跃、影响最广泛的技术。此外,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形态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很有必要。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防止两极分化。
(6)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 就必须促进“数实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正确处理四大产业之间、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还有现代化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齐头并进,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现在的45.5万亿元。
一是加强各经济活动部门之间的整体性联系,相融相长、耦合共生,促进技术渗透、链条延伸、业务关联,积极探索新业态、新路径和新模式。这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这就要发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力图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链、工程链、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顾客价值链以及产品、服务紧密融合在一起,可以全方位改变其业务流程、产品架构、生产方式、产出形态、生产效率。这就要力图加强实体经济部门与高端服务业的紧密结合,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二是着力推动制造业“数实融合”及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其范围包括企业内部全领域、价值链全周期和供应链全生态;应以数据为核心、以算力为支撑、以算法为驱动,实现要素融合、技术融合、设施融合、流程融合和产品融合。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是实现这一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李晓华,2022)。
三是谨防一窝蜂淘汰“低端”(基础)产业,一窝峰上“高端”(高新技术)产业。这是砍断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内在联系,这是使制造业“空心化”进而自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愚蠢行为。应该限制和淘汰的,是那些在该行业中技术落后而又无损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企业。我国国情是劳动力充沛,相当长一段时间居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大力限制和淘汰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普通劳动密集产业,不足为取。应发挥我国在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固有优势,可以根据国内外区域发展差距进行梯度有序转移,同时着力提升产业组织形式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由此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7)构筑多层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经济学说,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学术界的一个新动态。中国学术界某些学者提倡“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质量经济学理论”。(任保平,2018)西方学术界除了拓宽宏观发展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融合之外,还致力于“微观发展经济学”(史蒂文·N.杜尔劳夫、劳伦斯·E.布卢姆,2016),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体系结构,即渺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宇观经济学(程恩富,2016)。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五观”发展经济学,自不待言。而贯彻落实时代化中国化的科学发展观与高质量发展理念,构筑多层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经济学说,则是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大书特书的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