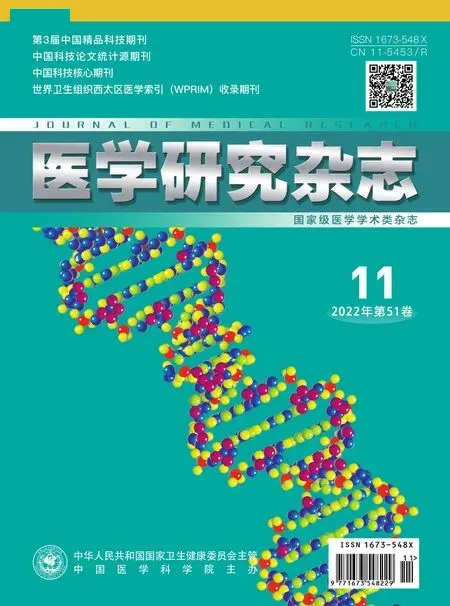慢性肾脏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及相关产物影响的研究进展
杨秀杰 方敬爱 王蕊花 张紫媛 张晓东 胡雅玲 李 慧
由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常见病因的多发,以及相伴随的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和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的发生,CKD已严重影响人群生活质量,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CKD患者病情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肠道菌群失调的作用不可忽视。目前认为,肠道菌群是人体的一个虚拟器官,不仅参与消化吸收,还通过其代谢产物作用于人体各个系统。因此提出了“肠-肾轴”理论:胃肠道与肾脏通过物质代谢及免疫途径相互影响,CKD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并促进了肠源性尿毒症毒素的产生,进而影响肾脏和其他系统[2]。因此,明确CKD患者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影响对于CKD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CKD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及主要的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于CKD患者的影响,以及临床上与其相关的治疗方法,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一、肠道菌群失调
1.肠道菌群:肠道是与外界相通的最大器官,是微生物群生长繁殖的理想地点。寄居于肠道的数量达100万亿的细菌及少数真菌等构成了肠道菌群。其主要包括6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和疣微菌门,前4门占据肠道菌群的绝大多数。肠道菌群是一种共生生态系统,与人体形成了微妙的平衡。肠道菌群不仅参与人体物质代谢,还具有维持肠道环境、生成必需营养物质以及免疫调节等作用。一旦平衡被打破,就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失调在心血管疾病、肾脏病、糖尿病等疾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2.CKD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由于CKD患者肾功能的受损,尿酸、尿素等含氮废物在肠道中的排泄增加。为了改善病情,CKD患者往往会保证低钾饮食使得肠道中氨、胺类、苯酚类、吲哚等生成增加。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抗生素、钙磷结合剂等药物也会影响肠道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CKD患者肠道菌群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CKD患者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及变形菌门占据优势,分解蛋白质的细菌数量增加而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受到抑制。有研究报道,相较于正常人群,CKD患者有190种微生物操作分类单元明显不同,并且占优势的19个微生物家族中,大多数拥有脲酶、尿酸酶以及吲哚和对甲酚合成酶,而拥有丁酸(短链脂肪酸的一种)合成酶的微生物家族(普雷沃菌、大肠杆菌属、真杆菌属、布劳特菌等)减少[3]。一项动物实验也证实,相对于假手术组,在慢性肾衰竭模型大鼠的结肠菌群中,不动杆菌属、大肠杆菌属、肠杆菌属和变形杆菌属增多,乳酸菌属和双歧菌属减少[4]。
在正常人群和CKD患者的差异菌属中,艾克曼菌(Akkermansia)值得关注。艾克曼菌被认为可以保护肠道黏膜屏障并调控免疫反应。Li等[5]研究发现,艾克曼菌在CKD患者中的丰度明显下降。Wong等[6]研究认为,艾克曼菌对CKD的发生具有较高的疾病诊断价值。但目前对艾克曼菌的研究较少,其影响CKD患者的方式仍需进一步探索。
3.肠道菌群失调对CKD患者的影响:肠道菌群变化后,其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功能被削弱。肠道酸碱失衡以及肠壁水肿的发生也损伤了肠道屏障功能。细菌移位或菌群代谢产生的毒素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微炎性状态,影响全身,进一步加重CKD的发展,使得CKD和菌群失调互相影响。
肠道菌群失调与CKD的病情发展密切相关。Gao等[7]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分析了不同阶段CKD患者中肠道菌群的变化。他们收集了不同阶段CKD患者的粪便样本,发现早期CKD患者和ESRD患者的微生物多样性无明显变化,但有24种微生物存在显著差异(FDR<0.1)。其中丁酸合成相关菌群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ESRD患者的丁酸合成相关菌群水平最低。
二、相关肠道菌群产物对CKD患者的影响
合成相关代谢产物是肠道菌群影响人体的主要途径。人体肠道菌群失调发生后,对人体有益的代谢产物明显减少。而随着蛋白质分解细菌的增加,肠源性尿毒症毒素的蓄积十分普遍,并在多个方面影响CKD患者。
1.硫酸对甲酚和硫酸吲哚酚:硫酸对甲酚(pcresyl sulfate,PCS)和硫酸吲哚酚(indoxyl sulfate,IS)来源于肠道中的苯丙氨酸和酪氨酸及色氨酸,在肠道细菌及相关酶的作用下形成,并经由肾脏有机阴离子转运系统(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OAT)转运。由于代谢底物的增加和拟杆菌门等细菌的增多,PCS和IS在CKD患者中的血浆浓度较正常人群升高54倍和17倍,且易与白蛋白结合,无法被血液透析有效清除。
(1)肾毒性:二者都能够调控炎症及纤维化相关信号通路,在肾脏病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硫酸对甲酚促进肾脏纤维化加剧肾脏病情进展,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PCS可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并上调肾素-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AT1R)表达,刺激肾间质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重肾组织纤维化;诱导单核-吞噬细胞在肾间质的浸润,加重肾间质纤维化;上调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调控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加速肾脏纤维化;研究发现,FGF23-klotho轴起到了延缓CKD患者病情发展的作用,而PCS促进DNA甲基转移酶的表达,使klotho的表达减少,加速了肾脏纤维化[8~10]。
IS同样可加速肾脏炎症及纤维化过程:IS刺激肾小管上皮细胞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进而激活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由此上调了Ⅰ型纤溶酶原抑制物激活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p53、α-平滑肌肌动蛋白(alpha-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等调节因子,下游的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ICAM-1)的表达增加,使单核-吞噬细胞在肾小管聚集,从而促进肾脏纤维化;同样,IS也可上调肾素-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表达,刺激RAAS系统及TGF-β表达,促进肾脏纤维化;IS通过去甲基化作用使klotho基因失活,促进肾间质纤维化;STAT3属于STAT蛋白家族的一员,诱导了巨噬细胞中IL-10的产生,还参与了依赖IL-6的T淋巴细胞增殖,并且,STAT3还在近端小管细胞参与MCP-1,TGF-β1、α-SMA、NF-κB的诱导表达。IS可以激活STAT3从而促进肾脏炎性反应和纤维化的发生;另外,IS可以降低肾脏特异性有机阴离子转运体SLCO4C1的表达,加重毒素的蓄积,加剧了IS对肾脏的损伤作用[11~14]。
(2)胰岛素抵抗:CKD患者早期即出现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已有研究证实,IR在CKD的进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CKD患者心血管疾病和营养不良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15]。IR的发生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Opdebeeck等[16]将CKD模型大鼠分为对照组、IS组和PCS组,并于试验开始、第5周和第7周采血,发现IS组和PCS组血糖水平升高,且葡萄糖转运体1(一种主要的葡萄糖摄取转运体)水平降低,且在PCS组更为明显。目前认为,PCS能够使胰岛素信号通路中的PKB/Akt的磷酸化受损,同时使胰岛素抵抗相关的细胞外信号调激酶ERK1/2的表达增加[17]。
(3)心血管病变:心血管病变在CKD患者中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3~4倍,也是CKD患者最常见的死因。IS和PCS与CKD患者心血管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
CKD患者血管钙化的发生十分普遍。一方面IS可通过活化NOX,使内皮细胞产生ROS增加,降低谷胱甘肽水平,进而激活NF-κB,增加了MCP-1、ICAM-1表达并且抑制内皮细胞修复;另一方面,IS和PCS可通过影响肝X/法尼醇样受体,干扰机体血糖及血脂代谢,削弱机体对炎症的抑制能力,造成了高脂、高糖以及炎性环境[18]。IS同时还促进了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在二者的作用下,患者循环中内皮损伤标志物内皮微粒(endothelial microparticles,EMPs)的增加,表明发生了内皮损伤及钙化。
IS和PCS可以被视为肾心综合征的生物学标志物。有研究观察到,IS通过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NF-κB信号通路以及诱发氧化应激反应并沉默klotho基因表达使心肌肥大或心肌纤维化。而PCS能够通过上调细胞NADPH活性以及诱导ROS的产生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和左心室舒张功能的下降[19]。
(4)矿物质-骨代谢紊乱(CKD-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CKD-MBD):CKD3~5期和透析患者通常伴有CKD-MBD,出现纤维性骨炎、低转化性骨病、骨软化等骨异常。CKD-MBD是CKD患者骨折以及死亡的危险因素。
尿毒症毒素的蓄积是CKD-MBD发生的原因之一。CKD-MBD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患者对甲状旁腺激素的抵抗。IS和PCS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3(OAT-3)能够介导尿毒症毒素的摄取,它被发现在成骨细胞中表达。PCS和IS通过OAT-3进入成骨细胞。PCS可以通过JNK及MAPK信号通路降低成骨细胞的细胞活力、对PTH的反应及诱导活性氧的产生;IS不降低成骨细胞对PTH的敏感度,但同样可作用于成骨细胞,通过抑制成骨细胞特异基因(osterix)、骨钙素和骨形成蛋白2(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BMP2)的mRNA表达并且诱导活性氧的产生,抑制骨形成和矿化从而导致低转化性骨病[20]。
2.吲哚-3-丙酸:正常情况下,吲哚-3-丙酸(indole-3-propionic acid,IPA)与IS都是由肠道中的色氨酸转化而来,且二者的生成处于平衡状态。由于尚不明确的机制,CKD患者中二者的平衡状态被打破,IPA的水平明显下降。IPA对IS等尿毒症毒素引起的机体损害具有抑制作用,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学标志物和保护剂。它主要通过以下机制起到对人体的保护作用:(1)芳基烃类受体(AHR)存在于多种细胞中,可以上调细胞色素P450(CYP)1A1、CYP1A2、CYP1B1等及MCP-1和内皮细胞组织因子的表达,是组织纤维化发生的重要机制[21]。研究表明,IPA可以有效抑制AHR的激活[22]。(2)IPA可以抑制Stat3在近端肾小管的活化进而下调MCP-1、ICAM-1等的表达,延缓肾间质纤维化。(3)ACE2-Ang-(1-7)-Mas轴可以抑制炎性反应,进而延缓CKD的进展。并且还可以对梗阻性肾病及糖尿病肾病患者起到保护作用。AHR和STAT3与近端肾小管Mas受体的减少有关,IPA可以通过抑制IS对两者的激活,保护Mas受体来抑制肾脏纤维化[23,24]。(4)IPA还可减少β淀粉样蛋白的生成,是一种抗氧化的神经保护剂,对于预防老年痴呆有很好的效果。(5)IPA对于胰岛β细胞有保护作用,能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25]。
3.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TMAO):TMAO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小并可被血液透析清除的代谢产物。卵磷脂、肉碱、胆碱等进入肠道后,经菌群代谢产生TMAO的前体三甲胺,进入门静脉循环,由肝脏经黄素单氧化酶合成TMAO。CKD患者体内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细菌的增加,使得血清TMAO浓度较正常人明显升高。
TMAO对于CKD患者的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它是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既往研究证明,TMAO可以通过激活PI3K/Akt/mTOR信号通路促进心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26]。Yang等[27]研究发现,TMAO给药后大鼠体内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巨噬细胞清道夫受体(CD36和SR-A1)的mRNA水平升高,从而造成胆固醇的积聚和泡沫细胞的形成。
此外,TMAO的肾毒性也不容忽视。实验证明TMAO给药大鼠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和胶原沉积,胱抑素C的水平也会上升[27]。Guo等[28]将65例CKD患者和65例健康人进行对比,发现TMAO水平的升高是CKD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且能够预测CKD的发生(AUC=0.96)。
4.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氨基酸发酵的主要产物。SCFA可能是肠道菌群正常功能最重要的体现,它对结肠上皮有极为重要的意义。CKD患者乳酸菌属和双歧菌属等相关细菌的减少,导致短链脂肪酸的水平明显下降。
SCFA主要在结肠产生,包括丁酸、乙酸、丙酸等多种物质。其中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底物,提供了细胞生长和分化所需能量的70%。丁酸盐能够抑制NF-κB来发挥抗炎作用、通过促进黏蛋白合成来改变黏液层的组成以及发挥抗癌活性。丙酸盐也是结肠细胞的能量来源,具有降胆固醇、抗脂的作用。乙酸是数量最多的SCFA,是细菌生长的重要辅助因子[29]。
综上所述,SCFA对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杜怡等[30]研究发现,丁酸盐能够通过增强miR-7a-5p(一种miRNAs)的表达来抑制大鼠模型体内TGF-β1/Smads途径来延缓肾脏纤维化。同时,SCFA有效改善了胰岛素抵抗并参与胆固醇代谢和脂肪生成,减少脂肪积累;研究证实,短链脂肪酸还具有调节骨代谢紊乱的作用[31]。
三、相应的治疗策略
基于肠道菌群及相关产物对于人体的广泛影响,近年来,通过改善肠道环境及菌群构成来延缓CKD患者病情进展的治疗方法已在临床上有所应用。
1.调节肠道菌群:“益生元”、“合生元”疗法是通过人为调节紊乱的肠道菌群来抑制有害肠道菌群产物的产生,减轻全身炎性反应进而减缓肾脏纤维化进程。此疗法可以有效降低体内蓄积的尿毒症毒素,而且患者依从性好。
益生菌是一类微生物的总称,它们可以改变肠道环境,抑制炎性反应,修复受损的肠道上皮连接,保护肠道物理屏障[32]。“合生元”即将益生菌和有益于益生菌生长的食物等(益生元)结合的制剂。“合生元”除了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构成外,还可以吸附含氮物质以及减少结肠排空时间来减少尿毒症毒素的蓄积;改善葡萄糖代谢,降低血浆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33]。
2.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指的是可被肠道菌群发酵的碳水化合物,并且发酵后还具有膨胀或松弛的特性。经典代表即抗性淀粉、阿拉伯胶等。膳食纤维代谢产生SCFA等物质,剩余不可发酵物具有促肠道蠕动作用。目前研究认为,膳食纤维能够改变CKD患者肠道菌群构成及人体代谢,并减少肠源性毒素的生成。但膳食纤维种类及具体比例仍需开展进一步探索。
3.减少毒素吸收:毒素通过受损的肠道屏障进入血液循环是影响人体的关键一步。AST-120是一种由多空碳颗粒组成的不溶于水不被人体吸收的有机溶剂。口服AST-120可以吸附相应的毒素,减少毒素吸收,加快转运,延缓肾功能恶化。研究表明,使用AST-120后,结肠上皮TJ蛋白、claudin-1和ZO-1等较不使用的患者增加,同时IS、PCS的产生和炎性反应得到了抑制[34]。
4.中医疗法:中医方法以及单味中药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大黄及其有效成分蒽醌类可以减少致病菌,减少IS和PCS等毒素的产生,降低内毒素含量,抑制全身炎性反应,并且还可以修复肠道黏膜物理屏障,防止细菌移位。
结肠透析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的疗法也在临床广泛应用。结肠透析利用了肠道本身的半透膜特性,能够有效清除尿毒症毒素,改善微炎性状态。此外,一项动物实验也证实结肠透析能够抑制内质网应激,延缓CKD进展。
四、展 望
“肠-肾轴”理论已逐渐被人所关注。CKD患者发生肠道菌群失调后,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的菌群产物逐渐减少,肠源性尿毒症毒素通过各种信号通路诱发或促进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等一系列过程造成肾损伤,并且干扰人体血糖、血脂代谢,引发了血管钙化,从多种方面影响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治疗及预后。肠道菌群作为研究新热点,各种与其相关的治疗方法已在临床应用。但此种疗法仍需观察完善,如益生菌的种类和数量及在体内的效果,活性炭的不良反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