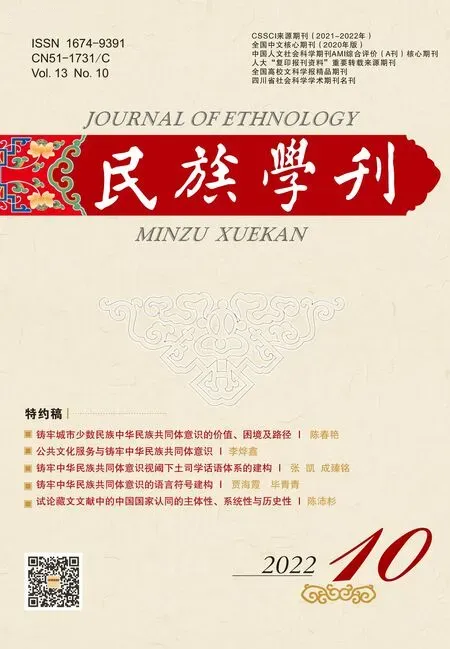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李烨鑫
自从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对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目前,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从发展脉络、内涵意蕴、建设意义以及铸牢路径等四方面展开。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郝亚明提出用强化族际纽带、加强民族“三交”的方式来增强共同性[1]56-65。二是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意识。如郝时远主张通过加强中华文化的自觉及自信以增强认同感[2]1-10;王延中认为大力推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五个认同”教育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3]7;严庆也认为开展“五个认同”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要求[4]14-21。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增强国民意识。如周平认为加强民族团结,增强国民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路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5]5-16。四是共享资源建设。如陈纪等认为应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享资源建设以构建具体实现路径[6]26-33。五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青觉认为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基础性工程是路径的新拓展[7]173-181;纳日碧力戈也认为各族人民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以做到语言互通[8]10。六是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辅助。如马惠兰认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作用[9]32-35。除此之外,还有结合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以及族别展开的铸牢策略研究。如青觉认为“文化润僵”是通畅中华文化润泽机制、夯实新疆特色文化与中华文化母体等的过程[10]1-12。这些成果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逐步深化,但基层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过程中还常常感受到缺乏行之有效的抓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学理意义出发,结合基层实际情况来扎实推进,尤其要利用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已经积淀的设施资源,通过适当调适以形成新的功能,从而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由来已久,但自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并公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以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快车道。特别是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下文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以来,在法律的刚性约束下,我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并能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的是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推进文化治理。该体系所具备的公共性、参与性和共享性特征能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
一、从“共同体”到“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但对于何谓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以及如何形成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则是学界不断探索的基础性问题。早在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就系统论述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共同体”的三种原型:古希腊和罗马的民社与城邦、中世纪的日耳曼王国以及近代的自由市镇等,并阐释了共同体的内涵和特征。滕尼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共同体强调有机联系和关系,而且具有亲密性和排他性。他在共同体原有“协同性”意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共同体的本质:“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们理解为真实的(reales)与有机的(organisches)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本质。”[11]68“真实”和“有机”是共同体的核心意涵,赋予共同体鲜活的生命感和互通感。他还提出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以及精神共同体这三种主要类型。他在分析了中世纪行会师徒之间传递技艺、指导人生所形成的牢固精神纽带(精神共同体)之后,认为精神共同体的心理基础是“本质意志”(Wesenwille)这个有机体的心灵结构[11]207,而本质意志的基本内涵是喜好(Gefallen)、习惯(Gewohnheit)和记忆(Gedächtnis),这些都是有机体诸本能的复合物[11]208-220。“精神共同体”这个有机体是与社会实体截然不同的存在,已经具有心理学层面的意蕴。从精神层面的共同体来说,共同体甚至可以等同于共同体意识。而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因为有某种稳定纽带的存在,容易产生对血缘和地缘的认同,从而产生共同体意识。滕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共同体意识”,但是我们可以把他的“精神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来源。《共同体与社会》作为全球畅销的学术著作,在滕尼斯生前就发行过七个版本,并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以及中文本等多国语言,足见他对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之巨大。而按照威廉斯的观点,共同体(community)具有五种意涵。前三种意涵指实体存在,后两种意涵分别指“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12]125,也鲜明表达了共同体的非实体内涵。安德森将民族和共同体结合起来研究,其主要思想见于1980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他认为民族不是许多社会现实的结合,而是想象的创造物和共同体。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推断出:民族是一种心理性和意识化的存在。滕尼斯、斯大林以及安德森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民族学的角度对“共同体”进行论述,使得其内涵更加立体和生动,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轫于19世纪末期。1899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提出了“一体”“一统”等概念。他在将中国与欧洲列国进行国体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体”的概念:“春秋战国以后,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渐渐无差别之可言。故国地一经合并,国民遂为一体也”,“欧洲自罗马以后仍为列国,中国自两汉以后仍为一统”[13]769-773。1903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说”,他将国家与器械相比较,认为二者殊异:“国家之为物,与彼无机之器械实异”,“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又有不同:精神与形体相联合;肢骸各官;宜联结此等肢骸以结构一全体……等。[13]451他的“有机”思想也进一步丰富了“一体”和“一统”的内涵。甚至可以说,梁启超的“一体”“一统”和“有机体”这些共同体是精神和形体的结合,已经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果说梁启超的“一体”“一统”和“有机体”偏重于学理分析的话,那么孙中山的“统一”思想则带有较强的社会治理的功能要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说道:“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4]95他的“统一”具体包括“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14]95-96。1939年2月,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原因,认为这种思想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萌芽了,认为“夷汉是一家”,“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15]773-785,这是事实,更是信念。“信念”指稳定的、坚定不移的想法,属于精神层面的阐释,包含着共同体意识的内核,而“一个”蕴含着共同体及其共同体意识的雏形。梁启超的“一体”“一统”和“有机体”,孙中山的“统一”以及顾颉刚的“一个”思想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我国面临内忧外患。这样的国家局势迫切需要国内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变化。在此情景下,费孝通在1988年“泰纳讲演”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9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6]1。他就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进行了阐释:“多元”指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组成多元化,其起源多元化[16]17;“一体”指“各民族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17]268,这种一体性,集中表现为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等。“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的多元中包含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17]268。他主要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并阐释了整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他还谈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主要从历史渊源阐释了共同性的基础,其表现是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具特长而又相互学习[17]123-152。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明确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他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8]44,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8]44。他的界定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文化自觉就是要在意识层面明白“我是谁”,对自身具有充分的认识,并自觉地传承、发展和创新的内部驱动力。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认识过程,实现了质的飞跃,也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纵观从梁启超到费孝通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的发展线索,其最主要的历史背景是我国近现代一百多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内部积弱、强敌入侵的紧迫情况下,中华民族紧紧团结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取得伟大胜利。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16]16。这个“自觉”也从“自在”的无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所以,历史经验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共同体,具有了共同体意识,就能取得各项事业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9]421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革命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通观全局、变中求进。应对这种大变局的新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环境是外部刺激,内部则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牢固的精神堡垒,进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前学界对于其内涵研究的关键词在于“认同”,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国家认同。如虎有泽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20]1-6。第二,集体认同。如哈正利认为集体认同是各民族在各方面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21]。第三,民族认同。各民族人民对本民族共同记忆、情感、意愿及信念等的认知。
毫无疑问,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在滕尼斯看来,精神共同体本身就属于意识范畴;费孝通的“多元一体”以及“整体性”是基于反帝反封的历史背景,在浴血奋战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已经建立牢固的整体意识,并由自在上升到自觉的精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中华民族在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中,也实现了由“共同体”到“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事业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我们的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踏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通过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凝心聚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加以推进。在我国现有基层治理体系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直接服务于基层民众精神层面的治理设施。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设施资源。
二、公共文化服务“认同感”生成逻辑及物质基础
公共文化服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两者联系的桥梁就是“认同感”的生成。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强调“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meaning)与经验的来源”,而文化认同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涉及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的认同概念,我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者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来理解,而这些文化属性相对于意义的其他来源要占有优先地位”[22]5。认同感首先是文化的认同,这是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内容相匹配的。因为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主要提供文化方面的服务。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认同的生成不能仅仅依靠角色,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22]5,认同可以使角色进行自我建构和个体化,从而获得更加稳固的意义来源。而这个意义被他定义为一种象征性认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认同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通过一些途径建构起来的。因此,“如何有效获得”就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认同感”生成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一是营造公共领域,凸显公共性;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主体性。三是建构共享意识,夯实公平性。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营造公共领域,凸显公共性。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共同的空间,具体来说,“公共的”内涵有二:一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听见和看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二是与私人地盘相对应的我们共同的世界,即世界本身[23]81-84。他使用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公共领域的作用:它就像一个四围坐满人的桌子,既将人区别开来,防止人民倾倒在一起,又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的基础上认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性表现的区域,这个领域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赋予公民对于国家活动实施监督的权利[24]2。在公共领域内,人们通过共同的活动产生紧密联系以产生共同体意识。公共文化服务就像阿伦特所说的“桌子”一样,可以提供公共领域和公共活动,具备凝聚的功能。它又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赋予人们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权利。人们在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交换思想进而产生公共意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硬件设施,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公园等可以营造有形的公共领域,形成固定的文化活动空间,从而使得“认同感”具有可达性。但是,认同感的生成仅仅具有这些物质条件还不够,还必须在公共领域内交流。帕克论述了共同体中交流的重要性:共同体就存在于交流中。在共同体内,人民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来调整他们的活动,就能形成共同体。生活在共同体中人民必须通过交流才能产生认同感并达成共识[25]183-184。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交流场域,并通过一系列活动促成了交流的产生。另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其他内容,如网络信号、电视信号、广播信号等也可以营造无形而便捷的公共领域;全民阅读、全民健身、全民普法以及全民科普等活动更是营造了全国范围内的无形公共空间和领域,有利于全民认同感的生成,从而促进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正如帕克所说,一本书或者一封信这种载体能够使相隔千里的人也能产生紧密联系[25]184。因为参与共同的文化活动、享受共同的文化资源以形成文化共同体,自然而然会对共同体产生认同感,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此,陈纪主张“以文化方面的共享资源建设提升各民族文化自信,从文化利益共同体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5]30。
第二,公共文化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主体性。登哈特认为对于公务员的基本要求是服务,而不是掌舵。他说:“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本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控制社会新的发展方向。”[26]103这种“服务”思想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也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原则。现代服务型管理更加重视人,而不是物。公共文化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7]2,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提供公共设施及其相关服务。其立法的总体思路之一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27]18,它还进一步强调:“公共文化服务是全体人民普惠性的服务,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7]19。由此可知,“以人民为中心”“均等化”以及“普惠性”等词语精练地传递了公共文化服务使人民产生认同感的可达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迫切需要满足基本的文化权益,得到文化滋养。公共文化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普惠性的文化服务,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人民群众通过不断与周围世界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确立自身的角色和定位而获得认同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地位,这能培养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促使他们以更强的主动性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事业中。
第三,公共文化服务能够建构共享意识,夯实公平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从哲学及道德角度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权力、义务时的正义(Justice)问题,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重要德性一样”。[28]3他提出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27]47他简明扼要地说明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不仅指出了公共文化服务面对全体公民服务,而且还要求对特殊人群和特殊地区做出更充分的保障。如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27]3,对务工人员和留守妇女儿童要提供便利服务;针对在校学生的特点提供相应服务;支持军队基层文化建设,促进军民文化融合。而针对特殊地区,第四章《保障措施》规定了“重点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27]13。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促进了全民、全域共享意识的形成,还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公平性。社会只有实现了文化公平,才能更好地实现和谐的目的。如傅才武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文化权利的全民共享”[29]130。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语境探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际,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操作层面确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正义原则”[30]37。鲍曼也认为,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31]177。全民共享而不排他,这也是社会公平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传递的全域、全民共享意识,促使全域、全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从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通过梳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有的建设成就和服务内容等因素也为“认同感”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速发展。2017年3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开始实施,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事业提供了法律保证。2021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也提出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资金投入来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为建设提供了经济保障。从建设成效来看,截止2020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2个,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1785.77万平方米,图书总藏量117929.99万册;群众文化机构43687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32825个,全国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85076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384个①。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主要积淀在基层,从业人员也主要面向基层群众提供服务。在我国现有基层行政体系中,县以下行政单位没有专门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导致县级民族工作部门在镇村两级的工作推进存在诸多困难。镇村两级要用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抓手,让镇村两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成为推进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窗口。
总之,无论是从生成逻辑还是工作抓手来说,公共文化服务的现有资源存量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用。正如周晓丽等人所说,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外部效应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主要指文化物品和服务在传播主流形态,形成特定政治体系所要求的公民政治文化,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文化安全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32]90。公共文化服务也必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的主线服务。
三、结语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上来说,它能够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覆盖城乡的服务体系和人员配备来说,它能够成为镇村两级推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33]的重要观点。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全区历史文化宣传教育、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城市标志性建筑建设、旅游景观陈列等相关方面”。[3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我们要用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各项设施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建设,也要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主动求变,承担相应工作职能,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