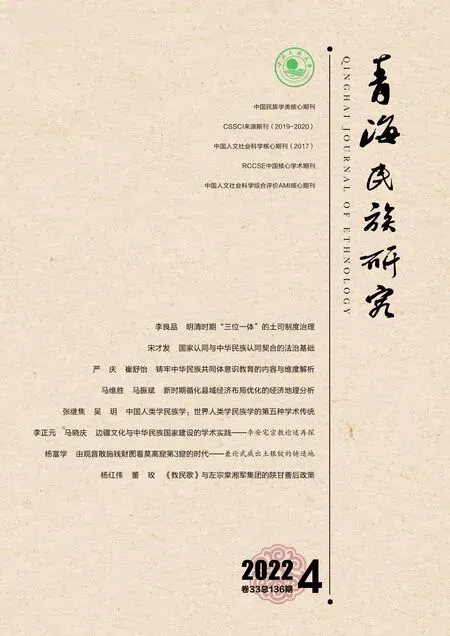先秦时期西域地区胡巫研究
杨贞明
(青海大学,青海 西宁 800016)
《说文解字》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许慎认为巫就是祝,是女性通过优美的舞蹈使神灵降临,以达到天地人神沟通的目的。《国语·楚语下》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从这段文字的记载可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为巫,而是那些精神专注、恭敬中正、具有贤德的人才可以为巫,男性被称之为觋,女性被称之为巫。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夏商周时期,巫是文化的承载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就如童恩正所言:“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在中国北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过程中,许多文明因素如法律、文字、天文历算、医学等的创造和积累与巫师的活动都分不开。……夏代开始,巫师的后继者祭师集团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1]由此而言,巫在先秦时期不仅担负沟通天地人神的职责,而且身兼数职,并掌握着大量的文化资源,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中的胡巫主要指先秦时期西北方少数民族之巫。而在先秦时期,胡巫作为西北少数民族的早期知识分子,他们既是知识文化的掌握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在西域与中原的往来过程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资料中所见之胡巫
2003年发掘新疆鄯善县洋海墓葬,发现个别干尸头骨上有钻孔现象。青海柳湾遗址中也有尸头骨有孔的类似现象。头骨钻孔是原始萨满教的信仰。先秦时期西域的匈奴、塞人、乌孙、康居、柔然等族都信仰过萨满教,从柳湾遗址有孔头骨可知,早在殷商时期西域萨满教习俗已传入中原与西域的交界之地湟水河流域。
1976年在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出土蚌雕人头像,“人头像系蚌雕,蚌的厚度为1.5—2厘米。1号头像完整,2号头像只存大半。1号头像的头顶刻有一‘巫’字,头像皆高鼻深目,系白色人种,属白色人种的大月氏、乌孙……1号头像的头顶所以刻有‘巫’字,可能就是充任‘巫’的司职。”[2]杨宽《西周史》就这两个雕像指出:“其中一个头顶刻有‘巫’字,这两个人头像是‘胡巫’是无疑的,说明胡巫从西北来到中国的都城为执政者所使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3]由以上出土文物可知,殷商时期青海湟水河流域已经有萨满巫活动,而西周初年周王室已启用胡巫充任“巫”的司职。胡巫已经在中原帝王心中具有一定的位置。胡巫的东来对中西文化交流势必起到促进作用。如杨宽所言:“西周初期胡巫的东来,可以说是早期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之中的一个特点。如同后来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中,首先佛教传来。”[4]
二、古文献中的西域胡巫
关于胡巫的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其云:“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5]司马贞《索隐》:“《孝武本纪》云:‘立九天庙于甘泉。’《三辅故事》云:‘胡巫事九天于神明台。’”便知九天巫即胡巫。从“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可见,汉代胡巫的职责不仅是祠九天,还要负责宫中的祭祀。比起梁巫、晋巫、秦巫和荆巫,西汉时期胡巫已深得统治者信任。《汉书·地理志》载:“朝那,属安定郡。”颜师古注曰:“有端旬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应召曰:‘史记故戎那邑也。’”在汉代朝那属于安定郡,有十五所胡巫的祭祀场所。胡巫祭祀之地如此之多,结合汉武帝时期“巫蛊之乱”来看,汉代胡巫东来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胡巫的直接记载先秦史料中比较缺乏,我们只能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来寻找胡巫的踪迹。
(一)“西王母”是第一位有史记载的胡巫
据《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厉及五残。”[6]郭璞注“蓬发戴胜”曰“蓬头乱发;胜:玉胜也。”但郭璞对“胜”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致使后代学者大多认为“戴胜”即戴发簪。当代学者韩高年在《〈山海经〉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及其他》一文认为:“西王母所佩戴的‘胜’,绝非用以束发的‘簪’,只能是象征‘王者’身份的面具。”[7]此说可从近年出土先秦时期大量玉璧、玉琮等祭祀玉器得到证实,早期人们以玉作为礼器祭祀神灵。如春秋战国时期秦人以玉人祭祀天神,那么盛产玉的西北少数民族,如中原殷商时期制作青铜面具一样用玉制作面具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可见,韩高年认为西王母所戴之胜非固定发型的簪而是面具是可信的。据《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8]从《汉书》的记载可知西王母居于西北塞外,这一地带在先秦时期为羌族游居之地,由此学界普遍认为西王母为羌的部族首领。结合《山海经》中西王母为蓬头乱发、带面具而以祠厉鬼,便知西王母不仅是历代羌族首领的代名词,更是能通天地人神而祠厉鬼的巫。早期巫大多是帝王或部落首领,他们不仅统领国家、部落,还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西王母便是如此。
西王母与中原帝王的往来源远流长,据《尚书大传》云:“舜以天德祠尧,西王母来献白环玉玦。”舜继王位,西王母以异族首领身份前来进献美玉以表示祝贺。又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舜九年,西王母来朝。”九年西王母又来朝见舜。可见西王母与中原帝王舜的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大戴礼记》《汉书》《中论》《晋书》《宋书》等对上古这段历史的论述中均有“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的记载。史书虽未有直接记载禹与西王母交集的文字,但《荀子·大略》云“禹学于西王国”却未说明西国是否为西王母之国,禹向西国所学什么?据《史记·六国年表》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9]禹在未称帝前,勃兴于西羌。根据东汉王充《论衡·无形》载“禹、益见西王母”便知禹西学于西王母。《太平御览》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而禹本身就是巫,所以“学于西王国”可能是向西王母请教了巫术。舜帝时期西王母大多以敬奉美玉的身份出现,而到禹时,则已求学于西王母。可见在禹的时代,西王母已对中原帝王产生了影响。
西王母与中原往来,西传而来的不只是巫术,还有医术和草药。《淮南子·览冥》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山海经·海外西经》郭注云:“殷帝大戊使王孟采药,从西王母至此。”族属于西王母的众巫,上天入地,采集百药,在医药不发达的夏商周时代,为人们解除病患延续生命,声名远扬于中原。这使得中原帝王谴使前往西王母之邦求不死之药,也就不难理解《山海经》中为何记载了如此之多的西域奇珍异草。
《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更为鲜明、更为突出。周穆王“执白圭玄壁,以见西王母”,郑玄注曰:“挚,所执以至者,君子见于尊敬,必执挚以将其后意焉。”可见周穆王是非常敬重西王母的。由西王母再拜受之,与周穆王在瑶池饮酒之时,从西王母为天子谣、为天子吟中原四言诗可知,周穆王时期的羌族首领西王母对中原文化已非常熟悉,完全没有了《山海经》中“蓬头乱发,面带玉胜”的狰狞一面,俨然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中原女王。西王母形象的这一转变,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西王母,在华夏文化熏陶和影响下,成为《穆天子传》中熟识华夏礼仪、作诗吟诗的羌族首领。
(二)“河宗栢夭”是胡巫、向导、翻译
关于《穆天子传》所述历史的真实性,杨宽在《西周史》言:“我们认为,周穆王在几个游牧部族的引导下,带着所谓‘六师之人’,沿着黄河上游西行,穿越戎、狄地区,经历许多戎狄部族,相互赠送礼品,做安抚的工作,都是真实的故事,其中参入神话传说,或有夸张增饰,当然是无可避免的。”[10]此说是对《穆天子传》史料价值较为中肯客观的评价。
中原天子周穆王西行,必然需要一个懂得西域语言、文化、地貌、风土人情的人为他做向导和翻译,而河宗栢夭是最合适担此重任的人。河宗氏是先秦时期游牧于黄河上游与河套地区的部族,从《穆天子传》记载来看,他们主要游牧于河套、温谷乐都及黄河上游。由于过着逐水草而迁的生活,所以与黄河上游以西的羌氐、大月氏、乌孙等少数民族部族交往密切。作为河宗氏首领的河宗栢夭自然熟知西域的语言、文化、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必然成为周天子西行向导和翻译的最佳人选。赵俪生对河宗栢夭的职责给予了充分肯定:“河宗栢夭看起来是穆天子一路上紧紧伴随的译员,对很多部落的献礼物品都是派遣栢夭代表天子接受,他对‘西膜’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似乎是相当熟悉的。陇坂、鸟鼠山一带,可能找不到这样的人才。”[11]出行前河宗栢夭替穆王举行了祭河大典。《穆天子传》载:“天子命吉日戊午。……河宗栢夭受壁,向西沉壁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时事。’南向再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珤,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珤,赐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河宗栢夭化身为河神传达帝命,劝诫穆王专心于治理政事,并对穆王西行予以肯定。在这里河宗栢夭以河神附体的方式沟通人神、传达天命,可见河宗栢夭为胡巫无疑。
河宗栢夭乘渠黄为天子先,伴随穆王一路西行,为穆王介绍所历西域诸国的山形地貌、奇珍异草、美玉奇石和风土人情,所到之处无不所知甚详。从栢夭对所经诸国情况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便知其对西域诸国文化非常了解。刘桂英认为:“古代西域语言大致分为汉藏语系、塞语、阿尔泰语系。”[12]河宗栢夭带领穆王一路西行,没有任何阻力,通过他的翻译使穆王与西域诸国首领沟通,可知栢夭掌握西域多族语言,其在穆王西游中不仅是巫和翻译还兼任了向导、使者等多重身份。
河宗栢夭不仅对西域语言和文化非常熟悉,对中原历史文化也了然于胸。离开河宗栢夭的地域,一路西行到达的第一站为膜昼,栢夭为穆王介绍曰:“□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郭璞注:“主,谓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为穆王介绍膜昼与殷商同为一姓、同出一族。到“舂山之泽”则言“先王所谓县圃”。介绍赤乌氏时则言:“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对赤乌氏的介绍中栢夭追根溯源,详述了大王亶父始作西土后的分封情况,最后言及赤乌氏为丌璧臣长绰的封地。又栢夭曰:“重击邕氏之先,三苗氏之□处。”由于文字有佚失,所以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众说不一,但学者们大多认为栢夭为穆王介绍重邕与三苗的族源关系。可见河宗栢夭不仅熟悉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历史、文化也相当了解。
周穆王东返时分封河宗栢夭。“戊午,天子东征,顾命栢夭归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天子感念而下诏令,封河宗栢夭为河宗氏诸国的盟邦之主,以表示感谢和对栢夭的肯定。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胡巫已跻身于中原王室,汉代时胡巫得到帝王的信赖,左右王室的决策,成为汉武帝时“巫蛊之乱”主要参与者,是有历史渊源的。
杨宽《西周史》言(《穆天子传》)“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眼光来分析,才可能从中找出它的真实来历。我的见解是:这部书之所以会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是由于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13]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足以说明在周代河宗栢夭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胡巫之于《山海经》与阴山岩画
1976—1980年,在阴山发现了许多属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部族的石岩画。据盖山林考察“其中绝大多数的画面,属于原始社会的晚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14]先秦时期游牧于阴山一带的部族据甲骨卜辞和金文记载有羌方、方、鬼方等名称,见于史籍的有犬戎、山戎、匈奴、北狄等部族。游牧民族大多追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这一地带在先秦时期游居过许多部族。阴山岩画是这些部族在阴山一带游牧过程中的创作。至于阴山岩画的作者,盖山林认为:“阴山大部分岩画的题材内容,既然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而胡巫的职司又是搞宗教活动的,由此不难推至,阴山中的大批岩画,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岩画是胡巫的作品。”[15]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阴山岩画与《山海经》的对比研究中认为,阴山岩画与《山海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盖山林从《山海经》所描述的“神灵形象”“动物形象”“植物图形”以及“眼睛”“浑敦无面之神”等与岩画对比分析后认为:“阴山岩画中有许多奇特的图形,从它们的形象看,显然不是在世间真正存在过的动物,而是以真实的动物为基础,增加或减少动物的腿、脚或头数后成新的动物形,或者是将不同的动物的部位凑合一起,组成新的动物形,这与《山海经》对某些鸟兽动物的记载情况是完全一致的。”[16]孙致中也持此说,他在《山海经与山海图》一文中谈到:“近年来,在我国境内云南的沧源、耿马、怒江、路南、丘北、弥勒、西畴、麻栗坡和它克等地以及内蒙古的阴山发现了大量的崖画,据研究,它们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作品。这些崖画的艺术形态很多与《山海经》的‘怪物’相似,这说明它们和原始巫术紧密相连,或径直是巫的作品,纵非全部,也必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古巫师之手。”阴山岩画与《山海经》所显现出的这种一致性和相通性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山海经》的另一半“山海经图”。据载,早期的《山海经》是有图的,因此又称“山海图”。陶渊明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郭璞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兽画中”这样的注释。袁珂认为:“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图画似乎还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此说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与肯定。对于“山海经图”的来源马昌仪在《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一文中总结了历代注家和研究者对《山海经》古图的推测,在研究分析禹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四种学说之后认为:“《山海经》母本(相当一部分)的成书过程很可能与这些民族的巫师活动和所用巫图巫辞相类,其文字部分最初作为古代巫图的解说词,几经流传和修改,才有了我们所见的《山海经》。因此,认为山海经图主要来源于巫图的说法是比较有根据、比较可信的。”[17]由此可见,胡巫作为少数民族的早期知识分子,在与中原交往中把自己地域的山形地貌、奇珍异产、神灵祭祀等传入中原,成为《山海经》中有关西域描写的蓝本。
三、先秦时期西域地区胡巫的作用
先秦时期,胡巫作为西域地区各部族知识精英阶层,作为西域各部族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掌握着大量的知识和文化,他们不仅主导着当时社会生活文化的发展,在西域各部族文明的起源、传承、创新、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字创造、历史记录、文化传承、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等方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创造文字、记载历史
胡巫在西域地区各部族文字的创造、历史记录中起到重要作用。“巫者担任巫祭职位,不但具有当时人们所普遍具有的知识技能,还精通部族的历史和人们的心理愿望,熟悉巫术仪式和占卜程序,所以就成为部族历史的记录者。”[18]同时,就如沈怀灵所言:“巫者创造文字以记录卜筮的过程和结果,卜辞成为上古历史的记载。”[19]胡巫在占卜祭祀时形成大量的卜辞,这些卜辞大多刻于兽骨和岩石,刻于兽骨上的卜辞被作为重要的占卜、祭祀工具被珍藏,刻于岩石上的岩画则以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下来。这些卜辞记录了当时西域各部族在狩猎、生存等方面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发展轨迹。相对于兽骨,大量刻于岩石的岩画被保存至今,在新疆地区出现大量岩画,其中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城西南雀尔沟镇雀尔沟村。岩画东西长约14米,上下高约9米,岩画画面面积达120多平方米,画中布满了身姿各异的人物近二三百人,大的人像超过真人,小的人像则仅一二十厘米。人像有男有女,形姿各异,或立或卧、或衣或裸。除人物主体岩画外,还有各种动物图案,有牛、马、羊、骆驼等,同时还有祭祀、狩猎等场面。如此巨型岩画,在中国目前仅见,在世界上也极少,这些早期的岩画充分记录了先秦时期西域地区各部族的生产、生活和祭祀状况,甚至文化艺术发展史。它对研究先秦时期西域地区原始社会史、原始宗教祭祀、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艺术及古代民族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卜辞因此成为人类早期知识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历史的忠实记录。”[20]
(二)文化传承
如上文所述,胡巫在占卜、祭祀过程中形成大量的卜辞,这些卜辞记载了先秦时期西域各部族的重要祭祀活动、文化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同时,整个巫术活动也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行为范式。“巫术仪式是最早的文化规范,巫则是这些法则、规范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巫俗乃是现在习俗的原始状态。”[21]胡巫在完成祭祀、人神沟通等巫术活动的过程中也自然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和行为规范。这些文化体系和行为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为这些部族群体的文化体系和行为规范,并不断被传承和发扬。同时,他们还肩负着保存、积累和阐释卜辞的职责,这一职责使得胡巫这一群体成为西域各部族的精神领袖和文化倡导者,并形成一个知识传授、文化传承、精神传导的具有严密而完整体系的阶层。“巫师阶层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卜筮的操作和传授,维持其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卜辞的保存、积累和阐释。”[22]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导者
游走于中原与西域的过程中,胡巫不仅把西域文化传入中原,还把独具中原艺术特色的文化带到西域。在阴山岩画中发现了大量具有中原特色的人面纹和饕餮纹。“阴山岩画中的人面纹题材,是受到了中原人面纹和饕餮纹的影响。在磴口县北格尔敖包沟畔的山腰上、莫里赫提沟石壁上和潮格旗大坝沟口石崖上,凿刻着许多兽面纹或啮牙裂咀的怪面状图形,从其形状和特征看,他与殷商饕餮纹有一定关系。”[23]从阴山岩画与《山海经》的相通性、一致性以及阴山岩画中所呈现的独具中原特色文化的人面纹和饕餮纹画像。结合前文提到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钻孔头骨、西周时期蚌雕巫相,胡巫在先秦时期已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这种往来对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传播工具不发达的先秦时期,胡巫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传播与交流最主要的先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