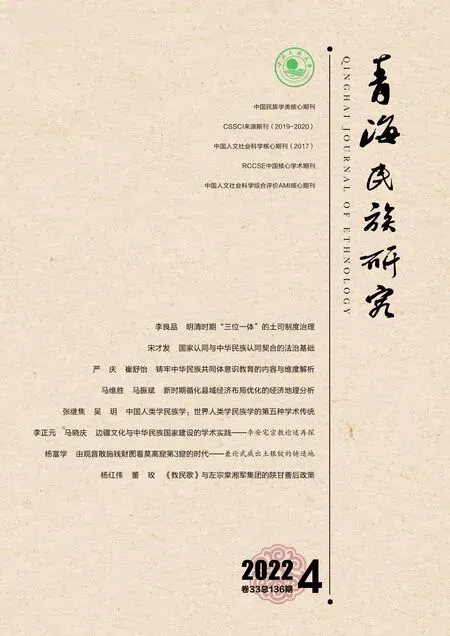唐蕃古道上的国色天香
——清代青海地区牡丹欣赏的三个面相及文化意义
韩 芳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3;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3)
牡丹是我国本土花卉,早期以药用为主,在南北朝时成为审美对象,“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一时名人高士,如邵康节、范尧夫、司马君实、欧阳永叔诸公,尤加崇尚,往往见之咏歌。”[1]唐宋是牡丹欣赏的第一次高潮期。至明清,牡丹的栽培更广,寻常可见,明代有诗云“国花长作野蔬看”[2],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上谕山东巡抚停止岁进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师皆能莳植,何必远道进献”[3]。牡丹的欣赏阶层广泛,从艺术形式来看,诗文、戏曲、小说、民歌、民间故事、绘画、剪纸、雕刻、陶瓷、刺绣等领域都有它的身影,具有富贵、繁荣、美人、盛世、国都、中央等多重内涵[4],并成为个人情操、集体认识、民族精神等多重意蕴的文化符号。学界注意到牡丹在不同时期(主要是唐宋)、不同艺术体裁以及不同个体(包括花瓣颜色和欣赏者个体两方面)欣赏中的意蕴差异①,而对牡丹欣赏中,因牡丹生长地域和欣赏者籍贯、身份而产生的差异鲜有人关注。
唐蕃古道,东起唐都长安,中经鄯城(今青海西宁),西至吐蕃王朝首府逻些(今西藏拉萨)。此道自文成公主入藏开辟以来,一直连绵不绝,后来路线虽有调整、开拓,但主要节点基本没变,使臣、商贾往来,商品交易、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枹罕(今临夏)花似小洛阳”“美人国色在西方”[5],明清时期作为中原象征的牡丹也在沿线尽情绽放,受人青睐。这些地区多民族聚居,饮食、风俗、文化与中原地区都有较大区别。居于此地的人们寄寓在牡丹中的情感,与中原地区的人们、与历史传统是否一致?是否带有高寒、极边、多民族聚居、古道节点等地域特征呢?青海地区地处唐蕃古道的主干线上,“距京师四千五百一十里”,[6]“其地右通海藏,左引甘凉;内接河兰,外达羌虏,所以为边陲屏翰,中原保障”[7],为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逐鹿之地。这里政权更迭频繁,又处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比较独特。清代这里不但诞生了一批吟咏牡丹的诗文,而且民歌、绣片、砖雕等中也有大量与牡丹相关的艺术作品。因此,笔者试以唐蕃古道上的青海地区为中心,从牡丹欣赏的三个群体:普通百姓、本土士人以及客籍官员出发来寻找答案。
一、“宜乎众矣”:牡丹的栽培及民众对牡丹的普遍喜爱
唐蕃古道沿线牡丹种植历史悠久。在甘肃武威柏树乡出土的东汉古墓医简中,有用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录[8],说明汉时西北地区就有牡丹。欧阳修说“牡丹西出丹州、延州”[9],可见宋时延安地区产牡丹。清代兰州、河州、临洮及陇西等均是当时全国牡丹栽培的次中心[10],甘肃合水、临夏至今还留存着巨大的野生牡丹群落。乾隆年间西藏“物产”记载中也有牡丹[11]。
至迟在明末,青海地区的庭院、寺观中已种植有牡丹,西宁城东的普现寺有百余年的牡丹一株,碾伯县城东南的越圣寺有牡丹十数本,“西宁府之花”中也载有牡丹。[12]清时,循化山上有野生牡丹,“打儿架山上野花极繁,多不知名,惟牡丹芍药可指数。”[13]至清末,这一地区牡丹已非常普及,“生植颇易,城乡皆有之”。[14]“生植颇易”,是因青海地区生长的牡丹品种具有抗旱、抗寒、耐盐碱、可逆性强且病虫害少的优势[15]。西北地区的牡丹与中原地区的牡丹外形上也有细微区别:植株高大、叶柄细长、花瓣相对单薄,多为单瓣或半重瓣,基部有紫色斑点。人们一般用西北牡丹、甘肃牡丹或紫斑牡丹来专指生长在这片区域的牡丹。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种植的都是这种牡丹,所观赏、吟咏的基本是这一西北独有的牡丹品种。
牡丹的身影几乎可见于青海地区的所有艺术形式中,尤以民歌“花儿”最为突出。“花儿”是发源于明初西宁地区和甘肃临夏,由汉、回、藏、撒拉、土、蒙古等民族共创、共唱的民歌[16],牡丹是“花儿”的中心元素之一:现存1252首花儿中常涉及的11个程式类型(内容划分)中,牡丹程式有156首,在所有程式中居第二位;[17]河湟花儿中的两个传统曲令——白牡丹令、二牡丹令,都以牡丹命名。牡丹在“花儿”中的含义非常单纯,代表的是歌者所追求的美丽的女子。
尕妹是牡园子里开,阿哥是凤凰(着)采来;千落万落地落不上,碰死在牡丹的树上。[18]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红牡丹红着破哩;尕妹的跟前有人哩,没人时我陪着坐哩。[19]
牡丹在“花儿”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牡丹文化最原初的共性文化基因——美丽、美好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经一代代河湟百姓的传唱,牡丹逐渐成为民俗性标志物和民族文化的代表物之一。
由美丽的恋人意象延伸,牡丹也被视为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出现在雕刻、刺绣、陶瓷、绘画乃至饮食文化中:互助县丹麻乡出土有西夏缠枝牡丹罐;互助县东山乡出土有缠枝牡丹纹“白釉剔花瓶”;北禅寺和南禅寺前檐木雕中有牡丹纹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乐都的碑坊上有木雕缠枝牡丹纹饰;清末互助土族李用才的宅院门上也雕刻有牡丹图案。在青海东部农业区,牡丹受到各民族群众的普遍喜爱:清真寺、佛寺常见牡丹纹饰,河湟汉族民居建筑的台基、柱础上的雕刻也常见牡丹图案。当地还有一种特色蒸面月饼,其上多捏叠各种图案,而牡丹是最常见的图案之一。[20]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青海地区各民族群众共爱牡丹,并创造出了边陲牡丹文化在多民族地区美美与共的艺术奇观,显示出清代青海地区各民族群众的交流与融合,亦是中华传统牡丹文化基因在边陲民间多向留存的见证。
二、本土文士:传统牡丹意蕴的继承与出新
因为身份、籍贯的不同,士人看待同一事物的文化心理会有所不同,生活在青海地区的士人寄寓在牡丹中的情感有着较大的差异。按照本籍可将他们分为两类进行考察——本土文士和客籍官员。首先看以张思宪、来维礼为代表的本土文士(即方志中所言“邑人”)。
与全国的风俗一样,明清时期,在青海地区也有牡丹花开文人相约赏花、饮酒赋诗之习,迄今可见一些咏牡丹诗,如张思宪的《贾氏园赏牡丹题小蓬莱壁》《夏日尊甫砚兄招饮将就园赏牡丹》(二首),董志儒的《咏牡丹》(二首),来维礼的《奉跂云司马命和汤孟生院长<湟中未开白牡丹>原韵并和唐桂舲明府例押原韵(七律三首)》、基生兰的《朱家花园赏牡丹小饮》等。这些诗歌一方面描写牡丹的美丽姿容,一方面表现“花间煮酒晚烟横”(张思宪)的闲情逸趣,似与其他地方及历史上的咏牡丹诗没什么区别。但也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主要有两点:
(一)清赏富贵花
传统文化心理上,牡丹花代表祥瑞、富贵,常被视为身份,甚至大唐气象、宋代政教精神[21]的象征。牡丹的雍容华贵与诗人的贫寒、蹇涩常形成对比,衬托出个体或时代的哀伤,如归庄的“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22]、吴昌硕的“酸寒一尉出无车,身闲乃画富贵花”[23]等。青海地区的士人几无高官显宦、大富大贵者,面对这历来寓示富贵、繁盛意象的花朵,他们似乎并没有自惭形秽或怨懑哀伤,相反,却十分坦然。
来维礼(1833—1904年),字敬舆,号友生、椒园。他的科举之途走得颇为艰难,46岁中举,50岁时中进士。他曾主讲乐都凤山书院、西宁五峰书院,受聘纂修《西宁府续志》。他曾作诗写过家乡一废弃园林中的牡丹——《朝阳宋氏废园中牡丹》:
任他桃李斗春华,国色从来冠众葩。若使此花誇②富贵,不应生在野人家。[24]
晚唐牡丹诗中,废园牡丹意象常出现,一般诗人或借此表达时代的感伤和身世的零落之感,或抒发蔑视富贵、孤芳自赏之情。但此诗却毫无衰败气、萧瑟象,也无对自我品行的夸赞。他一方面赞许牡丹艳压群芳的美丽,另一方面表现它不以富贵自傲,不厌弃环境的孤寂与清冷,坚持不懈释放美好的可贵品质。李逢春题解称“诗中蕴含着作者的自喻”[25],体现的是边陲文士不因边地偏远而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暗含着坚持努力,终可冠绝群伦的自信。再看下面这首诗:
名花却少金壶贮,辜负天香竟夜开。正欲园林寻艳去,何期富贵逼人来。乞阴思护云千朵,酣饮先酬酒一杯。安置明窗勤爱惜,落英莫使怨尘埃。[26]
名花不期然进入“我”这样的普通家庭,没有办法给它应有的“金壶”的待遇,但它也丝毫不嫌弃,开放如常。对此“富贵”客,来维礼表示一定会倍加爱赏、珍惜,充分享受它带来的美好。
类似清赏牡丹的情境在清代青海地区的士人中比较普遍。如“湟中高士,陇右名家”张思宪③,在当地讲学期间有诗句“第一名花向我开”[27]。基生兰④亦有“此花虽富贵,寒舍亦相宜”[28]。当时青海地区的文士认同牡丹所具有的繁华、富贵等象征义,并且不因牡丹的雍容富贵而自我菲薄、自惭形秽,而是回归对牡丹本身真淳的自然美的欣赏、赞叹。这或与以下原因有关:一是他们当时的境况虽称不上大富大贵,仕途有些坎坷,但基本是活跃于当地教育文化界的乡绅名流,即使晚年归乡,主讲当地书院,亦有安身立命之所,在当地颇受尊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外,生活在边地相对封闭、淳朴的社会环境下,文士内心的焦灼感也会少许多。诗中坦然书写自己与大富大贵之花的不相称,体现了他们对美好事物更为单纯的喜爱和知足常乐的精神。
(二)白牡丹融和众美
唐代人们追捧深色牡丹,“争认慈恩紫牡丹”,白牡丹因颜色清冷而“无人起就月中看”[29]⑤,在牡丹欣赏热潮之外,白牡丹被文人作为清高自持,满腹才华而不得施展的象征。[30]到清代,诗人们多赞美白牡丹的冰清玉洁,如天津人赵新的《杂咏牡丹十二首》[31]。由牡丹的冰清玉洁引申,加之古代本有的“花仙”因素,诗人们又赋予了白牡丹“仙”性,如天台太学生潘韶此诗:
千红万紫斗芳春,羌独生成洁白身。似厌繁荣存太素,甘抛富贵作清贫。琼葩到底羞争艳,国色原来不染尘。昨夜月明深似水,只疑瑶岛集仙真。[32]
白牡丹浑身素洁,甘于清贫,厌恶富贵繁华。它的素洁令其他色彩鲜艳的花朵为自己的争奇斗艳而羞愧,因此,潘韶认为只有这一尘不染的白牡丹才堪称“国色”。它是如此超凡脱俗,以致月明之夜看去,仿佛仙人一般。
清代青海地区种植有各色牡丹,白牡丹也进入诗人笔下。湟源人董志儒,为清同治、光绪年间人,曾任丹噶尔厅科稿书,“爱吟咏,生前所作甚多”,但存诗甚少,今存诗中有三首白牡丹诗,《咏牡丹》(两首)云:
天生粉脸玉为团,百卉甘心踞下坛。鹤氅轻披来紫府,蛾眉淡扫上金銮。后娴大体原贞静,妃亦方家厌绮纨。固是嘉名足称实,由来富贵不单寒。[33]
咸夸魏紫与姚黄,那识临芳别样妆。淡则居之高一格,冷然善也压群香。羞歌朱槛成微醉,嫩著练裙总大方。便许花妖持寸铁,谁能战胜此文章。
首联写白牡丹艳压群芳,百卉甘居下风;颔、颈两联具体描摹白牡丹的外形、气质,将白牡丹喻作花中的皇后和妃子。“紫府”指道家仙宫,“金銮”是皇家宫殿,这里指出白牡丹在仙界和凡界均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继续强调白牡丹的尊贵。尾联反用白居易“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34]诗句,指出白牡丹是名副其实的富贵之花。第二首诗承接历史上以宫人身份比喻牡丹地位的传统,但一扫姚黄、魏紫占据绝对优越地位的传统,将白牡丹封后封妃,以“淡则居之高一格,冷然善也压群香”立意,表现出咏物诗特有的堆叠意象的特征,也体现出诗人融合众多美好于白牡丹一身的愿望。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富贵色彩一般是金碧辉煌、艳丽灿烂,淡雅本是富贵、富丽的反面,二者基本不可能兼容。而本土诗人笔下的白牡丹集美好、富贵、高洁、尊贵等所有的美好为一身,既强调牡丹美丽、富贵的共性,又突出它淡雅超俗的个性。一方面消解了白牡丹所代表的文人的冷寂心态,另一方面也刻意忽略牡丹富贵意蕴中低俗的一面,赋予白牡丹诗意的美好:富贵高格,冰清玉洁。
前代及同时期其他地域的白牡丹诗词,尚未见如此立意者。在清代的青海地区,像董志儒这样赞颂白牡丹融合众美的十分普遍,似乎已形成套路,如张思宪诗“凡艳那能超富贵,天香原不染尘埃”[35],来维礼诗“悟彻凡葩色即空,仙姿羞入绮罗丛。丰神秀出繁华外,富贵迟来澹泊中”。[36]
青海地区虽是“外戎内华,山阻地险”[37],旧有“高尚力气,轻视读书”的风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受到较多的自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过,顺治十一年(1654年)苏铣编《西宁志》云,此地虽风俗与中原差异大,但“力农务学,不殊内地。”[38]乾隆十一年《西宁志》载,“圣朝开辟既远,教化亦浃,是以风气渐燠,物力滋丰,骎骎乎内郡矣。”[39]此言虽有夸张之嫌,但至少说明当时当地已渐开化。此后,经大批官员的建学努力,当地学风改观更明显。从本土士人的牡丹诗来看,他们十分熟悉历代在牡丹欣赏中层累的丰富的意蕴并进行选择性的接受,他们清赏牡丹的坦然与赞美白牡丹的融通兼美是中华牡丹欣赏史上比较独特的一道文化景观,具有值得玩味的深层文化意义:中华传统文化在遥远西陲边地的辐射力、影响力;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多民族、农耕与游牧交织地带、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区域成长起来的士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然的趋同性、向心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本土士人不因地域、身份自惭形秽,在赞美牡丹之美的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卓越出群、追求圆满、追求一切美好的文化心理。本土士人选择性地接受了历代诗人倾注在牡丹中的情感,扬弃了文士们的清高自傲与孤芳自赏,表现出极强的融通、集成的特性。同时,也毋庸讳言,士人文化的批评意识以及人格的独立性有所缺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集权政府影响文化的另一面。
三、客籍官员: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负载
青海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清政府加强对此地的控制,雍正初设青海办事大臣,总理青海蒙古诸旗和番人事务,并改置西宁府。清代本就有为防范官员与地方勾结的籍贯回避制度,因此,在此地任职的七品以上的职官及学官均来自外省。如杨应琚(1696—1766年,字佩之,号松门)⑥是辽海人,汉军正白旗;杨汝楩⑦(字工求)是仁和(今杭州)人,申梦玺(字受昌)⑧是阳曲(今太原)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及经历,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地方官无论在文化积淀还是在文化心理上,都与本地士人有较大的不同,他们从盛放的牡丹中所体味到的思想、情感必然也有较大的差异。
(一)“洛阳红”承载的美好回忆
唐代牡丹的栽培观赏中心在长安,北宋转移至洛阳,都位于政治经济中心。文人被贬谪、远离中心区后,再看牡丹,便容易产生与首都或中央之间的联系,因此,宋代之后的牡丹书写出现了迁谪之痛、离京之感这一新主题。⑨牡丹象征着国都、中心,京城之外的牡丹具有被冷落、被忽视、失意等多重意蕴。在清代,历史上寄寓在牡丹中的这份情感依然在继续。
洛阳牡丹富有盛名。欧阳修的名句“曾是洛阳花下客”,使得洛阳牡丹具有优雅、惬意与诗性等多重意蕴。地方官均为客籍,有多年西陲之外的生活经验。在西陲边地,他们看到牡丹,自然会直接回想起在洛阳(内地)赏花、饮酒的场景,回忆起之前温暖、安谧和相对舒适的生活。青海地区客籍官员笔下的牡丹诗,牡丹既是眼前现实场景,是具体的西陲经验,又是温馨的青春、洛阳、历史、文化等记忆的堆叠再现。
这在杨应琚的诗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雍正末期他为陕甘总督时,在酒泉城外⑩偶遇牡丹,赋诗曰:
百宝阑边木芍药,洛阳曾向花间酌。相逢不觉亲如昨,坐久几忘白日暮。云如泼墨风雨作,不忧衣湿愁花落。安得千重锦帐幕,紫金盏酒相为乐。[40]
“百宝阑”出自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装饰栏楯,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41]诗中用以说明牡丹被小心呵护,视为珍宝。第二句用欧阳修诗意,城外偶遇牡丹唤起了杨应琚久远的记忆。在那里,牡丹被人们珍惜;在那里,自己生活得惬意悠然。在边陲看到牡丹,仿佛他乡遇故知,杨应琚盘桓其侧不忍分别,享受着短暂的美好时刻,同时,又因牡丹会被风雨摧残,而忧心忡忡。表面看他是担心牡丹花,实则是忧虑于眼前的祥和安乐不能长久,边地随时会发生冲突摧损花容。他的另一首诗《湟中咏牡丹花》与此类似:
洛阳红向西陲发,粉印知从一捻来。天上有香真可到,世间无地不宜栽。才矜晓艳春风飏,又泣残阳暮雨催。惟是边人希珍重,年年辜负此花开。[42]
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一个品种,花瓣基部有墨紫色斑,在外形上与紫斑牡丹较为接近。首联指出洛阳牡丹在西陲盛开,同时强调中心“一捻”的重要性。然后说牡丹已经适应了各地的气候,可以任意栽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花会长久开放,“大抵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碎琉璃脆”。遗憾的是,边地百姓既不懂得欣赏,更不知道珍惜这美好,任这美丽的花儿寂寞地开放,寂寞地凋零。
杨应琚此诗作后,西宁太守申梦玺有一首次韵和作,如下:
镇愁春日荒荒过,却喜奇香款款来。黄紫尽夸梁苑种,清芬谁遣塞垣栽?檀心月姊相邀醉,碧蕊蜂媒取次催。我纵无怀希富贵,答君幽意满园开。[43]
“梁苑”,西汉梁孝王所建东苑,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出牡丹名品。西北的春天天气还很冷,风沙也大,令人愁闷,但这里却有珍贵的牡丹。花朵开放时,空气中会突然夹杂甜香,凤蝶飞来,一起赏月观花,多么美好。尾联反用牡丹象征义,“我”与您并非希图富贵,只是不愿辜负这苦寒之地满园盛放的名贵花朵。呼应杨应琚的尾联,也暗含自己与“边人”趣味的不同。
作为中原旧物,生长于边地的牡丹唤起人们对过去温情与美好生活的回忆,缩小了边地与中原的距离,但也凸显出两地气候、人文环境的差异。地方官们的牡丹诗,有些许的优越感,也有自我标榜之意。
上举诗例中诗人表现的是空间差异下牡丹欣赏的心境差异,还有一类是时间跨越后的主体心情。王以中⑪年轻时曾至西宁,二十年后重返故地,写下此诗:
雁行昔日居湟中,曾记屯田仿汉功。事去繁华原是梦,重来童稚半成翁。沙寒戍迥千山月,夜静楼高一笛风。几度荒园亭上望,廿年前醉牡丹红。[44]
“雁行”,兵法阵名,因横列展开、似飞雁的行列得名。此处指诗人在此地曾经历的军旅生活,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屯田(曰军屯)。往事如梦幻般美好而遥远,二十年后再次归来,诗人几成老翁。面对这依然苍凉辽阔的明月,听着塞上特有的悠远的笛声,他想起曾经的岁月,想起二十年前在牡丹花丛前的酒宴,想起逝去的青春,美好中带一些苍凉。“红”有两层含义:一是牡丹本身的红色,二是诗人酒醉后脸上的酡红。二者都是记忆中的温暖与明亮,是灰暗的边陲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二)“出塞”牡丹承载的地域认同
青海地区地处“邻番部”,属地汉、蒙、番、回等多民族错杂聚居,清政府以冲、繁、疲、难四字划分地方的重要程度及治理难度时,此地全占。避籍任职此地的官员需要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以及远离政权中心,难以被中央发现、政治前途渺茫等多重困难。但清王朝的官员考课以及士人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努力尽责履职。于是,借怜惜牡丹以自怜,借赞美牡丹以自夸,借牡丹的在边陲安然绽放表达安心行政等多重意绪自然成为牡丹诗的主题。
卢泳清⑫,字邵常,湖南宁乡人,曾知灵台,权礼县,部丹噶尔同知,其诗集《西问诗草》⑬中有四首作于西北的牡丹诗——《四月十八日行省东园观牡丹》(二首)、《牡丹》(二首)。这四首诗主题比较接近,基本都是赞美牡丹颜色艳丽而不自骄、不与百花争艳,于晚春寂寞开放,安然于寂寞荒寒,不怨愤的品格,如下面这首:
百花开尽尚姗姗,纵老深山骨不寒。约束家童好将护,他年留与子孙看。[45]
此诗继承了牡丹欣赏传统中以牡丹喻品格、操守的传统,甘于淡薄,积极为政,暗含要像呵护这美丽的花朵那样呵护边地百姓,令边塞事业千秋万代绵延不绝。
青海地区地方官的牡丹诗中类似的表达比较多,如杨汝楩此诗:
十年不见真奇获,裂鼻浓香底费寻。出塞明妃家万里,归曹蔡女值千金。来分绮谷繁华夜,不惹红尘富贵心。寄语灵和张令尹,洛阳珍重到如今。[46]
以美人喻花朵,很常见,人们一般是牡丹与杨贵妃相联系。此诗的不平常处在于用来作喻的美人是王昭君和蔡文姬。他们留名青史主要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被迫远离家乡,或和亲,或被虏。以归来的文姬“值千金”表达对中原的期待。颈联转,以花言志,表达尽管远离故园,但依然会履职守责,不期富贵,心向中央。文人风骨、地方官职守、西陲地域等均由此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如此书写,包含的是对中央的边陲、民族政策的认同,是传统历史文化发展到清代集大成的体现。汉至元,这片土地上战乱频发,屡收屡弃。从地方官兵将领的咏青诗来看,多呈现边地苦寒情景,多书写收复边地的豪情壮志,是“客”之视角。至明代,这一情形有所变化。明代御史詹理,浙江遂安人(今浙江淳南),他任职西宁道时有诗云:“湟中四镜接穷荒,揽辔西游肃命将。……自愧菲樗空倚剑,升平何以答明王?”[47]兵备副使露珠《边城感怀》云:“性戆慵成癖,苦寒今始尝。……胡笳不断耳,何计静边疆?”[48]诗中既有对既往边地主题的沿袭,也开始思索如何治理此地。至清代这一变化更明显,如:
贪把祁连照颜色,如何久住竟成家。(杨汝楩《雪中寄怀钱野堂》)[49]
十年抚字颠毛短,百岁升平化宇长。但愿吾民勤且俭,何妨湟水作桐乡。(杨应琚《郊原》)[50]
千里云烟飞眼底,万家忧乐系胸中。(丹噶尔同知封启云《登北极山归得》其一)[51]
谁言荒僻是边陲?酷爱南城会景楼。(碾伯令张恩《南楼远景》)[52]
上述诗句显示,在清王朝的统治下,青海地区地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地方官有了“主人”之感:他们以父母官自居,开始考虑如何促进地方的繁庶,提升地方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官一样,着力从事书院、义学等的兴办、管理工作,地方文化得以普及、提高。杨应琚曾在署衙栽一小松树,受限于当地的气候条件,“今已十年矣。仅高三尺,培养之不遗余力”“余爱其有岁寒之心,非利其有栋梁之致。培而养之,将成国器。弃而置之,恐与蓬蒿无异”。[53]他表达了对任地之民不遗余力地培养教化,及对他们的期望。他还说“何所独无芳草?况宁郡上应东壁之墟,乃图书之府,精气下注,人杰生焉。物产既不逊于中原,岂独于人而有闭?诸生勉乎哉”。[54]杨氏相信此地属于星象学所预示的人杰地灵之所,并以物产与中原对比,勉励诸生,表达了对当地倡兴文教的信心,并传递给当地学子及后来的为官者。经过几任地方官的接续努力,清代青海地区呈现儒学兴盛的局面,西宁府及下辖各县、厅均有数量较为可观的儒学、义学、回民社学、书院等,缔造了边地牡丹悠然盛开的状况。道光三年,陕甘学政张岳诵视学西宁时即言“美哉此邦人士可与论学矣”[55]。光绪三年,时任湟中书院山长的皋兰人金文同发出“欲使边陲媲邹鲁,雍容弦诵洽诸羌”[56]的期盼。他们努力消除边地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体现的是进用文治,化民成俗,增强边陲对中央的向心力的终极目的。
这种地方认同感还体现在对边地文化的认同上,看杨应琚此诗:
天彭旧号小西京,无计移根蜀到秦。秦人共说延安好,不道阳关别有春。[57]
“天彭”是著名的牡丹产地。杨应琚首先说名贵的天彭牡丹无法移栽到秦地,延州人也只认为他们本地出产的牡丹最好。言下之意是一方水土自有一方风物,不可随意移易以免水土不服。暗含与之相比,离家万里为宦的自豪。接着诗人写喜出阳关,本应是“无故人”,未料这里不但有故人可共同出游,共享快乐,而且还有珍贵的牡丹生长此地,“连辘并辔出城南,纷纷红紫来重沓,忽见疏篱烟雾斜,停鞭暂憩野人家。姚黄欧碧栏杆外,照耀祗园优钵花。”[58]“祗园”是释迦牟尼传法之所,“优钵花”,佛的瑞应之花。“祗园优钵花”在此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指城外“野人家”的牡丹突然出现在眼前所带来的喜悦感以及吉兆的期待,也有可能是实指,此花附近有佛龛或寺院,花朵与寺院相辉映。无论如何,牡丹与优钵花的互相辉映,反映出边地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多元并存的现实,也显示了杨应琚这样的地方官对地方文化的态度,极可能是对藏传佛教的包容。
总之,边陲牡丹本身昭示了边地与中原的同质,避籍官员借此表达对任地的地方认同感,对地方治理的信心,以及对中央王朝的使命与担当。他们积极推行中央王朝的文治政策,发展儒学和中原文化,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多民族聚集的边陲生根发芽,又使得区域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增强,边陲与内地的差异逐渐缩小。地方官的努力与地方面貌的改变互为因果,青海地区地方官的地方归属感、认同感大大增强,“出塞”不再是悲悲戚戚之事,“归汉”也不一定是唯一目标,寄寓在牡丹上的情感自然也明朗、壮大起来。也正是这些官员们的文化选择与态度以及化育,决定了很长一段时期青海地区士人的精神面貌与价值选择。
四、青海地区牡丹欣赏的文化意义
从上述对青海地区牡丹欣赏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下可能潜藏着地方文化生态、文化接受与文化传播、不同群体的文化心态、文化选择等诸多根本性问题。
其一,一地的文化生态是复杂、多元的。在同一时空下不同身份群体,分别有各自的文化空间,甚至会形成不同身份群体的文化群落。在某个特定时期,因为特殊因缘某些群体在某些文化方面可能发生迅猛的变化。有的空间会交叉、互相影响,如地方官与本土文士,有的就相对封闭、自足,发展缓慢,如民间百姓。综合来看,中央集权的古代社会,青海地区牡丹欣赏的文化生态体现为多元文化形态的杂态共生、和谐发展,既有本土化的特殊性,也有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融汇、贯通。这些共同反映出不同群体应对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选择和群体身份特性。
其二,在中国古代,决定地方主流文化发展方向及水平的是地方官。清代青海地区的地方官在文化建设方面是十分积极努力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规定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要对地方文化负责,“封疆大臣等并有导化士子之责,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59]顺应帝王要求,地方官在治地大力兴学,推行中央王朝的主流文化,这些会以强大的冲击力影响本土文士的思想、观念,上述青海地区本土文士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以及他们能够走向王朝仕途,无一不得益于地方官的教育和文化举措。本土文士对历代牡丹欣赏中层累的丰富意蕴的熟稔也应得益于此。地方官与本土文士有时会产生师生关系,如来维礼与豫师⑭。他们也经常风雅唱和,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文化风尚,如董志儒与当时丹噶尔同知王恩海⑮的《咏科斋白牡丹(七律)》唱和;如五峰书院落成时,地方官员豫师、张宗翰、邓承伟,邑人张思宪、来维礼等十几人唱和作诗近30首⑯,诗中多有对地方官兴学化俗、传播儒家文化、提高地方文化水平的赞誉。
实际上,清代青海地区的地方官是配得上这些赞誉的。他们大多有勤恳踏实、尽心职守的优秀品质。如封疆大臣广西人陈宏谋写给杨应琚的信中所说,“吾辈居官不择地、不择官,惟就可以尽心措手之处埋头做去,此外升沉迟速皆非所知,淡于仕进,切于措施,宁静致远,义取诸此役。”[60]他们身上涌动着对这片土地深切的地方认同感,出塞的使命、担当以及乐观自信的精神。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重读那些牡丹诗词,不仅是重温地方官寄寓牡丹的别样情怀,更是在接受一场精神洗礼。杨应琚强调,西宁重于河东西,“惟在任文武者,视国事如家事,加之意而已”[61],他们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家国同构的主流文化精神,将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回应着当下西部的建设与发展,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文化的融通、综合与创新。“清王朝没有割断自己与前代的联系,相反,文化传承是它存在的最堂皇的理由,它是以传统文化弘扬者的身份自居的。只要是古典的就是美的,只要是古典的,同时也就是自己的,这就是清人的审美观。”清人善于在“融通与综合当中构建自己的时代特色”[62]。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本土士人的牡丹吟咏表现出的是在融通,在综合历代的基础上使牡丹意象在边地呈现融通、集成的新特性。地方官员受时空、地域转化的激发,实现了中原与边地、昔日与当下“牡丹”的融通与综合,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这不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古代边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吗?
其四,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牡丹文化的共性因子在中原以外地区得以留存,并因地域和身份差异产生了多向发展,体现的是牡丹文化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普适性。无论是民间多民族对牡丹的共赏,还是本土文士对传统牡丹意象的继承与发展,抑或地方官员寄寓牡丹的双重负载,都体现了传统文化意象强大的包容性、凝聚力、向心力,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影响力。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在唐蕃古道、丝路南线近中亚的节点上,沿线的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面临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话题和难题,清代青海地区的牡丹欣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参看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王莹:《论唐宋牡丹诗词的政治文化意蕴及其表现艺术》,《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阿进录:《“牡丹”:一个“花儿”经典意象的文化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雷燕:《牡丹文化意象与西部多元民俗文化认同》,《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等;方丽萍:《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
②原文作“誇”,应为简体字“夸”。
③张思宪(1828—1906年),字慎斋。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拔贡廷试第一,分发湖南,后改派四川,因故未赴川。同治年间,为避祸与兄张思元入川谋官。候官八年,46岁始得永宁县知县职,仅一年因不满官场黑暗辞职,回乡后讲学于碾伯(今乐都)凤山书院和西宁五峰书院。
④基生兰(1870—1944年),字香斋,号半隐山人,西宁人,光绪年间岁贡,宣统元年(1909年)民国时任甘肃省咨议局议员等职,曾主讲湟中书院、五峰书院,曾与朱耀南等人结成‘吟楼诗社”,活跃了青海诗坛,著有《敬业堂史论》《敬业堂嚼蜡吟》,续修《西宁府续志》“志余”部分。
⑤此诗作者和题名有争议,参看路成文:《〈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作者考辨》,《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185页。
⑥杨应琚出身显宦世家,历任甘肃按察使、甘肃巡抚、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等,加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两次任职西宁道达十六年。
⑦杨汝楩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任西宁府知府。
⑧申梦玺于乾隆四年(1739年)任西宁府知府。
⑨以牡丹书写贬谪离京之感及牡丹象征首都、中央或中原的观点,参看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166页。
⑩探讨客籍官员时,材料使用兼及客籍官员任职周边时所作抒发相似情感的牡丹诗文。
⑪王以中(1691—1752年),字愫公,号时斋,晚号梅岑,汉军人。
⑫文献中对其名的记载有4种写法。一是“卢泳清”,见《西问诗草》刻本及光绪十一年刻《湖南通志316卷》“选举志”、民国三十年刻《宁乡县志(不分卷)》,《西宁府续志》卷九“艺文志”。诗集是其同乡挚友廖树蘅藏匿,命其子校刊的,其余方志出其家乡与任职地,较可信;二是卢咏清,如寻霖,龚笃清编著《湘人著述表1》(岳麓书社,2010年,第170页);三是庐咏清,如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102页);四是卢洞清,错误源于《丹噶尔厅志》,基生兰《西宁府续志》卷十“志余”“官师志”和清宣统元年刻《甘肃新通志100卷》沿袭。应是形近字传抄讹误。
⑬今有光绪三十四年宁乡廖氏珠泉草庐刻《西问诗草》一册三卷290余首诗,存湖南省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⑭有来维礼《五峰书院落成谨步豫都护夫子原韵四章恭呈张价翁观察》《上豫钦差老师七律四章》诗可证,见来维礼:《双鱼草堂诗钞》,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21,267—270页。
⑮王恩海,字星源,顺天宛平人。
⑯据笔者统计共有14人26首诗:《西宁府续志》“艺文志”录15首,张思宪诗集录2首,来维礼诗集录4首、卢泳清诗集录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