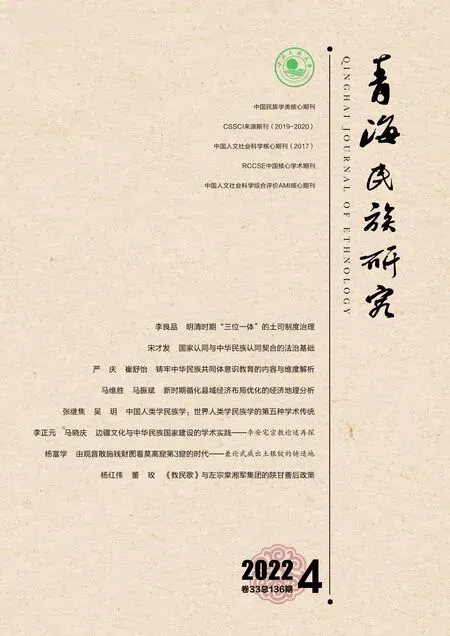跨越“对称”边界:礼物与礼数的交换
——以临夏八坊社会的礼品流动为例
鱼 耀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临夏是西北重要回族聚居区,也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地处农牧交错带的优越位置不仅为当地提供了良好的经商条件,也使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藏文化在此交汇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区域社会,八坊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聚落之一。这里不仅保留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还形成活跃的营商氛围,使得八坊人自然地熟知各类物品的流动规则,更将其中暗含的社会伦理与礼物交换相结合,发展出深嵌当地社会结构的“礼”①文化。
有意思的是,生活中八坊人相互间虽关系往来频繁并常伴有礼品的流动,但送礼者更多关注的却并非所赠之物的贵重与否,而是不同种类物品间的相互搭配组合,受礼者更多在意的则是物品所传递的情谊伦理,且前者不甚期待回礼,后者不太强调多寡。乍看之下,这一情况似乎与经典理论刻画的礼物交换中收受双方的对称语境有所矛盾,如若要进一步解读这一现象,则有必要回到人类学传统中关于礼物性质的讨论上。
一、问题的提出
“礼物交换”是人类学传统命题,早期围绕礼物本身的研究出现了诸多争论。其中,关于送礼与回礼的平衡问题一直是核心焦点之一。
礼物研究集大成者马塞尔·莫斯坚持对称观点,并发展出“全面报偿体系”以解释整个交换过程,还将其延展到人的问题,认为个体生来即有馈赠与接受的义务,对任一行为的不履行即可能引发双方冲突,他将之表述为“不管是一个氏族,抑或是一群人,都难以有所选择,只能寻求好客:通过姻亲或血亲关系接受礼物、进行贸易或达成联盟。……拒绝赠礼或失于邀约,就像拒绝接受一样,等同于宣战;因为这在本质上被视作拒绝联盟与共享。”[1]也就是说,本质上收受双方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二元关系的平衡,赠礼者与受礼者以礼物为纽带实现两者间关系的对称,即莫斯所说的“Symmetric”。若以此延伸,八坊社会盛行的并不太期待有所回馈的礼物赠予,则明显难以构建良好有序的人际网络,那这种失衡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朱利安·皮特·里弗斯是最早用自己的研究案例对这种情况进行阐释的学者之一,在关于安达卢西亚的著述中他提到,行乞者在有人给予施舍后,会用“愿上帝补偿您”回应。如此,“报偿”的义务便被转移给了“上帝”来完成,而非受惠者本人。[2]同时,非互惠特征不仅表现在交换主体上,也会出现在礼物自身。T.K.莱博若关于日本的研究发现,“在当地的等级情景下,处于下级位置的赠送者根本不能完全回报从上级那里收到的礼物。”[3]V.P.瓦图克和希尔娃·瓦图克对印度“檀施”之礼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此观点:“种姓地位低的人——特别是和赠礼者相比如果他们在经济上也处在从属地位的话——一般无须回报他们从高种姓者那儿收到的礼物。”[4]有鉴于此,乔纳森·帕里尝试利用“延迟互惠”概念对这种不平衡给予解释,他觉得“檀施”确实不要求回报,但最终则会以“业报”形式给馈赠者以报偿,只是在时间上被延迟而已。[5]罗伊·瓦格纳并不这么认为,他直接指出莫斯以来关于对称性的想法只是一种主观虚构,交换不平衡才是世界常态。[6]
既然礼物流动不能实现有效回馈,而互惠亦不是普遍存在,且还要面临时间上的风险,为什么交换活动却并未显现出式微迹象呢?詹姆斯·莱德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用耆那教的例子进行说明。他提出“檀施”作为一种馈赠,因存在无须受礼者回馈的特性,遂使信众与修士之间形成了长期的交换关系,“檀施”积累的功德作为神灵的回赐被施予给济施者,修士作为神灵的代表对施济的漠视进一步激发了信徒的赠予,为答以回报,修士则更需维持自身宗教实践。[7]
同耆那教信徒与修士相互促进的关系相似,八坊人也一直保持着互通礼品的习惯。但不同之处在于,八坊的赠予更多是一种日常生活之“礼”,与基于宗教信仰的“檀施”和“布施”皆有差异。如果结合当地多重文化交融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实际上,人们最终期待的是自己的行为能否被放在“社会伦理”的合适位置,这与经典理论强调交换双方在主体与对象上保持对称不同,其已在回报形式上超越主体,更多地表现为收受双方与社会间的关系。
若要更全面地理解这种特殊交换,最有效的途径即是将之放置在当地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加以观察,如此,方能更好发现为什么在八坊人生活里礼物既至关重要,又轻描淡写。
二、八坊人的送礼实践
列维·斯特劳斯说交换观念是人类固有本性,[8]八坊人的相互赠礼即真实地阐述了这一论述的理论效度,对当地个体交换行为的展示将很大程度上推动我们的理解。但进行深层讨论前,首先需弄清八坊生活中的礼物到底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与情境组合并实现伦理自洽,嵌入人们日常的,如此方能更好地分析当地社会“既有送礼事实,又不甚期待回应”的现象。
(一)不同类型的礼物
八坊人生活中所送礼品通常可分为三类,一是现金,一是实物,一是宗教义务。
1.现金类
以现金为礼,多出现在重要庆典,结婚时的“人情钱”即是典型代表。八坊是传统熟人社会,有快捷的消息传播渠道。通常,街坊邻里如得知某家有喜事,若跟此家平时有往来,就会准备参加喜事的事宜,大家会推选一人做代表询问彼此意愿。待意见相对统一,便敲定具体行礼时间。一般,鉴于婚礼待客考虑,此前已商议妥当的亲朋、邻里常会在“娶亲”前一天,即习惯称为“人情”这天去祝贺,同时送去一定礼金,也就是所谓送“人情钱”。数量多少往往取决于送礼者与受礼者关系的亲疏程度,多数人随礼金额在一百元以上,两三百块钱较常见,五六百元也不算少,一些近亲的礼金数额甚至会达到数千上万。笔者田野期间曾遇到一次婚礼,新郎的亲朋有多人随礼金额超过两千元,姑姑更是送礼五千元以上。由此,个体关系的差序性直接体现在了送礼数量上,并反衬出对应的社会结构。[9]一位调查对象说:
现在结婚都是搭钱,一方面是习惯了当下的生活习惯,一方面是不耽误事。身边人家中有了喜事的时候,作为亲戚、朋友,我们都会给东家送去一点“心意”。大多数人觉得拿现金对自己、对对方都好,都实用。(因为)有时候送过去的礼物对方不一定喜欢,拿现金也能在一定程度帮助(对方)。我同学或朋友他们结婚的时候,现在最少也要拿100元,关系好一点就“多多益善”了。②
2.实物类
与现金资助的差序等级相比,实物馈赠更能反映八坊人送礼中的社会伦理及情景调适。
一是日常礼物。平日亲戚朋友间串门是琐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们所言“关系在于你来我往”,不管是有求于他,还是无事“闲串”,大家都乐在其中,“礼”遂成为锦上添花之物。彼时,人们常比较随意,一只羊腿、一只鸡、一两板鸡蛋、一箱牛奶,甚至自己制作的认为值得与对方分享的任何东西都可成为礼品。但虽说这种往来带有随意意味,却亦暗藏一定规矩。多数情况,晚辈到长辈家,一般会带四分之一只羊,再加水果或其他东西。同辈间主要取决于关系亲疏,越是熟悉,礼越随意,有时甚至不送为好,送了反而让东家心生嫌隙。如果不是非常亲密,走访时也会带羊肉,再搭配三四种礼或饮品、水果等。
二是节日礼物。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八坊人亲朋间互动尤为频繁。送礼有时从开斋节前一天就已开始,以前主要是将自家制作的油香、馓子等送给亲友品尝,都是晚辈先到长辈家做客,再到同辈家走动。现在去长辈家送礼,通常包括鲜羊肉,水果、饮品、茶叶、桂圆、枸杞、红枣等。长辈给晚辈回礼几乎与之相差无几,但品类会相应减少。古尔邦节时,亲朋间会在宰牲结束后,带少许新鲜牛羊肉相互赠予,以营造节日氛围,共同分享佳品。八坊人认为节日之间的礼品互赠不仅是一种往来,也是一次契机: 八坊人的主要节日就是开斋节和古尔邦节,这两个节日期间亲友们走动和馈赠礼品是首要和必须的。开斋节时,第一天“邦达”散后,邻里间送礼就开始了。主要是把自己家做的油香、油果果、馓子、烩菜等送给邻居们品尝。而邻居家的节日美食也都会集到一起,看谁家果子又香又甜、造型更美,看谁家烩菜色、香、味俱全,这时候也是邻里间妇女们比拼厨艺的好时机。另外,节日送礼时,若此前邻里间有矛盾,现在相互道声“色俩目”,彼此恩怨勾销,以后就正常来往。
3.宗教类
八坊社区另一种特殊“礼物”即是宗教层面信仰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相互责任与义务。通常,八坊某家有丧事,便会第一时间将讣告传达给各清真寺,寺里又将讣告转达给前来礼拜的人,一般都会给亡人举行殡礼,多在晌礼后。这既是仪式,也是坊民给亡人的送行和对他的深切缅怀。“礼物”与宗教的双向关联性,在为这种行为赋予赠与性质的同时,使其更具有神圣性,表现出一定的相互性伦理。[10]
从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馈赠中可看到,送礼行为常与个体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是以现金为媒介,体现亲疏远近的不同梯度;有的是通过实物馈赠的搭配,说明长幼尊卑的社会秩序;有的是以宗教仪式为契机,履行共同体成员肩负的群体义务。但无论形式如何,其本质都可看作不同个体尝试以自我为中心,为寻求在社区结构中的恰当位置,不断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数”的实践,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活动中“礼物”与“礼数”密切相关,难以分割。那在八坊,这种深嵌社会结构的“礼数”究竟是什么呢?
(二)礼数——送礼的回赠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儒、伊、藏三重文化在八坊交融叠合,和谐共处。其中,儒家思想对当地影响特殊,不仅促使八坊人重视礼仪规范,而且使得他们的礼节观念尤有地方特色,多重因素影响下,八坊人亦有“儒回”之称。③这为本土社会“礼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推动“礼数”与交换发生关系,使其逐渐发展出“回赠”功能。但在具体送礼实践中两者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呢?
第一,“礼数”是维系当地交换关系梯度化呈现的重要原则。八坊人的礼品与自身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已融入每个人生活细节中,大多数人认为“反正去走亲戚,带点什么会比较好,否则好像缺了点什么。”也正是这些细微之处,他们遵循群体内部的“礼数”,如长幼尊卑。平日里,晚辈去长辈家拜访,所带礼物一定是经过精心准备,数量与质量合理搭配的“五色礼”“六色礼”甚至更多的“X色礼”;长辈到晚辈家通常在份数和搭配上比晚辈少一些,如“四色礼”“五色礼”等。另外,亲疏远近在日常“搭礼”中也表现明显,近亲属和关系亲密的友人所随金额多数较大,而远亲和普通交际往往随礼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不同情景中“礼数”对交换行为所展现的规范性亦有所不同,人们基本按照既定事实进行互动。
第二,“礼数”是八坊熟人社会相互赠与的往来基础。“礼数”在不同语境的映现使人们能延续符合自身社会身份和群体结构的行为,八坊人深谙其中道理。由于历史上与当下八坊活跃的商业活动,促使其内部至今保持着高度的熟人社会特征,生活中礼物交往很容易被其他人放大观察,不合规矩的礼品也会被周围人品评,这种压力往往让人们清楚懂得“礼数”的约束和规则,并在交往中加以注意。因为“这样一种交换关系总是把目标放在关系的维持上,而不是由自我利益产生的一次性平等地获得上。 ”[11]
第三,“礼数”是个体送礼实践中寻求结构性位置的标尺。因八坊社会多重文化交汇的特点,促使人们对公序良俗规范尤为重视,也就使得公众在送礼时不仅熟知普遍的礼物搭配,而且更注意把握自我身份,极力使不同情境中的礼物交换符合自身地位与声望,也就是寻求与本体社会结构位置相匹配。所以,他们会说“我和他关系很好”“他是寺上的学董”“他家里生意做的大得很”。恰是在这样一种既定设计中,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并形成某种超脱日常的契约关系。[12]
这样的语境下,“礼数”已然成为八坊社会的文化基础,人们在交换过程中自然地将之作为指导个体行为的内在逻辑加以遵循。最终,当其外显在实际生活往来中时,基于维系关系的需要,他们便并不太在意对方会不会立刻回礼以及回什么,什么时候回的问题。因为在当地文化场域内,自身行为已然符合“礼数”,这本身就是一种“回赠”。
不同礼品的流动构成了八坊生活中丰富多样的“礼文化”,个体对积极社会身份维持的需要,让与东家处在不同维度的亲友在确定各自亲疏远近的同时,送出礼物,并借助外在社会伦理完成回赐。可究竟该如何理解“赠—回”过程中交换主体在社会空间上的错位展演呢?
三、跨越“平衡”的交换
莫斯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补充需要,在结合集体互动、人物混融事实提出的交换理论始终包含着必须由受礼者归还给予者的本性。[13]然而,八坊人却在交换过程中引入社会机体来肩负回赠义务,一定意义“超越”了理论预设。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
(一)交换本身的“不平衡”
首先,八坊社会的赠礼与回礼在交换主体上并不完全对应。八坊人不论是串门走访,还是节日互访,抑或重要人生节点,他们所送之“礼”一方面是因受到不能空手而去的文化节制,一方面是要符合自我社会声望,是出于对礼仪或互助等因素的考量,并不认为是对此前别人所送礼品的归还。即便不能完全剔除这一可能,但最重要的回赐环节并不是实物层面的循环往复,而是人们通过赠礼所期待达到的“懂礼数”,就是所赠之物与送礼者身份在特定情景下的相互匹配。如此,在收受双方之上,八坊人的礼物交换在回礼主体上出现“超越”,它不再仅局限在人的层面,而是有了社会礼仪参与。也就是最终对给予者而言,其关注的回赠并不完全由受礼者完成,相反是通过“社会”这一整体性群体结构来实现的。“礼”并不等于“回”,而是等价于主体每一次社会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其次,八坊社会的赠礼与回礼在交换物品本身也并不对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礼品互赠过程中,因受区域文化影响,往往注重维护彼此身份阶序,这便使礼物在必要的归还阶段可能受到一定牵涉,即并不会在数量等外在形式上与此前所赠礼品完全一致,也就常会出现:晚辈送给长辈许是“五色礼”,长辈下次走访所带礼品可能是“四色礼”;另一方面,回赐多数情况下以“礼数”形式通过社会伦理实现,并不一定必须以对等实物的必要环节来达到交换循环。也就是说,礼品赠送时是由人作为主体完成的,但在回礼最重要的部分却是社会机体来实现的。这样,八坊人的礼物交换就超越了实物上的纠缠。
不过,这种表现在交换自身的超越,本质并不在于物与人的混融,而是要将之回归到本地社会整个交换结构的不一致。如此,才能从内核部分理解为什么八坊人的礼物交换似乎不同于经典命题。
(二)交换结构的“不对称”
若不对八坊人所送礼物的本身价值作过多关注,只围绕送礼过程来看,既可以说当地人的“礼”不太追求回馈,超越了经典理论所追求与强调的“平衡”状态,也可以说并不尽然。因为,一方面对礼物接受者而言,确实不用刻意回赠以寻求所谓的对等。另一方面,赠礼者又并非全无所求,他虽不甚期待受礼者回报,却更希望得到社会的“赠予”,使自身行为符合当地文化伦理,并得到与之相配的评价,以便能被安排在合适的结构位置。换言之,八坊礼物交换过程构建的并不完全是赠礼者与受礼者的二元关系,而是赠礼者、受礼者和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简单来说,送礼者的动机在于梳理与伦理的关系,而与受礼者的互动当属次要。实际上,送礼实践中人们也确实更关注送礼时所遵循的礼制规则,因为“礼数”才是最终的交换主体。另外,八坊社会独特的回赠方式启发我们,在思索礼物馈赠对称性时,要充分考虑真实交换对象的延续,回赠不应局限于“人”本身。如前所述,这种主体也可能会由“社会”这一非实在性的事实存在扮演。从这两种意义出发,八坊人的礼物交换实现了理论超越。
但通过分析也可发现,关于礼物对称性的讨论可以从主体与环境两个方面进行扩展思考。在八坊实际的送礼活动中,“社会”的进入即是主体的扩展,个体依据不同对象与需要作出的选择则是环境上的延伸,借助如此操作,八坊人的交换又实现了回环往复,他们的赠礼行为在此层面又不再跨越平衡,换言之。“对称性”真实存在。
(三)基于“非对称性”的思考
八坊礼物实践的整体表现不仅为理解不同情景中的交换行为提供了一种区域社会视角,同时亦提供了与既往研究对话的可能。“‘礼物’一词由两个字组成。‘礼’的意思是仪式、礼节以及诸如忠孝的道德理念的仪礼性表达,‘物’的意思是物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从词源上讲这个汉语词暗示礼物不只是物质的礼品,它承载着文化的规则并牵涉到仪式。”[14]阎云翔道出了礼物交换中的礼节性问题,并就此利用“表达性礼物”与“工具性礼物”描述日常生活场景里礼物流动的“非对称”现象,但他的关注点更多在于强调两种礼物类型从不同意义层面对构建个体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从八坊的现实场域看,当地送礼实践虽具有维护双方关系,保持阶序规则的意涵在其中,可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传递收受双方的社会声望,表现个体在当地社会的结构位置,以此使两者的往来被放置进符合社会预期的情景之中,这显然超出了简单形塑个体勾连的层面,与阎氏的立足点不太一致。另一方面,从礼物关涉的仪礼性入手亦可发现,阎著基于封闭性农业社区的文化基础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但八坊不仅被儒家文化浸染,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伊斯兰文化、藏文化底蕴,当地人发展的“二传手”商业,使区域社会呈现出显著的开放性、流动性特征。因此,这里的“礼”融合了多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内容,彰显着不同民族交往过程中的群体智慧,绝非单一背景中的策略性互动。前者与后者在“礼物”本身具有的工具性和赋予的“礼仪”问题上具有各自特点。
除日常礼物外,八坊“哲玛提”成员间的宗教义务是一种具有明显神圣特性的交换行为,生者尝试通过仪式性活动为逝者提供必要帮助,并以此积累自身功修,个体关系相对平等,与傣族社会在追求自我与佛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表达出的等级性形成鲜明对比。褚建芳通过追访田汝康的田野点,分析了傣族文化中的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发现在当地分化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根据双方所处地位及相应的需要、权利、义务等界定的不同施报内容与施报规范,这些内在规则构成了区域社会的核心道德和基本伦理。[15]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即秩序构建中的“等级性”。做摆、赕佛的神圣性交流虽为实现人神沟通建立了渠道,但因规模、规则、人员不同,这一过程所获得的功修常会表现出一定差异,与八坊社会信仰群体传递出的平等观念有所不同,彰显出多元文化基础间的张力,也说明在同一类情景中,因个体和群体追求的多样化,最终外在表现意义也会出现反差。
以此出发,立足整个中国社会内核结构可发现,传统亲缘关系中的人情交往,孝道传递亦是八坊区域内部礼物交换过程中的重要核心。[16]除此之外,八坊的“礼物”更在于形塑一种规范性社会模型,尤其注重“礼仪”发挥的作用,强调人情、孝道规则的重要性,通过物的流动表现情谊和维系个体阶序仅是其中一部分。这一过程虽难以超越亲缘网络的传统谱系,但亦在此之外形成了基于宗教体系的关系圈层,与单纯宗族社会场景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另外,八坊的社会结构不仅包含有九族五服的意义性关联,还融合了不同文化体系的宗教、民族知识。因此,很难利用基于单一背景提炼的理论模型对其加以解释或比较,不过这种视角亦可成为透射八坊礼物交换实践的一个镜像,从而更深刻地对其应有之意进行深度解构。
八坊的“礼物”从物品自身和社会结构两个不同方面表现出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内涵,从而提供了与前人著述对话的可能,但通过研究可发现,不同研究者面对的对象不同,其背后的文化铺垫不同,加之社会诉求不一致,促使同一行为在不同环境中意义不尽相同,着眼点也自然有了差异。故要理解八坊交换实践的“不平衡”问题,还应充分理解蕴藏其后的地方知识,并从现实角度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分析。
四、结 语
八坊送礼实践在整合传统中国“礼”文化包含的身份阶序的同时深嵌当地社会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凭借社会伦理调节个体行为与社会互动的事实。生活其间的人们则通过与社会创造联系扩展礼物交换的主体与时空,在现实层面创造出了一种看似“无需回礼”的不平衡状态。
但最终个体层面的不对称经过社会伦理的介入实现了理论角度上的对等,将看似超越经典的活动又拉回生活之中。同时,八坊礼物交换中个体表述差异的出现,使个体社会关系向不同维度扩展,形成了多重交织的情况,不仅具有一定的梯度差序,还融合了本土社会、信仰体系等多个内容,最终使群体互动中的个体赠与成为收受双方并连带区域社会的日常性行为,表现出小社会体系中的自我文化特征,为我们重新思考礼物交换实践中的主体性和空间性提供了可能。
人与社会间的往来拓展了囿于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主体存在,使我们的关注点可以延伸到更细致、多元的角度,从而有机会深思“礼物”所表现出的工具性,其不仅推动了不同主体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所传递出的礼仪问题。以往对这重特性的关注多出现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而八坊却是一个基于多重文化体系形成的多民族社区,礼物强调的“礼”自然地融合了不同语境的内涵,这从根本的基础层面对经典理论与既往研究形成了一定挑战。
除此之外,八坊礼物流动过程中话语空间的塑造亦具有明显的平等性特征,个体身份上的阶序因宗教文化的影响很难对交换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日常空间与神圣空间都表现出一种立足传统的文化惯习,利用结构性动力推进个体意义表达在社会层面的流转,并以此将物所内含的各重逻辑编织到区域社会网络之中。
注释:
①这里所讲的“礼”主要指“礼物”。
②文中所涉资料皆来自作者2017年7—9月、2018年5—8月在八坊调研所得。
③资料源自八坊民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