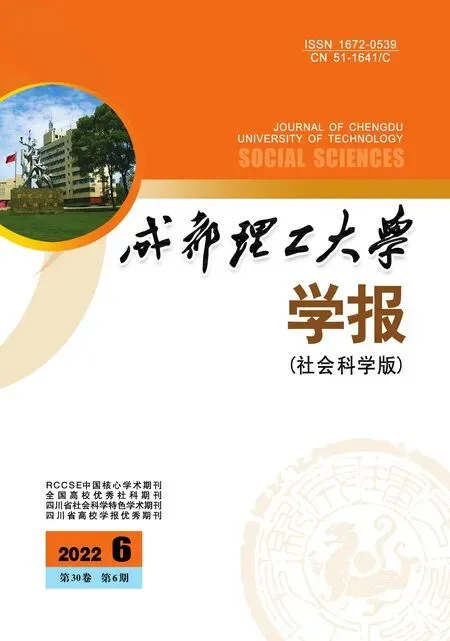《文城》中的“原型结构”分析
张少娇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余华从八十年代开始便想要写一部传奇小说,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文城》。《文城》不仅完成了余华对于传统浪漫传奇叙事的满足,在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后,《文城》饱含着余华对写作、对人性、对命运的思考与理解,同时也展现出其成熟的写作技巧以及重复出现的“原型结构”。提到原型结构就要分析一下“原型”“原型批评”的范畴,荣格对“原型”的定义建立在其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集体无意识”这部分理论。他认为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并且在“原型”应用到文学艺术创作的分析中,指出“一旦原型情境的发生,我们会突然感到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1]249所以荣格将“原型”与历史演进中的神话形象联系起来,将之视作普遍人类心理先验的投射。弗莱将“原型”引入文学领域并加以改造,指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2]99弗莱的“原型”不再局限于神话原型,而将其范围扩大到文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意象、主题、结构等,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原型结构”不仅是整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也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表露出的深层思考模式。纵观余华的创作,不难发现其作品中典型的重复出现的结构,这并非固化的叙事模式,而是余华使用虚构的权利安排笔下的人物经验未知命运的手段。余华在新作《文城》中对“原型结构”的驾轻就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写作技法,更成为一种对存在、对人性的思考方式。
一、“道路”原型结构
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余华总是将“道路”作为文本的一个原型结构。“道路”在余华 的文本中频繁出现,已经超脱于一个独立存在的意象,而进一步成为一种文本存在的结构方式,“道路”在余华的文本中起着叙事的框架作用,也是其叙事的一个重要的隐喻场。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余华小说创作的基调。这部小说的开篇就是一条道路,“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3]1余华给文中的“我”,送上的十八岁成年礼是踏上一段前途未卜的旅途,所以“我”离开家越远,就越是离“晴朗温和”的正常世界越远,途经的种种暴力、哄抢、冷漠等非正常客观秩序,便是这个“道路”结构的隐喻指向。余华有意在自己的文本中建立一个隐喻世界,将生活中事物的能指意义进行解构,进而按照自己对事物的认知与想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冒险和人性试炼。不难发现,在余华的文本中大量出现的“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叙事的结构性功能。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后,“道路”作为一种原型结构总是反复出现在余华的小说文本中。在《古典爱情》里,柳生赴京赶考,行走在一条黄色大道上。从初次踏上这条桃柳争妍、桑麻遍野的大道,到三年后这条路变成了尸横遍野、贩卖人肉的炼狱之路。小说情节的演进始终发生在这条黄色的大道上,同时,文中每一次出现黄色大道,都会是情节的巨大转圜之处,现世的才子佳人与噩梦般的人间炼狱,以黄色大道的反复出现将柳生的现实与迷梦混淆,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幻的错觉。人物的命运也同黄色大道的屡次变化保持了一致性,在这个层面上,道路具有了隐喻性,指向变得深刻而尖锐,当人世赫然幻化成鬼途,人间的伦理就显得荒谬可笑甚至可以肆意践踏。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一个完全隐喻的世界,在这个隐喻的世界里,每一件事物都有意指其他事物,似乎一切都是处于一个单一的无限本体之中”[2]150。“道路”在余华的文本里,便成了一个完全隐喻的世界,道路的无尽延绵引出了许多异于常规的情节,“道路”就是亘在文本里的骨架,这些现世不合理的故事唯有发生在“道路”中时,才具有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余华颠覆性地构建了一个充满讽喻的隐喻世界——“第七天”。这条处处游荡着亡灵的黄泉之路,理想中公平的审判之路,反而有一套森严的等级秩序,所谓的善有善报皆是妄谈,唯有金钱与权利才是转世投胎的筹码,这不啻是对现世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文城》中,余华已经非常娴熟地使用“道路”原型结构进行文本的创作,整篇小说围绕着两条“道路”展开,一条是林祥福从北方背着襁褓中的女儿南下寻妻的路,一条是纪小美和阿强由南向北流浪求生的路。正是这两条道路架构了整个文本的框架,分别作为《文城》的正篇和补篇。在正篇中,“林祥福向南而行,他将女儿放在胸前棉兜里,将包袱放在驴驮上,手牵缰绳走在尘土滚滚的路上”[4]53。正是这条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缥缈之路,开启了林祥福动荡又传奇的一生。在补篇中,“小美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明白了,阿强不是来接她回去溪镇沈家,而是带她走向未知之地”[5]270。小美和阿强这对小夫妻踏上的叛逃之路,彼此都心知肚明这将是一场流亡。两条“道路”作为介入小说中的结构,不仅承载了叙述的作用,也一如既往有着隐喻的指涉。
《文城》中的这两条道路看似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追寻——寻妻与投亲,而实质上却是一场徒劳的探索。“人化的无机物世界之运用,这种意象包括马路、车马小道以及街道纵横的城市,而且路这一隐喻是与所有的文学中的追寻故事分不开的。”[7]201林祥福最终并未能寻到文城与小美,小美和阿强也不曾抵达京城寻到姨父。在这里,文本中实体的道路,实际上是林祥福与小美的人生之路的隐喻。纵观全文,他们在最初都以为自己踏上的是一条通向希望的路,都倔强地想要追求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到头来却是一场无力的求索。
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在《文城》中倾注了对人性与命运的体察。他不再固执地用先锋时期那种锐利地搏杀与僵硬地对峙来检视人性之幽微、命运之不可预测,而是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与偶然,并且接受了这是人生的常态。这两条道路作为文本的结构,隐喻着两人的命运之路,道路曾经交汇,两人的命运也就安排了一次重逢。“兄弟四个歇了一阵子,再次扛起棺材板车,嗨呀嗨呀地走出这段最窄的路。然后他们上坡下坡,艰难前行,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了小美这里。他们见到七个墓碑,见到小路在这里中断了。”[4]335林祥福与小美死后在墓园中的短暂重逢,也许是余华对文中两条道路象征意义最慈悲的注解。余华用虚构的权利制造的这次偶然,更像是余华写作中的一次作弊,在命运的长途里旁逸斜出一条小岔路,用传奇的巧合装点世事无常的残酷。凡人无法揣度命运的轨迹,但将时间的线拉长来看,所有的谜题都会有一个答案。林祥福与小美的道路最终交汇,但马上又各自沿着原本的路径继续延伸下去。这样的收笔是余华对命运玄机的一次窥视,也许千万条道路不过是命运这部庞大机器的一个齿轮,相遇和离别看似无情却早已悄然注定。
余华笔下的“道路”作为文本行进的重要框架结构,使得叙事的推进总是发生在道路上。同时,“道路”也具有非常强的隐喻性质,行走在这些道路上的人并不知道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走,在道路上去遇见未知,进而承受命运的洗礼。所有在道路上的追寻都无意义,道路本身便是意义。
二、“出走”原型结构
余华创作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都充满了不安定的因子,他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出走的使命感,他们看似洒脱不羁乃至叛逆无序,仿佛挣扎在离经叛道中就能完成自我的认知与建设,实现个人的意义,但实际上他们却不约而同通过出走的方式走向既定的命运,“出走”也就成了余华创作的小说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型结构。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出走”就已经成为余华的一种叙事结构。父亲递来红色背包,“我”就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这次出走没有理由,而是像为了出走而出走的一次仪式。这篇小说对余华写作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他反复提及李陀在看完后,以相当肯定的语气对他说:“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展示出的先锋性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的先锋性,他不玩弄语言迷宫和叙事圈套,而是直指一种先锋精神,即“以非逻辑的内心真实为原则,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让人物在各种错位的生存环境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现人类存在的荒诞性”[5]51。余华曾提到过,李陀的鼓励使他越写越大胆,在制造背离正常秩序的结构中,余华钟爱使用“出走”原型结构,这为制造违背正常道德伦理秩序,并且消解人物性格做了很好的背景铺设。
自“五四”时期以来,“出走”原型结构被许多现当代作家所喜爱。“娜拉”式的人物有很多,他们的出走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实现自我独立,就是觉醒后宣布与旧势力彻底决裂。总而言之,这些“出走”中总是蕴藉着强烈的价值追求。“原型是潜伏在具体作品中的人类的或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社会性的共同情感’,它是由思想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6]97出走就是人类共同的一种心理范式,唯有离开熟悉的故土,才能在陌生世界的荆棘丛里,将自身的恐惧与战栗绽放出来,然后直面最真实的自己。
但在余华的创作中,他将“出走”原型结构先验的意义消解了,在这里出走变得无意义。余华笔下置身在“出走”原型结构中的人物,不再局限于寻求独立的女性,以及觉醒的青年,而是还有稚气未脱的少年。《鲜血梅花》是一个古典武侠小说的套子,一个复仇的叙事线索,这使阮海阔出走的动机非常充分。但余华将整个复仇事件的意义进行了彻底地消解,“阮海阔听到了茅屋破碎时分裂的响声,于是看到了如水珠般四溅的火星。然后那堆火轰然倒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7]3。母亲的自焚断了阮海阔的退路与归途。余华不仅没有给阮海阔一身惊世骇俗的武艺,更是让其在出门之前就找错了仇人,他追寻多年的白雨潇和青云道长其实并不是杀害阮进武的人,而真正的凶手刘天、李东死于他人之手。所以阮海阔的出走根本就没有意义,他漫长又孤独的复仇显得滑稽又荒诞。于是,阮海阔的出走就成了一次纯粹的“出走”。
余华看重“出走”结构能够指向纯粹与无意义,所以,《文城》看似是规矩的传奇小说模式,但这并没有妨碍余华用“出走”原型结构来搭建人物的命运框架。在《文城》的正篇中,林祥福放弃了北方那个累积了世代财富的家,挥别故土,毅然决然出走,去寻找一个存在于传说中的“文城”,而实际上,“文城”本就是小美和阿强编织的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直到补篇中才被戳破。所以,林祥福出走的意义,在小美撒谎的时候就注定要被消解殆尽。林祥福背着像山一样的包袱,经历了龙卷风与雪灾等重重磨难,保护着女儿一路南下,最终凭借记忆中小美轻快的语调与溪镇人们口音相似而在此定居。他在溪镇过完了余生,但即便是临终时分,他依然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他寻找的“文城”。执拗地出走并没有实现林祥福内心的期许,他始终没有找到小美并将之带回北方,命运的轨迹在他出走的刹那开始滑向未知,此后在溪镇的种种发迹、兵灾、匪患等等事件,表面看起来的偶然中似乎也蕴藏了一些必然。余华再次将林祥福出走的意义消解了,他用一种隐忍的笔法刻画出一个人的坚毅和抗争。
在补篇中,余华给小美和阿强的出走赋予了一些叛逆的色彩,看似是为了反抗母亲的钳制,与旧有的传统桎梏决裂,带着一些朦胧的觉醒姿态,甚至有一些先锋的精神内核。但这次出走在实质上不过是漫无目的的逃离,他们的出走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与鲁莽,在浏览了上海的都市浮光后,靠着模糊的记忆想要去投奔远在京城的姨父,他们恐惧家乡的权威而不敢返乡,同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往何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虚假的信念支撑自己前行,并安置好对未知的恐惧。这次出逃的意义,在小美给林祥福诞下一女之后,迅速被消解。“小美继续搭乘南去的马车,阿强不知道小美要去何处,只是一路跟随。”[4]311最终小美还是回到了溪镇,这个最初驱逐了她的地方。余华将小美的出走处理得非常具有传奇叙事的特质,小美似乎是落叶归根一般回归溪镇,而这次出走在本质上并没有解决她遭遇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困境,只是依靠时间和巧合完成了“出走”后的回归。
余华将林祥福与小美两人的出走模式安排为在出走后又以不同的方式回归故乡的闭环。他们奋力离开故土,毅然决然向未知的远方启程,人生的终点又回到生养自己的故里,越是挣扎着离开,最后越被故乡牵扯。当时间线索铺展开来,回溯两人的出走,实际上都在其人生实践过程中是无意义的行动。这也正是余华的一种写作企图,他试图消解现实秩序的意义。余华对任何客观秩序都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于是他在文本中总是有意颠覆时空秩序,当他能够自由从容地穿越日常生活的表象后,人的存在状态与内部结构便成了余华可以肆意言说的对象。林祥福和小美的出走都是错置,他们沿着看似合理的逻辑向未知的境地逐步逼近,最后都桎梏在一种不容反抗的生存境遇之中,他们在内心渴望故乡,但又身处异乡,出走的初衷是试图靠近一个美好的结果,却奇异地与所求总是错过,这可能就是余华建立出走结构想要探求的一种人生常态,力竭而求的是虚妄。
余华在“出走”原型结构中一直试图消解“出走”的意义,他试图建立或探讨的是一种写作带来的可能性,即“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5]161。余华尝试在文本中将现实秩序打乱,也不惮于用日常视角介入庸常生活,开掘一种否定的存在意义。“出走”作为一种原型结构,在其文本中始终持解构性的立场,人总是在离开。远方的未知是巨大的诱惑,却包藏着不可名状的灾难。
三、“父子”原型结构
“父子”在余华的文本中也是一个频现的原型结构,从他对“父亲”形象的设定与“父子”关系的审视来看,余华喜欢用“父子”原型结构阐释人性与人伦中的多重问题。余华对“父子”原型模式的建立与其自身的认知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余华曾提到过王安忆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上,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9]106这种焦虑感作为一种写作的原动力,始终在鞭策着余华的创作,他企图构建一种“父子”模式来审视这种关系,并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在余华的作品中,“父子”原型结构是稳定的,但这种结构的所指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这其中内蕴着余华对父子问题的不断审视。在余华初期的作品中,“父子”原型总是充斥着变态与扭曲,《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将“我”交付给世界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眷恋,父亲温和的神色与不容置疑的态度是一种对子的驱逐。《难逃劫数》中露珠的父亲老中医,是一个阴鸷狠辣的形象,他常年躲在窗帘后窥视别人的生活,甚至包括自己女儿的隐私,他内心的扭曲与阴暗像传染病一样感染了露珠。作为嫁妆的硝酸成为一对新人为捆绑彼此而造成杀戮的导火索。对于露珠的死亡,老中医平静、冷漠甚至将之视作验证预言正确与否的砝码,父辈与子辈之间没有任何亲厚温馨可言,只有赤裸裸的人性试探,甚至加诸各种暴力的行径去消解父子伦理。《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广才对其父孙有元日常的羞辱与谩骂,对儿子孙光林的驱逐与厌弃,不仅毫不避讳甚至将这种行径衍生为排遣自己苦闷的手段。
“父子”原型结构是余华创作中意义指向变动较多的一种结构,他没有使父子的敌对关系旷日持久,而是逐步将之铺设在日常生活中并注入温情后进行剖析。《第七天》中,以亡灵的视角回溯了杨飞的一生,余华为杨飞安排了一个有情有义堪称道德模范的养父,铁道工杨金彪为了杨飞成长过程不受委屈而终生未娶,这种难得的温馨情境在杨飞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烟消云散。亲生父母这里反而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嫌隙,杨飞在这是个局外人,他只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那里获得父子亲情的呵护与关爱。这种无奈又滑稽错位的关系里,折射出余华对父子伦理的不断思考,错位并不一定会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而血缘也不一定能成为维系彼此感情的纽带,人的感情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托,父子伦理建立的基石被置换后,从“父子”原型去透视的是一种人伦秩序和纲常伦理背后的深意。
“父子”原型结构本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它潜在地会引起人的反思。荣格指出:“这个层次既非源于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把这个更深的层次称为集体无意识,我之所以选择集体这一术语,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不同于人类心理的是,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并因此构成了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我们大家身上。”[10]5这种普遍性在先锋作家们的文本里,表现为父辈的权威被质疑、被挑战甚至被消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对父辈形象进行重构,对焦灼紧张的父子关系进行剖析。余华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不能免俗,他对父子关系的持续关注与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对人的存在与定位的思考。人如何获取自我的存在意义,怎么摆脱父辈权威的阴影而自立,都是余华在文本中进行探讨的命题。余华以父子伦理关系形成一种原型结构,在文本中不断试验人性的弹性极值与父子关系的尺度边界,这成为他的一种特殊的叙事伦理。
在《文城》中,余华对“父子”原型结构的处理完全卸下了先锋时期的剑拔弩张,林祥福被塑造成一个传统慈爱的父亲形象,他沉默隐忍,为了女儿的幸福不惜抛家弃业,因为幼小的孩子不能没有娘。林祥福寻找小美的路十分艰辛,独自把女儿养大,临终前,唯一的惦念就是女儿,“他临终之前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4]198。舐犊情深的林祥福,仍然是“父子”原型结构中父的形象,但是这个结构的隐喻意义指向有了新的变化,而这新的意义指向更像是余华期望达成的一种和解,并隔空回应了先锋时期那种“无父”“弑父”状态的迷惘。余华希望在“父子”原型结构的模式下,恢复“父”的秩序,以此来完成“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重建。唯有建立一种令行禁止的“父法”,才能形成一种前后有序的传承。这才使得林祥福的种种行为有合法的世俗动机,在机缘或者偶然的促使下被消解的行为意义指向,企图勘破的是命运的无常与机巧。余华不再执着地深究人本体的限度,而是将人放置于广阔的命运机器中,尝试阐释人性的深邃与法度。这其中,“父”的形象往往包含两段父子关系,人伦与道德都将在其中一点一点得以显形,人物的轮廓与命运的走向也将会慢慢露出轨迹。
林祥福为人处世有情有义,性格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韧,思想中也带有极传统的家庭观念,他为了女儿几乎赌上了自己的后半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父的形象。正是在精神领域的健全,使他能够代表一种更广泛的“父子”关系模式,以这样的“父子”原型结构去反观余华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他对人性扭曲思考的转圜。在早期的创作中,所有的苦难都是根植于人性之恶,甚至精神的残损也是不断传承的,而《文城》中的林祥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可能,即以人道主义的关怀力量和悲悯之情,去反抗世俗的天灾人祸。实际上,温和敦厚的姿态使批判的锋芒更加尖锐,被刺破后的人生悲苦底色,愈发显示出人性的苍凉与命运的荒诞。“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11]114“父子”原型结构就在这个层面上,完成了余华在创作中展现出的强烈主体意愿,其话语直指人性起点,如果人性不是本来就恶,那是什么导致了人的异化,而这种异化会不会有疗愈的可能,最终的救赎又是什么形态。于是,余华将林祥福塑造成一个中国传统的父亲形象,不再站在生活的对立面劈杀生活,反而有种《活着》里福贵身上的顽强,这何尝不是余华对浮沉无序的世事一种隐约的期待。
“父子”原型结构中意义指向的不断调整,透露出的是余华对父子伦理的深入思考,紧张对立渐进为相濡以沫,一路以来都是其对该原型结构能够建立一种怎样的秩序的不断试探,使这样的结构尽可能囊括多重可能,“他又极力怂恿人物按照自己命运朝着各种‘可能性’方向奔跑,使人物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逻辑”[5]52,以此来输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
余华在文本中建立了多种原型结构,这些尝试与探索不仅拓展了余华自身写作的宽度与深度,也构建起了多种叙事的价值追求与可能性。不论是建立一个叙事的框架结构,还是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结构,每种原型结构的建立都像是一个坐标系,叙述得以在其中辐散开来,继而进行多重人性的试验与考察。上述三种原型结构在余华的文本中颇具代表性,尤其在《文城》这部小说中,不仅技法醇熟,更是彼此协同,消弭了文本实验的痕迹,使整部小说在圆融的结构中得以将叙述深化,探寻出对“道路”结构的颠覆、对“出走”意义的解构、对“父子”模式的新赋值,以突出三种原型结构的隐喻意义。同时,余华建立的多种原型结构,也是对原型理论的一种推进,突破了原本对心理范式以及神话原型的探索,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写作场域,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通过对余华文本中原型结构的追踪与分析,可以看出的是余华不断变化着的思想,其中涵盖了他对人性的追思,也反映出一个作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丰富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