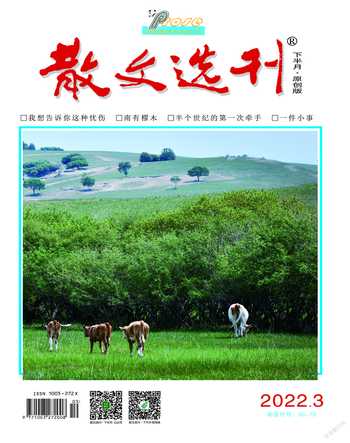大弟
陶诗秀

婚后首次携外子回乡省亲,月台上迎接我们的不是朝思暮想的爹娘,而是长年出海的大弟。他叼着烟蒂,趿着拖鞋,与满脸肃穆、衣冠整齐的外子形成鲜明对比。
我正暗暗叫苦,说时迟,那时快,我那蛮横无畏的弟弟已抢过行李,迭声向外子问好。他左一声姐夫,右一声姐夫,哄得外子笑逐颜开。
进得家门,外子和亲友行礼如仪,我一头钻进厨房,查看娘家备了哪些美酒佳肴,款待远来的刁嘴女婿。只见葱、姜、蒜在大弟手下跃动,鸡、鸭、肉于盘中待命。丝、条、粒、块,齐整美观,让人咂舌。炉头上,煎煮炒炸之声,此起彼伏;锅镬里,众食争香斗色,引人垂涎。大弟身高六尺,体重超标,说话粗声大气,性子浮躁不安。但面对食材时,他全神贯注,精雕细刻的水磨工夫,令自诩烹饪高手的我也不禁傻眼。
那晚的盛宴,虽比不上满汉全席,但牛羊猪禽、鱼虾膏蟹,一应俱全。外子喝得酩酊大醉,老爸乐得说唱不停,一向害羞的老妈也抿着嘴偷笑,瞅着外子对我耳语:他真能喝,又那么白。
大弟幼时染疾,高烧百日始退,所以脑子有些迟缓,加上他又不学好,一直不讨父母欢心。他中学勉强毕业,糊里糊涂地踏上商船,别人跑船皆发了财,唯独他把美元换成礼物,每次回乡便敲锣打鼓,大派利是。他曾送我一枚孔雀开屏的胸针,孔雀的羽翼缀着三层金箔,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我虽怀疑金子的成分,依然爱不释手,出国时,把它放进压箱宝盒,好些年后,掀开盒子,孔雀已失去光泽,金箔变成了铜片,不由得哑然失笑。当初大弟吹嘘它是如假包换的泰国纯金,指望我会表扬几句,但习惯板着面孔、对他不假辞色的我,硬是没有松口。
观察入微的外子,一眼看出大弟在家的“特殊地位”。俗话说,能干的儿女飞得远,没用的孩子靠得近,说的正是我家大弟。他婚后留守老家,成了爸妈的精神依靠,加上父母微妙的歉疚心理,父亲待他的态度,有时几近于溺爱。大弟下船后烟酒不离身,经常醉卧街头,邻居劝他,若想父母多活几年,少在外头喝酒滋事。他大约听进去了,自此便关起门来喝闷酒。他平日大大咧咧,醉后却小肚鸡肠,把从小到大受的委屈、芝麻绿豆的陈年旧事,全都宣泄而出。老妈叹息,没想到这个笨儿子的记性如此惊人。老爸自责,怎没及早发现,他吃饭时眯眼盯菜,是因为近视,而不是没规矩。我安慰二老:你们是模范双亲,九十九分!老爸一高興就跟着大弟烟酒齐来。我看了生气,就爷儿俩一起教训。喜好杯中物的外子,一面劝我做人别太认真,一面飞快加入饮酒行列。三人一起发酒疯,像三个拒绝长大的孩子。
助长酒疯之下箸菜,是大弟毕生的骄傲。他自制的卤味、红烧蹄髈、鱼下巴、酒烹河虾、九层塔海瓜子、虎皮椒、辣子小鱼干等,是我至今吃过最美味的家常菜。逢到过年,向他订购香肠腊肉的人要排队。
我年年返美时都冒着被海关查获的风险,也要挟几条他腌渍的腊味。除了抵不住那浓郁的香气,多少有几分做姐姐的自豪。
最让我服气的是,寻常一盘葱花炒蛋、一碟油酥花生,他都有本事做得比餐馆端出的香。问他秘诀,他不耐烦地说:“有啥秘诀?好吃而已。”
我猜他对美食的追求,从儿时抢不到桌上菜开始。他做饭时不喜人偷碰、偷窥和偷吃,仿佛厨房是他的王国,食物是他的禁脔,他是掌管天下粮仓的统帅。老爸嘴馋,想先尝为快,都得看他脸色,唯独对外子例外。我常笑他们是一对酒肉姻亲,把酒共欢,以食结缘。其实大弟做得多、吃的却少,除盼客人吃得满意,他更渴望听众满席。
有了听众,酒过三巡,他便扯开嗓门“吹牛”。某年墨西哥下岸,他以一美元换来整袋墨西哥辣椒,全船人辣得东倒西歪,唯他一人挺住;他曾在纽约被餐馆挖角,若非惦记爹娘,险些跳船当了大厨;1987 年两岸开放探亲,他陪爸妈回湖北老家,一下飞机,给了行李员5 美元小费,小伙子眉开眼笑,他却被乡亲一路念叨,大哥以浓浓的湖北腔惋惜:“你真是不把钱当钱用,5 美元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啊!”
关于前两则故事的真伪,我始终存疑。最后一项,则有爸妈作证。后来他屡次回乡,带领乡亲游山玩水,出手之阔绰,不仅亲友动容,也为娘家维系血脉亲情做出无比贡献。对此,他倒是相当低调。我从旁听说,他曾一次带着十九名亲友浩浩荡荡游江南。不免好奇,他哪来的银两?
老妈说,全靠标会啊,标到会,握有大把现钞,日后只需按月偿还。一旦旧债还清,又可另起新会,周而复始,不愁无钱。我为之气结,质问老爸为什么不管管他。老爸叹道,他到那边当“大爷”,受人尊重,心里痛快,做父母的何忍浇冷水?我听了无语。
遂以外子之名赠他“红包”。母亲得知红包数目,摇着头说,只怕还不够他这几天买菜。我又惊又愧,对这个弟弟,我到底知道多少?
母亲说他穷而大方,食材专挑最好最贵的,分量保证人人撑爆。我们返家之前,他已磨刀霍霍,天未亮即冲进菜市,精选活鱼鲜肉、时令蔬果。鱼头先腌后炸,卤味烧好冷藏,海参提前发透,蹄髈细火慢炖。我们回娘家三天,他前后得忙上一周。这些都能想象,我所不知的,却是我们走后,他尚需静养将息。
原来,他罹患糖尿病多年,腿脚逐渐麻木浮肿,却仍坚持掌勺,不肯假手他人。直待众人吃饱喝足,才悄悄休息泡脚。有一回水过热而不察,发觉时已烫掉整层皮。
他又极爱面子,凡事报喜不报忧,如此焉能不苦?
若干年后,外子亦得此病,两人酒友兼病友,愈发的惺惺相惜。外子形容他“多酒多肉多兄弟”,视他如亲兄弟一般。他感激外子不嫌他没有学问,故每次聚首,都挖空心思,满足我们的口欲。2007 年,他胃疾住院,没机会为我们洗手做羹汤。翌年,母亲二度中风,百忙之中,他还是做了两盆鱼下巴,补足去年之缺。记得那天,他数度离开厨房,坐在门外抽烟。问他是否累了,他低头装没听见。
我们离乡不久,他就病了。入院前,他炖了一锅卤猪脚和豆干。猪脚一向是母亲和他的最爱,豆干却是父亲的专宠。父亲让他留些当零嘴。他回以一句:“你们留着吃,我没儿没女的留了干嘛!”三个月后,他一病不起,这句“没儿没女留了干嘛”,是他留给父母的最后一言;猪脚豆干,则是他告别人间的最后余味。
他走后,父亲执意瞒着母亲,独自扛下丧子之痛。那段日子,他的名字无人提及,猪脚豆干亦从桌上消失。怕母亲起疑,我们不敢回去送别。一生喧哗热闹的大弟,就这么寂寞无声地走了。哥哥说他临终前双目已瞎。我一想到从小怕黑的他,在黑暗中不知会何等惊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般。如果时光能够逆转,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也来得及对他说,孔雀胸针是我这辈子收到最珍贵的礼物,它就是如假包换的24K 纯金!
父亲后来抑郁而终,母亲熬了几年也跟去了。不知,父亲生前有没有后悔,母亲闭目时知不知道真相,我们不愿深想。但父亲曾托梦给哥哥,抱怨很久没有吃到豆干。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父亲想念的不是豆干,而是会做豆干的儿子。
外子生前也念念不忘大弟做的鱼下巴,病榻上不时感慨:“下巴佐酒,鱼汁拌饭,好吃啊,好吃!”
我原想待他出院,照着大弟方式煮给他吃,让他开怀。未料他走得突然,他在人间最后一餐,只是一碗鸡汤蒸蛋,他却心满意足地吃个精光。
和猪脚豆干的命运一样,鸡汤蒸蛋从此亦从我家厨房黯然退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