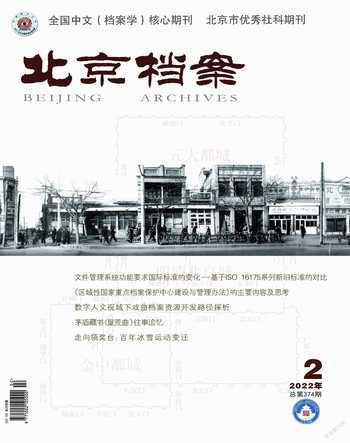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
〔德〕沃尔夫冈·恩斯特
摘要:“档案”一词已成为所有可想象的存储和记忆形式的普遍隐喻。然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恩斯特认为,档案并非专门用于记忆,而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纯技术实践:我们添加到档案中的任何故事都来自外部。档案没有叙事性的记忆,只有计数形式的记忆。恩斯特认为,在数字文化中,档案实现由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的演化,关键在于数据持续传输过程中的动态性。由此,档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蕴含无限的可能。
关键词:数字记忆 档案记忆 数字媒介 媒介考古学档案理论
首先,让我们采取档案的非隐喻性使用,即作为行政权力的记忆实践。随后,让我们直面传统档案所面临的数字挑战:在流媒体(streaming media)中,持久的、静止的记忆正被动态的、暂时的存储形式所取代。[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对数据传输的强调取代了文化存储的主导地位时,我们又回到了档案字面意义的“隐喻化”(metaphorization)。[2]
尽管“档案”一词已成为各种记忆和存储机构最流行的隐喻之一,但是“档案馆”是一个定义非常确切的机构,因而其范围是被限制的。档案管理员知道他是在神秘的帝国中进行操作,这是一个隐藏的权力场域(realm)。在空间和时间上远离与行政背景相关的公共检查文件有明确的司法目的;其他的一切都受制于话语。从字面上看,档案诞生于行政定义之中——在古雅典,当它由字母来表示时,被称为archeion,与新的戒律形式有关。
档案空间(archival space)是基于硬件的,而不是记忆的隐喻体。它的操作系统是行政性质的。在其存储的数据基础上,叙事只能从外部得到应用,如历史、意识形态和其他类型的叙述性的软件。非话语实践是特定规则下的档案现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互联网上的传输协议或计算机软件背后的代码。
档案馆不是特定社会中集体记忆的场所[3],而是对行政行为产生的数据进行分类、排序、整理和存储的场所,代表了一种将数据反馈给当前程序的控制论反馈选择。归档数据并非用于历史或文化的记忆,而是用于组织机构的记忆,如国家、企业或媒介。实际存在的档案将权限与数据存储设备关联。
自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提出文化符号学理论以来,文化被视为记忆机构的功能。洛特曼将文化定义为其内在的媒介机构和储存、传递文化知识实践的功能。媒介考古学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审视记忆文化。它以档案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作为处理“过去”数据模型的叙事性历史。媒介考古学关注信号处理而非符号学,将注意力转向记忆的技术的可寻址性,在文化記忆沉淀中发现了一个既非纯人类也非纯技术的存档层。从字面上看,它介于两者之间:将文化记忆的幻影作为记忆机器来分析的符号运算。
从古老的katechon(延迟)概念的意义上说,档案中止了无情的热力学物理定律,即所有事物都倾向于溶解为无序,直至死亡发生。档案通过投入大量的组织精力来维持秩序。文化档案的一个功能是确保不可能的(即看似无用的)数据被保存下来,以备成为未来的信息(根据克劳德·香农等人的信息论)。过去在档案中遗留下来的是象征性编码物质的物理痕迹,其物质性仅存在于空间中。以电子、离散形式处理的文化数据越多,传统档案就越能从羊皮纸、一般纸张、磁带等人工制品的物质性中获得权威——这是一种档案复古效应。
档案并不讲述故事。只有二次叙事才能使其不连续的部分具备有意义的连贯性。在其非常分散的情况下,档案反映了当前的操作水平,计数而非叙事。在档案中,没有任何事物,也没有人对我们“说话”——包括死者或其他任何事物。档案馆是空间建筑中的一个存储机构。我们不应将分散的档案文件的沉默与将数据转化为叙事的公共话语混为一谈。档案数据和文件之间并不存在必要的连续性,而是存在裂痕和缄默。基于此,档案成为媒介考古学的美学对象:与考古学家一样,媒介考古学家面对的是寂静无声但悄然运作的人工制品。尽管这种缄默是蕴含于媒介考古学工作中的力量,但被叙事性的话语所忽略。这种力量与媒介力量类似,取决于媒介通过其内容,隐藏和掩饰其技术设备这一界面效应。档案的句法能力只有从抵制语义需求的角度才能被看到。
档案的记忆是纪念碑式的(monumental)[4]。其由形态而非人组成。无论个人留下的是纸张还是录制的声音和图像,档案中的重点主题已经被分解成一个由比特组成、离散的文本。任何在档案文本阅读中加入与个人相关内容的人都是在制造虚构,用修辞生成学的模式去辨认已经“死去的”字母,声称死去的事物是“有生命的”。历史想象被应用于档案阅读,将幻觉误解为缺席。与和死者对话的幻想欲望相反,档案意识(archival awareness)将过去视为数据。
计数与叙事相关,但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进行。当谈到数字计算时代的记忆问题时,我提到了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关于“数据库作为一种符号形式”的文章[5]:数据模型成为主导,支配叙事。数据库颠覆了传统的范例和组合之间的关系。非叙事属于档案制度。档案信息对应的是媒介考古模式,叙事对应的是话语。
正如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论文(Laokoon)(1766年)中所说的:文学叙事是一种组织时间经验的艺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坚持认为人类对时间的感知(con? science)与用时间摄影记录时间过程是不一样的。时间本身现在正由技术组织。[6]档案的空间隐喻转化为时间维度。档案的动态化涉及基于时间的程序。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1936年的论文《叙述者》(Der Erz?hler)中指出,经验一旦脱离史诗传统,就不能再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交流。[7]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说信息必须通过实时分析立即被消耗掉——这属于计算和信号处理,不再是可叙述的。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文化处理的不再是“叙事性的记忆”,而是计数形式的记忆。档案中的文件证据已经表明:基于数据的记忆无法叙述,只能根据生成此类文件的管理逻辑进行计算。叙事也许是社会记忆的媒介。然而,档案媒介是结合了数据支持的物质性和符号运算符背后的协调程序的字母数字模式。权力是不会进行叙事的领域,剩下的只是解释。档案记录了,但并未进行阐述。只有在隐喻的意义上,档案才能与人类记忆相比较——除非从神经学角度进行比较。
如果档案中有缺失的部分,这些空白就会被人类的想象所填补。[8]对史学的渴望源于一种失落感。[9]档案不是历史记忆的基础,而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过去留下的只有手工书写的纸张,那么阅读应该被视为最字面意义上的回忆行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技术,产生了一种并列(paratactical)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应以档案为基础,或与之相关地进行书写,而应是及物地(transitively)书写档案。
将档案馆误解为社会记忆的场所,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真正记忆能力的注意:与人类记忆相比,存储媒介的运行机制是不对称的。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关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框架的著作中,明显没有体现出档案来。档案的隐藏力量依赖于其物理存储工程的物质性及其符号操作,从而形成了一个非有机的证据体。这种系统性的只读记忆与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描述的人类潜意识中的非自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有着根本性不同。从结晶行为(crystallisation)开始[10],档案将过程的无序还原为编码的、语法的结构——一种介于松散耦合和僵化形式的中介。在这里,这种还原真实出现了。
档案不是关于记忆的,而是关于存储实践的,一个功能性的存储器所在(lieu de mémoire)[11]。记忆是在档案之外的。但是,在成为各种存储和记忆的普遍隐喻的同时,“档案”被破坏了。它的存储技术正在被话语效应(discursive effects)[12]所掩盖,就像多媒体接口掩盖了计算的内部操作程序一样。将档案定义为编码存储方式的媒介批判理论正是现在所需要的。
如上所述,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受数字技术的影响而解构。自古代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记忆技术存储将记忆与空间联系起来。但现在静态的、持久的档案作为永久的存储正在被动态的临时存储所取代,基于时间的档案成为永久数据传输的拓扑场所。关键的是,档案从存储空间转换为存储时间。它只能暂时性地处理电子系统中的流数据。一旦档案数据获得纯粹的、暂时性的索引,它们就失去了空间的稳定性。在网络的封闭电路中,存档的最终标准——它与实际操作的分离性——已不再被设定。网络计算的本质特征是其动态可操作性。网络空间是移动元素的交集,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算法运算可以传输這些元素。在电子、数字媒介中,被期望为永恒存储的经典做法正被动态运作所取代,“即时生效”(on the fly)成为一种新的特性。经典的档案记忆从来不是交互的,而网络空间中的文档对于用户的反馈具有时间先决性(time-critical)[13]。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即在体制与地理意义上较为偏远地方仍适用的档案秩序,是与数据映射的动态档案实践,以及那些能够把传统档案与电子档案区分开来的、暂存的、动态的操作流程同时存在的。跟踪路由器不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的侦察者。随着档案本身从时间空间化的机构,转变为一个通过瞬间的中止来延迟更改的动态处理过程中的序化或中止程序,档案的空间架构转变为顺序化的、时间先决性的、同步通信的。
互联网被保守地认为是一个“档案”,它甚至还没有触及自己过去的中介。网络空间是交流的横向表现,因此,“网络空间没有记忆”[14]。只有提供了可寻址元数据的数据才能在文化档案中被访问。就互联网而言,这种存档基础设施本身在时间上是动态的,需要在虚拟文本中的给定时刻访问数据。纪念空间正被一系列有限的时间实体所取代。空间变得暂时化,档案范式被永久传输、不断回收的记忆所取代。
只有可寻址,才能被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产生了一种“新的记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记忆不再位于特定的位置,或根据传统的助记符号来进行访问,也不再是一个需要获取访问权限并由所有层次等级来控制的存储库”[15]。可寻址性对于中介记忆仍然至关重要。在柏拉图的对话录《美诺》(Meno)中,记忆似乎只是运用回忆技巧的一种效果。当临时“访问”数据成为互联网研究的主要特征时,传统的档案秩序就消失了:“信息商品需要的是访问,而不是占有。”[16]网络存储模式将电子档案转变为一个生成机构。传统上通过元数据进行的分类索引被动态(尽管仍然受规则和协议控制)的排序所取代。[17]档案并不存在于其文件的内容中,而是存在于作为媒介档案学(media archivology)研究对象的逻辑控制论中。当计算机中的并行分布式处理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机内存时,数据就变得可以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被定位了。档案被认为是一种“操作技术”(opération technique),它变成了一台控制论的记忆机器,一个关于数据延迟和数据实现,以及对现下的持存与预存(retentions and protentions)的游戏。只要文件仍被实际行政当局所掌控,它们便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在数字体制下,所有数据都要经过实时处理。在实时数据处理的条件下,过去本身就成为一种错觉。档案信息的剩余时间延迟缩短为零。
在网络“空间”中,档案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阻碍发展的隐喻。它应该用拓扑学、数学或几何术语来描述,用永久性的传输,也即数据迁移,代替强调的记忆。只有存储的内容才能被定位的旧规则不再适用。[18]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旧的“执政官的”(archontic)性质的档案之外[19],互联网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记忆文化。类似存储材料的数字化意味着传输式的存档。这种存档与网络相关联,而非与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相关联。组织形式的记忆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运行状态所决定的定义,建构性而非重构性的。
假设记忆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应用回忆技术的结果,那么就没有记忆了。与网络联通的数据库标志着与知识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打破了与经典存档相关的层次结构。
档案——虽然在制度上一直是国家或其他组织的行政和司法记忆——在认识论层面上从可寻址机制的只读记忆转变为福柯意义上的arché:一个生成性的、算法的、协议式的场域,字面意思是程序性的。在这方面,数字(而不是模拟)档案与抽样相关。传统的基于文本的档案由数字元素、字母表的基本字母组成。但在数字时代,字母表被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在冯·诺依曼(Von Neumann)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它不再将存储的数据和处理规则分开,就像在传统档案中一样,文件被保存在库房中,而档案程序规则被保存在书籍或管理元(metadocument)文档中。当数据和程序都位于同一个操作领域时,数据和元数据之间经典的文本记录(documentary)差异崩溃了(im? plode)。例如在图书馆中,书籍和签名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数据集。
数字化记忆打破了传统的纸质档案中字母至高无上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声音和图像也可以进入其中,它们可以在自己的媒介中被寻址:对于旋律、图像和模式都可以根据其形态进行检索。因此,一种新型的文化——技术记忆正在生成。计算机能够以数字方式“挖掘”的是一个真正由媒介生成的档案。这为互联网上的搜索操作开辟了新的视野:数字图像和文本可以链接到字母地址,同时这再次使图像和声音受制于文字与档案分类范式产生的外部元数据,而且现在它们可以在自身媒介中从内到外寻址到单个像素,允许随机搜索——字面上的“比特映射”,即按比特进行映射。
因此,图像和声音是可计算的,并且能够适应模式识别算法。这样的程序不仅可以是媒介考古学意义上的“挖掘”,而且能从视听档案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陈述和视角。对于档案而言,这是第一次,不仅可以根据元数据,而且可以根据其适当的标准来对其进行组织——在其自身媒介内生的视觉记忆中。在真正的数字文化中,生成性档案,即存档范式,正在被抽样——对信号的直接随机访问——所取代。
如今,不同的媒介记忆文化共存。欧洲文化记忆传统上以档案为中心,体现为持久的物质价值(图书馆、博物馆、2500年历史的建筑),而跨大西洋的媒介文化则以传输为基础。这就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恰当地称之为帝国(Em? pire)的东西。[20]在对当今权力的媒介考古学分析中,我们从帝国的领土概念重新转向拉丁语单词imperium的原始含义,即接触、延伸和动态传输。谈到遗产,美国联邦政府档案馆并非根据传统的档案倾向,简单地存储那些最好进行保密的文件,而是力图确保记忆的全面性,以多样化的形式向公众传递信息,甚至是通过广告来实现记忆的不断流传。如果没有版权,每一个在线用户也许都能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数字网络中,归档延迟和当前的信息实现之间的分离已经崩溃。未来将有两种存储器:模拟的、物质的存储器和数字信息存储器——永久数据传输的半透明技术。档案不再是多媒体记忆的信息。
译后记:
数字时代,我们如何想象档案,档案与记忆的关系如何,档案及档案馆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嬗变?技术的发展将上述问题悉数抛给了档案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记忆媒介的数字转向,国外学者开始以福柯式的考古学方法重新思考“档案”和“档案馆”的概念:新的记录媒体不仅带来了信息存储和传播的变化,还带来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变化,以及我们认识、思考和表达我们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方式的变化。[21]要系统理解档案与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便绕不开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 gy),抑或可以說是“媒介档案学”(media-archivology)。他的思想也启迪了一批数字记忆研究者,如安德鲁·霍金斯(Andrew Hoskins)、安娜·雷丁(Anna Reading)等人对记忆“连接转向”“物质性”的思考。
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这篇论文中,恩斯特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阐述了档案与记忆的关系,即档案是非叙事性的、用于数据存储的纯技术实践。档案馆是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存储的功能性场所,而不进行阐释和意义生产。在此背景下,档案、档案馆及其“隐喻”成为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恩斯特提出互联网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记忆文化,固化、稳定、静态的“空间”被瓦解,永恒更新、暂时、动态的“时间”成为新的档案范式。
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1959—),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德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媒介考古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斯特具有历史学、考古学和古典学的多重学术背景,在媒介理论的研究中,他明确地将其工作置于媒介考古学的旗帜之下。
本文最初由沃尔夫冈·恩斯特于2004年发表在Open: Cahier on Art & the Public Domain,原题为The Archive as Metaphor: From Archival Space to Archi? val Time,经与作者沟通授权后,译为中文刊发。在翻译过程中,为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对标题及关键词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微调及补充。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译者注:在流媒体传输过程中,缓存中存储的数据是不断进行更新的,每一段数据在被读取播放后都会被立即清除。
[2]原文注:The Ancient Greek word“metaphorein”means“transfer”.
[3] Halbwachs, Maurice.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25.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deFrance,1952.
[4]译者注: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遗迹或纪念碑(monument)是与文献(document)相对的概念,区别于对文献进行的阐述,遗迹需要采取非人类学的考古方法。
[5] Manovich, Lev.“Database as Symbolic Form.”Con? 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Technologies5(1999):80-99.
[6] Thom?, Dieter.“Zeit, Erz?hlung, Neue Medien. Philosophische Aspekte eines Streits der Medien um das Leb? en.”(1994):89-110.
[7] Benjamin, Walter. Der Erz?ler. Frankfurt: Gesam? melteSchriften,1972,439onwards.
[8] Kaplan, Alice Yaeger.“Working in the Archives”. Yale French Studies 77, theme issue“Reading the Archive: On Texts and Institu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 ven(1990):103-116.
[9] Certeau, Michel de. L’absent de l’histoire. Paris: Mame,1973.
[10]译者注:根据对恩斯特其他文本的解读,结晶(crystal? lisation)类似于一种时间凝结的比喻。
[11] Nora, Pierre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 limard,1984.
[12]译者注:人类学意义上的话语,具有阐释性。
[13]译者注:“时间先决性”源于基特勒式的,对于现代媒介时间轴操作的一种强调。
[14] Dr?sser, Christoph.“Ein- verh?ngnisvolles Erbe”. DieZeit(1995):66.
[15] Caygill, Howard.“Meno and the Internet: between Memory and the Archive.”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2(1999):1-11.
[16] Hayles, N. Katherine. Coding the Signifier: Re? thinking Processes of Signification in Digital Media. Berlin: LectureatHumboldt-Universit?t,2001.
[17] Esposito, Elena and Alessandra Corti. Soziales Ver? gessen. Formen und Medien des Gedachtnis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Suhrkamp,2002,43.
[18] Bradley, Harriet.“The Seductions of the Archive: Voices Lost and Found.”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2(1999):107-122.
[19]Derrida,Jacques.Mald’Archive.Paris:Gallimard,1985.
[20]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 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 2000.
[21] Schwartz, Joan M. and Terry Cook.“Archives, Re? 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Archi? valScience2(2002):1-19.
譯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