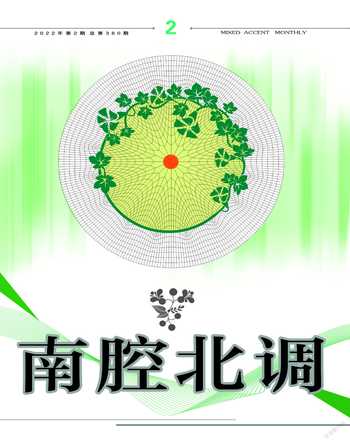神话的继承与破碎
艾嘉辰

摘要:近两年来,年仅22岁的蒙古族青年作家——渡澜受到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但是,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异质风格和独具特色的先锋气息尚未吸引到理论批评家的目光。面对“难解”的异类迷雾,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找到解读渡澜作品的“金钥匙”。本文以渡澜的代表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为例,从小说结构、人物原型和词语象征三个角度为切入点,运用“神话—原型”理论展示小说“神话的继承与破碎”这一特质。
关键词:渡澜 神话 “神话—原型” 批评 弗莱
渡澜以“出道即巅峰”的姿态,在短短时间内就于《收获》《十月》《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发表作品10余万字。她还获得《小说选刊》第二届禧福祥杯新人奖、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新人奖、第二届草原文学奖新人奖等诸多奖项。她的小说文风老练,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与苍茫。而评论界目前对其小说的分析多为感性的描述,缺乏理论与系统的解读。其代表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的小说母题即“丢失与寻找”和“死亡与复活”,通篇充斥着神话色彩。小说以主人公乌尼戈的三次消失与三次出现为主要线索,主要刻画了乌尼戈、柳泽真由娜、“我”这三个人物,同时运用弗莱的“四季说”[1]架构全文,内嵌三个四季轮回,根据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安排乌尼戈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命运,同时,小说中的每一位主要角色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神话人物原型,并且,小说出现了蛇、三角形等具有明显象征义的词语。评论者需要对这些小说要素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行剖析和阐释,只有明确小说的全文结构、将角色本身与其原型人物一一对应、挖掘出特殊词语背后的所指含义,才能一探渡澜作品中迷人的神秘色彩。
一、四季轮回的小说结构
弗莱的四季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着一个内化结构,此内化结构类似自然界中的四季循环:“自然界循环的上半部分是浪漫故事的世界以及天真的类比;下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世界以及经验的类比。因此有四种主要的神话运动。”[2]弗莱认为,春天,万物萌发与新生,对应文学作品中的喜剧;夏天是生命力展示得最为强烈的阶段,在夏天中主人公将会表现他的传奇能力,发生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秋天,万物衰亡与凋敝,在此阶段中主人公将会面临困境与危险,发生悲剧并在秋天“死去”;而冬天则是一个没有主人公的无趣的、沉默的、庸俗的世界,只剩下反讽与讽刺[3]。小说的第一句便是:“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4]作家一反传统,采用否定的形式宣告了乌尼戈(主人公)的出场,并明确告知读者“乌尼戈消失了”,这是乌尼戈的第一次消失。“看!一个漂亮男孩!”[5]预示着小说中第一个春天的开始。这是“我”和柳泽真由娜第一次遇见乌尼戈:“他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浑身散发出孩子与少女的气息。”[6]“他竟有着无限接近自然的美。”[7]这是初见乌尼戈时“我”和柳泽真由娜对他的印象。小说第二个夏天开始于乌尼戈显露他的与众不同,具体内容作家描述为乌尼戈的极速成长:“这20分钟里,乌尼戈至少长大了10岁,已经是个成年男子了。”[8]同时乌尼戈也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年龄,他可以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由一个青年变为一个垂暮老者,又可以在“睡了一整天”[9]后重新变成婴儿。这符合弗莱“四季说”中关于夏天的描述:主人公展露神力,发生传奇故事。小镇居民对乌尼戈进行迫害标志着小说中第一个秋天的开始,乌尼戈也在这时迎来了他的死亡:“他开始拼命吸气,却被达林台的弯刀割断了喉咙!”[10]乌尼戈被割喉而死。这也是小说中乌尼戈的第二次消失。在目睹了乌尼戈的死亡后“我”也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我”回到家发现乌尼戈在门口迎接“我”,这是乌尼戈的第一次“重生”与出现。
但“重生”后的乌尼戈丧失了曾经的自然美:“他总是白发苍苍,脸孔黑得像岩石。”[11]此处需注意,乌尼戈虽然重生,但并不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而是为将至的第一个凛冬拉开了序幕。这体现了渡澜对四季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主人公的生死与四季更迭的顺序不完全同步,在小说的第一个四季轮回中尤为突出。小说中,第一个冬天随后开始,这是一个只有懦弱的“我”而没有主人公的时期,同样也符合弗莱的“冬天”:一个没有英雄的无趣世界。但与弗莱的冬日说不尽相同的是,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冬天还预示着残酷、惩罚与死亡:“在中国文学中冬天的情感模式是终结是死灭是绝望。”[12]针对小镇上那些欺侮乌尼戈的愚蠢居民,冬天也预示着他们残酷的结局。
在小说的中间部分,作家明显地进行了层次划分,表现为用两种蒙古文字记录故事,用不同的“记录文字”将小说分成了上下两个不同部分。这是小说中第一个冬天结束的标志,也是第一个四季轮回结束的标志。
“春天到了,大自然铺青叠翠,镇子里满是豆荚爆裂的声音。”[13]此时故事进展的时间顺序与四季更迭顺序相吻合,小说的第二个春天开始。紧接着第二个夏天开始,乌尼戈继续他的传奇故事。这表现为他发现了一只喜鹊画家,他欣赏并喜爱喜鹊的画作。但随即第二个秋天来临,小镇居民继续对乌尼戈施暴,乌尼戈继续受难。在小镇居民对乌尼戈施加的暴力达到顶峰时,乌尼戈再一次惨死:“(乌尼戈)当着众人的面被毫无人道地注射了硫喷妥钠,当场变成了无数片齿状的娇叶,被一股脑儿塞进了火化炉里。”[14]这是乌尼戈的最后一次消失,同样是因为死亡。在乌尼戈死后的下一段,小说的第二个冬天便开始了。这个冬日不仅是没有主人公的冬天,还符合中国文学中具有死亡与审判隐喻的冬天。審判对象是不断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在小镇居民对乌尼戈的戕害达到最高潮的同时,他们也迎来了死亡的结局:“两个星期后,所有的人毫发无损地死掉,尸体黏在高得像是要把天戳破的铁房子的屋顶上,连苍蝇都飞不上去。”[15]这一幕颇有《圣经》中“末日审判”的意味——当人类作恶到了极点之时,大天使加百列便会吹响末日审判的号角,神会毁灭掉除善人之外的一切人类[16]。而小说中第二个冬天的结束,即第二个四季轮回终结的标志是小说中另一角色的消失——柳泽真由娜的消失。在柳泽消失后紧接的下一段的最后:“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终于回归了。”[17]这标志着小说中第三个春天的开始。但这个春天跳出了客观现实的四季轮回,也打破了弗莱“四季理论”的内在结构,“我”称之为永恒的春天。这个春天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结构,或者说在小说世界中依然存在四季轮回,但在“我”的心中春夏秋冬皆是春天,四季无二无别。此时的“我”颇有“证道”的意味,小说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其感受与威廉·布莱克的名句“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18]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我”最后一次见到乌尼戈时,“乌尼戈仰躺在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旁,迎着阳光,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19]。“他依旧是初次见面时的‘漂亮男孩’”[20]。这是乌尼戈的第三次出现,他恢复了一切,一如“我”初见他时的那般美好与青春。无法被摧毁的乌尼戈和他身上所具备的青春与美,便是永恒春天的象征,乌尼戈就是自然与美的化身。该段末句写道:“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21]开头是春天,结尾也是春天。开头是在春天消失,结尾是在春天遇见。小说开篇的春天和小说结尾的春天是同一个春天,比喻乌尼戈是既消失又存在的,是既短暂又永恒的。所以,开篇的消失反倒是存在,而结尾处的存在却预示着乌尼戈又即将消失。乌尼戈的消失就像是“水溶于水中”般,的确消失了,但又无处不在。这里的“消失”与小说首句的“消失”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永远停留在春日的闭环。而乌尼戈就是无数个永恒春日轮回本身。
小说以四季轮回为基本结构,但又体现了弗莱原有理论中不具备的关于冬日的中国文学情感模式,并且在第三次轮回中打破了“春—夏—秋—冬”的固定结构,将轮回静止,或是将轮回放置于某一具体季节——即春天中进行运动,是對传统叙述模式的尝试与突破。另外,主人公的三次“死亡与复活”与四季更迭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一套作家自己的突破了弗莱表象叙述层次的深层结构。这在创作上也值得肯定,避免了程序化、自动化的情节安排。
二、角色人物的原型对应
弗莱认为文学源于神话:“神话是文学中的一个结构因素,因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移位的’的神话。”[22]好的文学作品便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祖先们代代相传的神话。而每一个神话中都有相应的神话人物,将小说角色与神话人物原型对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作品。
现经笔者分析,小说中三个主要角色的神话对应原型各自为:乌尼戈—耶稣、柳泽真由娜—异化的圣母玛利亚以及“我”—异化的犹大。整篇小说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耶稣受难记”的民族异化新写,但又有主人公“二次受难”等不同于西方传统神话的本土新创造。这体现出作者对神话的继承与破碎。
乌尼戈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的神话原型对应角色即西方的“救世主”耶稣。在小说中存在多处叙述指向“耶稣受难”,如:“可怜的乌尼戈几乎散架,但他似乎完成了一场完美而彻底的奉献,与路面依偎紧靠,高兴得噙满了泪珠,宛若置身于天堂之中。”[23]“乌尼戈几乎散架”对应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美而彻底的奉献”对应耶稣的自我牺牲与奉献;“置身于天堂之中”则对应耶稣在死后三天获得神启、重生。但不同于神话中的“三天”,作家明显加快了乌尼戈的重生速度。在他第一次被杀害后,作者仅用了一小段进行过渡,唯一具体的时间词只是“出院后”三个字,抒发“我”梦魇似的感受。然后,紧接着在下一段中乌尼戈便已复活,而复活后的乌尼戈与复活后的耶稣在精神表现上完全一致,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我猛然发现乌尼戈闪闪发光的眼中竟满是神圣的宽宥时”[24],复活后的乌尼戈完全没有怨恨谋害他的凶手,而是选择了原谅,选择了“宽宥”。而作家给这种宽宥所下的定语是“神圣”一词,这与耶稣牺牲自我为全体人类承担罪责、拯救全体人类的《圣经》神话达到了本质上的一致。同时,这也与耶稣被钉死后由人化神的传说一致,乌尼戈的“新生”完成了他由“人”到“神”的彻底转变。而这一转变发生的唯一条件便是一次死亡,但乌尼戈这一主人公又与神话中的耶稣原型不完全一致。首先,从结构上看,乌尼戈和耶稣的“受难”轨迹不同。耶稣的轨迹是“出现-受难-死亡-复活”,而乌尼戈的轨迹是“消失-出现-受难-死亡/消失-出现/复活-受难-死亡/消失-出现/复活-消失”,比前者复杂得多。西方宗教神话中的耶稣,只“死”了一次,而小说的主人公“消失”了三次、明确“死”了两次。并且,作家刻意避开写明“复活”,而是留给读者去体味,体现出作家对传统神话的解构与创新。其次,从形象上看,与耶稣相比,乌尼戈不像人类:“我拍下他股间的黄色半日花花瓣和带着紫色金属闪光的乌鸦羽毛,替他拉上了裤子。”[25]“乌尼戈的掌心里长满了小巧玲珑的草,里面蛰伏着草爬子。他的每一个关节腔里都有蚂蚁在建造新的宫殿。”[26]种种话语都在说明乌尼戈与人类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更像是一种可以变化为任意形态的自然力量。而耶稣在传道时包括复活后都是以人类的姿态在世人面前显示的。这是从人物形象上作家对神话的继承与突破,而渡澜对神话的突破显得更为彻底。最后,从人物意义兼小说主旨上来说,乌尼戈和耶稣二者的“使命”不同。乌尼戈是自然与美的象征,作者多次使用了“漂亮男孩”“自然美”“美丽”等词语来描述和赞美乌尼戈,不断地强调他是自然与美本身,将乌尼戈与美紧密联系。而他“牺牲”自我且为之付出生命的是美和自然,并非人类。面对残害他的小镇居民——即“有罪人类”他可以做到不怨恨,但乌尼戈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使这些人得到解脱、升入“天国”而去牺牲自我的。他是为了捍卫或者坦然面对美究竟是要被毁灭的命运而去宽恕一切的,这与西方宗教神话中耶稣的牺牲目的不同。而且,小说让乌尼戈多次受难、多次死亡,为的是突出美的脆弱和大众的无知。美本身是神圣且永恒的,但它相当脆弱,任何一个无知群体的集合都可以用无数种暴力、凶残的方式来毁灭它;但美又是生生不息的,它可以被无数次毁灭,但也可以从无数次的毁灭中重生,就像小说中的乌尼戈一样。小说是在讲述一个美在凡俗中被血腥破坏但依然永恒不灭的故事。这与《圣经》的主题有着本质的不同。
除却耶稣这一基础神话原型,乌尼戈身上也具有其他一些神话人物的特征,如作者描写乌尼戈:“他竟有着无限接近自然的美,躺在地板上像一株柔软的植物,毫无违和感。”[27]他是一位花一样的美男子,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阿多尼斯[28],暗合弗莱对四季与神祇结合的阐释:“植物世界为我们展示了一年一次的四季循环,它常常以一位神的形象表现出来,或者等同于这样一位神:它在秋天死去,而春天又得以复活。这位神可以是男性(阿多尼斯)。”[29]另外,“我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年龄并不是固定的。”[30]这句话写出乌尼戈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自己的年龄,这也与希腊神话中掌握新生与衰老的两位神祇赫柏和革剌斯的能力一致[31]。综上所述,乌尼戈的对应神话原型是耶稣,但又与《圣经》中的耶稣大有不同。
柳泽真由娜的神话原型人物是异化的圣母玛利亚,在小说中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她的异化成分。在形象塑造上,柳泽真由娜虽然是一只黑鸦的后代,但在小说中最具“人性”的角色反倒是她。她有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她看到美丽的、还是一个小孩子时的乌尼戈会有人类母爱的泛滥:“柳泽真由娜的眼中柔柔泛起薄雾,她眯着眼,拍他的背,揉自己的乳房,仿佛一腔母爱无处发泄。”[32]而当乌尼戈长成一个英俊成年男子后,她再看到他会瞬间燃起自己最原始的欲望:“她身上坚硬的黑色轮廓被自己心间满溢出的淫欲之水泡软了,转变为红色球形糖果的弧度。”[33]“柳泽真由娜饱满厚重的唇肉狂热地黏上他的嘴唇时,就像呻吟的肉团撞上了冬天的玛瑙。”[34]比起“我”,柳泽真由娜更多地给予了乌尼戈爱与温暖,虽然这种爱与温暖很大程度上是由本能欲望驱使的。作家用柳泽真由娜这个角色来代表“自然人”,即没有受过规劝与训诫、充满本能欲望与生命活力的人。在小说中,作家对这种本真自我的张扬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不同于中世纪西方的“禁欲思想”,对从柳泽真由娜身上体现出的原始蓬勃的生命力乃至旺盛的生殖本能,作家毫无保留地进行讴歌与赞美。作家通过对原始自然欲望的歌颂,来表现最质朴的生命之美。柳泽真由娜这一角色的塑造是为强调自然的爱与欲望,所以,当象征着美与爱的乌尼戈在柳泽真由娜看来彻底地消失后,她也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那么,与爱和美一同“消失”便是她唯一的结局。作家在写柳泽真由娜的消失时很清淡:“她没有再回来,我的厨娘像她清脆的鸟啼一样随风而散了。”[35]她像风一样地消失,就好似她从未来过一样。这蕴含着作者对“自然人”和自然欲望能否在现实中存在并满足的沉思。
“我”所对应的神话原型人物是异化的犹大。在小说中“我”被塑造为一个普通人,但与充盈着“人性”的柳泽真由娜相比,“我”反倒更像是自然的“物”,带有很大程度的克制与冷漠:“对小镇居民糟糕的‘消灭乌尼戈计划’所造成的创伤,我仅仅对之实施无害化处理。”[36]“甚至被柳泽真由娜称为‘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37]这种能指与所指的颠倒也富有极强的文学性。小说中对“我”的描写与乌尼戈和柳泽真由娜相比是缺失的,起初只是蛛丝马迹般罗列了些“我”的特征,如有胡子、中年人、博学,只有在小说的靠后部分,作者才明确地告知“我”是一个“单身老头儿”[38]。乌尼戈的第一次死亡是由“我”引起的:“让他住下来是个错误的决定”[39],这也是小说第一个四季中秋天的开始。正是因为“我”留宿了乌尼戈,小镇居民才开始了对乌尼戈的迫害,由此可以看作是“我”“出卖”了乌尼戈,对照犹大出卖耶稣的神话,而出卖耶稣的“金钱”即乌尼戈的“美”与“无害性”。在乌尼戈成为“我”的房客之前,小镇居民只是对他怀有敌意,没有实际的迫害举动。“但现在——乌尼戈成为我们的房客,人们却开始羞辱折磨他。”[40]这是因为“我”和柳泽真由娜共同向小镇居民昭彰了乌尼戈的无害性,他们才敢对乌尼戈进行暴力迫害,最后导致乌尼戈的死亡。但同时,“我”对乌尼戈的死亡又一直抱有内疚:“我想我的理智和严谨成为我绝望和痛苦的根源。”[41]这就与为了金钱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完全不同了。“我”清楚地知晓自己严谨、睿智、理性,但在某些方面这些特质就转化为了古板、僵化和懦弱,但因为我是“老师”,是“镇上知识最渊博的人”,所以“我”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我”被自己和知识限制、囚禁了。这颇类似《浮士德》中的“书斋悲剧”。小说中“我”的“功能性”要远远大于“我”的“人格性”,与乌尼戈和柳泽真由娜相比,“我”的符号化特征更为明显。但“我”仍是小说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我”既是一系列事件的经历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唯一有完整视野的“目击者”和“幸存者”。“我”对整篇小说的意旨表达起着传声筒的作用。“我”是人却象征着“物”,是生命力不旺盛的,是怯懦的。正因为我不具备或者缺失了“自然人”的某些特质——原始欲望,“我”才能更好地接近自然与美,而不至于迷失或者消失。与肆意彰显生命欲望的柳泽真由娜不同,“我”更像是一名严格遵守“教义”的“苦行僧”。“我”的生活恰恰是柳泽真由娜所要摒弃和打破的宗教“禁欲”生活,但最后“我”回归了,并且见到了重获青春与美的乌尼戈。小说最后一句写道:“我并未停下脚步,心中一片平静,就像看到跃出水面的鱼儿又坠回了水中。”[42]此时的“我”颇有佛教中“顿悟”的意味,“我”明白了谁也无法改变自然法则,哪怕是自然法则本身。一切就是本该如此,一切又重回宁静,这再次突出小说永恒的“自然与美”的主题。“我”是人,但不是像柳泽真由娜那样的“自然人”,更像是一名在尘世中的修行者。“我”始终在美的自然与恶的人类之间徘徊,既能感受到自然与美,又有着人类伪饰的“理性与克制”,具有“中间物”的性质。但最终“我”回归并拥抱了美与自然。“我”可以被当作乌尼戈虔诚的“信徒”,在他的一路指引下最后“悟道”成功,获得了圆满自得的境界,这与背叛耶稣的犹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我”这一角色上,作家也体现出对神话的新意翻写,表达作者对当下知识分子群体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真的期盼与呼唤。
三、特殊词语的隐喻象征
在明晰了小说的结构层次和人物原型的对应关系后,这篇小说中富有深厚隐喻义的词语同样不能被忽视。弗莱认为:“某些原型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程式化的联想,以至于它们几乎无法避免暗示那个联想,就像十字架的几何图形不可避免地暗示基督之死一样。”[43]所以,笔者有必要对小说中出现的含有隐喻象征的特殊词语进行剖析。
小说中主要角色的名字都并非源于汉语,并且在其各自的源头语境中都含有丰富的隐喻色彩。“乌尼戈”是蒙语词汇,意为“狐狸”。在东方语境下狐狸是魅惑的、狡诈的,但在西方文化中,狐狸是优雅的、智慧的,比如法国著名的民间故事集——《列那狐的故事》中的主角便是一只狐狸。而狐狸正是小说开篇中提到的“鼬鼠”的天敌。鼬鼠在小说中象征那些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作者将“乌尼戈—小镇居民”与“狐狸—鼬鼠”这套隐喻系统连接,从开篇便建构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二者是从根本上敌对的关系,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44]“鼬鼠满世界跑”说明它们的天敌——狐狸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回应了“乌尼戈的消失”。当小镇居民依然无知地去迫害乌尼戈时,鼬鼠——即小镇居民内心邪恶的外化象征也无法遏制地蔓延开来:“镇里的鼬鼠的确变多了,它们铺天盖地地涌出,满大街乱跑。”[45]居民认为鼬鼠灾是乌尼戈造成的,便对乌尼戈进行欺虐,而恰恰只有乌尼戈(狐狸)可以解决鼬鼠灾,以此讽刺人类的无知与狂妄。这种讽刺到最后便上升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而结局是鼬鼠灾的爆发和人类的死亡。小说中“我”的名字“边巴”则来源于藏语,意为“土曜日、土星”。在小说中,作者把“我”塑造为一个年纪大的有学问的男人,这与土星在占星学上的意义一致:“土星是星盘里代表父亲的重要元素之一。”[46]同时,“土星的特质是沉重与缓慢”[47],与土星联系的关键词有“冷漠、沉重、迟缓、单调、干枯”[48]。“边巴”的这一土星隐喻义在名字上暗示了“我”的性格特征。
小说中有层出不穷的与动物、植物相关的譬喻。例如:鼬鼠、蘑菇 、乌鸦、白鸽、韭菜、新几内亚桉树、半日花、紅嘴松鸡、瓢虫、马兰花、向日葵、毒蛇、喜鹊、草爬子、蚂蚁、山羊等等。作者运用如此多丰富的譬喻不仅是为了使得某一叙述变得更为生动和形象,还有在其背后所隐藏的象征含义。例如“毒蛇”这一意象,“毒蛇”或者“蛇”在西方符号系统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圣经》中诱惑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那条蛇。从那时起,“蛇”便与欲望、诱惑、危险、狠毒等意义绑定。在小说中,毒蛇被小镇居民用来扔进“我”的房子里对“我”展开报复,同样,毒蛇也是狠毒残暴的小镇居民的象征,作家明确写出:“我说:‘我的老天爷,太恶心了!蛇长着一张镇长的脸。’”[49]这表明了对小镇居民蛇蝎一般的内心和举止的憎恶。同时,正因为蛇的诱惑,亚当和夏娃才偷食禁果,有了基督教中的“原罪说”,所以,蛇也可象征“原罪”,在小说中即寓意每个残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都是蛇,都是有着“原罪”的。所以,在故事后期,“原罪”与小镇居民的“暴死”这一惩罚相照应。
小说中频繁出现与数字和形状相关的隐喻。在结构方面,小说按照三个四季轮回谋篇布局;在线索方面,小说围绕乌尼戈的三次消失与三次出现为主要线索连缀全文;在内容方面,毒蛇的毒液堆积处的形状是“紫色的三角形”[50],镇民们殴打乌尼戈时使用的是“三角形石头”[51]。无论是全文的结构线索还是小说的故事内容,数字三与三角形都贯穿作品始终。布鲁斯·米特福认为:“数字‘3’被视作神圣的数字。”[52]而三角形的“象征涵义多与数字‘3’有关,它代表着开始、中间与结束”[53] 。并且,“许多文明都将三角形与神联系在一起。”[54]三角形中包含数字三,二者本质上都有着神圣的含义,充满浓厚宗教色彩。数字三和三角形的使用加强了小说的神话意味。
除了上述神话宗教象征色彩较为明显的词语,小说中还多次提到了“梦”“玛瑙”以及各种颜色。这些词语的运用,为小说增添了更多的神秘元素,并加深了小说的神话色彩。
余 论
面对渡澜“别是一家”的作品,其表达、譬喻和想象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生活经验去解释,评论者仅仅用印象式的文字去解读也是对其作品价值的极大低估。渡澜的小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头脑风暴,也是精致用心的解谜游戏。评论者如果对渡澜的作品批评失去了理论基础,就如同空对着一座用繁华珠玉搭建起的世上独一的城堡,而不解其中蕴含的究极质朴之美。因此,评论者未来针对渡澜作品的分析应着重注意运用合适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分析而轻描写,这或许可以更好地回应与之相关的问题,并给予“滞缓”的当代文坛更多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3][22][29][43][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袁宪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90,190,190,163,187,104.
[4][5][6][7][8][9][10][11][13][14][15][17][19][20][21][23][24][2][26][27][30][32][33][34][35][36][37][38][39][40][41][42][44][45][49][50][51]渡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J].收获,2019(4).
[12]傅道彬.《月令》模式与中国文学的四时抒情结构[J].学术交流,2010(7).
[16]马佳编著.圣经典故[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182.
[18]王艳霞.威廉·布莱克诗歌译评[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211.
[28][31]曹乃云编.希腊罗马神话小百科[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7,175.
[46][47][48][英]苏·汤普金斯.当代占星研究[M].胡因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183,181.
[52][53][54][英]布鲁斯·米特福、[英]菲利普·威尔金森.符号与象征[M].周继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294,294,286.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3127500338252